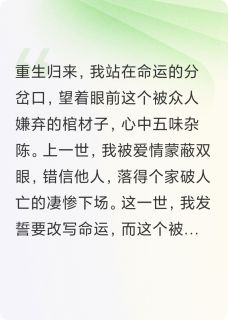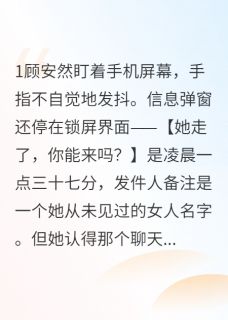我死在了手术台上,再睁眼成了大景朝里的病秧子世子赵邺。御医断言我活不过半年,
父亲战死沙场,兵权被薛侯爷夺走,妹妹还被逼嫁给薛家纨绔。我咳着血笑纳所有嘲讽,
暗中却用现代商业手段操纵粮价,用孙子兵法训练私兵。大婚当日,
薛家迎亲队伍被我的私兵截杀,妹妹安全回府。朝堂上,我坐着轮椅咳血指控薛侯贪墨军饷,
证据确凿。薛侯狗急跳墙逼宫造反,我扔掉药瓶站起身:“本世子装病半年,等的就是今天!
”当薛侯被押走时,我轻声补刀:“忘了说,你儿子没死,正在诏狱里问候你呢。
”……1重生世子心电图发出尖锐刺耳的哀鸣。惨白刺目的无影灯光晕吞噬意识。冰冷,
无边无际的冰冷包裹着我。最后一点感知沉入永恒的黑暗深渊。再睁眼,
是古色古香的木质承尘。鼻尖萦绕浓重苦涩药味,挥之不去。“世子…世子醒了!
”侍女带着哭腔惊呼。人影晃动,几张焦虑卑微的陌生脸庞凑近。喉咙火烧火燎,干裂疼痛。
我费力挤出嘶哑声音:“水…”温热的药汤送到唇边,浓苦刺鼻。我皱着眉,勉强吞咽下去。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啊!”忠伯激动搓手。须发皆白的老管家,眼中含泪。“老天保佑,
祖宗显灵!”他不住念叨。身体沉重如灌铅,动弹艰难。每一次呼吸都牵扯肺腑深处剧痛。
我闭上眼,原主破碎记忆汹涌而来。大景王朝,靖王府,世子赵邺。我是赵邺。
靖王世子赵邺。记忆里那个英武挺拔的父亲赵峥。不久前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噩耗传回,
原主本就孱弱的身子。遭受致命一击,彻底一病不起。“世子爷,”御医官服中年人靠近。
语气带着职业化的冷漠疏离。“您脉象虚浮紊乱,沉疴入骨。”他避开我目光,
声音低沉下去。“需…需静养。若精心调养…”他顿了顿,吐出判决:“或可延寿…半载。
”半年。他判了我缓期执行的死刑。忠伯身子晃了晃,老泪纵横。满屋仆婢扑通跪倒一片。
压抑的啜泣声在死寂中弥漫开。“哭什么?”我开口,声音嘶哑破败。“我还没死。
”语气平静无波。御医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他大概见惯了贵人们的色厉内荏。
“世子宽心,微臣定当竭尽全力。”他敷衍躬身退下。窗外,秋风萧瑟,卷起枯黄落叶。
打着旋儿,沙沙撞在雕花窗棂上。像命运无声而冷酷的嘲弄。2薛侯逼婚御医刚退下不久,
沉重脚步声传来。带着不加掩饰的倨傲与力量感。紫袍玉带,壮硕身影闯入视野。薛昱,
当朝炙手可热的武威侯。他眼神锐利如鹰隼,扫过病榻。嘴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
“赵邺贤侄,身子可好些了?”他径自走到榻前,居高临下俯视。“赵兄不幸殉国,
陛下痛心疾首。”“念及北境军务繁重,不可一日无帅。”他故意停顿,欣赏我虚弱模样。
“陛下特旨,命我暂领北境军务。”“安抚边关将士之心。”字字清晰。父亲尸骨未寒,
兵权被他攥入掌心。一股郁气直冲喉头,我剧烈咳嗽。侍女慌忙递上素白绢帕。
一抹刺目猩红瞬间洇开在雪白之上。薛昱眼底的得意几乎要溢出来。“还有一事,
”他慢悠悠补充。“令妹赵霓,温婉贤淑。”“我家那不成器的小子薛蟠,心仪已久。
”他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陛下亦觉两家门当户对。”“已欣然应允赐婚。择吉日,
便完婚吧。”赵霓…记忆中那明媚少女。策马扬鞭,笑声清脆。薛蟠?京中有名的纨绔恶少。
欺男霸女,恶名昭著。一股暴怒猛地窜起,烧灼眼前。我死死攥紧被角,指节泛白。
压下喉头翻涌的血腥气。“薛…薛侯爷,”我艰难喘息。声音断断续续,气若游丝。
“家父新丧…赵霓尚在孝期…”“这…于礼不合吧?”我微弱**。“礼?”薛昱嗤笑一声。
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贤侄病糊涂了?陛下金口玉言!”“便是最大的礼!安心养病便是。
”“这些俗务,自有本侯操持。”他不再看我,转身大步离去。袍袖带风,
卷起一股浓烈熏香。“世子爷!”忠伯扑到榻边。老泪纵横,声音颤抖。
“这…这是要绝了王府的根啊!”“老奴…老奴拼了这条命也要…”“忠伯,”我打断他。
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扶我起来。”不容置疑。忠伯一愣,惊愕看着我。
连忙和侍女小心翼翼扶我坐起。背后塞入好几个柔软靠枕。“王府的所有产业账簿。
”**在枕上,闭目调息片刻。“还有,府里所有身契清白的家生子名册。
”“尽快拿来给我。”睁开眼,目光沉静。忠伯浑浊眼中满是惊愕不解。“世子爷,
您身子虚弱…”“去办。”我目光平静,却带着力量。那目光让忠伯瞬间噤声。他怔怔看我,
仿佛第一次认识我。“是…是!”他猛地醒悟,踉跄奔出。3暗流涌动日子一天天过去。
靖王府依旧门庭冷落,死气沉沉。在外人眼中,我仍是病榻废人。每日汤药不断,
咳嗽声不绝于耳。只有忠伯和几个绝对心腹管事知道。世子的内书房,灯火常亮至深夜。
厚厚的账簿堆满了宽大紫檀案头。我强忍身体疲惫和剧痛,逐页翻阅。
指尖划过密密麻麻的数字。大脑在飞速运转,整合信息。原主零碎记忆,前世商海经验。
逐渐交融,织成清晰的网。“盐引,”我指着账簿巨大亏空。声音因久病而沙哑干涩。
“账面显示去年盐引收益锐减三成。”“但同期盐价并未跌落,反略上浮。
”侍立一旁的张诚,外务管事。闻言一惊:“世子爷明鉴!小的也觉蹊跷。
”“但盐运使那边…”他面露难色。“不是盐运使。”我打断他。
指尖精准点向另一处不起眼记录。“是粮商。看这里,去年江南大熟。”“粮价本应大跌,
京畿粮价却异常平稳。”“甚至小涨。大批本该流向粮市的银子。”“被谁吸走了?
”我抬眼看他。张诚眼睛猛地睁大,倒吸凉气。“盐商囤粮?
他们哪来那么多现银…”“所以,”我咳了几声,掩住嘴。“有人在用盐引巨额收益,
暗中操控粮价。”“左手倒右手,虚增成本,掏空王府盐利。”我放下帕子,
苍白脸上浮起冷笑。张诚恍然大悟,随即忧心忡忡。“世子爷,那…如何是好?
”“薛侯爷那边…势力庞大啊…”“他胃口太大,吃相太急。”我声音冰冷。
“反倒容易噎着。按我说的做…”窗外寒风呼啸,呜咽如泣。书房内,炭火噼啪,低语不断。
一条条指令通过可靠渠道悄然发出。流向京城各大商行、不起眼钱庄。一场无声风暴,
在死寂下酝酿。王府后院深处,废弃演武场。厚厚的积雪掩盖了所有声响。寒风卷着雪沫,
打在脸上如刀割。三十名精壮汉子,灰布棉袄。在雪地中站得笔直,纹丝不动。
他们是忠伯从世代忠仆中千挑万选。眼神里有疑惑、忐忑,也有一丝轻视。
看着裹着厚厚貂裘,坐圈椅里的我。脸色苍白如纸,仿佛一碰即碎。“从今日起,”我开口。
声音不大,穿透寒风,奇异清晰。“你们不再是王府的杂役。”“你们,是我的刀。
”字字清晰。众人面面相觑,茫然不解。“战场之上,瞬息万变。”我继续。
目光扫过他们年轻粗糙的脸。“想活命,想立功,想护住身后家人。”“靠蛮力?
”我轻轻摇头。“不够。要靠脑子,靠阵势。”我抬了抬手。一旁肃立的雷啸。沉默寡言,
脸上带着刀疤的统领。立刻上前一步,展开简易阵图。“看这里,”雷啸声音粗粝沙哑。
指着图上标识:“三人成组,背靠背。”“攻时如锥,无坚不摧!”“守时如磐,坚不可摧!
”“进,同进!退,同退!”“一人受袭,两人援护!生死相依!”“这叫‘三才阵’,
”**椅背上。气息有些急促,语调却平稳。“练熟它,你们三十人,可挡百人冲击。
”汉子们眼神变了,惊讶专注。紧盯着那蕴含杀机的阵图。“雷统领,”我看向他。
“每日卯时开练,酉时方歇。”“练协同如一,练令行禁止。”“练耐力如铁。
雪地、泥泞、黑夜…”“都要练!”我加重语气。雷啸抱拳,目光灼灼如星。“属下遵命!
必不负世子所托!”风雪更狂,呼啸着席卷天地。演武场上,汉子们依令笨拙移动。
呼出的白气瞬间消散寒风中。沉重脚步踩在厚雪上,咯吱作响。三人一组,靠拢,变换,
再靠拢。呼喝声渐渐有了力量与节奏。我裹紧貂裘,刺骨寒意依旧。
看着雪中逐渐有了章法的身影。一丝冰冷的锐意,悄然爬上心头。
4血染松林赵霓出嫁的日子,终究到了。靖王府挂起了刺眼红绸。
却掩不住满府凄清与死寂。没有宾客,只有薛府派来的人。像闯入墓穴的秃鹫,趾高气扬。
闺房里,赵霓一身凤冠霞帔。红得刺目,映得她小脸更加苍白。她没有哭,死死咬着下唇。
几乎要咬出血痕。那双曾经灵动飞扬的眸子。此刻黯淡无光,空洞望着铜镜。
镜中那个陌生而华丽的囚徒。“阿兄…”她声音干涩嘶哑。像被砂纸磨过喉咙。“我…走了。
”带着无尽绝望。她站起身,红盖头流苏晃动。两个薛府派来的粗壮仆妇上前。一左一右,
几乎是架着她往外走。动作粗暴,毫无半分尊重怜悯。我坐在轮椅上,被忠伯推着。
停在冰凉的回廊下,寒风灌入。我剧烈咳嗽起来,单薄身子蜷缩。仿佛下一刻就要散架,
咳出心肺。赵霓被粗暴推搡着经过面前。盖头下,她的身影似乎停顿了一下。
“咳咳…赵霓…”我喘息微弱。
声音几乎被风吹散:“保重…自己…”盖头下的身影剧烈颤抖了一下。最终,
还是被仆妇强硬架着。走出了垂花门,消失视线外。凄厉的唢呐声陡然撕裂空气。
混合着薛府家丁嚣张的吆喝。花轿摇摇晃晃地抬起。红色的队伍像一条蜿蜒毒蛇。
消失在长街尽头,带走最后光亮。王府沉重的大门,轰然关上。隔绝了外面虚假的喧嚣。
府内,死一般的寂静笼罩。忠伯推着我的轮椅,缓缓向内。轮椅碾过青石板,单调轱辘声。
“世子爷…”忠伯声音哽咽。我抬起手,冰凉指尖止住他的话。回到内室,门扉紧闭。
脸上病弱哀戚瞬间褪尽。只剩下一片寒潭般的沉静。“雷啸。”我唤道。屏风后阴影微动,
雷啸闪身而出。一身不起眼灰布短打,气息冷硬。带着雪与铁的寒意。“都准备好了?
”我问,声音平稳。再无一丝病气。“回禀世子,”雷啸抱拳。声音低沉有力,隐含杀气。
“按您吩咐,三十人分三队。”“已提前出城,埋伏十里亭外松林坡。
”“弓弩、绊索、陷坑齐备。”“只等信号。”他目光如炬。“很好。
”我拿起案几上羊脂玉佩。温润莹白,刻着古篆“靖”字。父亲赵峥的遗物,承载着英魂。
我轻轻摩挲,感受冰凉触感。“动手吧。”松开手,玉佩无声落锦垫。“记住,
”我的声音冷得像冰。“我要薛蟠,活着。毫发无损。”“其他人…”我顿了顿。
“一个不留。”杀意凛然。雷啸眼中厉色一闪,躬身。“属下明白!”身形一晃,融入阴影。
室内重归死寂,窗外风声呜咽。胸腔里那颗千疮百孔的心脏。正缓慢而有力地搏动着。
“赵霓,”我无声低语。“等等阿兄。”唢呐的嘶鸣撕裂郊外寒风。锣鼓喧天,
透着虚张声势的浮夸。迎亲队伍逶迤而行,红得刺眼。薛蟠骑高头大马,大红喜服。
脸上涂脂抹粉,掩不住青白。眼神不耐,频频回头望花轿。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
“妈的,磨蹭什么!快点!”“误了爷的好时辰,仔细剥你们的皮!”家丁们唯唯诺诺,
加紧脚步。队伍行至松林坡下,官道狭窄。两侧松林茂密,积雪压弯枝桠。突然!“咻——!
”一支响箭带着凄厉尖啸,直冲云霄!“有埋伏!”护卫头领脸色剧变,拔刀!“嗡——!
”密集破空声如死神低语!数十支弩箭从两侧松林激射而出!角度刁钻狠辣,箭镞闪着幽光!
“噗嗤!”“啊——!”惨叫声瞬间炸开!血花四溅!外围护卫如被割倒麦子,纷纷倒地!
鲜血瞬间染红洁白雪地,刺目惊心!“保护公子!结阵!”头领嘶吼格箭。
袭击者根本不给他们喘息之机!“杀!”低沉吼声从林中爆发!
数十条灰色身影如鬼魅般扑出!三人一组,动作迅猛如电!配合精妙绝伦,
刀光织成死亡之网!“噗!”护卫挡住正面劈来的刀。侧面同伴的刀锋已精准捅入肋下!
“呃啊!”另一护卫被绊索猛然绊倒!未及爬起,数柄短刀已狠狠斩落!
薛府的护卫多是花架子。平日欺压良善尚可,何曾见过此等阵仗?瞬间被杀得人仰马翻,
溃不成军!“鬼!是鬼啊!”薛蟠吓得魂飞魄散!胯下骏马受惊,人立而起!他尖叫一声,
重重摔落马下。啃了一嘴冰冷泥雪,喜袍污秽不堪。“蟠儿!
”一个骑马的谢府管事目眦欲裂。想冲过来救援。一道灰色身影如旋风般卷至!刀光一闪!
寒芒掠过脖颈!那管事人头冲天飞起!血泉喷涌!无头尸体轰然栽倒马下!
薛蟠眼睁睁看着人头滚到脚边。圆睁双眼,死不瞑目。“嗷!”他怪叫一声,裤裆瞬间湿透。
腥臊气弥漫开来。他手脚并用。涕泪横流地向后爬去,哀嚎求饶。“别杀我!别杀我!
我爹是薛昱!”“我爹是武威侯啊!饶命啊!”混乱中,花轿被粗暴掀翻在地。
穿着大红嫁衣的赵霓挣扎爬出。头上盖头早已掉落,小脸苍白。写满惊愕,
看着眼前血腥修罗场。看着地上屎尿齐流的薛蟠,呆住了。一个灰衣人迅速上前,动作轻柔。
小心扶起她:“郡主,得罪了。”声音低沉却异常恭敬。“属下奉世子之命,接您回府。
”赵霓猛地一震,难以置信。“阿兄…?”声音带着颤抖。灰衣人没有回答,将她护在身后。
警惕环视四周。周围杀戮近尾声。薛府护卫和家丁,几乎被屠戮殆尽。
只剩几个瘫软在地、抖如筛糠的轿夫乐手。雷啸提着滴血的刀,大步走来。
停在瘫软如泥、浑身恶臭的薛蟠面前。厌恶地皱了皱眉,猛地一掌劈下。精准砍在后颈。
薛蟠哼都没哼一声,像条死狗昏厥。“捆了,带走!”雷啸冷声下令。两名灰衣人立刻上前,
用牛筋绳。将薛蟠捆得结结实实,像拖死猪。拖向松林深处,消失不见。雷啸走到赵霓面前,
抱拳躬身。“郡主,此地不宜久留。”“请随属下速速回府。”“世子正等着您。
”语气坚定。赵霓看着眼前浴血煞气的雷啸。看着满地尸体和刺目鲜血。
看着昏死过去的薛蟠…最后,她用力点了点头。眼神从惊惧迷茫,变得复杂坚定。“走!
”雷啸护着赵霓。一行人迅速消失在茫茫松林。只留下满地狼藉,浓重血腥。
喜庆的唢呐早被寒风吹散。唯余一片死寂,宣告终结。靖王府内院。
《咳血病秧子?这天下我说了算!》这本书巧妙地将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作者七月禅山通过精湛的笔力,描绘出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主角薛昱赵霓忠伯的形象鲜明,她的聪明和冷静为整个故事注入了强大的力量。情节跌宕起伏,每一个转折都让人意者会被情节的发展所吸引,无法自拔。配角们的存在也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张力,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这本书充满了惊喜和感动,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深刻的思考和共鸣。《咳血病秧子?这天下我说了算!》是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值得推荐给所有热爱[标签:小说类型]小说的读者。
作者七月禅山的文笔娴熟,故事情节独特,吸引了我对《咳血病秧子?这天下我说了算!》的极高关注。
薛昱赵霓忠伯在《咳血病秧子?这天下我说了算!》中的出色表现,让我难以忘记。他的性格特点和独特的剧情让我记忆犹新。
《咳血病秧子?这天下我说了算!》这本书令人惊喜不断。作者七月禅山的文笔优雅而动人,每一个场景都仿佛跃然纸上。主角薛昱赵霓忠伯的性格鲜明,她的聪明和冷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个故事结构精巧,前后呼应,扣人心弦。配角们的存在也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张力。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佳作,读者会被它的魅力所吸引,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