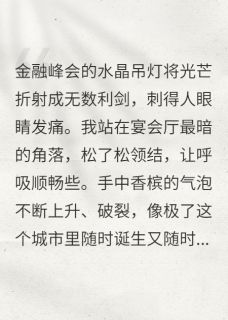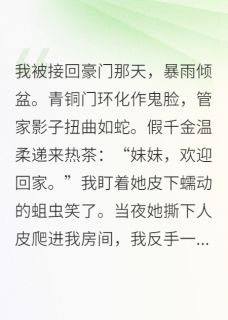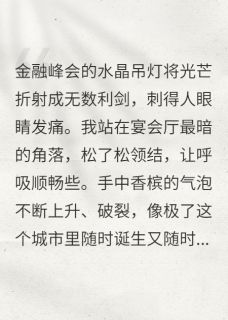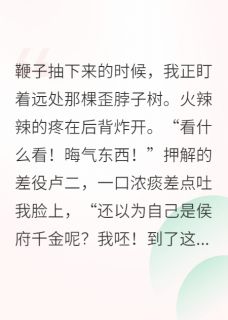1人生若只如初见红烛高烧,明珠府邸的喜字烫得人眼眶发疼。
我攥紧袖中表妹绣的并蒂莲帕子,任由冰凉的丝线勒进掌心。“少爷,该掀盖头了。
”喜娘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水。绣金盖头下露出一双清凌凌的眼,
眸子里盛着整片破碎的星河。“原来是你。”我呼吸骤停。三年前广源寺的春雨里,
这双眼睛的主人曾蘸着雨水在石阶上写:“风也萧萧,雨也萧萧。
”喜袍的赤色滚边刺得我眼底生痛。外头喧天的锣鼓鞭炮炸进耳膜,每一声都碾在骨头上。
明珠府今夜灯火通流,映得北京城的夜空都泛着虚妄的红光。贺喜的人潮水般涌过回廊,
谄笑混着酒气糊在雕花门扇上——“纳兰公子大喜啊!”什么大喜。
一把钝刀子割在心口罢了。袖中那方丝帕已被冷汗浸透。表妹绣的并蒂莲在指尖下扭曲,
最后一针收尾时她哭肿了眼,金线缠着血丝融进花瓣里。宫门合拢的闷响至今碾在我梦里,
而此刻,父亲明珠的声音穿透门板,刀刃似的劈进来:“容若!宾客都等着,
你想让整个京城看相府的笑话吗?”我猛地拽开门。廊下红灯笼的光泼了父亲满身,
他蟒袍上的金线狰狞地反着光。“儿子不敢。”喉咙里挤出的声音嘶哑如裂帛。
“卢兴祖之女是满洲贵女典范,配得起你纳兰容若!”他掌心压在我肩上,千斤重,
“忘了你表妹,除非你想让她在宫里死无全尸。”喜娘将一截红绸塞进我掌心,
绸缎另一端连着新妇。她脚步轻得听不见声息,盖头垂落的流苏却在我余光里晃,
荡出细碎的金影。拜天地时我膝骨僵冷,高堂上母亲的笑声像裹着蜜的针。
礼官拖长的调子刺破满室喧腾:“礼成——送入洞房!”新房的红烛烧得太旺,
蜡泪在鎏金烛台上堆成小山。我盯着烛火,直到眼眶灼痛。菱花镜里映出个鬼影:金冠蟒袍,
面色惨白如纸。门外宾客的哄笑浪涛般拍在门板上,一声“纳兰公子快掀盖头啊!
”扎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盖头下的身影微微晃了晃。“请公子……掀盖头吧。
”她的声音从盖头下渗出来,清泉似的,却激得我心头火起。“急什么?”我冷笑,
一把抓起合卺酒金杯,“卢**是怕误了洞房吉时?”杯中酒液猛晃出来,
溅上她嫁衣袖口的金鸾鸟。那鸾鸟的翅膀被酒渍晕开,像折断了羽翼。她突然抬手按住杯沿。
指尖莹白,指甲盖泛着贝壳似的淡光。“公子不愿饮,不必强求。”盖头随动作轻颤,
流苏扫过杯上凸雕的鸳鸯,“只是酒无罪,何必糟蹋?”我掌心一空。她竟抽走了酒杯。
“好个伶牙俐齿!”我几乎咬碎牙,伸手攥住盖头一角。赤金流苏刮过指节,
底下的人呼吸一滞。红绸撕裂的脆响里,烛光泼了她满头满脸——杏眼,菱唇,
左颊一粒小痣恰落在梨涡浅处。广源寺烟雨里的眉眼撞破记忆,轰然炸开。“是你?
”我踉跄退半步,撞得烛台乱晃。她仰着脸,睫毛上沾了烛光碎金:“三年前广源寺**,
公子为一群论词女子解围时,可没这般凶悍。”三载光阴倒灌回眼前。暮春的广源寺,
我隔着竹篱听见少女清音。“秋水轩唱和词卷贺新凉,韵脚该是‘遣’字接‘泫’字,
张姐姐错了!”几个华服少女围着石案争执,被指错的紫衣少女涨红了脸。
石阶边独坐的素衣姑娘忽而搁下笔:“卷字后接遣字原无错,
只是张姐姐方才吟的‘粉脂都遣’意境稍俗,不若‘愁痕都遣’?
”紫衣少女柳眉倒竖:“卢雨蝉!轮得到你教训我?”“她没错。”我拨开竹枝走过去。
满庭春色骤然死寂,少女们惊惶的目光钉在我身上。唯石阶边的素衣少女抬了眼。
细雨濡湿了她额发,眸子清亮如浸在寒潭里的星子。“贺新凉词牌第四句当押险韵,
‘愁痕’确比‘粉脂’更合萧瑟词境。”我目光扫过她面前宣纸——疏影临书卷,带霜华,
高高下下,愁痕都遣。她忽然起身,罗袜沾了青苔泥渍也浑然不觉:“公子既懂词,
可敢依眼前景续作下半阕?”雨丝斜掠过她皓腕,腕骨伶仃得让人心惊。
我解下披风罩在她身上,提笔蘸墨:“别是幽情嫌妩媚,红烛啼痕休泫……”笔锋游走间,
风卷起她袖角,暗香拂过鼻尖。待写到“帘幕西风人不寐”时,她突然轻念:“恁清光,
肯惜鹴裘典?”我顿笔。她竟猜中我腹稿末句。“雨大了,公子保重。
”她将披风塞回我怀中,转身没入烟雨。杏色裙裾扫过阶前残红,像惊鸿踏碎春水涟漪。
“原来卢**还记得当日落魄书生。”我扯下胸前红绸团花。金线勾连处发出撕裂的哀鸣。
“纳兰公子说笑。”她自行摘下凤冠,珠翠碰撞声清泠如碎玉,“广源寺一面后,
秋水轩新词传遍京城。‘肯惜鹴裘典’一句,家父抄录在书房整整三月。
”她竟知道那词后来传唱之事。我攥着红绸的手指松了又紧:“今日卢总督嫁女,
可曾告知你纳兰容若心里早葬了人?”烛火“啪”地爆开一朵灯花。
她正拆鬓边最后一支金簪,闻言指尖停在发间:“公子是说那位入宫的表妹?
”金簪尖头寒光一闪,“雨蝉斗胆,公子既放不下旧情,何不抗旨拒婚?相府嫡子,
连这点胆色也无?”“你!”我伸手攥住她手腕。玉镯磕在床柱上铮然作响。她疼得抽气,
眼底却烧起两簇火苗:“捏碎腕骨也改不了你懦弱!困在旧情里自苦,拖着旁人殉葬,
这便是第一词人的傲骨?”我像被滚水烫着般甩开手。她雪白腕骨上已浮起红痕,
玉镯裂了道细缝。“殉葬?卢**高看自己了。”我嗤笑,心底却有什么被那裂缝撕开,
“你我皆是家族棋局里的死子,谈什么情?”“棋子?”她忽然笑出声,
裂镯在烛光下晃出细碎的光弧,“广源寺论词那日,公子递来披风时手在发抖。
若真是冷心冷情的棋子——”她逼近一步,发间茉莉香混着药气袭来,“为何怕我受凉?
”我喉头一哽。檐外更鼓沉沉敲响,梆子声撞碎满室死寂。她忽地咳嗽起来,
单薄肩胛在嫁衣下绷如蝶翅。我下意识去扶,触到她冰凉指尖。“放手……”她喘息着抽手,
袖口滑落。皓腕内侧一道旧疤狰狞盘踞,像雪地里冻死的蛇。我猛然想起广源寺那日,
她抽回披风时袖口露出的纱布——当时只当是闺阁女儿不慎烫伤。“这道疤,
”她拉下袖子遮住伤痕,声音疲如枯絮,“是听闻圣上指婚纳兰氏那夜,我砸了药碗划的。
”烛泪轰然滚落,烫在我手背上。她仰头看过来,眸中星河碎成冰碴:“所以公子你看,
世间苦命人,谁比谁清醒?”风卷着残花扑上窗纸,沙沙如夜蚕食叶。
合卺酒在杯中凝成冷琥珀。她蜷在拔步床最里侧,锦被裹得密不透风。
**坐在窗下贵妃榻上,腕间还缠着她扯断的红绸。“广源寺那日,
你续的词里有句‘但得白衣拾慰藉’。”她的声音从锦被里闷闷透出来,“白衣指什么?
”我摩挲着杯中残酒:“白雪。取自谢惠连《雪赋》‘既因方而为圭,亦遇圆而成璧’。
”被褥窸窣响动,她支起身子:“公子错了。白衣是丧服。‘拾慰藉’是替亡人敛骨。
”帐外烛光勾出她伶仃的肩线,“你在广源寺落笔时就预感会失去什么,是不是?
”酒杯脱手砸在地毯上。半年前表妹被抬进神武门的画面割开脑髓——朱红宫门吞噬喜轿时,
她腕间戴着我送的玉镯撞在轿窗上,碎玉声刺透风雪。“卢**好利的刀。
”我盯着地上蔓延的酒渍,像一滩污血。“容若。”她第一次唤我名字,惊得我脊骨发麻。
她赤足踩过满地狼藉,裂镯的玉臂环住我后颈。药香混着血腥气钻进鼻腔,
腕间旧疤贴上我侧颈,粗粝如毒蛇吐信。“你表妹没死。”滚烫的唇息烙在耳畔,
“她在长春宫当差,上月托人给我捎了信。”她指尖在我掌心一笔一划写下两个字,
指尖冰凉如刀锋:绿萼。表妹的闺名!我死死钳住她肩膀:“她人在哪?
”“嘘——”她染着凤仙花汁的指甲抵住我嘴唇,眼底烧着幽暗的火,“公子先告诉我,
当年广源寺石阶上,我蘸雨写的那句是什么?”“风也萧萧,雨也萧萧!”我几乎吼出来。
她笑了。烛泪淌过鎏金烛台,像凝固的血泪。“瘦尽灯花又一宵。”她轻轻续完下半句,
将染血的指尖按在我心口,“容若,这一局棋,你我皆是执子人。”檐外惊雷炸响,
暴雨倾天而落。2药香烬雨声砸在琉璃瓦上,像千万只鬼手在抓挠。
她腕间的旧疤贴着我的颈动脉,随呼吸起伏。“绿萼……”我齿缝里碾着这个名字,
喉头涌起铁锈味,“她当真活着?”卢雨蝉的指甲陷进我肩胛骨,
凤仙花汁染红的指尖像蘸了血:“长春宫西配殿第三间厢房,夜夜能听见玉镯撞窗棂的声音。
”我眼前发黑。表妹被抬进神武门那日,腕上戴的正是我送的翡翠缠枝莲镯——她说过,
若有不测,便以玉碎为信。雷声碾过屋脊时,我钳着她肩膀的手骤然失了力。
她踉跄退开半步,赤足踩上翻倒的酒杯碎片。血珠从足心沁出来,
在猩红地毯上晕成更深的暗斑。“疯子。”我扯下外袍裹住她,“你拿什么证明?
”她倚着拔步床的朱漆立柱喘息,嫁衣领口蹭开了些,露出颈侧一道浅疤:“上月廿七,
长春宫小太监福顺来府里送广储司的缎子。”她从撕裂的袖袋摸出个油纸包,
抖开时药气刺鼻,“认得这个么?”半枚翡翠莲瓣躺在她掌心,断口处还沾着褐色的污渍。
我抓过来对着烛光细看——莲瓣内侧刻着极小一个“婉”字,是我当年亲手用金钢钻刻下的。
表妹名唤绿萼,小字婉清。铜漏滴答声里,暴雨淹没了整个京城。我攥着那枚碎玉,
冰凉的棱角几乎嵌进掌纹:“条件?”她忽然笑起来,咳得肩头乱颤:“容若公子果然痛快。
”染血的足尖在绒毯上划了道弧线,“第一,每月初五我要见福顺;第二,
书房西墙多宝格里那套《饮水词》手稿归我;第三——”她顿了顿,
染着蔻丹的指甲点向我心口,“人前做恩爱夫妻,人后各不相干。”烛火爆响。
我盯着她足下蔓延的血迹,想起广源寺石阶上她罗袜沾染的泥污。“成交。
”齿缝里挤出的字眼带着血腥气,“但你若骗我……”“那便叫我腕上这道疤烂穿肺腑,
生生呕血而死。”她截断我的话,眼神冷得像广源寺后山的冻泉。五更梆子响时,雨势暂歇。
卢雨蝉蜷在床角睡了,裂开的玉镯仍套在腕上,烛光一照便泛出凄冷的青晕。
我合衣倒在窗下贵妃榻,碎玉的棱角硌在掌心,一夜未眠。晨光刺破窗纸时,
门外响起剥啄声。明珠府大管家福安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少爷少夫人,老爷传话,
辰时三刻前需到颐和堂敬茶。”卢雨蝉倏然睁眼。四目相对的刹那,
她眼底还残留着梦魇的惊惶,却在看清我面容的瞬间冻结成冰。“更衣。”她掀被下床,
足心伤口触地时眉头都没皱一下。妆匣打开时寒光微闪。我瞥见匣底压着把三寸长的银匕首,
刀柄缠着褪色的红绸。“夫人还备着凶器?”我拈起合卺酒的空杯把玩。她正对镜绾发,
闻言从铜镜里斜睨我一眼:“防狼。”玉梳“啪”地拍在妆台上,
“劳烦公子递件外衫——总不好叫满府上下看出纳兰少爷有虐妻之癖。
”我抽了件月白绣竹纹袍子扔过去。她接住时袖口滑落,腕间红痕在晨光下愈发狰狞。
“彼此彼此。”我指她颈侧那道浅疤,“卢**的见面礼也不遑多让。
”颐和堂的晨风带着雨后的腥气。穿过游廊时,我故意落后半步。她脊背挺得笔直,
嫁衣后领却掩不住微微颤抖。行至荷花池畔,她脚下一滑,我下意识伸手去扶——“别碰我!
”她触电般甩开,眼底掠过一丝真切的恐惧。池边湿泥留下半个凌乱的脚印。
我收回僵在半空的手:“卢**是怕我,还是怕水?”她猛回头,
鬓边步摇乱颤:“公子想听真话?”她突然逼近,药香混着血腥气扑面而来,
“广源寺那日你冒雨赠袍,我回去高烧三日。家父说……”她喉头滚动一下,声音压得极低,
“纳兰氏的男人,温柔是把淬毒的刀。”颐和堂里熏着浓烈的苏合香。
父亲明珠端坐紫檀太师椅上,蟒袍玉带勒出威严的轮廓。母亲觉罗氏捧着珐琅手炉,
目光像针尖般扎在卢雨蝉身上。“新妇敬茶。”福安将缠枝莲盏递到卢雨蝉手中。
她跪得笔直,茶盏高举过眉:“儿媳卢雨蝉,请父亲大人用茶。”父亲没接。
堂内静得能听见香灰坠落的簌簌声。“卢氏。”父亲指尖敲着扶手,“你可知明珠府的规矩?
”茶盏边缘泛起细微波纹:“请父亲示下。”“第一,晨昏定省不可误;第二,
内宅不得干外事;第三——”父亲目光如鹰隼般攫住她,“纳兰氏子嗣为重,若三年无所出,
休书自备。”卢雨蝉指节泛白,滚烫的茶汤泼溅在手背。我上前半步接过茶盏:“父亲,
昨夜……”“你闭嘴!”父亲劈手夺过茶盏掷在地上。瓷片混着热茶炸开,
卢雨蝉裙摆瞬间洇开深色茶渍。“卢兴祖教的好女儿!”父亲指着她冷笑,
“新婚夜竟让姑爷宿在榻上?当我明珠府是市井戏台么!”母亲忽然轻笑出声,
腕间佛珠捻得飞快:“老爷息怒。媳妇年轻不知事,
容若又是个怜香惜玉的……”她眼风扫过卢雨蝉腕间玉镯的裂痕,“瞧瞧,小夫妻蜜里调油,
连玉镯都折腾碎了。”满堂仆妇的视线毒虫般叮在裂镯上。卢雨蝉垂眸盯着裙上茶渍,
忽然伸手捡起一片碎瓷。锋利的豁口划过她指尖,血珠滴进地毯的缠枝莲纹里。“儿媳愚钝。
”她将染血的碎瓷捧给父亲,“茶盏既碎,以此代盏可好?血染莲花,也算应了府上祥瑞。
”父亲瞳孔骤缩。堂内死寂中,她腕间旧疤随动作从袖口露出来,像条僵死的蜈蚣。
母亲捻佛珠的手停了。“好,好个卢兴祖之女!”父亲突然抚掌大笑,眼底却结着冰,
“福安,取我的犀角杯来!”沉重的犀角杯压进卢雨蝉掌心时,她几不可察地晃了晃。
杯身阴刻的饕餮纹硌着她指腹伤口,新血覆上旧血。“谢父亲赐杯。”她声音稳得出奇,
“儿媳定日日捧此杯为父亲祈福。”母亲忽然起身扶她:“快起来,地上凉。
”镶宝石的护甲却狠狠掐进她肘弯。卢雨蝉闷哼一声,被我一把拽起。“母亲当心。
”我挡开那只手,觉罗氏护甲尖划过我手背,带出三道血痕,“儿子送雨蝉回房换药。
”踏出颐和堂的刹那,卢雨蝉身子一软。我抄住她腰肢时触到满手冷汗。“撑住。”我低喝,
“满院子眼睛看着!”她指甲抠进我臂弯,借力站直:“公子放心……戏还没唱完呢。
”唇角却渗出缕血丝,被她舌尖飞快卷去。东厢房的药气比昨夜更重。我摔上房门时,
卢雨蝉已瘫倒在玫瑰椅里,袖口洇开大片暗红。“你服了毒?”我扯开她衣领,
颈侧浅疤周围泛着诡异的青紫。她格开我的手,从枕下摸出个珐琅小盒。
挖了坨墨绿药膏抹在腕间旧疤上,那青紫竟肉眼可见地褪去。“雕虫小技。”她喘着气笑,
“家传的‘朱颜改’,服下能暂改脉象,骗过太医罢了。
”药膏辛辣的气味冲得我太阳穴直跳。广源寺初遇时她袖口的药气,昨夜合卺时的血腥味,
此刻都串成了毒线。“卢**究竟有多少秘密?”我攥住她抹药的手,
“令尊可知你随身带毒?”她忽然抬眼,眸中闪过广源寺雨幕般的凉意:“纳兰公子又可知,
你表妹绿萼在长春宫日日服什么药?”她蘸着药膏在我掌心写了个“避”字,
“皇后赐的‘长春汤’,一碗下去,终身难孕。”我如遭雷击。表妹入宫前夜,
曾剪下一缕青丝与我:“若得自由身,为君生儿育女。”她最爱孩提……“所以容若,
”卢雨蝉的叹息像淬毒的针,“在这吃人的地界,没点保命的东西,怎么活?
”窗外忽然传来环佩叮咚。母亲觉罗氏的声音伴着推门声响起:“雨蝉呐,
母亲给你送补身子的……”锦帘掀开的刹那,卢雨蝉猛地将我拽倒在榻上。温热的唇压上来,
药香混着血腥气灌满口腔。母亲惊愕的抽气声中,她染血的指尖**我发间,
喘息着偏头:“母亲恕罪……媳妇和容若,一时情难自禁。
”觉罗氏手中的炖盅“哐当”砸在地上。滚烫的参汤溅上她裙角,
她却死死盯着卢雨蝉散开的衣领——那抹过药膏的颈侧,正印着我方才情急掐出的红痕。
“不知羞耻!”母亲拂袖而去时,门扇摔得梁上灰尘簌簌落下。卢雨蝉立刻推开我,
掏帕子狠狠擦嘴。“委屈公子了。”她冷笑,“权当被狗咬了一口。
”我舔过唇角被她咬破的伤口,血腥味弥漫开来:“彼此彼此。”暮色四合时,福顺来了。
小太监缩在东角门阴影里,递包袱的手抖得像秋风中的叶子:“少……少夫人,
这是您要的绣线。”包袱皮散开一角,露出里头灰扑扑的太监服。
卢雨蝉塞给他一锭银子:“福顺,上月托你打听的事……”“长春宫西配殿看得紧!
”福顺声音发颤,“绿萼姑娘挪去北三所了,
说是失手打碎了贵妃娘娘的玉屏风……”他忽然噎住,惊恐地望向我身后。
父亲明珠的身影从芭蕉丛后转出来,蟒袍下摆沾着夜露:“容若媳妇,私会阉人是何体统?
”福顺噗通跪地磕头如捣蒜。卢雨蝉却将包袱往我怀里一塞,盈盈下拜:“父亲明鉴,
福顺公公是来送广储司新到的苏绣样子。”她抖开包袱,五色丝线在暮色里流淌如虹,
“儿媳想着给容若绣个扇套。”父亲脚尖碾过一地丝线:“深更半夜?
”“白日里母亲教导儿媳要晨昏定省,只得趁夜备礼。”她捡起绞金线捧给父亲,“您瞧,
这是给父亲绣荷包用的金线。”月光照着她低垂的脖颈,新掐的红痕与旧疤交错,
像张破碎的网。父亲忽然俯身,枯枝般的手指捏住她下巴:“好孩子。”他声音温柔得瘆人,
“既如此,往后每月初五,让福顺走正门送绣样。”福顺瘫软在地。
卢雨蝉睫羽轻颤:“谢父亲体恤。”父亲转向我时,脸上温情尽褪:“容若,随我来。
”书房门合拢的瞬间,耳光裹着厉风抽在我脸上。“孽障!”父亲指着多宝格里空出的位置,
“《饮水词》手稿呢?”血腥味在口腔漫开。我摸过案上镇纸——冰凉的石质下压着张诗笺,
是卢雨蝉的字迹: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烧了。
”我迎上父亲暴怒的目光,“既娶新妇,旧物留着徒增伤怀。”镇纸“砰”地砸在额角。
温热的血淌进眼眶时,我听见父亲切齿的冷笑:“好得很!
你且记着——”他染血的指尖戳着我心口,“再敢碰卢氏一根指头,北三所的枯井里,
明日就多具无名尸!”血滴在青砖地上,绽开细小暗花。我捂额返回东厢时,
卢雨蝉正对灯穿针。银针在她指间翻飞,绣绷上已显出半朵墨梅。“公子这伤该用金疮药。
”她头也不抬,“左边抽屉第三格。”我拉开抽屉,药瓶下压着张泛黄的纸。
展开竟是广源寺那日我续词的残稿——别是幽情嫌妩媚,
红烛啼痕休泫的“泫”字被朱砂圈住,旁侧蝇头小楷批注:泪垂为泫,公子落笔时,
心在滴血否?烛火噼啪一响。她剪断绣线,墨梅的蕊心竟用金线绣了个极小“婉”字。
“绿萼最喜墨梅。”她将绣绷递来,梅枝虬结处暗藏针脚:北三所,枯井东。我攥紧绣绷,
竹骨硌得掌心血痕崩裂:“为何冒险?”她吹熄烛火,月光照亮半边脸颊:“广源寺那日,
你替我披衣时……”窗棂透进的冷光映着她唇角极淡的弧度,“手是暖的。
”更鼓声穿透夜色。她忽然剧烈咳嗽起来,帕子掩住口唇,指缝间渗出暗红。
“朱颜改的毒性发了。”她喘息着摸向药盒,“劳烦公子……倒杯水。
”我冲向桌案时踢翻了矮凳。青瓷壶入手冰凉,壶底却黏着异物——半片翡翠莲瓣,
断口处沾着新鲜的血迹。表妹又自残了!壶身“哐当”砸在桌面。卢雨蝉蜷在榻上,
咳出的血染红了半边衣襟。我扳过她身子,
将药膏狠狠抹在她颈侧青紫处:“你要把自己折腾死才甘心?”她抓住我手腕,
带血的唇贴上来。这次没有伪装,
只有冰冷绝望的气息:“容若……帮帮我……”窗外骤然亮起火光。
福安的呼喊伴着拍门声炸响:“少爷少夫人!北三所走水了!”卢雨蝉瞳孔骤缩。
她染血的指尖抠进我手臂,
喉咙里滚出破碎的气音:“绿……萼……”3裂帛烛泪凝成猩红的瘤子,堆在鎏金烛台底。
她咳出的血溅在绣绷墨梅上,蕊心的“婉”字被洇成紫黑。
“绿……萼……”气音像漏风的破口袋,从她染血的唇间挤出来。窗外火光冲天,
将北三所方向的夜空烧成炼狱。---福安的拍门声混着铜锣狂响,震得窗纸簌簌发抖。
“少爷!北三所走水了!老爷让您即刻带人去救!”仆役的呼喊踏碎了东厢死寂,
杂沓脚步碾过回廊青砖,如同千军万马奔袭。卢雨蝉在我臂弯里抽搐一下,
染血的指尖死死抠住我前襟。她涣散的瞳孔被窗外火光映亮,像两簇濒死的鬼火。
“容…若…”破碎的气音裹着血沫,“井…东…”“闭嘴!
”我扯下幔帐金钩上的汗巾塞进她嘴里,血腥气直冲鼻腔。她腕间旧疤在火光下狰狞凸起,
青紫毒痕正蛛网般向心口蔓延。“不想死就咽下这个!”我从她枕下摸出朱颜改药盒,
挖了满指墨绿药膏强塞进她齿关。药膏辛辣刺鼻。她喉头剧烈滚动,
呛咳着将药和血一同咽下。我扯开她染血的嫁衣前襟,
将剩余药膏狠狠抹上她颈侧蔓延的青紫。指尖触到肌肤滚烫如烙铁,她猛地弓起身,
一口黑血喷溅在我袖口,金线绣的竹纹瞬间污浊。“少夫人这是……”福安撞开门时,
正看见我染血的袖子按在她半裸的胸口。“滚出去!”我抓起药盒砸过去。
珐琅盒擦着福安额角飞过,在门框上撞得粉碎,“备马!去北三所!”福安连滚爬爬退出去。
卢雨蝉忽然抓住我抹药的手,指甲陷进皮肉:“不…不能去…”她急促喘息,
眼底竟恢复一丝清明,“调虎离山…他们要灭口…”窗外火光更炽。
北三所方向的哭嚎声隐约随风传来,像地狱门缝里漏出的哀鸣。我掰开她手指,
扯过锦被将她裹紧:“卢雨蝉,你听着——”我俯身贴近她耳畔,声音压得极低,
“绿萼若死,我让你陪葬。”她染血的唇弯了弯,忽然抬手拔下我束发的玉簪。
青丝散落肩头时,
冰凉的簪尖抵住我喉结:“公子…咳咳…最好祈祷我活着……”她喘息着将簪子塞回我掌心,
“否则…谁给你递刀?”门外马蹄嘶鸣。我攥紧玉簪起身,簪尖在掌心硌出深痕。
冲出院门时,父亲明珠的蟒袍在火光中翻涌如毒云:“带人围住北三所西角门!
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北三所已成人间炼狱。火舌舔舐着朽败的梁柱,
焦臭混着皮肉烧灼的气味灌满鼻腔。太监宫女如无头苍蝇乱撞,一桶桶井水泼向烈焰,
腾起的白雾里裹着凄厉哭嚎。“绿萼!绿萼姑娘在哪?”我揪住一个满脸烟灰的小太监嘶吼。
小太监抖如筛糠:“西…西厢烧塌了!人都挤在枯井那边……”话音未落,
西厢方向轰然巨响,梁柱坍塌的烟尘冲天而起。枯井!我劈手夺过一桶水浇透全身,
埋头冲进火场。热浪灼得面皮发疼,火星溅在湿衣上滋滋作响。绕过烧成火笼的西厢,
枯井旁已挤满逃命的人。几个太监正踩着人肩往井口爬,女人的尖叫和孩童的啼哭绞作一团。
“绿萼!沈绿萼!”嘶吼声被火焰吞噬。井栏边忽地伸出一只污黑的手。
翡翠缠枝莲镯卡在腕骨,半截袖子烧成焦炭,
露出小臂上蜿蜒的烫疤——那是表妹幼时为替我挡滚茶留下的。
“表哥…”微弱的呼唤从井口飘出。我疯魔般拨开人群冲向井沿,
却见攀在井绳上的绿萼突然睁大眼:“后面!”脑后厉风袭来。我偏头急闪,
沉重的木棍擦着耳廓砸在肩胛,骨裂声清晰可闻。剧痛中回身,
只见福安狰狞的脸在火光里扭曲:“少爷对不住了!”第二棍直劈天灵盖!千钧一发,
斜刺里忽地飞来半截烧着的椽子,正砸中福安面门。惨叫声中,枯井东侧坍塌的院墙后,
卢雨蝉扶着断壁喘息。她裹着我那件月白外袍,脸上蒙着湿帕,露出的眼睛被烟熏得通红。
“跳井!”她嘶声厉喝,手中火把掷向福安翻滚的身影。我纵身扑向井口。
绿萼的手冰冷如尸,抓住我的瞬间,井绳“嘣”地断裂!失重感攫住全身,
井壁湿滑的青苔擦过脸颊,最后映入眼帘的是卢雨蝉扑向火场的残影——“轰隆!
”井口被坍塌的梁木彻底封死。***刺骨的阴寒渗入骨髓。井底积水漫过腰际,
腐臭的淤泥裹着碎骨硌在脚下。绿萼瘫在我怀里,翡翠镯卡在嶙峋的腕骨上,
镯身裂痕里渗着血丝。“表哥…”她指尖抚过我肩胛肿胀的伤处,“疼吗?
”井壁渗下的污水滴在额角,混着血水流进眼睛。
《碎玉惊风:纳兰容若与雨蝉劫》这本书展现了作者黑暗料理制造机卓越的想象力和写作天赋。他通过精妙的叙述和恰到好处的情节铺排,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奇幻而真实的世界。主角卢雨蝉绿萼的形象立体而生动,她的聪明和坚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个故事扣人心弦,情节紧凑而又引人入胜。配角们的存在也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张力。这是一本充满魔力和感动的佳作,读后让人回味无穷。
黑暗料理制造机的书真的让人欲罢不能,特别是《碎玉惊风:纳兰容若与雨蝉劫》。故事情节意想不到,跌宕起伏,吸引人的同时又充满了悬疑。这是一本我一直想读下去的好书,太喜欢了!
《碎玉惊风:纳兰容若与雨蝉劫》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令人回味无穷。
对于我来说,《碎玉惊风:纳兰容若与雨蝉劫》是一部真正值得推荐的佳作。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感人至深,男女主角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感谢黑暗料理制造机的才情,写出了这么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