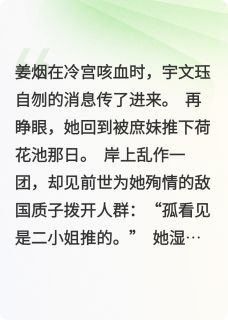二十岁生日那天,我被豪门生父接回苏家。他慈爱地摸着我的头:“晚晚,
爸爸给你找了门好亲事。”三天后,我穿着百万婚纱,嫁给了商业巨鳄顾淮之。婚礼后台,
我对着镜子擦掉眼泪。身后突然响起男人清冷的声音:“哭什么?
”他捏着我下巴抬起:“嫁给我很委屈?”我颤抖着摇头。“那就别怕。
”他擦掉我眼角泪痕,“以后跟着我。”直到那天,我在书房发现一份婚前协议。
协议末尾写着:“保护苏晚晚,直至苏氏破产。”原来我只是他报复苏家的棋子。
我撕碎协议夺门而出。却在庭院被顾淮之抓住手腕。他把我按在墙上,
声音沙哑:“你以为这只是交易?”“十年前孤儿院后巷,
那个递给我面包的女孩……”“我找了她整整十年。”---雨水,
总是这样不合时宜地落下来。冰冷,黏腻,带着一种洗刷不净的沉闷气味,
固执地渗入孤儿院门口那道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深处。苏晚晚站在屋檐下那片窄小的阴影里,
雨水顺着破瓦的缝隙滴落,砸在她洗得发白的帆布鞋尖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旧得脱线的帆布书包,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仿佛那是连接过去某个安全世界的唯一缆绳。书包里没有书,
只有几件同样单薄、洗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衣物,
还有一张边角磨损得厉害的小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模糊的、年轻女人的笑脸,
早已在无数次摩挲中变得模糊不清。二十岁生日。多么奢侈又陌生的一个词。
一辆通体漆黑、线条冷硬得如同刀锋劈凿而成的轿车,碾过门口坑洼积水的水泥路面,
悄无声息地滑停。车轮带起的泥点溅上旁边干枯的杂草,留下几点污浊的印记。
车身光洁如镜,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和孤儿院破败的红砖墙,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割裂感。
车门无声打开。一个穿着笔挺黑色西装的男人走下来,皮鞋踩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没有一丝多余的声响。他的目光精准地锁定了屋檐下的苏晚晚,锐利得像手术刀,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审视。“苏晚晚**?”男人的声音平板无波,没有丝毫疑问的语气,
纯粹是确认。苏晚晚下意识地后退了小半步,脊背抵上身后冰冷潮湿的砖墙。
那凉意透过薄薄的衣衫,直刺入骨。她喉咙发紧,只是很轻、很轻地点了一下头。男人侧身,
拉开了厚重的后车门。车内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柔软奢华的深色皮革,
散发着新车的味道和一种昂贵皮革特有的气息,温暖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
瞬间隔绝了外面潮湿阴冷的雨幕。“请。”男人做了一个无可挑剔的手势。
苏晚晚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孤儿院那扇熟悉又沉重的铁门,在雨雾中沉默着,
像一个褪色的旧梦。几个小小的身影挤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后面,模糊的脸贴在玻璃上,
好奇又畏惧地望着这边。她吸了一口气,那冰冷的空气带着水汽,沉甸甸地坠入肺里。然后,
她弯下腰,钻进了那片干燥、温暖,却更让她感到无所适从的黑暗之中。
车门在她身后沉重地关上,发出闷响,彻底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和过去二十年的人生。
引擎低沉地启动,车子平稳地滑出,
孤儿院模糊的轮廓在布满雨痕的后车窗里迅速变小、消失。车窗外,
城市冰冷的钢铁森林飞速掠过,霓虹灯在雨雾中晕染开一片片迷离的光斑。
苏晚晚蜷缩在宽大柔软的后座一角,像个误入禁地的幽灵,身体僵硬。车内暖风开得很足,
吹拂着她**在廉价T恤外的手臂,却怎么也驱不散那股从骨髓深处透出来的寒意。
她无法思考,大脑一片空白,只有车轮碾过湿滑路面的沙沙声,单调地重复着。
不知过了多久,车子驶入一片截然不同的区域。
道路两旁高大茂密的梧桐树在雨幕中投下浓重的阴影,隔绝了喧嚣。
雕花的黑色铁艺大门无声滑开,轿车驶入一个庞大而寂静的庄园。
雨点砸在精心修剪过的草坪和名贵的观赏植物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最终,
车子停在一栋灯火通明的巨大白色建筑前。西装男人撑开一把巨大的黑伞,拉开车门。
苏晚晚几乎是本能地抗拒着踏出车门,但身体还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挪了出去。
伞隔绝了雨水,却隔绝不了那股无处不在的、属于陌生与权势的压迫感。踏入苏宅大厅,
光线骤然变得明亮而刺眼。巨大的水晶吊灯从高耸的天花板上垂下,折射着冰冷璀璨的光芒。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昂贵香薰、新鲜插花和某种难以名状的陈腐气息的味道。
脚下是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倒映着她局促不安的身影和身上格格不入的旧衣服。
“老爷在书房等您。”一个穿着整洁制服的中年女人不知何时出现在面前,
脸上带着训练有素的、无可挑剔的恭敬微笑,但那笑容里没有丝毫温度。
她的目光在苏晚晚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和帆布鞋上飞快地扫过,像羽毛拂过,
却带着针刺般的审视。女人引着苏晚晚,穿过空旷得能听到脚步回音的巨大客厅,
走上铺着厚厚地毯的旋转楼梯。走廊两侧挂着巨大的油画,画中人物神情威严,
目光似乎穿透画布,落在她身上。书房的门厚重而沉实。女人轻轻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一个低沉威严的声音:“进来。”门开了。书房比苏晚晚想象中还要大,
几乎像一个小型图书馆。深色的实木书架顶天立地,塞满了厚重的书籍。
一张巨大的红木书桌摆在中央,像一艘航行在知识海洋中的旗舰。
一个穿着深色丝绒睡袍的男人坐在宽大的皮椅里,背对着门口,面朝着巨大的落地窗。
窗外是庄园里在雨中显得模糊而阴郁的景观。听到脚步声,皮椅缓缓转了过来。苏明诚。
苏晚晚在财经杂志的封面上见过这张脸无数次。如今,这张脸真实地出现在她面前。
保养得宜,看不出太多岁月的痕迹,只是眼角有些细密的纹路,眼神锐利如鹰隼,
带着长期上位者特有的审视和不容置疑。他看起来并不老,
却有一种沉淀下来的、岩石般的厚重感。他站起身,朝着苏晚晚走来。他很高,步伐沉稳,
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苏晚晚几乎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在空旷的书房里回荡。
他在她面前站定,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片刻,
像是在仔细辨认一件失而复得、却已陌生的旧物。那目光复杂难辨,有审视,有估量,
唯独没有久别重逢的温情。然后,他抬起手。苏晚晚的身体瞬间绷紧,下意识地想躲开。
那只手却只是轻轻地落在了她的头顶,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生疏的温和,
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动物。“晚晚,”苏明诚的声音低沉,
带着一种奇异的、类似慈爱的腔调,每一个字都敲在苏晚晚紧绷的神经上,“这些年,
让你在外面受苦了。”他的掌心温热,但苏晚晚只觉得头顶被烙铁烫了一下,浑身僵硬。
“爸爸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他继续说,手指甚至在她有些枯黄的发丝上轻轻梳理了一下,
动作有些生硬,“现在好了,回家了。”家?
苏晚晚看着眼前这巨大、冰冷、奢华得令人窒息的空间,这个词像一颗尖锐的石头,
卡在喉咙里,带来一阵刺痛和窒息感。她喉咙发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苏明诚似乎并不需要她的回应。他收回手,踱回书桌后,双手撑着桌面,
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直接,穿透了刚才那层虚伪的温情面纱。“爸爸这次接你回来,
”他看着她,眼神平静无波,仿佛在宣布一项早已决定的商业决策,“是给你找了门好亲事。
”苏晚晚猛地抬起头,瞳孔骤然收缩。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
血液瞬间冲向头顶,又在下一秒冻住。“顾氏集团的掌舵人,顾淮之。
”苏明诚的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青年才俊,前途无量。
配得上我们苏家的女儿。”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苏晚晚瞬间变得惨白的脸上,
嘴角似乎几不可察地向上牵动了一下,那更像是一种对猎物反应的评估,而非笑意。“婚礼,
三天后举行。”这几个字像冰锥,狠狠凿进苏晚晚的耳膜。
“爸爸……”苏晚晚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
“我……我不认识他……”“重要吗?”苏明诚打断她,语气陡然转冷,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顾家是苏家重要的战略伙伴。你能嫁过去,
是苏家给你的体面,也是你该尽的义务。”义务?体面?
苏晚晚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四肢百骸都僵硬冰冷。原来所谓的“回家”,
所谓的“惦记”,不过是为了一场**裸的利益交换。她不是女儿,
只是一件被找回的、可以用来交易的物品。“你只需要听话。
”苏明诚的声音恢复了那种掌控一切的平稳,带着一种令人绝望的笃定,
“安心准备做新娘子。苏家不会亏待你。”他挥了挥手,
那个一直静立在门口、面带职业微笑的中年女人立刻走上前来,
姿态恭敬却不容抗拒:“**,请跟我来,您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设计师和造型师稍后就到。”苏晚晚被那女人半搀扶半引领地带离了书房。
厚重的木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苏明诚的身影,
却无法隔绝他那句冰冷的话语在脑中反复回响。三天。她像个提线木偶,
被推进了一个疯狂旋转的漩涡。无数陌生的人围着她打转。
顶尖的设计师团队带着挑剔的目光为她量体裁衣,高级面料冰凉的触感滑过皮肤,
带来一阵阵战栗。珠宝顾问捧着丝绒托盘,上面陈列着璀璨得令人眩晕的钻石项链和耳环,
冰冷的光芒刺得她眼睛生疼。造型师们在她脸上、头发上忙碌,
带着各种她叫不出名字的瓶瓶罐罐和工具。她们的手指灵巧而冰凉,动作专业而疏离,
偶尔低声交谈几句,目光偶尔扫过她时,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
苏晚晚全程沉默。她像一个被精心装扮的展品,一个即将被献祭的祭品。身体被摆弄着,
灵魂却抽离出来,悬浮在半空,冷漠地看着这一切荒诞的进行。
每一次试穿那件价值不菲、缀满手工刺绣和水晶的婚纱,沉重的裙摆都像无形的枷锁,
勒得她喘不过气。镜子里映出的那个妆容精致、华服加身的陌生女子,眼神空洞,
仿佛一具没有灵魂的美丽躯壳。没有人问她是否愿意,没有人关心她的恐惧。
苏明诚只在一次晚餐时出现,看着一身华服、局促不安地坐在巨大餐桌另一头的苏晚晚,
满意地点点头:“很好。顾家会喜欢的。”那语气,如同在验收一件即将交付的货物。
时间在麻木的忙碌中流逝得飞快,又慢得像钝刀子割肉。转眼,便到了婚礼当天。
苏晚晚坐在苏宅主卧宽大奢华的梳妆台前。巨大的椭圆形镜子清晰地映出她此刻的模样。
雪白的头纱如一层朦胧的薄雾,笼罩在精心梳理、盘起的发髻上。
婚纱的蕾丝领口贴合着颈项,勾勒出脆弱的弧度。脸上是化妆师耗费数小时打造的完美妆容,
掩盖了苍白,修饰了轮廓,精致得如同橱窗里昂贵的瓷娃娃。唯有那双眼睛,
像两口枯竭的深井,空洞地望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美丽的新娘。镜子里的人很美,
美得不真实。婚纱的每一寸蕾丝,头纱的每一根细纱,都散发着金钱堆砌出的昂贵光泽。
可这美丽之下,是冰冷的交易,是注定的牢笼。外面隐约传来婚礼进行曲悠扬的旋律,
还有宾客们模糊的谈笑声。那声音隔着厚重的门板传来,像另一个世界的喧闹,
与她此刻的寂静格格不入。一种巨大的、无法言喻的悲凉和荒谬感,如同冰冷的潮水,
瞬间淹没了她。胸口憋闷得快要爆炸。她猛地吸了一口气,试图压下那股汹涌的情绪,
却徒劳无功。眼眶迅速发热,酸涩刺痛。一滴滚烫的泪珠,毫无预兆地挣脱了眼眶的束缚,
顺着光洁的脸颊滑落,砸在婚纱细腻的缎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不规则的湿痕。
她慌忙抬起手,指尖带着细微的颤抖,用力地、近乎粗暴地去擦拭眼角和脸颊。不能哭!
妆会花!苏明诚会不高兴!顾家的人会怎么看?这念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她脆弱的神经。
她不能失态,她必须扮演好这个“完美新娘”的角色,哪怕心如刀绞。
镜中的影像因为泪水而扭曲模糊。她用力眨眼,想看清,想把那该死的眼泪憋回去。
可越是用力,泪腺反而像失控的闸门,更多的泪水争先恐后地涌出,顺着她擦拭的指缝溢出。
就在这时,一个清冷低沉的声音,毫无预兆地在她身后响起,
像一块冰投入死寂的水面:“哭什么?”苏晚晚浑身剧震,擦拭眼泪的手猛地僵在半空。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骤然停止了跳动,随即又疯狂地擂动起来,
撞得胸腔生疼。她僵硬地、极其缓慢地转过身。一个高大的身影,
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梳妆间光线稍暗的角落。他斜倚着深色的丝绒窗帘,
姿态带着几分慵懒的随意,却散发着一种无形的、极具侵略性的压迫感。
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礼服,衬得他肩线宽阔平直,身形挺拔如松。
光线勾勒出他深刻而冷峻的侧脸线条,鼻梁高挺,下颌线绷得有些紧。他的目光,
像淬了寒冰的利刃,穿透梳妆台前明亮的灯光,精准地锁定在她脸上,带着审视,
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悦?顾淮之。她的“新郎”。苏家为她选定的“良配”。
也是那个即将用婚姻禁锢她一生的陌生男人。空气仿佛凝固了。
梳妆间里只剩下苏晚晚自己失控的心跳声,咚咚作响,震耳欲聋。
她甚至能清晰地听到泪水滴落在婚纱缎面上那细微的、啪嗒的声响。顾淮之站直了身体,
迈开长腿,不疾不徐地朝她走来。锃亮的黑色皮鞋踩在厚软的地毯上,没有发出丝毫声音,
却像一步步踏在苏晚晚紧绷到极致的心弦上。他停在她面前,
距离近得她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清冽冷峻的雪松气息,混合着淡淡的烟草味,
强势地侵入她的感官。他的目光沉甸甸地压下来,落在她犹带泪痕、努力维持平静的脸上,
带着一种冰冷的穿透力。“嫁给我,”他开口,声音低沉平稳,却字字清晰,
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质询,“很委屈?”那冰冷的、审视的目光,像无形的针,
扎进苏晚晚慌乱的心脏。委屈?这个词太轻了,
轻得无法承载她此刻被当成货物般交易的屈辱和绝望。她猛地低下头,
不敢再看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仿佛那样就能藏起自己所有的狼狈。喉咙被巨大的酸涩堵住,
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用力地、幅度很大地摇着头。乌黑的发丝拂过苍白的脸颊,
沾上未干的泪痕。头纱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那层朦胧的薄纱,此刻更像一个脆弱的囚笼。
一只骨节分明、带着薄茧的手伸了过来,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捏住了她的下巴。
指尖的温度微凉,却像烙铁般烫得苏晚晚浑身一颤。她被迫抬起头,
再次迎上顾淮之深不见底的目光。他的指尖微微用力,迫使她完全仰起脸,
清晰地暴露出那双盛满泪水、写满惊惶和脆弱的眼睛。他俯视着她,眼神锐利如鹰隼,
似乎在仔细分辨她眼底每一丝情绪。苏晚晚的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
像一片被狂风撕扯的落叶。下巴被他捏住的地方传来清晰的痛感,混合着巨大的羞耻和恐惧,
让她几乎窒息。她想挣脱,身体却僵硬得如同石雕。眼泪更加汹涌地溢出,顺着眼角滑落,
流过他捏着她下巴的手指。顾淮之的眉心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浪漫的倾听者的作品总是让人眼前一亮。在《契约新娘是白月光》中,他展现出了极高的文笔技巧和深厚的人性洞察力。
《契约新娘是白月光》是一本让人感动至深、跌宕起伏的作品。男女主角的形象塑造出色,故事牵动人心,让人沉浸其中。感谢作者浪漫的倾听者的智慧,写出了如此精彩的作品!
作者浪漫的倾听者的文笔细腻而出色,《契约新娘是白月光》展现了他独特的风格。故事的剧情紧凑,扣人心弦,读完之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令人喜爱的作品,我对作者的才华感到十分钦佩。
浪漫的倾听者的《契约新娘是白月光》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故事情节紧凑,人性描绘细致,让人期待后续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