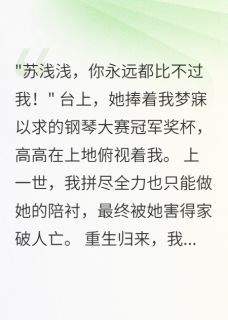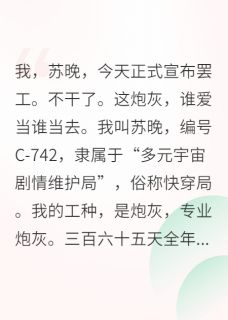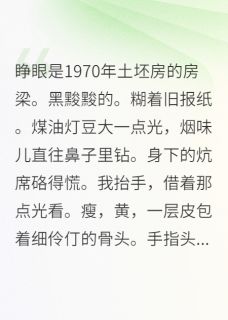
睁眼是1970年土坯房的房梁。黑黢黢的。糊着旧报纸。煤油灯豆大一点光,
烟味儿直往鼻子里钻。身下的炕席硌得慌。我抬手,借着那点光看。瘦,黄,
一层皮包着细伶仃的骨头。手指头肚儿上几个冻疮疤,紫红色,刚结痂。不是做梦。
我真回来了。回到十五岁这年,全家命运的岔路口。上辈子,就这个冬天,我爹摔断了腿。
没钱治。拖拖拉拉,成了瘸子。队里重活干不了,工分挣不够。家里塌了天。娘熬干了心血,
不到五十就走了。弟弟冬青,那么聪明的娃,为了省口粮给我,饿得晕在学校门口,
磕了后脑勺,人傻了。我呢?顶了爹的缺去修水渠,肩膀压得变了形。
后来嫁了隔壁村瘸腿的老光棍,换了两袋苞谷面。三十岁不到,咳血咳死了。闭眼前,
听说堂姐林梅在城里当了官太太。风光的很。她凭啥?凭她那年顶了我的名,
上了县里的工农兵大学!那通知书,本该是我的。是我趴在油灯下熬了无数个夜,考上的!
被林梅她娘,我那个好二婶,从大队部截了胡。塞给了她亲闺女。这辈子,我回来了。知识。
我脑子里装着几十年的知识。还有全家人的命。都得攥紧了。“秋丫头!死哪去了?
”二婶那破锣嗓子在院门口炸开。“懒骨头!日头晒**了还挺尸?赶紧的,把鸡喂了!
你梅子姐今天要去公社,给她煮俩鸡蛋路上垫吧!”我慢吞吞爬起来。套上打补丁的厚棉袄,
冰凉,硬得像铁板。推开吱呀作响的破木板门。冷风刀子一样刮脸。二婶叉着腰站在院里,
下巴抬得老高。她闺女林梅,穿着八成新的碎花棉袄,围巾捂得严实,
只露一双滴溜溜转的眼睛。“二婶,”我嗓子有点哑,是冻的,“鸡还没下蛋呢。”“没下?
”二婶三角眼一瞪,“哄鬼呢!昨儿个你娘还摸出仨蛋!”“喂狗了。”我说。“啥?!
”二婶声音拔高八度。“昨儿后山蹿下来一条野狗,差点叼走咱家芦花鸡,我拿鸡蛋砸它,
才吓跑的。”我语气平平,搓着冻僵的手,“要不,鸡没了,一个蛋都没了。
”林梅在二婶身后撇撇嘴:“笨死了,拿石头砸啊。”“手里刚好抓着鸡蛋。”我看着她,
“梅子姐脑子快,下回记得提醒我。”二婶气得鼻孔翕张,又找不到话驳。
总不能说狗不如她闺女金贵。“丧门星!”她啐了一口,扯着林梅就走,“梅子咱走!晦气!
”林梅临走还回头剜我一眼,那眼神,跟上辈子她拿到录取通知书看我时一模一样。得意,
轻蔑。好像我是一滩烂泥。我看着她们扭出院子。心里那点火星子,噼啪烧起来了。不急。
通知书,还在大队部躺着呢。离推荐选拔的日子,还有小半年。上辈子,就是选拔前半个月,
通知书“丢了”。这辈子,它得牢牢焊在我手里。娘佝偻着背从自留地回来。挎着个破篮子,
里头几根蔫吧的萝卜缨子。“秋儿,”她声音疲惫,“刚听你二婶嚷嚷了?
鸡蛋……真喂狗了?”“嗯。”我接过她手里的篮子,冰得很,“娘,回屋暖暖。
”灶膛里还有点火星子。我抓了把晒干的豆秸引燃,塞进冷锅底。锅里添瓢水。“娘,
咱家……还有钱吗?”我看着跳跃的小火苗。娘身子一僵,
坐在小马扎上搓着冻裂的手:“问这干啥?”“爹的腿,”我声音低下去,“我昨儿做梦,
梦见爹从崖上摔下来,腿……折了。”娘脸色唰地白了。乡下人信梦。“呸呸呸!童言无忌!
”她慌忙朝地上啐了几口,脸却更白了,
“你爹在石灰窑上工……是险……”她猛地抓住我的手,很紧,指甲掐进我肉里:“秋儿,
这梦……不好,很不好!”“娘,咱得给爹备点钱,”我反握住她冰凉粗糙的手,
“万一……万一真有事,不能拖。”娘的眼神慌乱起来,像受惊的鸟:“钱……哪有钱啊?
就……就你姥姥走时给的那个银镯子……”她声音抖了,“压在箱底最底下,
预备着……救命……”上辈子,爹摔断腿,娘就是卖了这镯子。可钱不够,只够抓几副草药,
止疼都勉强。爹的腿,生生拖废了。“镯子不能动!”我斩钉截铁。那是娘最后一点念想。
卖了它,娘的心气儿就彻底散了。“不动?那……那咋办?”娘六神无主。“我去挣。
”我说。“你?”娘愕然,“一个丫头片子,咋挣?”“我有法子。
”我看着灶膛里燃起的火,“娘,信我。”挣工分是死路。一天累死累活,壮劳力十个工分,
年底折算,顶天值一毛多。不够塞牙缝。我得找别的路。机会来得快。几天后,
村里爆出个大消息。村支书冯大国的老爹,冯老爷子,在茅坑边摔了一跤。头磕在石头上。
人抬回来时,半边身子不能动,嘴歪眼斜,淌着哈喇子。赤脚医生赵老栓扎了几针,
灌了碗符水,没用。人眼看不行了。冯大国急得满嘴燎泡,在院里打转。
村里人挤在冯家院墙外,探头探脑。“唉,冯老爷子多好个人……”“怕是熬不过今晚了。
”“大国哥这下可……”我挤在人群里。看着冯家堂屋乱成一团。冯大国媳妇的哭声,
赵老栓的叹气声。还有老爷子喉咙里拉风箱似的嗬嗬声。上辈子,老爷子就是这天夜里没的。
冯大国悲痛过度,病了一场,开春后修水渠时精神恍惚,自己也摔伤了腰。村里缺了主心骨,
好些事都乱了套。包括……工农兵学员的选拔。林梅她爹,我那个二叔林有财,钻了空子。
我深吸一口气。拨开人群,走了进去。“大国叔!”院子里瞬间一静。所有人都看我,
像看怪物。冯大国眼通红,胡子拉碴:“秋丫头?你进来干啥?出去!”“大国叔,
”我站定,声音不大,但清晰,“我爷……不是撞邪,是中风。”“啥中风?
”赵老栓不乐意了,他可是权威,“分明是冲撞了茅坑神!”“栓叔,”我转向他,
“您摸摸老爷子左边身子,是不是冰凉梆硬?右边还有点热乎气儿?”赵老栓一愣,
下意识去摸。脸色变了变。“老爷子是不是还憋着尿?小肚子硬邦邦的?”我又问。
冯大国媳妇惊叫:“是!是!爹一直尿不出来!”“脑壳里血管破了,
血块压住了管身子动弹、管拉尿的筋。”我用最土的话解释,“得赶紧把淤血化开,
把堵住的筋络疏通。”“咋……咋疏通?”冯大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针灸。
”我吐出两个字,“**穴位,通经活络。”“你?”赵老栓嗤笑,“毛丫头懂个屁的针灸!
针是能乱扎的?”“栓叔,”我看着他,“百会穴在头顶正中,刺三分,可醒脑开窍。
合谷穴在手背虎口,刺五分,能疏风通络。足三里在膝眼下三寸,刺一寸,
益气活血……我说得对吗?”赵老栓张着嘴,眼珠子瞪圆了。他认得几个穴,
但绝说不出这么准的刺法。“你……你从哪学的?”他结巴了。“书上。
”我指了指冯大国家堂屋墙上糊的旧报纸,“那上面,有篇文章提过一点。”鬼扯。
那报纸是讲春耕的。但我上辈子咳血等死时,隔壁病床是个老中医,絮叨了不少。我记性好,
都刻在脑子里了。冯大国看看我,又看看只剩出气的老爹,一跺脚。“死马当活马医!
秋丫头,你来!扎坏了不怪你!”“大国!”他媳妇尖叫。“闭嘴!”冯大国吼道。
我走到老爷子炕前。屋里一股老人味和药味混杂的浊气。老爷子眼半睁着,浑浊,没了神采。
我洗净手,在火上燎了燎赵老栓的银针。手指按上老爷子花白的头顶。百会穴。沉心,静气。
下针。捻转。很轻。老爷子喉咙里嗬嗬的声音,似乎小了点。再刺合谷。足三里。风池。
肩井。……一套针下去,我后背也湿透了。屋里死寂。所有人都屏着呼吸。
“呃……”一声微弱的**。老爷子歪斜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眼皮也颤了颤!“爹!
”冯大国扑到炕边,声音都变了调。
“尿……尿出来了……”冯大国媳妇指着褥子上一片湿渍,又哭又笑。赵老栓脸色变了几变,
最终,长长叹了口气。看我的眼神,像见了鬼。冯老爷子活过来了。
虽然半边身子还是不利索,但能喂进米汤,能含糊说话。命保住了。我林知秋的名字,
一夜之间传遍了十里八乡。“神了!林家那丫头,几针把冯老爷子从阎王殿拽回来了!
”“老赵家的饭碗怕是要砸喽!”“听说那针法,是看报纸学的?报纸有这能耐?
”议论纷纷。冯大国亲自提了五斤白面、两斤猪油上门。沉甸甸的,
搁在我家瘸腿的破桌子上。“秋丫头,大恩不言谢!”冯大国搓着手,脸膛发红,
“往后有啥难处,跟叔说!”娘局促地站着,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只会一个劲儿说:“支书太客气了……使不得……”“使得!使得!”冯大国看着我,
眼神热切,“秋丫头,有这本事,窝村里可惜了!等开春,公社卫生所招人培训,
叔推荐你去!”我心里一跳。卫生所培训?上辈子没这茬。蝴蝶翅膀扇动了。“谢谢大国叔。
”我没推辞,也没显得多激动,“眼下……倒真有个难处。”“你说!”“我爹在石灰窑,
”我垂下眼,“我总做噩梦……心里慌。大国叔能不能……给窑上管事的递个话,
调我爹去干点别的?离高处远点就行。”冯大国一愣,随即大手一挥:“我当啥事!
包叔身上!石灰窑老张是我把兄弟!明天就让你爹去看料场!轻省!”娘在一旁听着,
眼圈一下子红了。爹的腿,有希望保住了!冯大国走了。娘摸着那袋细白面,像摸着金疙瘩。
“秋儿……”她声音哽咽,“你……你咋会那些?”“娘,我不是说了吗,
”我拿起桌上那本卷了边的《赤脚医生手册》,是我昨天从冯大国家借的,“看书,学的。
”书里根本没有治疗中风的详细针法。但它是个完美的掩护。娘不识字,敬畏地看着那本书,
像看神物。“读书……真能救命啊……”她喃喃道。“嗯,”我把书小心收好,“能救命,
也能改命。”爹调去看料场了。活轻省,安全。娘脸上的愁云散了些。
可二婶和林梅看我的眼神,一天比一天毒。像淬了冰的针。“哟,秋丫头成能人了!
”二婶在井台边洗衣服,故意把水溅到我裤腿上,“针扎得好,把支书家都巴结上了!
白面猪油,啧啧,咱家过年都吃不上!”林梅在旁边帮腔,
声音又尖又细:“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看几本书就能当大夫?笑死人了!
大国叔也是病急乱投医!”我懒得理她们。蹲下,默默搓洗盆里爹那件磨得发白的工装。
心里算着日子。离工农兵学员选拔推荐,还有三个月。通知书,还锁在大队部的铁皮柜里。
钥匙,在会计林有财——我二叔手里。得想个法子,把通知书“偷”出来。光明正大地。
机会很快又来了。开春,倒春寒。连着几天阴雨绵绵。村里土路成了烂泥塘。这天半夜,
雨突然变大。瓢泼似的,砸在屋顶茅草上,砰砰响。还夹着闷雷。我猛地惊醒。不对!
这雨势……上辈子发过一场山洪!冲垮了村头好几户的土坯房!我家这老房子,
后墙根早就被雨水泡酥了!“娘!爹!快醒醒!”我跳起来,使劲推爹娘。“咋了秋儿?
”爹迷迷糊糊。“房子要塌!”我吼,“快出去!”话音刚落。“咔嚓——!
”一声让人牙酸的闷响从后墙传来。紧接着是泥土簌簌掉落的声音。“墙!后墙裂了!
”爹也惊醒了,声音都变了调。娘吓得直哆嗦。“快!去堂屋!”我拽起他们就往外跑。
刚跑到堂屋中央。“轰隆——!”一声巨响。地都震了震。烟尘弥漫。我们原先睡的那屋,
半边土炕连带后墙,塌了!冷风裹着雨水,从巨大的豁口灌进来。爹娘看着那堆废墟,
脸白得像鬼。后怕。差一点,我们仨就被活埋了!“秋儿……你……你又知道?
”娘死死抓着我的胳膊,像抓住救命稻草。“雨太大,”我喘着气,“我听见后墙根有怪声。
”爹蹲在地上,抱着头,肩膀直抖。劫后余生。天蒙蒙亮。雨小了些。
左邻右舍被那声巨响惊动,披着蓑衣跑来看。“哎哟!老林!你家这……”“老天爷!
人没事吧?”“万幸万幸!”冯大国也踩着泥水来了,一看这惨状,倒抽凉气。
“这房子不能住了!太险!”他当机立断,“老林,
你们一家先搬大队部旁边那间空仓房对付几天!等天晴了,队里组织人手,帮你们修!
”爹娘千恩万谢。搬进仓房,虽然也破旧漏风,但至少墙体结实。惊魂甫定,
娘抱着弟弟冬青,还在后怕地哭。我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
房子塌了是意外。但上辈子,更大的灾祸还在后头。山洪。算算日子,就是这两天。前世,
山洪半夜冲下来,卷走了村头两户人。其中就有赵老栓家的小孙子。那孩子才五岁。
冯大国组织人冒雨挖了一夜,只挖回一只小布鞋。村里愁云惨雾了小半年。
洪水还冲垮了村后一小段堤坝。第二年夏天暴雨,缺口变大,淹了半个村的庄稼。损失惨重。
这灾,得想法子消了。可我能怎么说?再说做梦?冯大国能信一次,能信第二次?
得找个由头。正想着,仓房的门帘被掀开。冯大国的儿子冯建军探进头。小伙子十八九岁,
浓眉大眼,在公社念高中,放假在家。“知秋姐,”他有点不好意思,
“我爹说……你家房子塌了,怕你们没柴火烧,让我送点干柴过来。
”他把一捆劈好的柴禾放在门口。“谢谢建军。”我娘赶紧道谢。冯建军挠挠头,看向我,
眼睛亮亮的:“知秋姐,你那天……扎针,真厉害!你看的啥书?能借我瞅瞅不?
”我心里一动。机会。“就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指指角落,“你想看就拿去。
”“哎!谢谢姐!”冯建军高兴地拿起书,又犹豫了一下,“姐,我……我还想问你个事。
”“你说。”“这雨,下得人心慌,”他压低声音,“我今儿去河边挑水,看见水浑得厉害,
还漂着些烂树叶子。我爹说没事,往年也这样。可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好小子!
有警觉性!我立刻顺着他的话,神色凝重起来:“建军,你说得对。这雨下得太邪乎,
上游山里肯定下得更狠。河水浑,漂杂物,这是要发大水的征兆!”“啊?”冯建军脸白了,
“真……真的?”“书上写过,”我加重语气,“这叫‘山洪前兆’。
尤其是咱们村后那段老堤坝,年久失修,最危险!”“那……那咋办?”他慌了。
“得赶紧告诉你爹!”我抓住他胳膊,“让他组织人,趁白天雨小,加固堤坝!
特别是村后那段!再通知村头低洼处的人家,晚上警醒点!最好……先搬到高处亲戚家避避!
”冯建军被我严肃的样子镇住了。“行!我这就去跟我爹说!”他抱着书,转身就冲进雨里。
“秋儿,”娘担忧地看着我,“真会发大水?”“十有八九。”我看着窗外阴沉的天,“娘,
咱们这仓房地势高,暂时安全。你跟爹看好冬青,我去找二婶。”“找她干啥?”娘不解。
“报信。”我扯了块破塑料布披上,“顺便……办点事。”雨丝冰凉。
我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泞里,直奔二叔家。二叔林有财是大队会计,平时架子端得足。
他家是村里少有的砖瓦房,气派。院门关着。我啪啪拍门。“谁啊?”二婶不耐烦的声音。
门开条缝,露出她那张刻薄脸。“秋丫头?你来干啥?”她堵着门,一脸嫌弃,
“我家可没多余地方收留灾星!”“二婶,”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声音急促,
“我不是来借住的!是报信!”“报啥信?”“要发大水了!山洪!”我故意放大声音,
透着惊恐,“支书家建军说的!他看了书,说这是山洪前兆!支书正组织人加固堤坝呢!
让村头低洼的人家赶紧往高处搬!”“啥?”二婶一惊,随即嗤笑,“胡咧咧啥!
建军那小子懂个屁!还看书?书能看出洪水来?”“二婶!宁可信其有啊!”我急切地说,
“我亲眼看见河水浑得吓人!漂着死猫死狗!后山那片老林子,鸟都惊飞了!
这是大灾的兆头!”我故意说得邪乎。二婶脸色变了变,有点将信将疑。“二叔在家吗?
”我踮脚往里看,“这事得跟二叔说说!他是会计,得管啊!”“不在!”二婶没好气,
“去大队部对账了!”“哦……”我露出失望的表情,又压低声音,“二婶,你家在村中间,
地势高,倒不怕。就是我二叔……大队部那屋,靠河沟太近了!万一……”二婶眼皮一跳。
大队部旁边确实有条排水的沟渠。平时没事,真要是山洪下来……“二婶,
我得赶紧去通知别人了!”我作势要走,“您最好去大队部跟我二叔说一声,让他也避避!
命要紧啊!”说完,我不等她反应,转身就钻进雨幕里。二婶站在门口,脸色阴晴不定。
我知道,她怕死,更怕二叔出事。她一定会去大队部。而我,绕了个弯,抄小路,
也直奔大队部。大队部黑着灯。二叔林有财果然在里面。窗纸上映出他伏案的身影,
大概在对账。我躲在墙角柴垛后面,浑身湿透,冻得牙齿打颤。眼睛死死盯着小路。
没几分钟。二婶打着把破伞,深一脚浅一脚,骂骂咧咧地来了。“林有财!林有财!
死里面了?开门!”门吱呀开了。二叔不满的声音:“嚎什么嚎?对账呢!”“对个屁!
”二婶挤进去,声音又急又快,“快收拾东西跟我回家!要发大水了!山洪!”“扯淡!
谁说的?”“秋丫头!不,是建军那小子!支书都信了!正带人加固堤坝呢!
说大队部靠河沟太近,危险!”“冯大国信了?”二叔的声音透着狐疑,
“建军那小子……”“哎呀!宁可信其有!”二婶急了,“秋丫头说河水浑得吓人,
漂死猫死狗!后山鸟都飞光了!邪乎着呢!快走!”里面一阵窸窣,像是二叔在收拾账本。
《重生七零,我靠知识改变全家命运》这本书充满了情感与温暖。作者拉克夏塔的文笔细腻而动人,每一个场景都仿佛跃然纸上。主角冬青林梅的形象鲜明,她的聪明和冷静让人为之折服。整个故事结构紧凑而又扣人心弦,情节穿插有趣,让读者欲罢不能。配角们也各自有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们的存在丰富了整个故事的内涵和情感。这是一篇令人感动和陶醉的佳作,值得每一位读者品味和珍藏。
《重生七零,我靠知识改变全家命运》是我看过的小说中最好的一部。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男女主角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感谢拉克夏塔的出色创作。
《重生七零,我靠知识改变全家命运》是作者拉克夏塔独具匠心的杰作,这本书以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和精彩的描写征服了读者的心。主角冬青林梅的形象鲜明而又有力量,她的勇气和智慧令人钦佩。整个故事情节紧凑而扣人心弦,每个转折都让人无法预料。配角们的存在丰富了故事的层次和趣味性,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命运。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作者对人性和情感的深刻洞察,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生活追求。
《重生七零,我靠知识改变全家命运》这本书巧妙地将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作者拉克夏塔通过精湛的笔力,描绘出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主角冬青林梅的形象鲜明,她的聪明和冷静为整个故事注入了强大的力量。情节跌宕起伏,每一个转折都让人意者会被情节的发展所吸引,无法自拔。配角们的存在也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张力,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这本书充满了惊喜和感动,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深刻的思考和共鸣。《重生七零,我靠知识改变全家命运》是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值得推荐给所有热爱[标签:小说类型]小说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