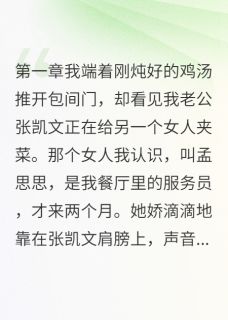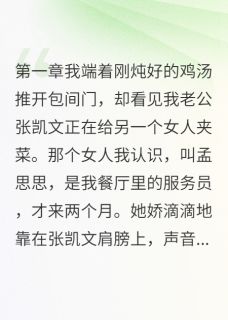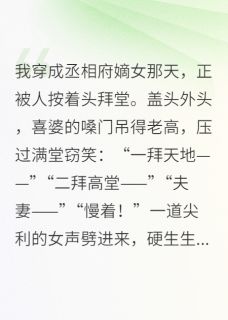
我穿成丞相府嫡女那天,正被人按着头拜堂。盖头外头,喜婆的嗓门吊得老高,
压过满堂窃笑:“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慢着!
”一道尖利的女声劈进来,硬生生截断了流程。盖头下,我只能看见一双缀着珍珠的绣鞋,
嚣张地杵在我面前。是我那庶出的姐姐,沈玉露。“父亲,母亲,
”她声音里裹着蜜糖似的甜腻,却淬着冰碴子,“就这么让妹妹嫁了?
王爷他……可是个活死人啊!冲喜而已,犯得着行全礼么?别冲撞了妹妹的好‘福气’。
”满堂宾客的哄笑像针,密密匝匝扎过来。“就是,沈家嫡女配活死人王爷,绝配!
”“冲喜娘子罢了,还真当自己是正头王妃了?”“听说这位大**是个草包,
琴棋书画样样稀松,倒也不算委屈了端王……”我爹,当朝丞相沈崇山,端坐上首,
一声没吭。我继母柳氏,用帕子掩着嘴,眼里的幸灾乐祸藏都藏不住。
心口那股属于原主的悲愤和绝望,像烧开的滚水,咕嘟咕嘟顶着我的天灵盖。原主沈檀兮,
顶着嫡女的名头,活得还不如柳氏身边的一条狗。亲娘早逝,留下个“废柴”的名声,
被继母和庶姐踩在泥里十几年。如今,更被当成弃子,
塞给传说中中毒昏迷、形同废人的端王萧烬冲喜。沈玉露见无人阻拦,胆子更大,
竟伸手来掀我的盖头:“妹妹,让大伙儿瞧瞧,
你这‘好福气’……”就在她指尖即将触到红绸的刹那——“本王的王妃,也是你能碰的?
”一道低沉、微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的男声,突兀地响起。
像一块巨石砸进沸腾的油锅。整个喜堂,瞬间死寂。所有哄笑、议论,戛然而止。
连沈玉露伸出的手,都僵在半空,脸上的得意凝固成滑稽的惊恐。
我猛地攥紧了藏在袖中的手。这声音……是那个“活死人”王爷?盖头遮挡了视线,
我只能循着声音的来源,微微侧过头。一阵极轻、极缓的轱辘声碾过地面。由远及近。
停在……我身侧。浓重的药味混杂着一丝清冽的冷梅香,钻进我的鼻腔。“王……王爷?
”司仪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您……您怎么……”“本王还没死。
”那声音带着一丝病气的虚弱,却字字清晰,砸在每个人心上,“拜堂这等大事,岂能缺席。
”他顿了顿,气息似乎有些不稳,低低咳了两声,才继续道:“礼,继续。”“本王听着。
”喜堂里静得可怕。只有红烛燃烧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还有我身边那人压抑的、断断续续的轻咳。司仪像是被掐住了脖子,
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抖抖索索地重新喊:“夫……夫妻对拜——”我被人扶着,
僵硬地转身,对着旁边那个坐在轮椅上的模糊轮廓,弯下腰。盖头晃动的缝隙里,
瞥见一角玄色暗金纹的袍角,搭在毫无生气的腿上。还有一只苍白修长、骨节分明的手,
随意地搭在轮椅扶手上,指尖微微蜷着,透着一股病态的无力。礼成。
“送入洞房——”我被两个手脚发软的喜娘几乎是架着,离开了那片令人窒息的死寂。身后,
是无数道惊疑不定、探究恐惧的目光,死死钉在我和那个轮椅上的人影上。
新房设在王府主院,静得吓人。龙凤红烛高燃,映得满室通红,却驱不散那股子沉沉的死气。
药味更浓了,几乎盖过了熏香。伺候的下人屏息凝神,动作轻得像猫,
放下合卺酒和子孙饽饽,就逃也似的退了出去,仿佛多待一刻都会被这屋里的“晦气”沾染。
门被轻轻带上。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那个坐在轮椅里,背对着我,面向窗外的男人。
窗外是沉沉夜色,无星无月。他依旧穿着那身玄色婚服,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
仿佛随时会被风吹散。轮椅的扶手边,放着一碗漆黑的药汁,早已凉透。
我扯下那碍事的盖头,随手扔在铺满红枣花生的喜床上,发出“哗啦”一声轻响。
他像是被惊动,轮椅缓缓转了过来。烛光终于映亮了他的脸。我呼吸一窒。
那是一张……近乎妖异的脸。苍白,瘦削,颧骨微凸。
长久的病痛折磨在他脸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眼下带着浓重的青影。可偏偏,那双眼睛。
漆黑,深邃,像寒潭古井,沉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没有久病之人的浑浊,
也没有被冲喜的愤怒或屈辱。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平静得让人心头发毛。
他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我,审视,探究,不带任何情绪。“沈家大**,”他开口,
声音依旧是那种病弱的沙哑,却字字清晰,“沈檀兮?”“是我。”我挺直背脊,回视他。
怕什么?再糟能糟过在沈家当受气包?我径直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冷茶,一口灌下去,
压下喉咙里的干涩,“端王殿下,萧烬?”他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
目光落在我随意丢在床上的红盖头上,又移开。“委屈你了。”他说,
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我扯了扯嘴角:“彼此彼此。冲喜娘子,活死人王爷,
谁也没比谁强多少。”他闻言,那双深潭般的眼眸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极快的微澜,
快得让我以为是错觉。“你倒是……直白。”他低低咳了两声,
苍白的脸颊因咳嗽泛起一丝不正常的潮红。“直白点好,省得猜来猜去累得慌。
”我放下茶杯,走到他轮椅前,蹲下身,平视他的眼睛,“王爷,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知道你醒着,外头那些人不知道。这亲事怎么回事,你我都清楚。你不想娶,我也不想嫁。
但眼下,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浓密的长睫垂下,遮住了眼底的神色,
只看到一片鸦羽般的阴影。“哦?”尾音微微上扬,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兴味。
“沈家把我当废棋扔过来,是料定你活不长,我掀不起浪。你府里那些牛鬼蛇神,
估计也盼着你早点咽气好分家产。”我语速很快,“我呢,只想找个地方喘口气,
不想莫名其妙死在你这王府里。所以,合作吗?”我朝他伸出手。“我帮你稳住局面,
当个合格的‘挡箭牌’王妃。你保我平安,给我一处安身立命的地方。井水不犯河水,如何?
”他没有立刻回答。房间里只剩下红烛燃烧的细微声响,还有他压抑的呼吸。他抬起眼,
重新看向我伸出的手,那目光沉静依旧,却仿佛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沈檀兮,
”他缓缓念着我的名字,声音低哑,“‘檀’香清贵,‘兮’语助雅。可惜了。
”他在可惜什么?可惜这名字配了我这个“废柴”?我心头莫名一刺,正要反唇相讥。
他却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抬起了那只苍白的手。指尖冰凉,带着常年浸染药味的微苦气息,
轻轻搭在了我的手心。他的手很冷,没什么力气,虚虚地握着。“成交。”两个字,
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过,”他话锋一转,
深黑的眼眸里似乎闪过一丝极淡的促狭,“王妃,戏要做足。”我还没明白他什么意思,
就见他眉头猛地一蹙,脸色瞬间煞白如纸,身体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起来,
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嗬嗬声,整个人像是要蜷缩进轮椅深处。
“咳…咳咳咳……药……药……”他断断续续地**,声音破碎,痛苦不堪。我懵了一瞬。
随即反应过来。好家伙,影帝啊!这无缝切换的演技!“王爷!王爷您怎么了?!
”我立刻拔高嗓门,声音里瞬间染上哭腔,慌乱地扑到桌边端起那碗冷透的药,“药!
药来了!”我手忙脚乱地想把药碗凑到他唇边,脚下却“一个不稳”,整碗黑漆漆的药汁,
“哗啦”一声,全泼在了他胸前华贵的玄色婚服上!浓重的药味瞬间弥漫开来,浸透了衣料。
萧烬的咳嗽声……诡异地停顿了半秒。我清晰地看到他搭在扶手上的那只手,
指节猛地攥紧了一下,青筋都绷了出来。“哎呀!妾身该死!妾身笨手笨脚!
”我哭得更大声了,扑过去用袖子胡乱地擦他胸前的污渍,暗中却狠狠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
压低声音,“忍住了!敬业点!”萧烬的身体似乎僵硬了一下。随即,
更剧烈的咳嗽爆发出来,伴随着痛苦的喘息,仿佛下一秒就要背过气去。“来人!快来人啊!
王爷不好了!”我声嘶力竭地朝着门外喊。房门被猛地撞开。
守在门外的老管家福伯带着两个小厮惊慌失措地冲进来,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他们“病危”的王爷,胸前一片狼藉,
被新王妃哭哭啼啼地抱着胳膊摇晃,咳得撕心裂肺,一副随时要驾鹤西去的模样。“王爷!
”福伯吓得魂飞魄散,扑过来。“快!快扶王爷去歇息!换身干净衣裳!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
“都怪我……都怪我笨……”福伯等人哪还顾得上我这个“笨手笨脚”的新王妃,
手忙脚乱地推着轮椅,簇拥着咳得惊天动地的萧烬,迅速消失在通往内室的屏风后。
房门被重新带上。我脸上的眼泪瞬间收得干干净净。抬手抹掉嘴角不存在的泪痕,
我走到桌边,给自己重新倒了杯茶,慢悠悠地啜了一口。啧,这王府的水,有点深啊。不过,
开局……还不算太坏。至少,这位“活死人”王爷,是个明白人。第二天,
整个京城都炸了锅。端王萧烬,
那个中毒昏迷大半年、被太医判了“死刑”只等咽气的活死人,在冲喜当晚,竟然醒了!
虽然据说只是回光返照,被新王妃笨手笨气差点送走,但毕竟睁眼了,说话了!
这消息比长了翅膀飞得还快。沈家自然也得了信。我那丞相爹沈崇山,继母柳氏,
还有庶姐沈玉露,来得那叫一个快。美其名曰:探望王爷,关心女儿。
我坐在萧烬床榻边的绣墩上,手里捧着一碗厨房刚送来的、黑乎乎散发着怪味的“补药”,
用小银勺慢条斯理地搅着。萧烬半靠在床头,脸色依旧苍白得吓人,闭着眼,呼吸微弱,
一副油尽灯枯的模样。只有搭在锦被外的那只苍白的手,指尖偶尔会极其轻微地动一下。
柳氏一进门,目光就像探照灯似的在我和萧烬身上扫了几个来回,
最后定格在萧烬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上,眼底飞快地闪过一丝失望,随即堆起满脸的关切。
“哎哟我的王爷啊!”她捏着帕子,几步就扑到床前,声音哽咽,“您可算醒了!
菩萨保佑啊!妾身和老爷在家是日日悬心,夜不能寐啊!
”沈崇山也摆出一副沉痛忧心的样子,捋着胡须:“王爷吉人天相,醒来就好,醒来就好啊!
檀兮,你可得尽心伺候王爷,万不可再出差错!”他意有所指地瞪了我一眼。
沈玉露则站在柳氏身后,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先是贪婪地扫过这间布置华贵的内室,
又落到我身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和嘲弄。“妹妹,”她捏着嗓子,声音甜得发腻,
“昨晚可吓坏姐姐了!听说你笨手笨脚地把药都泼王爷身上了?啧啧,
在家时母亲就总说你毛躁,这嫁了人,伺候王爷可是天大的事,你可得好好改改这性子,
别连累王爷……”她话里话外,都在坐实我“草包”、“笨手笨脚”的名声。我抬起眼皮,
瞥了她一眼,没搭理她。只是把手里搅得温热的药碗,往前送了送,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王爷,该喝药了。”床上的萧烬,眼皮微微动了动,
极其缓慢地掀开一条缝,露出那双深潭般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又虚弱地闭上,
嘴唇翕动了两下,声音细若蚊呐:“……苦。”“良药苦口利于病,”我语气平静,
把勺子凑到他唇边,“王爷,张嘴。”那姿态,平静中带着一丝不容置喙。
柳氏和沈玉露都愣住了,大概没想到我这个在家唯唯诺诺的“废柴”,敢这么跟王爷说话。
沈崇山眉头一皱:“檀兮!怎可如此无礼!”我没理会他,勺子又往前递了半分,
几乎碰到萧烬苍白的唇:“王爷,喝药。”萧烬闭着眼,眉头痛苦地蹙起,
似乎在抗拒那苦味。僵持了两秒。他终于极其不情愿地,微微张开了嘴。
我手腕稳稳地将一勺药汁喂了进去。动作算不上温柔,甚至有点公事公办的生硬。
萧烬吞咽下去,眉头皱得更紧,发出几声压抑的闷咳。柳氏和沈玉露交换了一个眼神,
那眼神分明在说:看吧,果然是个没规矩没眼力见的草包!连伺候人都不会!
沈崇山脸色更沉了。我像是完全没看到他们的反应,又舀起一勺药,面无表情地继续喂。
一勺。两勺。三勺。房间里只剩下勺子偶尔碰到碗壁的轻响,还有萧烬压抑的咳嗽喘息。
气氛诡异得让人窒息。“咳……咳咳……”萧烬突然一阵猛烈的呛咳,身体剧烈起伏,
苍白的脸上泛起不正常的红晕。“王爷!”柳氏惊呼一声,像是终于逮到了机会,
一步上前就要推开我,“你这孩子!怎么伺候的!笨手笨脚!”她的手还没碰到我胳膊。
“滚开!”一声嘶哑却带着冰冷戾气的低吼,猛地从床上响起!是萧烬!
他不知何时睁开了眼,那双深潭般的眸子里寒光凛冽,像淬了毒的冰刃,
直直射向柳氏伸过来的手。柳氏被那眼神吓得魂飞魄散,伸出的手僵在半空,
整个人像被冻住。萧烬胸膛剧烈起伏,咳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
他颤抖地抬起手指着柳氏,又指向门口,
声音破碎却充满暴戾:“滚……都给本王……滚出去!
”“惊扰……惊扰本王……咳咳咳……想……想本王……死吗?!”最后几个字,
带着濒死的疯狂和恨意,让在场所有人都不寒而栗。沈崇山脸色大变,一把拉住吓傻的柳氏,
连声道:“王爷息怒!王爷息怒!贱内无知,我们这就走!这就走!”他狠狠瞪了我一眼,
那眼神复杂,有警告,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惧。沈玉露更是吓得花容失色,躲在她娘身后,
再不敢看我一眼。一家人,来时气势汹汹,走时狼狈不堪,
几乎是连滚爬爬地被福伯“请”了出去。房门重新关上。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还在“剧咳”的萧烬。我把药碗往旁边小几上重重一放,
发出“哐当”一声。“行了,别装了,人都走了。”我揉了揉被震得发麻的耳朵,
“再咳下去,真把肺咳出来了。”床上的咳嗽声戛然而止。萧烬慢慢止住喘息,
脸上的痛苦神色瞬间褪去,只剩下惯常的苍白和深不见底的平静。他抬手,
用袖子随意擦了擦因为剧烈咳嗽而溢出眼角的生理性泪水,动作带着一丝病弱的优雅。
“王妃,”他看向我,声音恢复了那种微哑的平静,
眼底却残留着一丝方才未曾消散的冰冷戾气,“方才,做得不错。”我哼了一声,
走到桌边给自己倒茶:“彼此彼此。王爷这嗓子,不去唱戏可惜了。”他没接话,
只是目光落在我刚才重重放下的药碗上。“那药,倒了。”他淡淡道。“知道,
”我端起茶杯,“闻着味儿就不对。里面加了点‘好东西’,喝多了,能让你咳得更逼真,
但也死得更快。”萧烬的眸光瞬间沉了下去,像结冰的湖面。“王府的‘耗子’,
也该清一清了。”他语气平淡,却带着森森寒意。我喝着茶,没说话。清耗子?谈何容易。
这端王府,水浑着呢。萧烬是先帝幼子,生母早逝,出身不算顶好,但天资聪颖,
曾经也是先帝属意的储君人选之一。可惜,三年前一场宫宴后莫名中毒,从此缠绵病榻,
成了“活死人”,被新帝“恩养”在这王府里,形同软禁。他这一“病”,
最大的受益者是谁?不言而喻。王府里伺候的人,除了福伯等几个早年跟着他的老人,
其余都是各方势力塞进来的眼线。尤其是厨房和药房,更是重灾区。想清耗子?
先得看看自己手里有几把趁手的“扫帚”。我放下茶杯,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院子里,
几个洒扫的粗使婆子看似在干活,眼神却时不时往主屋这边瞟。“王爷,”我看着窗外,
声音不大,“想钓鱼,光有鱼饵不行,还得有耐心,有网。
”萧烬顺着我的目光也瞥了一眼窗外,苍白的唇勾起一抹极冷的弧度。“网,会有的。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萧烬依旧“病”着,大部分时间昏睡,偶尔“清醒”一阵,
也是咳得天昏地暗,脾气暴躁,动辄打骂下人。我这个“草包”王妃,
也尽职尽责地扮演着角色。伺候汤药?笨手笨脚,经常泼洒。打理庶务?一窍不通,
把账本看得头大,最后全推给福伯。应对各府借着探病名义来打探虚实的访客?
更是木讷寡言,问三句答不出一句,只会低着头绞帕子。很快,
京城里关于端王府的传言又有了新版本:端王萧烬,回光返照,离死不远。端王妃沈檀兮,
草包废物,不堪大用,连冲喜都冲不利索。王府内外,原本紧绷的气氛,似乎都松懈了一些。
那些暗处的眼睛,窥探的频率也降低了。只有我知道,那些被萧烬“打骂”撵出去的下人,
第二天总会因为各种“意外”被调离主院附近,或者被福伯不动声色地“清理”掉。
而我每次“笨手笨脚”泼洒的汤药,都精准地倒进了窗台那盆不起眼的兰草里。几天下来,
那盆原本茂盛的兰草,叶子已经开始发黄枯萎。“网”,在悄无声息地收紧。这天,
宫里突然来了赏赐。说是陛下听闻端王病情略有起色,龙心甚慰,
特赐下上好的人参、灵芝等滋补药材,还有几匹时新的贡缎。来送赏的,
是皇帝身边一个姓李的副总管太监,面白无须,眼神活泛,带着几个小太监。
东西被抬进院子,李总管皮笑肉不笑地对着“强撑病体”出来谢恩的萧烬和我行礼:“王爷,
王妃,陛下隆恩,特意叮嘱,这老山参是百年难遇的极品,最是补气养元,
让王爷务必按时服用,龙体要紧啊。”他特意加重了“务必”两个字。萧烬靠在轮椅上,
裹着厚厚的狐裘,脸色在阳光下白得透明,闻言剧烈地咳嗽起来,好半天才喘着气,
虚弱地道:“臣……谢陛下隆恩……咳咳咳……”我赶紧上前,笨拙地替他抚背,
一边对李总管赔笑:“公公辛苦,快请里面用茶。”“不了不了,”李总管摆摆手,
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萧烬灰败的脸色,又扫过我身上那件半新不旧、料子普通的家常袄裙,
眼底闪过一丝轻蔑,“咱家还要回宫复命。王爷,王妃,留步,留步。”送走了宫里的人,
看着院子里堆着的“赏赐”。那几匹贡缎流光溢彩,确实是好东西。
至于那所谓的“极品”老山参……我蹲下身,拿起那根装在锦盒里、品相极佳的人参,
凑到鼻尖闻了闻。一丝极淡的、几乎被浓郁参味掩盖的、若有似无的甜腥气,钻进鼻腔。
我眼神微冷。好东西?催命符还差不多。“福伯,”我站起身,
把那锦盒递给旁边垂手肃立的老管家,“把这参,好好收起来。陛下赐的‘好东西’,
可别糟蹋了。”福伯接过锦盒,浑浊的老眼看了我一眼,又看向轮椅上闭目养神的萧烬,
微微躬身:“是,老奴明白。”当天下午,沈玉露又来了。这次,她是一个人来的。
穿着一身崭新的桃红撒花袄裙,梳着时兴的发髻,插着赤金点翠步摇,打扮得花枝招展,
比我这正经王妃还像主人。“妹妹!”她一进门,就亲亲热热地挽住我的胳膊,
声音甜得发腻,“几日不见,姐姐可想你了!听说宫里刚赏了好东西下来?快让姐姐开开眼!
”她那双眼睛,贪婪地在我屋里扫视,最后定在了内室屏风旁,
小几上随意放着的那几匹流光溢彩的贡缎上。“哟!这就是贡缎吧?可真好看!”她松开我,
几步就走到小几前,伸手就去摸那光滑的料子,啧啧赞叹,“瞧瞧这颜色,这光泽,
到底是宫里的东西!妹妹,你穿这个肯定好看!”我慢悠悠地走过去,没拦她,
只是在她身后淡淡开口:“姐姐喜欢?”沈玉露摸着缎子的手一顿,回头看我,
脸上堆满笑:“这么好的东西,谁不喜欢?姐姐就是羡慕妹妹你有福气,嫁了王爷,
连贡缎都能穿上身了。”话里话外,酸气冲天。“哦。”我点点头,语气没什么起伏,
“那姐姐就多摸两下,过过手瘾吧。毕竟,”我顿了顿,看着她瞬间僵住的笑容,
“这是陛下赏给王爷养病的。我一个‘笨手笨脚’的王妃,哪配穿这个。
”沈玉露脸上的笑容有点挂不住了,讪讪地收回手:“妹妹这话说的……姐姐就是替你高兴。
”她眼珠一转,又凑近我,压低声音,带着几分神秘:“妹妹,其实姐姐这次来,
是有好事告诉你!”“哦?什么好事?”我端起茶杯,不动声色。“母亲说了,
”她脸上带着施舍般的得意,“看你在王府过得也不容易,身边连个得力的人都没有。
特意让我给你送个人过来!”她朝门外喊了一声,“翠浓,进来!”一个穿着水绿色比甲,
梳着双丫髻,模样颇为伶俐的丫鬟低着头走了进来,规规矩矩地行礼:“奴婢翠浓,
见过王妃。”“这丫头机灵,手脚也麻利,是母亲精心**过的。”沈玉露拉着翠浓的手,
往我面前推,“放在妹妹身边伺候,母亲和我才放心!总比你身边那些粗手笨脚的下人强!
”我看着眼前这个低眉顺眼的翠浓。柳氏精心**过的?呵,
是精心**来监视我的眼线才对吧?“姐姐和母亲真是……费心了。”我放下茶杯,
脸上没什么表情。“应该的!都是自家人!”沈玉露见我似乎没反对,松了口气,
脸上笑容更盛,“那……妹妹,姐姐就不打扰你休息了。翠浓,你可要好好伺候王妃,
听见没?”“是,奴婢遵命。”翠浓恭敬地应道。沈玉露心满意足,
又假惺惺地关心了“病重”的萧烬几句,这才扭着腰走了。她一走,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新来的翠浓。翠浓立刻变得低眉顺眼,手脚麻利地开始收拾我喝过的茶杯,
又去整理床铺,嘴里还乖巧地说着:“王妃,奴婢给您换盏热茶吧?这屋里有些凉,
奴婢去把炭盆拨旺些?”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没说话。直到她把床铺整理好,
又准备去倒茶时,我才淡淡开口:“翠浓。”“奴婢在。”她立刻停下手里的活,垂手恭立。
“你会煎药吗?”我问。翠浓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回王妃,奴婢会的。以前在夫人院里,
就常帮夫人煎药。”“很好。”我指了指旁边小炉子上温着的药罐,“去,把王爷的药煎上。
记住,三碗水煎成一碗,文火慢炖,中间不许离人,更不许旁人插手。煎好了,立刻端来。
”我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王爷的命,就靠这药吊着。出了半点差错,我要你的命。
”翠浓被我眼中骤然迸出的冷意吓得一哆嗦,脸色微微发白,连忙低头:“是!
奴婢……奴婢明白!绝不敢出错!”她小心翼翼地端起药罐,退了出去。
看着她消失在门口的背影,我唇角勾起一丝冷笑。眼线?好啊。正好缺个“试药”的。
日子一天天滑过。有了翠浓这个“得力”帮手,我的日子似乎更“清闲”了。
煎药、送药的活儿都交给了她。她确实“尽心尽力”,每日煎好的药,都按时按点,
小心翼翼地送到萧烬床前。萧烬每次喝药,依旧是那副痛苦不堪、仿佛喝毒药的模样,
咳得惊天动地。翠浓在一旁垂手侍立,低眉顺眼,眼神却总忍不住往萧烬身上瞟,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和……期待?这天午后,我正歪在窗边的软榻上,
拿着一本杂书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翠浓端着刚煎好的药进来,脚步比平时轻快了几分。
“王妃,王爷的药煎好了。”她把药碗放在床边小几上,声音带着一丝刻意压制的兴奋。
我放下书,懒洋洋地起身,走到床边。萧烬半躺着,闭着眼,呼吸微弱。我端起药碗,
拿起勺子,像往常一样搅了搅。一股比平时更加浓郁的、带着一丝诡异甜腥的药味扑面而来。
我动作一顿。来了。我舀起一勺,作势要喂。勺子刚凑到萧烬唇边,他眼皮动了动,
刚要张嘴。“哎呀!”我手猛地一抖!整碗滚烫的药汁,毫无预兆地,
朝着床边侍立的翠浓身上泼了过去!“啊——!”翠浓猝不及防,被滚烫的药汁泼了个正着!
胸口、手臂瞬间湿透,烫得她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我立刻惊慌失措地叫起来,手里的空碗“哐当”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翠浓!你没事吧?
快!快擦擦!”我手忙脚乱地抓起旁边一块布巾就往她身上按,
暗中却狠狠掐了她烫红的手臂一把。翠浓痛得眼泪都出来了,又惊又怒又怕,想躲又不敢躲,
只能强忍着:“没……没事……王妃,奴婢自己来……”“怎么能没事!都烫红了!
”我声音带着哭腔,转头就朝外面喊,“来人!快来人!拿烫伤膏!快去请大夫!
”外面的丫鬟婆子闻声冲了进来,看到的就是翠浓胸前一片狼藉,皮肤红肿,
而我正“焦急”地拿着布巾往她身上按。“快!扶翠浓下去!找大夫!用最好的烫伤膏!
”我连声吩咐,一副心疼坏了的样子。几个婆子赶紧把痛呼连连、狼狈不堪的翠浓架了出去。
房间里乱成一团。我站在原地,看着地上的药碗碎片和泼洒的药汁,
脸上还残留着“惊慌”的表情,眼底却一片冰冷。我慢慢蹲下身,
用指尖沾了一点溅落在地上的、尚且温热的药汁。凑到鼻尖闻了闻。那股诡异的甜腥气,
比之前浓烈了数倍不止。果然,狗急跳墙了。柳氏,沈玉露……你们就这么等不及,
想让我和萧烬一起“病逝”?我站起身,目光转向床榻。萧烬不知何时已经睁开了眼。
他靠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那双深潭般的眸子里,
翻涌着冰冷刺骨的杀意。“网,”他薄唇微启,声音沙哑低沉,像毒蛇吐信,“该收了。
作者十六爪章鱼的《废柴王妃:王爷他不嫌弃》令人沉醉其中,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意想不到的转折让人难以预测。男女主角的形象独特而深刻,使整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真心希望作者能关注到这个评论,期待更多精彩的情节!
作者十六爪章鱼的文笔娴熟,故事情节独特,吸引了我对《废柴王妃:王爷他不嫌弃》的极高关注。
《废柴王妃:王爷他不嫌弃》这本书让人陶醉其中。作者十六爪章鱼的文笔细腻流畅,每一个描写都让人感受到他的用心和情感。主角萧烬沈玉露的形象生动鲜明,她的坚韧和聪明让人为之倾倒。整个故事紧凑而又扣人心弦,每一个情节都令人意想不到。配角们的存在丰富了故事的内涵和戏剧性,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魅力。这是一本令人沉浸其中的佳作,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不同的情感和思考。
《废柴王妃:王爷他不嫌弃》的剧情十分精彩。萧烬沈玉露的性格特点和剧情发展让人意想不到,令人期待后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