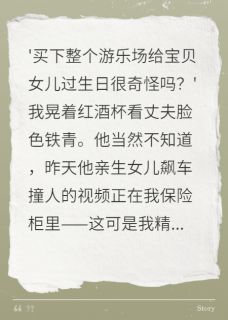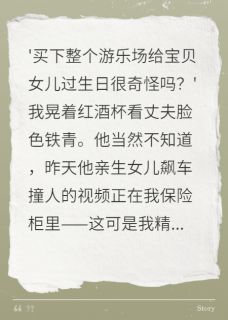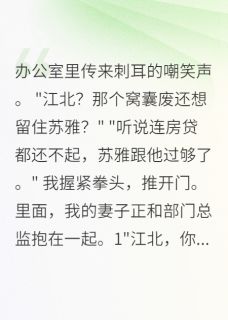三年前暴雨夜,弟弟陈枭将一枚冰冷金属环扣上我濒死的心口。我的人生如流沙般被他抽干,
财富、名誉、未婚妻尽数成为他王冠上的宝石。
三年后他站在云端问我:“现在知道谁是天选之子?
”我只看着藏在他心口、那枚已变成灰蓝色的金属环微笑。他永远不会知道,
当年医生诊断我仅剩三个月的遗传性绝症,正随着他抢走的一切,在他血脉深处倒数归零。
圣罗兰拍卖厅的空气沉重如同凝固的香膏,昂贵的寂静悬浮在镀金吊灯投下的冷光里。
陈暮蜷在边缘一张褪色的丝绒椅中,像一块投入精美湖面的粗粝顽石。
四周是浮动的人声、珠宝的轻碰、雪茄的微甜与香槟的凉气。这些上流的涟漪触碰到他,
便绕道而行。他枯瘦的脊梁紧贴着冰冷的椅背,灰旧夹克下的身体如同一具已被风干的标本。
唯有一双眼睛,未曾死去,死死钉在拍卖台上。那是一只小小的青花笔洗,釉色温润如旧梦,
安静卧在丝绒衬垫之上。聚光灯打在上面,流淌出的光芒刺痛了陈暮的心房。
那是他父亲书房里仅存的旧物,记忆海洋里最后一枚未沉没的贝壳。
他垂在膝上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指甲刮擦着粗糙的椅布,带起一丝干燥的瘙痒。
门廊深处,优雅的嗡鸣忽然被一道裂隙劈开。陈枭手臂环绕着林晚秋,
像展示一件与他身份相配的艺术珍品,从容步入。
剪裁完美的午夜蓝西装勾勒着勃发的力量感,向后梳拢的黑发下,一双眼睛锐利如鹰隼,
瞬间就攫住了角落那片格格不入的阴影。一丝微不可察的、饱含毒液的满意,
滑过他精致的唇角。林晚秋身上那条冰蓝色的绸裙流淌着昂贵的光泽,
贴合着她纤细姣好的曲线。当她的视线不可避免地滑过那片角落的阴影,
撞上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时,她的呼吸猛地一窒。像被无形之针扎穿了精心维持的完美表象,
她纤长的睫羽飞速垂落,死死钉在自己紧攥着镶钻手包的指节上,那里已一片惨白。
一丝慌乱,如投入静湖的石子,在她完美无缺的姿态上漾开细微的涟漪。
拍卖师槌音清脆地落下。那方小小的青花笔洗吸引了场中所有目光。“三万。
”角落传来沙砾摩擦般的声音,划破了精心营造的上流乐章。
无数道审视的目光像聚光灯灼烫地打在陈暮身上,探究着他褴褛衣衫下隐藏的妄想。
陈枭甚至懒得侧目,唇齿间吐出两个字,轻佻得像在赶走一只苍蝇:“五万。”他抬手,
姿态闲适地整理自己一丝不苟的袖口,腕间昂贵的手表闪烁着冰冷的微光。空气仿佛被冻结。
众人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如同观赏一场滑稽剧。“六万。”陈暮的喉结艰难滚动,
声音拔高了一丝,带着被紧压到极限后的粗砺沙哑。他放在膝上的手背上,
那条斜贯的陈旧疤痕被绷紧的肌肉牵动着,如狰狞的蜈蚣扭动了一下。这道疤,
曾属于一个雨夜,为了护住父亲怀中这唯一的旧物,被碎裂的瓷片所赠。“十五万。
”陈枭报出数字,终于侧过脸,目光如淬冰的刀刃,直刺角落。
他唇角勾起清晰而刻薄的弧度,没有看陈暮,
反而低头端详手中不知何时被侍者递来的香槟杯,指尖在金黄的杯壁上轻轻一弹,
发出一声极细微、却令人心悸的脆响。“听个响儿,也算值了。”他对着杯中的液体低语,
更像是对着空气投下一句轻蔑的判决。寂静变成了粘稠的胶质。拍卖槌沉重地砸下,
回声像是给这幕羞辱敲下的休止符。侍者捧着那方温润的笔洗,小心翼翼走向新的主人。
陈枭伸出两根骨节分明的手指,姿态优雅却饱含亵渎,仿佛拈着一件令人恶心的秽物。
他看都没看笔洗一眼,目光始终锁在角落那片阴影里,嘴角的笑意残忍地扩散到眼底最深处。
他优雅地俯身,灼热又带着陈年旧怨的气息拂过陈暮僵冷的耳廓:“哥?”声音轻柔,
却如同毒蛇的信子舔舐耳膜,“喜欢这玩意儿?”捏着笔洗的手指倏地松开。
温润的瓷器坠向陈暮脚边昂贵但冰冷的地毯,滚了两圈,停了下来。
釉面蒙上了细小的绒毛尘埃,暗淡无光。林晚秋的肩膀猛地一抖,像是被无形的鞭子抽打,
眼中迅速蓄满了晶莹的泪水,却死死咬住下唇,倔强地不肯让它落下。那笔洗滚动的轨迹,
仿佛也碾碎了她心中最后一点尚未崩塌的屏障。陈枭手臂用力,
将林晚秋僵硬的身体往前一揽,强迫她直面那片被她亲手舍弃的深渊。他再次凑近陈暮,
鼻尖几乎要碰到对方冰冷的鬓角,嘴唇微动,低沉粘稠的每一个字都裹挟着剧毒的恶意,
精准注入耳蜗:“现在知道……”冰冷的空气突然灌入口鼻,割裂了拍卖厅里窒息的香氛。
城市的寒夜毫不吝啬地将冰冷的锥刺扎进陈暮单薄的衣料。他趔趄着走向地铁站冰冷的入口,
身后厚重的玻璃门隔绝了虚假的繁华与真实的酷刑,
但陈枭灼热的低语和空气中细微的香槟味,却如附骨之疽般缠绕着他的感官,渗入骨髓。
旧居民区的窄巷狭窄、扭曲,像一个被城市遗忘的伤口。两侧的墙壁覆盖着厚重的黑绿霉斑,
如同岁月沉积的疥癣。腐坏的垃圾袋堆积如山,散逸着刺鼻的酸臭与尿臊气息。
仅剩的几盏昏黄路灯光芒微弱,在地上泼开一团团浑浊的光晕,
更多的黑暗则蛰伏在更深的角落和门洞的阴影里,无声地呼吸,觊觎。
陈暮踏入三单元门洞的阴影,污浊的空气几乎凝滞。两道粗壮的身影便如守候腐肉的鬣狗,
从更深沉的黑暗中挤出。一人脸上刀疤横贯眉眼,另一人穿着满是油污的皮夹克,
带着浓重的廉价烟草气味。“哟!落魄大少舍得回来了?”刀疤脸的声音油腻地钻入耳膜,
带着**的嘲讽,“哥几个等你等得火气都上来了!”“少他妈废话!钱!
”皮夹克男不耐烦地猛推陈暮一把,力道凶狠。陈暮的后背狠狠撞上身后冰冷湿滑的砖墙,
脊椎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他稳住身体,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空洞的目光掠过两张写满贪婪和恶意的脸。左手缓慢地探入旧夹克最里层,
在冰冷的皮肤前摸索了片刻,才抽出一小沓被体温熨得温热的、皱巴巴的零钞,
最大面值是一张破旧的棕褐色纸票。他沉默地将钱递出。“操!就这点烂钱?
”刀疤脸一把夺过,粗鄙地朝陈暮脚边湿滑肮脏的地面啐了一口浓痰,“塞牙缝都不够!
下个月再这点鬼钱,”他眼神凶狠如刀,在陈暮脸上剜过,
“老子把你浑身骨头拆散了卖废品!”皮鞋狠狠碾过地上的浓痰,
与皮夹克男一同重新隐入巷子另一头更为浓稠的黑暗里。楼道狭窄陡峭。
生锈的铁制扶手冰冷黏腻,覆盖着一层混杂了油垢与灰尘的奇怪滑腻物。
空气中充斥着尿臊、霉菌和陈年灰尘的浑浊气味。
一盏接触不良的声控灯伴随着陈暮的咳嗽声,才吝啬地闪动几下,投射下晕黄不稳的光晕,
随即又迅速归于黑暗。在三楼右侧锈蚀的门前停下,插入钥匙,反复拧动数次,
才打开那扇沉重的铁门。室内的空气瞬间包裹了他,像浸过冰水的裹尸布。
灰尘、霉菌、腐烂的食物残渣以及隔壁渗入的劣质烟草气味混合成一种难以言喻的污浊味道,
凝固在这不足十平米的狭小空间里。一张嘎吱作响的单人木床,一张瘸腿的木桌,
角落堆叠着空瘪的矿泉水瓶和泡面纸桶,
墙壁大片剥落的水泥露出黑黄色的陈旧污迹——这里像一个被时间遗忘的监牢。
陈暮反手关上铁门,沉重的撞击声将外界最后一点声息彻底隔绝。
沉重的疲惫感如同灌满全身。他几乎是一寸寸地挪到床边,
枯槁的身体轰然砸落在早已失去弹性的床垫上,激起一小片浮尘。
破床发出一连串濒死的**。呼吸带着灼热的痛感,
心口传来熟悉的、如同生锈铁钳绞紧的沉钝痛楚。
右手下意识地按住左胸薄衫下那块微微起伏的位置,
掌心下能感受到单薄皮囊下那颗心脏努力却显得无力的搏动。目光不经意抬起,
凝固在对面墙上。一张小小的、边角严重卷翘泛黄的照片被图钉钉着。
照片里是两个穿着旧校服的少年,在盛夏的石榴树下肩并肩,笑容灿烂得几乎刺伤此刻的眼。
旁边站着他们的父亲,怀里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只青花笔洗。背景是老旧平房,暮色温柔,
石榴枝头星星点点吐露着生机。剧烈的刺痛猛地击穿胸腔,排山倒海般碾过陈暮全身!
他蜷缩起身体,滚烫的额头重重抵在冰冷粗糙的墙皮上,左手成拳塞进嘴里,
牙齿深深陷入指节皮肉,压制住喉间即将冲出的嘶吼。墙壁的冰冷穿透肌肤,渗入骨头,
是此刻唯一能对抗那灭顶窒息感的慰藉。轰——咔!惊雷炸裂,撕裂了窗外浓稠的夜色。
冰冷的雨点噼啪抽打着肮脏的玻璃窗。那一夜的记忆如同蛰伏的猛兽,
精准地咬中了三年前那道撕裂灵魂的伤口,将陈暮猛地拖回那个泥泞的终点。
消毒水刺鼻的气味霸道地占据着每一寸空气。他躺在冰冷的、似乎某种金属构筑的平台上,
浑身湿透,单薄的衣物紧紧贴在皮肤上,带来致命的寒意。
每一次呼吸都像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在撕扯一口破风箱,心脏沉重得如同一块浸满冰水的铅块,
每一次搏动都虚弱得几乎无法将血液送进缺氧的大脑。视野边缘全是惨白的雪花,
耳边是永不停歇的沉重嗡鸣,如同巨锤不断砸击着头骨。
意识在黑暗冰冷的深潭上方无望地悬浮,随时准备坠落,而深潭的边缘,
陈枭那张年轻、英俊却染着疯狂的脸在阴影中晃动。“哥?别睡!看着我!
”陈枭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焦灼的迫切,冰凉的指头用力拍打着陈暮麻木的脸颊。
身体的感知早已瘫痪,只剩下纯粹的寒冷和麻木在骨髓深处蔓延,
以及肺部那不受控制的、撕裂般的痉挛在拉扯全身。身体不再属于自己,
只是一个承载着绝望的容器。在视野模糊摇荡的边缘,陈枭猛地俯下身,逼近陈暮的胸口。
那张英俊的面孔在陈暮放大的瞳孔里扭曲、变形,
眼瞳深处燃烧着一团怪异的、混杂着兴奋与贪婪的幽火,
如同狂赌徒在轮盘最终定格的刹那看到的疯狂光芒。
陈枭粗暴地撕开了陈暮黏腻在胸口的湿衣!“哧啦——”布帛裂帛声刺耳欲聋。
陈暮**在冰冷空气中的胸膛暴露无遗。
陈枭冰凉的、带着雨水和黏腻汗液的手掌紧紧贴了上来。他的呼吸骤然变得粗重灼热,
如同热烘炉的风箱,喷在陈暮冰冷的皮肤上。
一只沉重、精密、泛着冰冷金属光泽的圆环从陈枭的贴身口袋中掏出。
环体边缘薄如蝉翼却锋芒暗藏,
内缘蚀刻着极其繁复、绝不属于任何人类文明的深紫色几何纹路,
如同某种古老的、黑暗的契约印记。环的核心嵌着一块卵形半透明灰蓝色物质,
像凝固的异星海洋。其内部,
无数道极其细微、驳杂混乱的光束疯狂地旋转、扭曲、碰撞、湮灭,又重生出一个新的漩涡,
如同一个濒临崩溃、在熵增与重组边缘挣扎的微型星尘宇宙。
陈暮的喉咙深处发出破风箱般的“嗬嗬”气音,整个身体却在无法抵抗的力量下彻底僵死,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冰冷的环体底部,
悄然无声地探出了数根细如黑发、闪烁着无机质寒光的尖锐金属触须!
它们带着令人头皮发麻的细微摩擦声,如同活物般游弋而出,精准地刺向他胸骨下方,
心脏搏动最激烈的区域——嗤!轻微的、带着皮肉和隔膜撕裂感的穿刺声,
清晰地传入陈暮被嗡嗡声灌满的耳膜。极致的痛苦并非来自皮肉的穿透,
而是来自灵魂深处被硬生生剜走一片的虚无感!仿佛维系着他整个存在的基石被猛然抽走!
一股庞大冰冷的“空”瞬间攥紧了他的心脏!
紧接着便是血肉被连根拔起、从生命本源上粗暴剥离的恐怖幻觉!
冰冷的环箍紧紧贴合在心口皮肉上。其内部那混乱、疯狂的光束漩涡猛然膨胀,
爆发出灼目的、仿佛要吞噬一切的惨白光芒!强光几乎要熔穿陈暮涣散的瞳孔!
光芒如同饥饿的深渊巨口,瞬间笼罩陈暮全身。
他感觉自己构成“存在”的无数根丝线被这光残忍地咬住、绷紧、然后一根根地绷断!
一种比死亡本身还要冰冷彻底的“失锚感”席卷全身。他像一个被瞬间掏空的布袋,
轻飘飘地悬浮在毁灭的边缘。视野被强光吞噬。在最后彻底失去意识前的迷离中,
自信的封面照片、项目路演会议上挥斥方遒的身影——被粗暴地、不可逆转地从他身上剥离!
像被无形的导管疯狂抽走生命和未来的洪流!
法想象的庞大“本源”被强行注入了陈枭此刻按在自己心口的另一枚几乎相同的冰冷环箍中!
那枚环箍的核心骤然爆发出更加刺目、贪婪、仿佛宇宙初开般混沌的深蓝色光潮!
陈枭猛地挺直了身体,如同沐浴在神恩之中。他张开双臂,
喉咙深处爆发出一种非人的、充满极致狂喜和毁灭性满足的嘶吼!
那声音如同从地狱深渊挣脱的古老魔神发出的咆哮!
外狰狞的闪电惨白光芒瞬间将他脸上的表情刻画得如同嗜血魔鬼——双目圆睁几乎撕裂眼角,
嘴角向耳根后咧开,整个面孔因纯粹的贪婪满足而扭曲变形!
而平台上那个被彻底抽空的躯壳,只是极其微弱地、如同垂死鱼类的尾巴般弹动了一下,
便彻底瘫软下去。心口的搏动微乎其微,如同风中残烛。冰环悄无声息地脱落,
在陈暮心口留下一个硬币大小的灰白色印记,犹如一块死去的胎记。
陈暮的身体在冰冷的床上剧烈抽搐,如同离水的鱼,弓起后背又重重砸落。
剧烈的咳嗽撕扯着他的喉咙和胸腔,冰冷的汗水浸透了后背单薄的衣衫,
心脏在破碎的胸腔中疯狂擂动,几乎要撞开肋骨的牢笼。雨夜的冰冷穿透时光,
再次将他死死按在绝望的砧板上。他挣扎着从床底一个隐藏的凹槽里抠摸出几张纸。
最上面是一张复印件的复印件,纸张边缘磨损毛糙得如同枯叶。
……预期生存期不超过三个月……猝死风险极高……建议……”下面几张是手写的潦草收据,
落款一个模糊的“张”字,散发着廉价钢笔水和破旧纸张的味道。陈暮支撑着站起,
挪到房间最里面那面覆盖着大片污浊水渍的墙角。手指在那片异常松软的地方抠弄着,
一块墙皮应声剥落,露出里面嵌入的一个廉价塑料药盒。小心撬开盒盖,
里面静卧着一枚边缘带着精密紫色蚀刻纹路的金属圆环。
环心不再是三年前那种吞噬一切的混沌深蓝,
而是一片毫无生气的、冰冷的、均匀的死灰色尘埃。他将圆环翻转过来,
将环体内部底部极其细微的几个针孔状结构,凑到眼前死死盯着。
他拿来桌上那个布满划痕的浑浊放大镜,凑近那一片死灰的核心内侧边缘。
一丝微弱到几乎无法辨认、如同风中残烛的幽蓝色光点,正极其缓慢地、极其迟缓地,
在灰烬的海洋中挪动着,每一次微乎其微的移动都耗费着无法想象的时间。
它正以一种肉眼可见却又无比煎熬的速度,靠近那个标志着彻底灰败的终点刻度线。
三年零三个月零十七天。陈暮猛地吸了一口气,污浊的空气灌入胸腔,带来一阵刺痛。
他转身走到那张瘸腿木桌前,拉开了吱呀作响的抽屉。在几件同样破旧的衣物下面,
压着一个用厚厚胶带缠裹的牛皮纸信封。取出里面为数不多但被压得极其平整的纸币。
他又从一个皱巴巴的烟盒里,倒出所有零碎的硬币和几张更小面值的脏污纸票,
金属的轻响在寂静中格外刺耳。城郊结合部一家名为“杏林”的二十四小时药店,
灯牌老旧昏暗。玻璃柜台后一个胡子拉碴的药剂师正趴在桌上打盹,
空气里弥漫着过期的藿香正气水和西药片的混合气味。“一盒**针剂。
”陈暮的嗓音干裂得像沙漠里的砾石。药剂师眼皮都没抬,
不耐烦地从柜台深处摸出一个塑料小药盒丢过来:“三十五。
”陈暮沉默地放下皱巴巴的纸币和叮当作响的硬币。拿起药盒转身时,
药剂师似乎刚被那硬币声吵醒,眯缝着眼瞥向他过分瘦削的背影,
用带着浓重睡意的沙哑嗓音含混道:“小伙子,悠着点……脸白得跟纸糊的似的,
别光顾着快活,把自个儿命根子掏空了!”寒风猛地扑在脸上,带着刺骨的恶意。
陈暮死死捏住那盒轻得几乎没有分量的救命毒药。心口的位置,那已经沉寂多年的地方,
又开始了熟悉的、如细针穿刺般的细微刺痛。那痛感微弱却固执地蔓延,
如同已经深深扎根在这具身体的记忆角落,
冰冷地提醒着他这具身体也曾是被判了极刑的残骸。他下意识地用空着的左手,
更用力地按紧了心脏上方的位置,在那灰白的疤痕周围反复摩挲着,加快了脚步,
几乎跑了起来,融进街道尽头更浓重的夜色里。仿佛那些记忆里的针,在身后紧紧追赶。
帝豪顶层,“天池”无边际泳池包厢。脚下是整个城市匍匐的灯火星河,
喧嚣被极度的隔音玻璃隔绝在外,室内只剩下悠扬的背景爵士乐。
陈枭陷在主位那张宽大柔软的白色躺椅里,昂贵的真皮散发着冰冷的质感。
几个或秃顶或大腹便便的男人围在旁边,涎着脸不停劝酒。
一个身材**的女模刚给陈枭点燃手中的古巴雪茄,
空气中弥漫着醇厚的烟草香、顶级白酒的辛辣以及女性香水的甜腻,粘稠得令人作呕。
“陈总!再敬您!这一杯,代表兄弟们的感激!
”红光满面的矮胖子几乎要把整个肥硕的上身压在水晶桌面上,手中的酒杯举得老高,
酒液晃荡着溅出几滴,“要不是您牵头拿下那块地,
我们……”陈枭嘴角挂着无可无不可的浅弧,指尖夹着雪茄,微微抬了抬下巴,算是回应。
胖子立刻如蒙大赦般,“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喉结滚动发出响亮的吞咽声,
然后满足地喟叹一声。“小意思。”陈枭的目光飘向窗外那片由金钱堆砌的光之海洋,
手指无意识地碾着雪茄灰。就在胖子放下空杯直起身的瞬间,
一声极轻的、仿佛瓷器破裂般的脆响钻进陈枭的耳膜。嗤啦——他捏着雪茄的右手食指指尖,
突然如同烧焦的蜡般裂开一道细小的口子!殷红的血珠迅速渗出,染红了浅色的雪茄烟灰!
一股突如其来的、仿佛心脏被一只冰冷的铁手猛地攥紧再狠命一扯的剧痛,
毫无预兆地在他胸腔深处爆炸!眼前猛地一黑!雪茄从指间滑落,
未燃尽的烟灰簌簌洒落在价值不菲的手工地毯上。
杯中暗红色的昂贵酒液如同被无形之手掀动,泼洒出来,弄脏了他深色的袖口。
周围的人毫无察觉,胖子还在唾沫横飞地吹捧。桌面之下,陈枭的左手猛地攥成了铁拳,
骨节因极度用力而发出轻微的“咔”声!那拳头死死抵在自己左侧胸膛心脏的位置,
隔着昂贵的西装和丝质衬衫,
试图将那里面那颗骤然发狂、下一刻又骤然沉重得如同死铁、疯狂下坠的冰冷心脏死死按住!
那块坚硬的、已经与他血肉长成一体的冰冷环形硬物紧贴着剧烈震动的胸骨!
一股强烈的窒息感让他不得不猛地吸进一大口带着甜腻香水和酒精的空气,
那空气冲入喉咙竟带出一种灼烧的刺痛!
短暂的麻痹感和失控的失重感如同冰冷的电流瞬间击穿了四肢百骸,
让他险些控制不住地从躺椅上向前栽倒!“……陈总?
”旁边一个戴着金丝眼镜、一直小心观察着陈枭脸色的男人试探性地开口,
《命运黑手:夺生倒计时最后三日》是一部令人沉浸其中的优秀作品。作者佚名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精巧的结构,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神奇而真实的世界。主角陈枭陈暮的形象栩栩如生,她的聪明和冷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整个故事充满了悬念和惊喜,读者会随着情节的发展而紧张、感动、欢笑。这本书的文笔流畅,情节紧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命运黑手:夺生倒计时最后三日》中的陈枭陈暮具有鲜明的个性,让人难以忘记。剧情中的其他角色也各有特色,使人记忆犹新。
《命运黑手:夺生倒计时最后三日》这本书充满了戏剧性和张力。主角陈枭陈暮的形象鲜明,她的聪明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为故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作者佚名的文笔流畅而细腻,每一个情节都能牵动读者的心弦。小说的结构精巧,前后呼应,扣人心弦。配角们也各自有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们的存在丰富了整个故事的内涵和情感。这是一篇文笔出众、情节引人入胜的佳作,值得推荐给每一个喜欢[标签:小说类型]小说的读者。
对于我来说,《命运黑手:夺生倒计时最后三日》是一部真正值得推荐的佳作。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感人至深,男女主角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感谢佚名的才情,写出了这么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