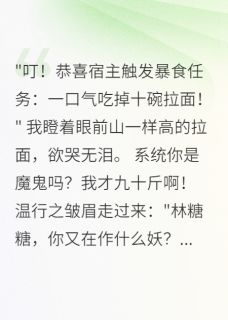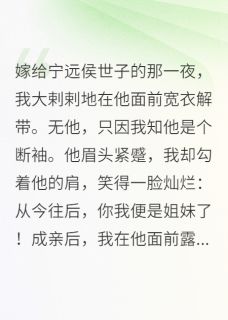1血癌晚期的绝望>傅司寒的白月光回国那天,我确诊了血癌晚期。
>他搂着白月光在沙发缠绵:“别装病,滚去客房。”>我默默吞下止痛药,
看着白月光撕碎我的救命处方单。>后来我死在手术台上,傅司寒却疯了。
>他翻遍全城找到我的骨灰盒,嘶吼着说爱我。>直到那天,
他亲眼看着我的骨灰被冲进下水道。>“傅先生,苏**遗嘱交代——”>“您碰过的东西,
她嫌脏。”---浓稠的黑暗压得人喘不过气。窗外最后一点天光被厚重的丝绒窗帘吞噬,
客厅里只余下沙发边一盏落地灯,投下一圈昏黄暧昧的光晕。空气里浮动着昂贵红酒的醇香,
还有……一丝若有似无的、属于另一个女人的香水味。**在冰冷的玄关墙壁上,
指尖死死抠进掌心,试图压住胸腔里那股翻江倒海的恶心和锐痛。诊断书就揣在外套口袋里,
薄薄几张纸,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五脏六腑都在抽搐。——急性髓系白血病。晚期。
医生说,还有三个月。前提是,立刻住院,接受最积极的治疗,
用上那些能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的进口药。可那些药,贵得令人绝望。
视线无法控制地投向客厅中央那片暖色的光晕里。傅司寒陷在宽大的沙发深处,
昂贵的丝质衬衫领口松垮地敞开着,露出一段线条流畅的锁骨。他怀里依偎着林薇薇,
他心尖上失而复得的白月光。林薇薇穿着一身丝质吊带睡裙,
柔软的身体像没有骨头似的贴着他,纤细的手指正捏着一颗饱满的紫葡萄,
巧笑倩兮地送到傅司寒唇边。他微微低头,就着她的手含住那颗葡萄,
深邃的眼眸里漾着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宠溺的温柔。那温柔像淬了毒的针,
狠狠扎进我的眼底。“寒哥哥,这葡萄好甜,你尝尝嘛。”林薇薇的声音又软又媚,
带着刻意的撒娇。傅司寒低低地“嗯”了一声,薄唇擦过她的指尖。林薇薇咯咯地笑起来,
像只得意的小猫,眼神却越过傅司寒的肩膀,精准地落在我身上,
带着毫不掩饰的挑衅和胜利者的怜悯。胃里一阵剧烈的痉挛,喉头涌上熟悉的腥甜铁锈味。
我猛地捂住嘴,压抑的咳嗽声还是不受控制地从指缝里溢了出来,沉闷又破碎。
沙发那边的旖旎气氛骤然一滞。傅司寒抬起头,望过来。
客厅昏暗的光线模糊了他大半张脸的轮廓,只有那双眼睛,锐利得像结了冰的寒星,
穿透昏暗的距离,直直钉在我身上。那里面没有半分担忧,只有被打扰的不悦,浓得化不开。
“苏念?”他的声音低沉,听不出情绪,却像裹着冰渣,“杵在那里做什么?
”一阵尖锐的眩晕袭来,我眼前发黑,不得不伸手扶住冰冷的墙壁才勉强站稳。
口袋里那张轻飘飘的诊断书此刻重逾千斤,压得我几乎窒息。我需要钱,需要救命。
这个念头疯狂地撕扯着我的神经。“……司寒。”我开口,声音嘶哑得厉害,像破旧的风箱,
“我……我有事想跟你说。”每一个字都耗费着巨大的力气。林薇薇像是受惊的小鸟,
立刻往傅司寒怀里缩了缩,手臂紧紧环住他的腰,脸颊贴在他胸膛上,
怯生生地说:“寒哥哥,苏念姐看起来好凶哦……她是不是不喜欢我回来?
”那楚楚可怜的模样,和她眼底一闪而过的得意形成刺眼的对比。
傅司寒安抚性地拍了拍她的背,目光重新落回我脸上时,那份不悦已经彻底沉了下去,
只剩下冰冷的审视和不耐烦:“有事?
”胸腔里的剧痛和那股不断上涌的腥甜几乎要冲破喉咙。我深吸一口气,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用尽全身力气才把话说完整:“很重要……关于我的身体……”“身体?
”傅司寒的眉头不耐地蹙起,嘴角甚至勾起一抹极淡的、带着讽刺的弧度,“苏念,
同样的把戏玩一次就够了。”他搂紧了怀里的林薇薇,语气是毫不掩饰的厌烦,
“收起你那套装病的把戏,别在这里碍眼。今晚薇薇睡主卧,你,滚去客房。”装病?
这两个字像淬了剧毒的匕首,精准无比地捅进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脏,然后狠狠一绞。
喉咙里的腥甜再也压制不住,我猛地弯下腰,剧烈地咳嗽起来,
温热的液体顺着指缝滴落在地板上昂贵的手工地毯上,洇开一小片刺目的暗红。我摊开手,
掌心一片粘稠的猩红。血。我的血。林薇薇夸张地倒吸一口冷气,捂住嘴:“天啊!寒哥哥,
苏念姐她……她吐血了!”那声音里,与其说是惊恐,不如说是某种按捺不住的兴奋。
傅司寒的身体似乎僵了一下,眼神落在我掌心的血迹上,有一瞬间的凝滞。
但也仅仅是一瞬间。随即,那点微澜便被更深的冷漠覆盖。他烦躁地捏了捏眉心,
仿佛我弄脏了他的地毯是件多么不可饶恕的事情。“够了!”他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一种被冒犯的愠怒,“苏念!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非要把这地方弄得乌烟瘴气你才满意?薇薇身体弱,受不得惊吓,你别在这儿发疯!
”身体弱?受不得惊吓?我看着林薇薇那张红润健康、写满看好戏的脸,
再看看自己掌心的血和镜子里苍白如鬼的自己,一股荒谬绝伦的悲凉瞬间淹没了所有痛楚。
原来在他傅司寒的剧本里,我这个咳出血的人,
才是那个无理取闹、惊吓了他“娇弱”白月光的疯子。心口那片空茫的剧痛,突然就麻木了。
我慢慢直起身,不再看他,也不再看那个依偎在他怀里的女人。所有的力气,
都用来对抗身体里那台疯狂运转的绞肉机。我拖着灌了铅的双腿,一步一步,
艰难地挪向通往客房的走廊。身后,传来林薇薇刻意放柔却又清晰无比的声音:“寒哥哥,
别生气嘛……苏念姐可能……真的不舒服呢?”尾音拖得长长的,带着虚伪的关切。
“不舒服?”傅司寒的冷笑像冰锥,狠狠扎进我的脊梁骨,“她最擅长的不就是这个?
装模作样。”紧接着,是衣料摩擦的窸窣声,还有林薇薇一声娇软的惊呼,
伴随着傅司寒压低的、带着某种暧昧暗示的嗓音:“乖,别管她,
扫兴……”后面的话语模糊了,被关上的厚重房门隔绝在外。2骨灰盒的秘密冰冷的客房,
像个巨大的冰窖。月光惨白地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隙里漏进来,
在地板上投下一道冷清的、窄窄的光带。我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滑坐在地,
浑身的骨头都在叫嚣着散架般的疼痛。手抖得厉害,几乎握不住那个小小的白色药瓶。
瓶身上冰冷的标签硌着掌心——那是维持我残喘生命的止痛药,
也是我口袋里那张天价处方单上,最便宜的一种。我哆嗦着倒出两粒,没有水,
就那么干涩地、用力地咽了下去。药片刮过火烧火燎的喉咙,带起一阵更剧烈的咳嗽,
喉咙里全是血腥味。我闭上眼,绝望像冰冷的潮水,从脚底一寸寸漫上来,淹过头顶。
钱……没有钱,那些救命的药,那些能让我多活一天、多痛苦一天的治疗,都是镜花水月。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艰难地摸出来,屏幕幽蓝的光照亮了我毫无血色的脸。
是一条短信,来自那个始终对我抱有善意的老管家陈伯。「苏**,
傅先生让我交给您的体检报告,我放在您书房办公桌最上面那个抽屉里了。
他说……让您自己看看。」体检报告?心脏猛地一缩。几个月前,傅司寒确实突然心血来潮,
让家庭医生给我安排了一次全面体检。难道……那个时候他就……不,不可能。
我立刻否定了这个荒谬的念头。他怎么会关心我的死活?大概只是傅家例行公事般的程序。
但那个抽屉……鬼使神差地,我撑着墙壁,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拖着沉重的脚步挪向这间临时客房角落那张小小的书桌。拉开最上面的抽屉。没有体检报告。
只有几张散乱的设计稿,和……一个孤零零的、熟悉的白色药瓶。和我刚才吞下的一模一样。
瓶底压着一张折起来的纸。我颤抖着拿起那张纸,展开。
上面是傅司寒助理那公事公办、毫无温度的打印字迹:「苏**:傅总吩咐,
这是最后一次为您提供此类药物。请勿再以此为由打扰傅总及林**。助理:李铭」日期,
是一周前。原来,连这点可怜的止痛药,他都早已不耐烦施舍了。
一股冰冷的绝望瞬间攫住了心脏,比血癌的侵蚀更甚。**着书桌,身体控制不住地往下滑,
跌坐在地板上。月光冷冷地照着我,像一个无声的嘲笑。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几分钟,
也许一个小时,外面客厅里那令人作呕的暧昧声响似乎终于消停了。死寂的深夜里,
只有我压抑的、破碎的呼吸声。突然,轻微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了客房门外。接着,
门把手被轻轻拧动。我猛地抬起头,心脏在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是傅司寒?
他……他改变主意了?还是……终于有那么一丝丝……门被推开一条缝。站在门口的,
是林薇薇。她显然刚沐浴过,身上只裹着一件傅司寒宽大的白色丝质浴袍,
湿漉漉的头发披散着,水珠顺着纤细的脖颈滑入微敞的领口。浴袍下摆下,
两条光洁的小腿在昏暗的光线下白得晃眼。她脸上带着一种餍足的、慵懒的红晕,
眼神却清醒锐利得像淬了毒的针。她倚着门框,居高临下地看着跌坐在地、狼狈不堪的我,
红唇勾起一个胜利者般甜美又恶毒的笑容。“哟,还没睡呢?”她的声音轻飘飘的,
带着刻意的关心,“地上多凉啊,苏念姐,你身体本来就‘不好’,可别再‘病上加病’了。
”她把“不好”和“病”字咬得格外重。我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林薇薇似乎毫不在意我的沉默,她慢悠悠地踱步进来,像巡视自己领地的女王。
目光扫过书桌上那个空了的药瓶和我手里捏着的那张冰冷的“最后通牒”,
她眼底的得意几乎要溢出来。“啧啧,真可怜。”她在我面前蹲下,
昂贵的浴袍下摆拖曳在地毯上。她伸出手指,那涂着精致蔻丹的指尖,
带着沐浴后微凉的湿意,轻佻地想要抬起我的下巴。我厌恶地偏开头。林薇薇的手落了空,
也不恼,反而咯咯地笑起来,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脾气还挺倔。”她收回手,
抱着膝盖,歪着头看我,像在欣赏一件有趣的失败品,“苏念,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真觉得你挺可悲的。守着个心里根本没你的男人,演着自以为深情的独角戏,
累不累啊?”她凑近我,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亲昵,
吐出的字眼却字字如刀:“寒哥哥刚才还说呢……说你就像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
看着就让人倒胃口。他搂着我的时候,连你的名字提都不想提,嫌晦气。”每一个字,
都精准地凌迟着我早已破碎不堪的心脏。我死死咬着下唇,口腔里弥漫开更浓重的血腥味,
才勉强抑制住喉咙里翻涌的悲鸣。“哦,对了。”林薇薇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随即又转为一种虚假的担忧,“听说你身体不舒服,需要钱治病?
”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眨了眨,里面闪烁着猫捉老鼠般的残忍兴味,“寒哥哥的钱,
以后可都是要用来养我和我们的孩子的。一分一厘,都跟你苏念没关系了。”她站起身,
浴袍带起一阵香风。她走到书桌前,
目光再次落在那张被我揉皱的处方单上——那是今天下午医生开给我的,
上面列着几种关键的、价格不菲的靶向药名称。是我活下去的一线微光。
林薇薇伸出两根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像捻起什么肮脏的垃圾一样,拈起了那张薄薄的纸。
“这种垃圾……”她红唇轻启,声音甜得发腻,眼神却冷得像毒蛇,
“就别留着碍寒哥哥的眼了吧?”在我骤然收缩的瞳孔注视下,她脸上带着极致恶意的笑容,
双手捏住那张承载着我最后希望的处方单。“嘶啦——”纸张被无情地撕裂的声音,
在死寂的房间里尖锐地响起。一下,又一下。她慢条斯理地,带着一种近乎享受的残忍,
将那张纸撕成了无数细小的碎片。白色的纸屑,像一场冰冷的、绝望的雪,
纷纷扬扬地从她指间洒落,飘散在我冰冷的地板上,也飘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看,
”她拍了拍手,仿佛掸掉什么灰尘,笑容灿烂得刺眼,“干净了。
”她欣赏着我瞬间褪尽最后一丝血色的脸,欣赏着我眼中那最后一点光亮彻底熄灭的绝望。
然后,她像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演出,优雅地转身,赤着脚,无声无息地走向门口。
手搭上门把手的瞬间,她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回头,
对着瘫坐在地、如同被抽走了所有魂魄的我,投来轻飘飘的、最后一瞥。“哦,忘了说,
”她笑得天真无邪,吐出的字眼却淬着剧毒,“寒哥哥让我告诉你——”“要死死远点。
别脏了他的地方。”门,在她身后轻轻合拢。“咔哒”一声轻响。像是什么东西,
在我身体里彻底断裂了。3最后的告别世界骤然失声。眼前所有的景象都扭曲、旋转,
最终坍缩成一片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黑暗。耳朵里嗡嗡作响,盖过了窗外微弱的风声,
盖过了自己胸腔里那颗心脏疯狂又徒劳的跳动。林薇薇那张带着恶毒笑容的脸,
傅司寒冰冷嫌恶的眼神,
还有那漫天飘落的、代表着死亡判决的白色纸屑……无数画面在脑海里疯狂闪现、炸裂,
最终都归于一片死寂的灰白。身体里那股日夜不休的剧痛,在这一刻,奇异地消失了。
不是缓解,是彻底的、冰冷的麻木。仿佛灵魂已经从这具千疮百孔的躯壳里抽离,
悬浮在半空,冷漠地俯视着地板上那团蜷缩的、了无生气的影子。“要死死远点。
别脏了他的地方。”这句话,像淬了冰的魔咒,一遍又一遍地在空茫的脑海里回荡。原来,
我连死在他屋檐下的资格都没有。原来,我耗尽五年时光、燃尽所有爱意去捂的那块石头,
最终给我的回报,是连一块葬身的方寸之地都吝于施舍。手指无意识地动了动,
触碰到地板上冰冷的纸屑碎片。那曾是我活下去的凭据。现在,只是一堆垃圾。也好。
黑暗温柔地包裹上来,带着一种解脱般的诱惑。意识像断线的风筝,
不受控制地向着深渊飘去。最后一点残存的力气,只够支撑我微微侧过头,看向窗外。
惨淡的月光,被厚重的云层彻底吞噬。无边无际的黑暗,终于降临了。不知过了多久,
也许是一瞬,也许是永恒。一阵急促尖锐的、仿佛要刺破耳膜的**,
硬生生将我从那片虚无的黑暗边缘拽了回来。是手机在震动。身体沉重得像灌了铅,
每一次细微的动作都牵扯着濒临崩溃的神经。我艰难地挪动着手臂,指尖摸索着,
终于触碰到那个冰冷坚硬的物体。屏幕在黑暗中亮起,刺得我眼睛生疼。
来电显示跳动着两个字——陈伯。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
迟来的钝痛感蔓延开。我几乎是凭着本能,用尽最后一丝残存的力气,划开了接听键。
“喂……”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气若游丝。“苏**!苏**!您怎么样?您在哪里?
”电话那头,陈伯的声音焦急万分,带着明显的喘息,背景音嘈杂混乱,
隐约还有汽车喇叭声,“先生……先生他刚走!林**突然说心口疼,
先生抱着她急急忙忙去医院了!我……我偷偷溜出来了!您是不是不舒服?您说话啊苏**!
”陈伯……这个在傅家唯一对我释放过善意的老人。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猛地冲上鼻腔,
眼眶瞬间滚烫。我张了张嘴,想告诉他我没事,想让他别担心,
想让他快回去……可喉咙里堵着厚重的棉絮,一个字也发不出,
只有压抑不住的、破碎的喘息声透过听筒传过去。“苏**!您别吓我!
您是不是……是不是……”陈伯的声音带着哭腔,“您等着!您一定要撑住!
我这就叫救护车!您告诉我您在哪儿?在别墅吗?”在哪儿?我的意识又开始模糊,
视线涣散。天花板在旋转,吊灯变成了重影。只有陈伯那焦急的呼喊,像一根细细的线,
勉强维系着我即将消散的意识。“……客……房……”我用尽全身力气,
从齿缝里挤出两个字,声音轻得像叹息。“客房?好!好!您撑住!千万别睡!
救护车马上到!苏**!您听见了吗?一定要撑住啊!”陈伯的声音带着绝望的祈求。
电话那头传来他大声呼喊地址、催促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远,
越来越模糊……手机从无力的手中滑落,砸在冰冷的地板上,发出一声闷响。
屏幕的光闪了几下,彻底暗了下去。世界重新陷入黑暗和死寂。这一次,连那根细线也断了。
身体的温度在飞速流逝,四肢百骸都浸泡在刺骨的冰水里。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无比艰难,
每一次吸气都像吸进滚烫的刀子,每一次呼气都带着生命流逝的冰冷。意识沉沉浮浮,
像暴风雨中即将倾覆的小舟。彻底沉入黑暗之前,脑海中闪过的最后一个画面,
不是傅司寒冰冷的脸,也不是林薇薇恶毒的笑。是很多年前,
傅家老宅那棵开得如火如荼的石榴树下。穿着洗得发白校服的少女,
被几个趾高气扬的富家子弟推搡着,弄脏了她熬夜打工才买到的、准备送给奶奶的生日蛋糕。
她蹲在地上,看着一塌糊涂的奶油和水果,死死咬着唇,倔强地不让眼泪掉下来。然后,
一个穿着昂贵球鞋的男生停在了她面前。阳光透过浓密的石榴树叶,
在他身上投下跳跃的光斑。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皱着眉,
带着少年人特有的不耐烦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别扭,
把他手里那个包装精美、一看就价值不菲的蛋糕盒子,塞进了她怀里。“哭什么哭,吵死了。
这个给你。”少年清冽的声音,带着不容拒绝的霸道,却像一道光,
劈开了她当时灰暗的世界。那个别扭又傲慢的少年,是十六岁的傅司寒。
那个沾着泪痕、捧着蛋糕茫然无措的少女,是十六岁的苏念。原来……那么早,那么早以前,
光就曾短暂地眷顾过她。可惜,光终究是光,不会为尘埃停留。也好。这样……也好。
黑暗温柔地覆盖上来,像一张巨大的、柔软的网。
所有的痛苦、屈辱、不甘、爱恋……都在这片无边的寂静中,渐渐消融、远去。
意识彻底沉入虚无的最后一刻,恍惚间,似乎听到了遥远的地方,
传来尖锐急促的、象征着某种救援的鸣笛声。那声音穿透层层黑暗,忽远忽近。
但……已经太迟了。黑暗温柔地吞噬了一切,连那微弱的鸣笛也彻底沉寂下去。
无边无际的寂静。冰冷的手术灯光,白得刺眼,悬在头顶,像一个冷漠无情的审判者。
我漂浮在一片混沌里,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只有一种奇异的、剥离般的轻松。下方,
似乎很遥远的地方,穿着绿色手术服的人影在晃动,
、心电监护仪发出的、代表生命流逝的尖锐长鸣……所有的声音都像是隔着一层厚重的水幕,
作者喜欢龙笛的明元帝的《我把命赔给你,够不够?》展现了他老辣的文笔和成熟的故事构思,让人欲罢不能。这是一本值得书虫们强烈推荐的好书!
《我把命赔给你,够不够?》结构精巧,环环相扣。配角的形象栩栩如生,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身份和情感共鸣。作者喜欢龙笛的明元帝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巧妙的安排,展现了多样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转折,使整个故事生动有趣。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
总之,我对《我把命赔给你,够不够?》这本书的点评可以用以下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有趣、真挚动人、精巧结构、环环相扣、新奇设定、细腻文笔、美好感受。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佳作,值得广大读者品味和推崇。
《我把命赔给你,够不够?》是一本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故事情节紧凑扣人心弦。作者巧妙地塑造了[主角]的性格,让人念念不忘。整个故事令人意犹未尽,时而感动,时而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