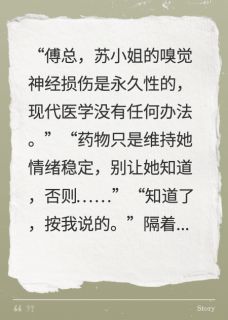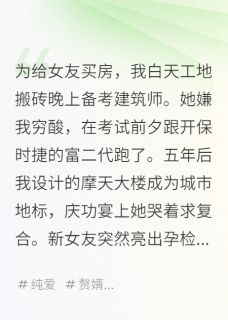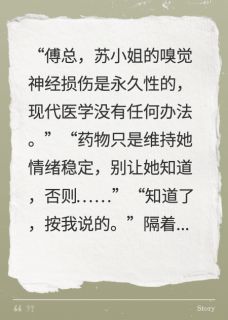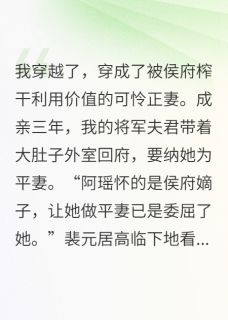民国二十一年冬,雪下得极大。赵家的汽车碾过北平积满雪的青石路,车轮压出两道深痕。
我裹着狐裘斗篷,怀里抱着鎏金暖炉,指尖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炉壁。车窗外,
灰蒙蒙的天压得极低,街上行人寥寥,偶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蜷在墙角,冻得瑟瑟发抖。
"**,前面路堵了。"司机老陈突然开口。我蹙眉,掀开车帘一角。
寒风裹着雪粒子灌进来,刺得脸颊生疼。只见车前横着个人影——是个少年,约莫十七八岁,
瘦得惊人,身上的单衣破得遮不住风,**的手腕冻得青紫。可他站得笔直,
像一柄插在雪地里的刀。"求**赏口薄棺,安葬家父。"他的声音沙哑,却字字清晰,
不卑不亢。街上零星的行人驻足观望,窃窃私语飘进车窗——"这不是赵家三**的车吗?
""这乞丐胆子忒大,赵家的车也敢拦......"我眯起眼打量他。
少年眉骨上一道新伤还渗着血,眼睛却黑沉沉的,像是两口深井,望不见底。
那里面没有乞怜,只有孤注一掷的决绝。"老陈。"我唤了声,老陈会意立刻递来钱袋。
我拈出几块大洋,从车窗递出去:"拿去。"他怔了怔,似乎没想到这般顺利。
冻裂的手指接过银元时,我看到他掌心厚厚的老茧。他后退半步,忽然撩起衣摆跪下,
在雪地里结结实实磕了个头。"谢**大恩。"雪落在他瘦削的肩头,很快积了薄薄一层。
我忽然觉得这场景莫名刺眼:"你叫什么?""赢安。"他顿了顿,"没有姓。
"我望着他挺直的脊梁,忽然想起父亲书房里那柄未开刃的唐刀。鬼使神差地,
我脱口而出:"以后跟着赵家姓罢。"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堂堂赵三**,
当街捡个乞丐算怎么回事?正懊恼着,却见他摇头:"赢安只报恩,不改姓。
"我挑眉气笑了。好个硬骨头!暖炉往座位上一搁,我推开车门下车。
老陈急得直喊"**仔细着凉",我充耳不闻,绣着缠枝梅的鹿皮靴踩在雪地上咯吱作响。
"抬头。"我垂着眼眸扫过他的脸。他仰起脸,雪花落在他的睫毛上。
我这才发现他生得极好——眉如刀裁,鼻梁高挺,只是眼神太过沉寂,像口古井。
"知道我是谁吗?"我问。"赵家三**。"他竟答得准确,"上月您在教堂发冬衣,
我见过。"我一时语塞。那日我确实去了慈善会,
还因为嫌弃嬷嬷准备的棉衣针脚太粗发过脾气。没想到这乞丐......这人竟记得。
雪越下越大,老陈捧着伞追过来。我接过伞柄,突然将伞面倾向他那边:"会写字吗?
""不会。""会算账吗?""会心算。"我挑眉。有意思。我转动伞柄,积雪簌簌落下,
"赵家缺个库房副手。明日辰时来角门找周管家——"故意顿了顿,"迟到片刻,
这差事便给别人。"转身时,我听见他在身后问:"为什么?"雪花落在我烫卷的鬓发上。
我想起刚才他跪在雪地里,背却挺得笔直的模样。"因为......"我回头看了看他,
"你拦车的架势,很像我们赵家人。"汽车驶远时,我从后窗望见他还站在原地。雪幕中,
那身影渐渐变成一个墨点,最后消失在北平的隆冬里。暖炉重新回到手中,
我才发现自己的指尖竟有些发抖。一定是冻的——赵家最骄傲的三**,
怎么会因为个乞丐失态?车转过街角时,我无意识地摩挲着暖炉上"明月照积雪"的刻字。
父亲总说我性子太跳脱,该学学大哥的稳重。可方才那一刻,
我分明觉得自己做了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辰时未至,我便醒了。窗外天色还暗着,
雪已经停了,屋檐下结着长长的冰溜子。我裹着睡袍走到窗前,
正看见角门处有个模糊的人影。
赢安竟来得这样早——灰布棉袄外面套着件半旧的藏青色褂子,想必是周管家临时找给他的。
他站得笔直,像株青松似的戳在雪地里,呼出的白气在空中凝了又散。"傻子。"我嘟囔着,
却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那件褂子分明是大前年府里统一给杂役做的,
穿在他身上竟显得格外挺拔。丫鬟春桃端着铜盆进来时,我正往手腕上抹桂花头油。
"**今日起得真早。"春桃拧着热毛巾笑道,"周管家天没亮就来了,
说您捡回来那个赢安......""什么叫‘捡回来’?"我睨她一眼,
"赵家雇不起账房了?"春桃吐了吐舌头,麻利地帮我梳头。玳瑁梳子划过发丝时,
我望着镜子里自己眼下淡淡的青影,忽然有些说不清的烦躁和紧张。"让他去书房等着。
"我啪地合上梳妆匣,"告诉周叔,按三等管事的例份给。"春桃瞪圆了眼睛。
赵家三等管事月例八块大洋,比铺子里的老师傅还多两块。
我想他那样古板的人应该有件体面的衣裳穿。行至书房时,我故意放重了脚步。
赢安果然站在书架旁,听见声响立即转身行礼。晨光透过雕花窗棂落在他半边脸上,
我才发现他左眉尾有道浅浅的断痕,像是被什么利器划过。"会研磨么?
"我指着案上的松烟墨。他摇头,却径直走到案前,拿起墨锭观察片刻,
然后舀了三勺清水入砚。动作虽生疏,手腕却极稳。我故意找茬:"水多了。
""松烟墨质轻,水少反易滞笔。"他声音很低,像古琴的余韵,"《墨经》第三卷写过。
"我心头一跳。父亲收藏的《墨经》是宋刻本,寻常人别说读,见都未必见过。正要追问,
忽见窗外人影晃动——是二哥拎着鸟笼经过。"低头!"我下意识拽住赢安衣袖。
他猝不及防被我拉得一个踉跄,砚台里的墨汁溅了几滴在他前襟上,像突然绽开的梅。
二哥的脚步声远了,我才惊觉自己还攥着他的袖子。慌忙松手时,指尖蹭到他腕间的茧子,
粗粝的触感让我耳根发烫。"你......"我强作镇定,"你以后见着二少爷要避开。
"赢安看着衣襟上的墨渍,忽然问:"为什么?""因为......"我绞着帕子,
"因为我说了算!"我还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让赢安来了家里,大哥总要过问几句,
二哥虽然护着我也难免唠叨些。他抿了抿唇角。那或许眼里淡漠的冷意消散一些,
又或许只是我的错觉。阳光突然穿过云层,满架线装书上的金漆题签同时亮起来,
晃得人眼花。"识字吗?"我抽出一本《千字文》。"认得三百余字。""写给我看。
"他执笔的姿势很怪,拇指压着笔管,像握刀。宣纸上的字却意外工整,
笔画间透着股凌厉劲儿。写到"赵"字时,笔尖突然顿了顿,洇开个小小的墨团。
"我的姓很难写?"我凑过去。清苦的松烟味忽然萦绕鼻尖。他侧脸在晨光中轮廓分明,
睫毛投下的阴影里藏着我看不懂的情绪。"不难。"他重新蘸墨,
"只是......""只是什么?"笔锋落在纸上,力透纸背。那个"赵"字写得极大,
几乎占满半张宣纸。"只是分量太重。"赢安声音太低,我没听清,
再想问发现窗外传来二哥唤我的声音。我匆匆抓起他写的字塞进袖中,
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赢安正在收拾案上的笔墨,藏青褂子上的墨渍像幅写意山水,
而他站在光影交界处,仿佛随时会融进书架投下的阴影里。午后我去库房查账,
故意绕道经过西厢。赢安正在檐下擦洗一尊青铜爵,听见脚步声立即起身。
阳光照着他挽起的袖口,小臂上蜿蜒的旧伤疤触目惊心。"谁让你干这个的?"我皱眉。
"周管家说......""你现在是赵家的人。"我打断他,
从怀里掏出那页宣纸拍在石桌上,"先学会把这个字写漂亮。"风吹起纸角,
那个力透纸背的"赵"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民国二十六年的春分,赵公馆的海棠开得正好。
我踮脚去够最高处那枝花,却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轻笑。"三**要哪一枝?
"赢安不知何时站在了回廊下。军装笔挺,皮带勒出劲瘦的腰线,肩章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五年前那个在雪地里拦车的少年,如今已是父亲麾下最年轻的参谋。"要你管。"我缩回手,
绢帕却勾在了枝桠上。他三两步走过来,抬手取下帕子。
这个角度刚好能看清他新换的领章——父亲果然提拔他了。"大哥回来了?"我接过帕子,
故意不看他眼睛。"大少爷在书房。"他顿了顿,"我给你带了苏州的杏仁酥。
"我眼睛一亮。赢安每次回家都会带点心,
偏偏上次赶上我被禁足——就因为在女校辩论会上把警察厅长的千金驳得哑口无言。
"大哥还在气头上?"赢安从公文包里摸出个油纸包,四角折得方正,隐隐透着甜香。
我正要接,他却突然收手:"大少爷说,要考校您《孙子兵法》第十三篇。""叛徒!
"我气得跺脚,一定是赢安告状,却见赢安唇角微扬。他最近越来越常笑,
虽然总是这样转瞬即逝的弧度。油纸包被塞进我手里,带着体温。我拆开一看,
杏仁酥缺了一角。"你偷吃?""子弹擦的。"他轻描淡写地指了指自己左臂,
"路过闸北时遇上流弹。"绢帕啪嗒掉在地上。我这才注意到他军装袖口有深色痕迹,
根本不是新换的墨渍,分明是......二哥赵春的汽车恰在此时驶入院落。
他拎着公文包风风火火闯进来,西装革履活像个洋行买办。
几年前二哥放弃北洋的生意转头出了国,说要学医救国,年初才回来。"深深!
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二哥一把揽住我肩膀,"周家那个病秧子少爷居然从德国回来了,
还打听你呢!"赢安突然咳嗽起来。二哥这才注意到他,惊讶地松开我:"赢参谋?
父亲不是派你去保定......""临时军务。"赢安敬了个标准军礼,
眼神却飘向我的手腕——二哥方才抓过的地方。晚饭时气氛凝重。父亲和大哥军装肃穆,
二哥的意大利西装显得格格不入。当父亲说到日军在丰台增兵时,
大哥的筷子在碗沿磕出清脆的响。"商会明天开始募捐。"二哥突然开口,
"我联系了《申报》记者。"父亲眉头舒展些许。赵家三个孩子,大哥是锋利的军刀,
二哥是玲珑的算盘,只有我......"嫣然深深也来帮忙吧。"二哥冲我眨眼,
"周家公子捐了五百套棉服。"瓷勺撞在碗底。赢安站在父亲身后添茶,壶嘴却歪了半分,
茶水在红木桌上洇开一片。父亲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深夜我溜去厨房热杏仁酥,
却撞见赢安在擦枪。月光从气窗漏进来,照得他眉眼如刀刻。"周庭什么样?"他突然问。
我故意把油纸包弄得哗啦响:"病恹恹的,但眼睛很亮。"其实我早忘了那人长相,
只记得他德国带回的巧克力很好吃。赢安组装枪械的手指顿了顿,
咔嗒一声推上保险栓:"**可喜欢?"我咬着杏仁酥,含糊的唔了一声,
以为他问的是杏仁酥。赢安沉默了一会,声音极低:“**该嫁这样的人家。
”我没听清,他说话总是声音低沉。我掰开点心递给他一半。他手上还沾着枪油,
却小心翼翼地用干净的两根手指捏住,像捧着什么易碎的珍宝。远处突然传来空袭警报。
赢安瞬间绷直脊背,枪已上肩。月光下我们四目相对,
他最终只是轻轻说了句:"三**保重。"次日清晨,我在募捐处见到二哥。
他西装口袋插着钢笔和计算尺,正给穿长衫的商会老爷们鞠躬。
转身时我瞥见他后腰鼓起一块——这个书呆子居然别了把勃朗宁。"深深,
"他把我拉到角落,递来一张支票,"帮我换成盘尼西林。"支票落款是周庭。
我心头突然涌起莫名的烦躁,抬头却看见街对面军车旁站着的赢安。
他手里拿着我刚登报的募捐倡议书,朝我微微颔首。阳光穿过梧桐叶,
在他肩章上投下跳动的光斑,像无声的誓言。民国三十年的冬天,连雪都是灰色的。
我站在赵公馆的台阶上,看着勤务兵把大哥的遗物一样样搬进来——染血的怀表,
磨破的作战地图,还有半盒没抽完的老刀牌香烟。父亲坐在太师椅里,
手里攥着大哥的军官证,指节泛白,一夜之间白发丛生。
我想起大哥临走前说答应这次回来带我去吃苏州的枣泥糕。厅堂里那架德国自鸣钟突然敲响,
惊得檐下白灯笼晃了晃,投下惨淡的影子。赢安是半夜回来的。我正跪在祠堂给长明灯添油,
听见军靴踏过青砖的声响。他军装挂满硝烟味,右臂缠着绷带,血迹已经发黑。
我们隔着两盏新供的牌位对视,烛火在他眼里明明灭灭。"赢安,大哥不在了。"我看着他,
突然泪如雨下。赢安回来了,我仿若卸下了所有的逞强。他单膝跪下来,
与我平视:"三**,是我没保护好大少爷。.""二哥呢?
"我知道二哥偷偷和周庭去了南边。大哥出事二哥都没回来,我哭着看赢安,
父亲经受不起更大的打击。"在徐州前线。"赢安喉结动了动,
"带着商会筹的药品......扮成货商走的陇海线。""我劝不了二哥。"我声音轻颤,
"也劝不了你。"赢安突然抓住我手腕,掌心粗粝的茧子磨得生疼。他眼里有血丝,
还有更深的、我读不懂的东西:"三**,你依旧是赵家的三**......"我挣开他,
指着供桌上两盏白灯笼,"现在家里只剩我了,你们还要我当个摆设?"月光透过窗棂,
把我们的影子投在祖宗牌位上,扭曲得像两个孤魂野鬼。赢安从贴胸口袋掏出个油纸包,
已经压得变了形。"经过苏州时买的。"他声音很轻,
"枣泥的....我知道大少爷答应了三**。"油纸包在供桌上发出轻微声响。
我望着大哥的牌位,突然想起他每一次离家时,都是这样半夜悄悄走的。赢安站在廊下等他,
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柄出鞘的剑。祠堂外传来脚步声。赢安迅速退开三步,
恢复成那个克制的军官模样。父亲拄着拐杖进来,目光扫过满地狼藉,
最后落在那包枣泥糕上。"深深。"父亲唤我小名,声音苍老得陌生,
"明天起你跟着赢安学电报密码。"赢安猛地抬头。父亲却已经转身,
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重重帷幔后。檐下白灯笼被风吹得摇晃,投下的影子像两只惨白的手,
死死攥住赵家的门楣。两个月后,二哥的死讯随着一场春雨到来。
那日我正在译电处抄录密电,赢安浑身湿透地闯进来,手里捏着封电报。
雨水顺着他的下颌滴在电报纸上,洇开了"赵春""殉国"几个字。我继续抄写密码,
铅笔尖却断了。赢安蹲下来,用军刀削好铅笔递给我。刀柄上刻着大哥的表字——是遗物。
"第三战区急电。"我把译好的电文推给他,声音平静得自己都害怕,"需要立即呈报父亲。
"赢安没接电文,却突然握住我拿笔的手。他的掌心滚烫,
带着战场带回的硝烟味:"哭出来。"我盯着他军装上斑驳的雨渍,
忽然发现赢安的肩膀更宽了。"放手。"我抽回手,铅笔在电报纸上划出长长一道,
"赵家还有人。"当夜我在祠堂点了第三盏白灯笼。赢安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
手里端着碗冒着热气的杏仁茶。"喝点。"他声音沙哑,"你一天没进食了。
"月光照在两个牌位上,大哥爱抽的香烟,二哥常用的计算尺,
还有我偷偷摆在角落的半块枣泥糕。赢安的影子笼罩着我,像是最后一道防线。
"父亲咳血了。"我把额头抵在供桌边缘,"医生说......熬不过今年冬天。
"赢安的军靴在地砖上碾了碾,像是要把什么碾进土里。他突然单膝跪地,
与我视线齐平:"三**,赵家还有我。"我望着他新换的领章,
想起五年前那个在雪地里拦车的少年。如今我们都沾了太多血,再也回不去了。"赢安,
"我伸手拂过他肩章上的星徽,
"下次别带点心了...."檐下第三盏白灯笼突然被风吹灭,
黑暗中只听见他沉重的呼吸声。远处隐约传来炮火轰鸣,像命运的鼓点,
一声声碾过北平的夜。民国三十三年秋,赵家后院的桂花开了第二茬。我站在父亲病榻前,
看着周家送来的聘礼单子——棉衣五千套,盘尼西林二十箱,
还有足以装备一个营的德制步枪。纸上的金粉沾了手,在指尖亮得刺眼。
"深深......"父亲枯瘦的手抓住我,"你可以不......""我愿意的。
"我把聘礼单折好塞进袖中,上面周庭两个字写得格外工整,"聘礼能救不少战士。
"窗外传来汽车引擎声。赢安已经半个月没回赵公馆了,
自从那次我亲眼看见他把受伤的士兵背进战地医院,白大褂下摆全是血。
周家派来的嬷嬷正给我试嫁衣,大红喜服上金线绣的凤凰,每一针都像扎在肉里。
《深深未有归》是一部令人沉浸其中的优秀作品。作者青梅子酒酒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精巧的结构,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神奇而真实的世界。主角赢安深深的形象栩栩如生,她的聪明和冷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整个故事充满了悬念和惊喜,读者会随着情节的发展而紧张、感动、欢笑。这本书的文笔流畅,情节紧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作者青梅子酒酒的文笔娴熟,故事情节独特,吸引了我对《深深未有归》的极高关注。
《深深未有归》以其精彩的情节和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吸引了读者的目光。每个章节都扣人心弦,故事中男女主角之间曲折传奇的爱情故事令人深思。在众多小说中,这是最好的之一。
青梅子酒酒的《深深未有归》是一部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的佳作。情节扣人心弦,人性描绘入微,让人对后面的剧情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