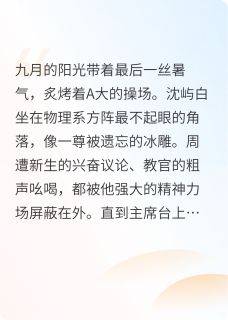第一章杏花微雨少年郎暮春的京城总爱落雨,细密的雨丝斜斜织着,
把镇国公府的青石板路润得发亮。沈清辞撑着柄素面油纸伞,站在回廊下看院角的杏树,
花瓣被雨打落,沾在她月白的裙角,像落了场轻薄的雪。“**,风凉,该回屋了。
”侍女晚晴捧着件素色披风,轻声劝道。沈清辞微微颔首,转身时袖口扫过雕花木栏,
带起一串细密的水珠。她自小便是这副模样,身子弱得像琉璃,性子冷得像玉泉山的冰,
镇国公府上下都小心翼翼地捧着,生怕碰碎了这朵娇贵的白梅。唯有一人,敢在她面前放肆。
“沈大**,赏杯茶喝?”墙头突然冒出颗脑袋,玄色劲装沾着雨珠,少年郎咧嘴一笑,
露出两颗小虎牙,正是刚从演武场回来的萧策。他身后还跟着个气喘吁吁的身影,
是湘潭侯家的小公子湘潭鞋,此刻正扒着墙沿,费力地往上爬。沈清辞皱眉,
却还是让晚晴去沏茶。她与萧策的相识,说起来倒像话本里的桥段——三年前的宫宴,
她被席间的熏香呛得咳个不停,父亲正蹙眉训斥她“失仪”,
一只温热的手突然从桌下伸过来,塞给她颗蜜饯。“含着,甜的。”少年的声音压得极低,
带着点狡黠的笑意,呼吸扫过她耳廓,烫得她耳尖发红。那时萧策刚随父从北境回京,
一身的野气还没褪尽,穿着不合时宜的玄色劲装,在锦衣华服的勋贵子弟中像株扎眼的青松。
沈清辞后来才知道,他父亲是镇守北境的忠勇侯,在平定蛮族时战死,陛下怜他年幼,
才让他袭了爵位,留在京城教养。自那以后,萧策便成了镇国公府的常客。有时是翻墙进来,
手里拎着包城南老字号的糖糕,说“听晚晴说你爱吃甜的”;有时是带着柄刚打磨好的匕首,
笨拙地解释“女子也该学点防身术”;更多时候,是坐在她窗下的石凳上,
看她临帖、看书、对着药炉发呆,自己则拿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嘴里念念有词。
“这是北境的地形,”某次他见她望过来,献宝似的指着地上的划痕,“你看,
这里是咽喉要道,守住了就能一夫当关。”沈清辞垂眸,继续翻着手里的医书。
温砚言送的《本草纲目》被她翻得卷了边,
书页间夹着几片晒干的薄荷——那是她幼时在药铺玩,温砚言教她认的第一种草药。
“温大哥说,薄荷能治风热咳嗽。”她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雨丝。萧策的手顿了顿,
抬头看她。窗外的雨停了,阳光透过云层落在她脸上,睫毛投下淡淡的阴影,
苍白的唇瓣因为刚喝过药,泛着点不正常的红。他忽然觉得,那些枯燥的兵法,
竟不如看她翻书有趣。“等我将来去了北境,”他丢下树枝,拍了拍身上的灰,
语气里带着少年人的意气风发,“就给你种一大片薄荷,让你再也不咳嗽。
”沈清辞握着书页的手指紧了紧,没说话。晚晴端着刚炖好的冰糖雪梨走进来,
见两人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像幅静止的画,忍不住笑:“萧公子又在给**讲兵法呀?
”萧策挠了挠头,嘿嘿一笑。沈清辞却在他转身时,悄悄抬眼,望了望他挺拔的背影,
耳尖悄悄爬上一抹红。那年的杏花落了又开,萧策的军功册上渐渐有了名字。
他从最初的御前侍卫,到后来能跟着老将出征,每次回来,
都会给她带些新奇玩意儿——北境的狼牙、草原的奶酪、甚至是一小袋带着风沙气息的泥土。
“这是北境的土,”他献宝似的递给她,“埋在花盆里,能种出不一样的花。
”沈清辞真的找了个白瓷盆,把那捧土埋进去,种了颗不知能不能发芽的梅核。
她每日给它浇水,看着它在晨光里慢慢抽出嫩芽,像看着一个小心翼翼藏起来的秘密。
温砚言来看她时,见她对着那盆幼苗发呆,温润的眸子里掠过一丝黯然。
他如今已是太医院的院判,却总在休沐时往镇国公府跑,带些新药,说些医案,
像个尽职尽责的兄长。“萧策在边关立了功,陛下要赏他良田美宅了。
”温砚言一边给她诊脉,一边状似无意地说。沈清辞的手顿了顿,
指尖拂过梅苗的叶子:“与我何干。”温砚言笑了笑,没再说话。他看得出,
她窗台上那只装狼牙的锦囊,被摩挲得边角都软了;看得出她枕头下,
藏着他某次随口说“北境的星星很亮”时,她偷偷画的星图;更看得出,
她提起“萧策”二字时,眼底藏不住的光。只是那时的他们都不知道,命运的网,
早已在杏花纷飞的午后,悄然收紧。第二章圣旨如霜裂锦帛盛夏的风带着蝉鸣,
吹得镇国公府的葡萄架沙沙作响。沈清辞坐在廊下,看着晚晴摘刚熟的葡萄,
忽然没来由地心慌。三日前,皇帝在御花园设宴,她陪太后赏花,中途去偏殿休息,
撞见皇帝正与贴身太监说话。那句“镇国公的女儿……倒是个好苗子”像根针,扎在她心上,
让她连着几夜都睡不安稳。“**,您脸色不好,要不要回屋歇着?”晚晴递来颗冰镇葡萄,
担忧地看着她。沈清辞摇摇头,刚要说话,却听见府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她心里一紧,
下意识地站起身——萧策说过,今日会从边关回来。可冲进府的不是萧策,
是宫里的传旨太监。明黄的圣旨展开在正厅,
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午后的宁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公嫡女沈清辞,娴雅淑静,
性资敏慧,着册封为贵妃,择吉日入宫。钦此。”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沈清辞跪在冰凉的金砖上,听着父亲山呼“万岁”,听着母亲压抑的啜泣,
只觉得浑身的血都被冻住了。那盆她精心照料的梅苗,此刻正放在窗台上,
叶片在风中微微颤抖,像在替她哭泣。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房,
只记得太监临走时意味深长的眼神,记得父亲苍白的脸,记得母亲抓着她的手,
一遍遍说“这可如何是好”。夜里,她发起高热,咳得撕心裂肺。晚晴急得团团转,
刚要去请温砚言,窗外突然传来轻响。“别动。”萧策翻窗进来,
身上还带着边关的风尘和血腥气,玄色劲装的袖口破了个洞,沾着暗红的血迹。
他几步冲到床边,伸手探她的额头,滚烫的温度让他猛地皱眉。“怎么回事?
”他的声音发紧,带着压抑的怒火。沈清辞烧得迷迷糊糊,看见是他,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她抓着他的衣袖,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语无伦次地说:“他们要我入宫……萧策,
我不想去……”萧策的心像被狠狠攥住,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他知道圣旨的事,
他是拼了命从边关赶回来的,马跑死了三匹,还是晚了一步。“别怕。”他蹲下身,
用粗糙的拇指擦去她的眼泪,眼神坚定得像北境的山,“有我在,不会让你入宫的。
”那一晚,萧策守在她床边,给她换帕子,喂她喝药,像个最虔诚的信徒。天快亮时,
他握着她的手,轻声说:“清辞,再给我三个月,信我这一次。”沈清辞迷迷糊糊地点头,
看着他翻窗离去的背影,心里忽然安定了些。她信他,就像信春去秋来,信花开花落,
信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执念。萧策回到将军府,立刻进宫求见皇帝。他跪在太和殿前,
从清晨到日暮,额头磕出了血,声音嘶哑地请求皇帝收回成命。“陛下,沈**体弱,
不堪宫廷繁役,求陛下成全!”皇帝在殿内看着奏折,听着外面的动静,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他要的从来不是一个病弱的贵妃,而是镇国公府的兵权,
是萧策手里那支只认他本人的北境铁骑。“告诉萧策,”皇帝放下朱笔,语气平淡,
“北境蛮族又蠢蠢欲动,他若能在三个月内平定叛乱,朕就允他一个请求。
”太监将话传到殿外,萧策猛地抬头,眼里迸发出惊人的光。他叩首,声音响彻午门:“臣,
领旨!”那三个月,成了京城百姓口中最传奇的岁月。萧策带着五千精兵,
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掠过北境的草原和戈壁。他凿冰饮雪,露宿风餐,
身中数箭仍死战不退;他用奇兵突袭蛮族王帐,擒获首领,
将蛮族赶回了极北之地;他甚至单枪匹马闯入敌营,斩杀了挑衅的蛮族勇士,
吓得敌军三天不敢出战。捷报一封封传回京城,红绸裹着的军功章,从最初的小木箱,
堆成了小山。街头巷尾都在说萧将军的英勇,说他是天上的战神下凡。沈清辞每日坐在窗前,
看着那盆梅树抽出新枝,把他的战报读了又读。她知道他在拼命,知道他为的是什么,
所以连温砚言送来的新药,都带着几分甜意。她绣了个平安符,用最细的丝线,
在里面缝了根自己的头发。红绳绕了九圈,像绕了九个轮回的期盼。
晚晴打趣她:“**这针脚,比给老夫人绣的寿屏还用心呢。”沈清辞没说话,
只是将那平安符贴身藏着,像藏着一颗滚烫的心。三个月期满那天,
京城的钟声响了整整一夜。萧策平定北境,班师回朝,百姓沿街相迎,欢呼声震彻云霄。
沈清辞站在阁楼的窗边,看着那支玄色的队伍从街尾走来,看着那个骑在黑马上的少年将军,
身披金甲,腰悬佩剑,接受万民朝拜。他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眉宇间多了几分凌厉,
眼神却依旧亮得惊人。他的目光穿过人群,准确地落在她的窗上,像跨越了千山万水的重逢。
沈清辞的心跳得飞快,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平安符。她以为,
他们终于可以像话本里写的那样,有个圆满的结局。可她等来的,不是八抬大轿,
不是凤冠霞帔,而是湘潭鞋。那个总是跟在萧策身后,嘻嘻哈哈没个正形的湘潭侯小公子,
此刻正坐在镇国公府的花厅里,脸上没了往日的笑,只有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神情。
“沈**。”他端起茶杯,又放下,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沈清辞的心,没来由地一沉。
湘潭鞋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他抬起头,避开她的目光,
语气带着刻意的轻佻:“萧策兄让我来告诉你,以前的话,都是玩笑。
”沈清辞握着茶杯的手猛地收紧,指尖泛白。“他说,”湘潭鞋的声音越来越低,
却像冰锥一样扎进她的心里,“他从没打算娶你。以前是看你可怜,如今他功成名就,
要娶的是能助他平步青云的世家贵女,不是你这样……咳咳,体弱多病的。”“他还说,
”湘潭鞋别过脸,不敢看她的眼睛,“能被陛下看中,是你的福气。别不识抬举,
坏了他的前程。”最后一个字落下时,沈清辞手里的茶杯“哐当”一声摔在地上,
碎裂的瓷片溅起水花,像她瞬间崩塌的世界。她看着湘潭鞋落荒而逃的背影,
看着地上的水渍慢慢晕开,忽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砸在冰冷的地砖上,
像一颗颗碎掉的星子。晚晴冲进来,看着满地狼藉和自家**苍白的脸,
吓得手足无措:“**,您别哭,是不是萧公子……”“他说得对。”沈清辞擦干眼泪,
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是我痴心妄想了。”她不知道,此刻的将军府里,
萧策正死死攥着一份圣旨。明黄的卷轴上,皇帝的朱笔写着:“萧策平定北境,功高盖世,
特封镇北王,赐金册金宝。沈氏清辞,免入宫之命,准其自择婚嫁。萧策需镇守北境,
非诏不得回京。”“值得吗?”湘潭鞋红着眼眶,一拳砸在桌上,“你让她恨你,
让她以为你是负心汉,这就是你要的结果?”萧策背对着他,望着窗外北境的方向。
阳光落在他身上,却暖不了他眼底的冰。他慢慢松开手,掌心被圣旨的边缘勒出了血痕。
“恨总比等好。”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她身子弱,等不起一个可能永远回不来的人。
”他从怀里掏出一支白梅簪,簪头的梅花雕刻得栩栩如生,是他在北境的寒夜里,亲手刻的。
刀锋划过指尖,血滴在梅花上,像开了朵永不凋零的花。
“帮我把这个……”他想说“送她”,却又顿住,“烧了吧。”湘潭鞋接过那支簪子,
看着上面的血迹,终究没舍得。他偷偷把它收了起来,像藏起一个永远不能说的秘密。
第三章江南雨冷葬痴心沈清辞离开京城的那天,下着小雨。她没告诉任何人,
只带了晚晴和一个老仆,坐上了南下的乌篷船。船开时,她回头望了一眼,
镇国公府的朱漆大门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像个模糊的旧梦。她没去告别,没去解释,
甚至没去看一眼那盆她精心照料的梅树。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留着只会更疼。
温砚言是在三天后追到江南的。他骑着快马,一身白衣被雨水打湿,
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站在渡口的石阶上,望着缓缓驶离的船影,
温润的眸子里第一次有了失态。他动用了所有关系,顺着水路追了七天,
终于在苏州的码头追上了她。“清辞。”他站在船头,声音带着旅途的疲惫,却依旧温和,
“我陪你。”沈清辞靠在船舷上,看着江南的烟雨朦胧,没说话。她的心已经空了,
像被北境的风吹过的草原,只剩下荒芜。谁陪在身边,好像都一样。温砚言没再强求,
只是默默地在她住的小院隔壁,租了间屋子。他请了最好的大夫给她调理身体,
寻遍江南的名医,只为让她的咳嗽好一点。江南的日子,是缓慢而湿润的。
沈清辞住在内城的一个小院里,院墙边种着芭蕉,窗台上摆着青瓷瓶,里面插着随摘的野花。
她每日看雨打芭蕉,听晚晴说些街坊趣事,偶尔翻一翻温砚言带来的医书,像个隐居的居士。
温砚言成了江南有名的神医,他的医馆开在街角,每日门庭若市,却总会在她咳嗽的时辰,
准时出现在小院门口,手里提着刚炖好的润肺汤。“今日用了新采的川贝,你试试。
”他把汤碗递给她,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沈清辞接过汤碗,
温热的瓷壁烫得指尖发麻。她小口喝着,听他说些医案,说些药材,像个尽职尽责的听众。
日子久了,街坊邻里都以为温砚言是她的夫君,
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个温润如玉的神医,一个清冷绝美的佳人。
晚晴私下里劝她:“**,温公子是真心待您的,您……”“晚晴。”沈清辞打断她,
声音平静,“他是温大哥,永远都是。”晚晴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她知道自家**心里的那道疤,太深了,不是时间和温柔就能抚平的。
沈清辞偶尔会听到关于萧策的消息。从北境来的商人说,镇北王萧策镇守边疆,铁面无私,
把北境治理得井井有条;从京城来的信使说,萧将军身边有了个红颜知己,是副将的妹妹,
温柔贤淑,两人常并辔出游;甚至还有人说,萧策在庆功宴上喝醉了,说当年在京城,
不过是玩了场年少轻狂的戏,哪当得真。这些话像细小的针,一点点扎进沈清辞的心里。
她表面上不动声色,夜里却咳得更厉害了。温砚言给她诊脉时,
总能在她眼底看到深藏的疲惫,却只能叹着气,给她换更温和的药。“清辞,”一个雪夜,
温砚言给她披上披风,轻声说,“北境苦寒,他……或许也是身不由己。
”沈清辞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忽然笑了:“温大哥,你不必为他开脱。爱与不爱,
我还是分得清的。”她想起那年杏花巷,
她撑伞时的笨拙;想起他说要种满院薄荷时的认真;想起他战报里那句“待我归来”的坚定。
那些曾经让她心动的瞬间,如今都成了刺,扎得她生疼。温砚言看着她苍白的侧脸,
终究没再说下去。他知道,有些伤口,需要时间自己愈合。江南的五年,
就这样不疾不徐地过去。沈清辞的咳嗽好了些,却依旧爱穿白衣,
像一朵开在江南烟雨中的梨花。她学会了辨认草药,学会了酿桃花酒,
甚至学会了在温砚言忙不过来时,去医馆帮忙抓药。只是她再也没绣过平安符,没种过梅树,
没再提起过京城的任何人和事。温砚言始终陪在她身边。他拒绝了所有说亲的媒婆,
把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给了这个病弱的女子。街坊邻居都在说,
温神医是被沈**迷了心窍,放着好好的前程不要,非要守着一个心有所属的人。
沈清辞不是不知道,只是她给不了回应。她的心,早在那个听到湘潭鞋话语的午后,
就已经死了。第五年的秋天,温砚言的母亲从京城来了。老太太是个明事理的人,
看着儿子日渐憔悴,看着沈清辞眼底的疏离,拉着沈清辞的手,叹了口气:“清辞丫头,
我知道你心里苦。可砚言他……也苦了五年了。”沈清辞沉默了很久,
对温砚言说:“温大哥,你该有自己的家。”温砚言望着她,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他笑了笑,声音有些哽咽:“我知道了。”半年后,温砚言娶了邻县的一个绣娘。
那女子性情温婉,手很巧,绣的鸳鸯栩栩如生。大婚那天,温砚言来请沈清辞喝喜酒,
沈清辞看着他穿着喜服,牵着新娘的手,忽然松了口气。
她送上一份贺礼——一支用江南竹根雕的梅花簪,是她亲手雕的,花了整整三个月。
“祝你……平安喜乐。”她说。温砚言接过簪子,眼眶红了。他知道,这是她能给的,
最体面的告别。婚后的温砚言,依旧常来小院。他的妻子很贤惠,
从不计较他对沈清辞的照顾,有时还会让他带些刚做好的点心过来。两年后,
他们有了个女儿,小名叫十一,粉雕玉琢的,像个小天使。十一很喜欢沈清辞,总爱缠着她,
喊她“清辞姨”。沈清辞会给她讲故事,教她认草药,甚至会亲手给她做小衣服。
看着孩子天真的笑脸,沈清辞冰封的心,似乎有了一丝松动。只是在某个寂静的夜晚,
她还是会想起北境的风,想起那个说要给她种满院薄荷的少年。
她会拿出那个磨得光滑的平安符,对着月光看了又看,直到眼泪模糊了视线。
温砚言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知道她没放下,只是把那份执念,藏得更深了。
第四章狭路相逢不识君萧策再次踏入江南,是在十年后的一个初秋。北境的战事暂歇,
皇帝特许他回京述职三个月。他婉拒了京城的繁华,快马加鞭,直奔江南。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或许是想看看她过得好不好,或许是想了却十年的牵挂,又或许,
只是想再闻闻江南的桂花香。他住在城外的驿站,每日穿着便服,像个普通的旅人,
徘徊在沈清辞住的小院附近。他看见她牵着十一的手,去镇上买糖人;看见她坐在窗前,
安静地看书;看见温砚言提着药箱,走进她的小院,两人相视一笑,像一对和睦的夫妻。
眠星雨夜的《白衣锁:十年雪落北境风》是一部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的佳作。情节扣人心弦,人性描绘入微,让人对后面的剧情充满期待。
眠星雨夜的作品总是让人眼前一亮。在《白衣锁:十年雪落北境风》中,他展现出了极高的文笔技巧和深厚的人性洞察力。
《白衣锁:十年雪落北境风》这本书让人陶醉其中。作者眠星雨夜的文笔细腻流畅,每一个描写都让人感受到他的用心和情感。主角沈清辞萧策温砚言的形象生动鲜明,她的坚韧和聪明让人为之倾倒。整个故事紧凑而又扣人心弦,每一个情节都令人意想不到。配角们的存在丰富了故事的内涵和戏剧性,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魅力。这是一本令人沉浸其中的佳作,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不同的情感和思考。
作为一名热爱[标签:小说类型]小说的读者,我对《白衣锁:十年雪落北境风》赞不绝口。这本书的结构精巧,文笔流畅,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力。主角沈清辞萧策温砚言的形象栩栩如生,她的聪明和冷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整个故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悬念和震撼,读者很难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紧张感让人欲罢不能。作者眠星雨夜的文笔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他用细腻的描写将读者带入了一个令人陶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