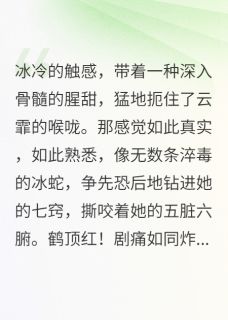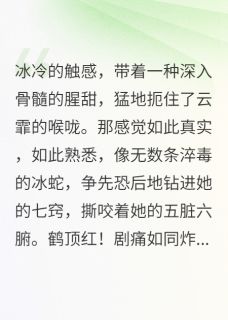“顾霆琛,你白月光回国就嫌我土?行,这替身我不演了!”我当着满堂宾客撕了结婚证,
净身出户。三个月后,暴雨夜送外卖,
保温箱里蜷缩着浑身湿透的俊美男人——正是破产被追债的顾大总裁。他攥着我衣角,
眼尾猩红:“求你,收留一晚…”我轻笑,拨通电话。“老公,楼下有流浪狗,能报警吗?
”1酒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滑落,洇湿了我的指尖,一片冰凉。“顾霆琛,
你那宝贝白月光一回国,我就成了你眼里上不了台面的米饭粒?”我的声音不大,
但在小提琴曲悠扬的间隙,足够清晰地传到他耳中。今天,是顾霆琛为他归国的初恋,
林婉儿,举办的接风宴。也是我们的结婚三周年纪念日。他没回头,甚至连肩膀都没动一下,
只是稍稍侧过脸,给了我一个冰冷的眼风。林婉儿穿着一身洁白的高定长裙,
手臂正亲密地挽着我名义上的丈夫,她闻声看来,嘴角噙着一抹得体又疏离的微笑,
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陌生人。而我,这个正牌顾太太,身上这件尺码不合的礼服,
还是他助理在半小时前匆匆买来丢给我的。裙子的腰线卡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让我每一次呼吸都感到束缚。周围的窃窃私语汇成一片嗡鸣。我能捕捉到一些碎片。
“那个就是林浅?乡下来的……”“跟林**站在一起,简直是公开处刑。
”“听说顾总当初娶她就是为了气林**,现在正主回来了,好戏开场了。
”那些目光不再是针,而是一把把鈍刀,在我身上反复切割。顾霆琛终于彻底转过身,
他松开林婉儿的手,朝我走了两步。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眉头拧紧,
像在看一件弄脏了的昂贵摆设。“林浅,闹够了没有?”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丢人现眼?我盯着他,忽然扯出一个笑容。
嘴角的肌肉不受控制地颤抖着,我索性任由它越咧越大,直到眼眶发热,视线模糊。
我从手包里拿出那本红得刺眼的结婚证。它的边角已经被我摩挲得有些发白。“顾霆琛,
你说的对。”我点点头,把证件递到他面前。“我不配。”在他伸手要接的瞬间,我收回手,
在所有人震惊的注视下,双手抓住证件两端。“刺啦——”一声脆响。纸张断裂的声音,
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显得格外刺耳。结婚证被我撕成了两半。“这顾太太的位子,
”我将其中一半扔在地上,用鞋跟碾了碾,“谁爱坐谁坐!”然后,我将另一半碎片,
对准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狠狠砸了过去。纸片轻飘飘地,打在他高挺的鼻梁上,然后坠落。
“从今天起,你我,一拍两散,各不相干!”我转身,背脊挺得像一杆标枪。
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每一步都发出清脆的响声,像是在为我这场难堪的婚姻,
敲响丧钟。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金碧辉煌的牢笼。净身出户。……三个月后。
“轰隆——”暴雨如注。我的小电驴在积水中艰难前行,车轮溅起的水花,冰冷刺骨。
【超时警告!您的订单即将超时!】手机导航嘶哑地吼叫着。我咒骂了一句,
拐进一个黑漆漆的小巷,想抄个近路。巷子没有路灯,只有远处居民楼透出的零星光亮,
勉强勾勒出轮廓。空气中弥漫着雨水和垃圾发酵的酸腐气味。巷子深处,
一个没盖严的绿色垃圾桶旁边,缩着一团黑影。我心里一紧,车速下意识地放慢。这个点,
这种天气,在这里的……会是什么人?我捏紧了刹车,将车头灯对准了那团黑影。
光柱刺破黑暗,照亮了一切。那团黑影动了一下,似乎被强光**到,他用手臂挡了一下,
然后缓缓抬起头。雨水正顺着他凌乱湿透的黑发往下滴。水珠划过他高挺的鼻梁,
苍白的脸颊,最后没入他紧抿的、毫无血色的嘴唇。那是一张,就算烧成灰我也认得的脸。
顾霆霆。他身上那件曾经价值不菲的高定西装,此刻被雨水和污泥毁得看不出原样,
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一只昂贵的定制皮鞋不知去向,赤着的左脚泡在泥水里,
脚背上满是细碎的划痕和污渍。他看着我,不,准确来说,
是看着我车头那个印着黄色笑脸的外卖保温箱。他的眼神,先是茫然,然后是震惊,最后,
凝固成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祈求。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他已经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向我扑了过来。他一把抓住了我的雨衣下摆,
力气大得惊人,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唯一一截浮木。
“林浅……”他的嗓子完全哑了,每个字都像是用砂纸磨出来的。“是我……”他眼尾猩红,
瞳孔里映着我电驴车灯的光,昔日那种俯瞰众生的傲慢荡然无存。此刻的他,
只剩下一具被剥夺了所有尊严的、狼狈的驱壳。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忽然就笑了。
发自内心的,畅快淋漓的笑。天道好轮回。真是报应。我没有甩开他的手,而是空出一只手,
慢条斯理地掏出手机。屏幕的光亮,映出他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当着他的面,
点开通讯录,拨出一个我置顶的号码。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通。
那边传来一道温润磁性的男声,带着一丝笑意:“浅浅,下班了?”我嘴角的弧度更深了,
用一种我自己都觉得腻人的甜美声音回道:“老公,我马上就到家啦。
”顾霆琛抓着我衣角的手,猛地一僵。他豁然抬起头,那双曾经对我只有厌恶的眼睛,
此刻死死地盯着我,里面盛满了破碎的惊愕和痛苦。我没看他。
我的视线落在不远处那个敞口的垃圾桶上。我继续对着电话柔声说:“对了,
我们楼下好像有只流浪狗。”“浑身都湿透了,看起来怪可怜的。
”“你说……”我停顿了一下,故意拖长了尾音,感受着他抓着我衣角的手在不住地颤抖。
“我要不要报警,让动物收容所来处理一下?”2电话那头,裴时宴的声音带着低沉的笑意,
穿透雨幕,清晰地钻进我的耳朵。「别闹。」「狗会咬人,你离远点。」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宠溺。「快回来,汤要凉了。」「好。」我应了一声,
掐断通话,手机屏幕暗下去。周遭的世界,只剩下雨声和眼前这个男人粗重、压抑的喘息。
顾霆琛抓着我雨衣下摆的手,指骨因为过度用力,在昏暗中泛着死人般的惨白。
雨水从他下颌的轮廓滴落,砸进脚下的泥潭,溅开一圈圈浑浊的涟漪。「老公?」
他终于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声带像是被砂纸狠狠磨过,每一个音节都艰涩无比。
「你什么时候……」我的视线,缓缓下移。落在他那只沾满泥污的手上。那只手,
曾经戴着我亲手为他挑选的婚戒,签下过上亿的合同,也曾毫不留情地推开过我。现在,
它只配抓着我送外卖的雨衣。「顾先生。」我刻意加重了最后两个字。「这跟你有关系吗?」
我空出一只手,伸进口袋,摸索了几下。掏出来的是几张被雨水浸透的纸币。一百的,
五十的,皱巴巴地黏在一起,像一团湿透的垃圾。我捏着那团钱,没有直接塞给他,
而是伸到了他眼前。他僵住了。他看着那几张湿透的、肮脏的钞票,
就像在看什么致命的侮辱。「拿着。」我的声音很平,没有一丝波澜。「去买碗热的,
找个能挡雨的屋檐。」「别死在这儿,脏了别人的地方。」我的语气,
是在处理一件麻烦的废品。他猛地向后一缩,仿佛被我的话烫伤,身体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我松开手。那几张湿漉漉的钞票,轻飘飘地,打着旋儿,落尽他脚边那片最浑浊的积水里。
红色的,绿色的纸,瞬间被泥污吞噬。他眼中的光,彻底碎了。
那双曾经永远写满高傲和不耐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一种被碾碎后的、**的痛苦。
「林浅……」他的嘴唇在抖,却发不出完整的音节。「你非要……」他想说“羞辱”两个字,
但喉咙里发出的,只是一阵漏风般的嗬嗬声。羞辱?我差点笑出声。「顾霆琛,三个月前,
林婉儿的接风宴上。」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提醒他。「你当着几百人的面,
说我身上的礼服让你丢人现眼。」「你忘了?」「比起你当时给我的,我今天这点善心,
又算得了什么?」我懒得再看他。用力一甩胳膊,想挣开他的钳制。小电驴的车把跟着晃动,
发出“咯吱”一声轻响。我准备走了。这个地方,这个男人,都让我感到生理性的恶心。
「别走!」一声嘶吼。那不是顾霆霆的声音,而是一头濒死野兽的哀鸣。他再次向我扑来。
这一次,不是抓我的衣服,而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死死地抱住了我的腿。“噗通”一声。
曾经不可一世的顾家大少,天之骄子,就这么双膝跪进了冰冷的泥水里。
他彻底抛弃了最后一丝名为“尊严”的东西。「求你……」他的脸埋在我的膝盖处,
滚烫的眼泪混着冰冷的雨水,迅速浸透了我厚实的骑行裤。「林浅……求你……别走……」
他像个溺水的孩子,语无伦次地重复着,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我低头。能看到的,
只有他湿透了的、凌乱的黑发,和沾在我裤腿上的大片泥污。
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那股雨水、霉味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气息。就在这时。巷口。
一束刺眼的光柱撕裂了浓稠的夜色和雨幕。光线先是扫过远处堆积的垃圾桶,然后缓缓移动,
最后精准地定格在我们身上。我和跪在我脚下的顾霆琛,像一出荒诞舞台剧的主角,
被这束光钉在了原地。一辆黑色的宾利,无声无息地停在了巷口。它的车身线条流畅,
漆黑如墨,仿佛能将周围所有的光和雨都吸进去。车门打开。先落地的,
是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手工皮鞋。鞋尖精准地避开了地上的所有水洼。随即,
一把巨大的黑伞撑开,伞面隔绝了所有的风雨,撑起了一片干燥安宁的天地。
一个身形挺拔的男人,撑着伞,从光里走了出来。他步履从容,不疾不徐。
雨水仿佛都在为他让路。他走到我身边。那把巨大的黑伞,微微倾斜,将我和我的小电驴,
完全笼罩。风雨声,瞬间远了。他身上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灰色风衣,面料挺括,
没有一丝褶皱。是裴时宴。他的目光甚至没有分给地上那个卑微的影子一分一毫。
他只是伸出手,用温热的指腹,轻轻擦去我脸颊上冰冷的雨滴。「怎么这么久?」
他的声音温润,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责备。「路上滑,怕摔。」我轻描淡写地解释。
裴时宴的目光,这才落下去。像是在审视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脏东西。他微微蹙眉,
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温和眼眸里,闪过一丝清晰的冷意。「这位是?」
顾霆霆也缓缓抬起了头。他的视线,从裴时宴那双一尘不染的皮鞋,
到他那身价值不菲的风衣,再到他为我撑伞的亲密姿态。最后,
定格在裴时宴眼中那毫不掩饰的、对我一个人的珍视。那是他顾霆琛,在我三年的婚姻里,
从未给过我的东西。嫉妒、不甘、怨恨、绝望……无数种情绪在他那张惨白的脸上疯狂交织,
最终,凝固成一种彻底的、死灰般的寂静。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忽然就笑了。发自内心的,
畅快淋漓。我转向裴时宴,挽住了他的手臂,身体自然地靠向他。「不认识。」我说。
「一个大概是喝醉了认错人的疯子。」说完,我从电驴上下来,摸出车钥匙,
递给不知何时跟上来的司机。「麻烦帮我把车骑回去。」然后,我挽着裴时宴,一步步,
走向那辆在雨夜中依旧温暖、明亮的豪车。我们身后,是顾霆琛撕心裂肺的嘶吼。
「林浅——!」我没有回头。一步都没有。车门在我身后“砰”地一声关上。那声音,
将他和他的嘶吼,连同那个不堪的过去,一起隔绝在了这个冰冷的、肮脏的雨夜里。
永不相见。3车内暖气开得很足,风口吹出的热风带着一股干燥的木质香。
裴时宴递来一条干毛巾。「擦擦。」他的声音总是这样,平稳,温和,
像车窗外被路灯晕染开的雨丝。我接过毛巾,胡乱在脸上和头发上按了按,
毛巾柔软的触感吸走了一身狼狈的寒气。车子无声地滑入一个灯火通明的高档小区地库。
电梯直达顶层。“叮”的一声轻响后,门向两侧滑开。眼前没有过度的装饰,
只有冷灰色的大理石地面,倒映着窗外城市的璀璨灯河,像一片颠倒的星空。
线条利落的意大利沙发,墙上一幅看不懂但显然昂贵的抽象画,
空气里浮动着和我刚在车上闻到的一样的木质香气。这里是裴时宴的家。也是我这三个月,
用来隔绝全世界的壳。「去洗个热水澡,衣服我让阿姨送新的过来。」
裴时宴没多问巷子里的事,他只是伸出手,指尖勾过我那件滴着水的廉价雨衣,
挂在玄关的衣架上。雨衣上的泥点,和那个光洁如镜的衣架,格格不入。我点点头,
径直走向浴室。热水从头顶浇下,冲刷着皮肤,也试图冲走心里那点挥之不去的烦躁。
镜中的自己,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是平静的。我和裴时宴的婚姻,是一桩心照不宣的买卖。
我净身出户那天,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在人才市场排着长队,试图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
然后,他的车停在了我面前。他说,他需要一个妻子,挡掉家里无穷无尽的催婚和商业联姻。
而我,需要一个身份,一个住处,一个能让我喘口气的机会。我们甚至没怎么讨价还价,
一拍即合,当天就去了民政局。没有戒指,没有仪式,只有两本崭新的红本。讽刺的是,
那颜色竟和被我撕碎的那本一模一样。他给了我一张没有额度上限的黑卡,我一次没用过。
他给了我这间顶层公寓的居住权,我只睡在客房。我们的约定是,
在必要的时候扮演恩爱夫妻,私下互不干涉。他做得很好。像一个完美的合伙人。
洗完澡出来,换上松软的家居服。客厅的矮几上,放着一碗姜汤,还在冒着丝丝热气。
裴时宴坐在单人沙发上,腿上放着一台平板,屏幕的光映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趁热喝。
」他头也没抬。我走过去,捧起碗,辛辣的暖意顺着喉咙一路烧进胃里,驱散了最后的寒意。
我小口喝着,视线无意间落在了他的平板上。财经新闻的推送标题,字号大得刺眼。
【商业帝国一夜倾塌:顾氏集团正式申请破产清算】我的手,顿了一下。
裴时宴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划,点开了那条新闻。
女主播公式化的声音从平板的扬声器里流出,清晰,又遥远。「……据悉,顾氏的崩盘,
源于其在欧洲的一项关键投资失败,以及核心盟友的致命背叛……」「……而这位盟友,
正是顾霆琛先生曾经的挚友,以及他的前未婚妻,林婉儿**……」新闻配图上,
林婉儿笑靥如花,亲密地挽着另一个男人的手臂。那个男人我认得。陆氏集团的继承人,
顾霆琛商场上最大的死对头。所以,是这样。他奉为珍宝的白月光,
不过是一条早就盘算好如何将他一口吞下的毒蛇。当他失去利用价值,
就毫不犹豫地联合外人,敲碎他的骨头,吸干他的血。何其讽刺。又何其……公平。
「痛快吗?」裴时宴不知何时放下了平板,正看着我。他的眼神很深,
像一潭被夜色笼罩的湖水,看不真切。我放下手里的空碗,碗底和桌面碰撞,发出一声轻响。
我扯了扯嘴角,想笑,却发现脸上的肌肉有些僵硬。「痛快?」我重复着这两个字,
然后摇了摇头。「不。」「只是觉得,我那三年的笑话,终于讲完了。」
那些被踩在脚下的尊严,那些被无视的付出,那些深夜里的独自等待,在这一刻,
终于有了一个尘埃落定的结局。不是痛快,是终结。是一笔烂账,终于被划清了。
裴时宴看着我,没再说话。他起身,走进开放式厨房。「饿不饿?冰箱里有食材,
给你下碗面?」这三个月,他总是这样。体贴,却有分寸。尊重,也带着疏离。
他从不问我的过去,我也从不提。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客气,礼貌,
却又在某些时刻,流露出一点家人般的温情。就在这时,我放在茶几上的手机,
突兀地振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一串陌生号码。我盯着那串数字,犹豫了几秒,
还是划开了接听键。「喂?」电话那头,背景音嘈杂,一个女声显得虚弱又急切。
「请问……是林浅**吗?」「我是。」「您好,我是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护士,
这里有一位叫顾霆琛的病人……」护士后面的话,我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
只觉得耳朵里一阵嗡鸣。「……他送来时高烧昏迷,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我们从他手机的紧急联系人里,只找到了您的号码……」我握着手机。指节,不自觉地收紧,
用力到泛白。4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像是一种宣告。我站在病房的玻璃窗外。
里面,顾霆琛躺着,一张脸白得像床单,干裂的嘴唇上起了皮。他手背上插着针管,
透明的液体正一滴滴注入他的身体。他睡着了,但眉心拧成一个死结。护士说,
环卫工在小巷里发现他时,人已经烧得快说不出话了。急性肺炎,再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我站在这里,只是想亲眼确认一下。确认他到底有多惨。“林浅?
”一个拔高的、充满错愕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转过身。顾霆M琛的母亲,周琴。
一身剪裁精良的香奈儿套装,手里拎着一只崭新的爱马仕铂金包,
和这条为生死奔忙的走廊格格不入。她看我的眼神,像是看见一只蟑螂爬上了她的餐盘。
“你来这里做什么?”她踩着高跟鞋走近,不等我回答,一只手就推在我肩膀上。“滚。
”力道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离婚前,这位顾夫人就从没正眼瞧过我。
她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们霆琛,天之骄子,不是你这种乡下来的野丫头能高攀的。
”我被她推得后退半步,站稳了。“顾夫人,”我平静地开口,“医院给我打的电话。
”我看着她保养得宜的脸,一字一句。“他手机紧急联系人那栏,只有我的号码。”这句话,
像一把锥子,精准地扎进了她的痛处。周琴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垮了下去,那份高傲瞬间碎裂。
“你胡说!”她声音陡然尖利起来,“我儿子怎么可能还留着你的电话!你动了什么手脚?
”周围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不想和她在这里上演泼妇骂街。“您来了,他有您照顾,
我走了。”我转身,迈步。“站住!”手腕猛地一紧,是她抓住了我。
她的指甲修剪得十分精致,此刻却毫不留情地掐进我的皮肤。“你不能走!”她的语气,
从刚才的盛气凌人,变成了一种近乎哀求的急切。“霆琛他……他现在这样,你不能不管他!
”她的眼眶红了,声音里带上哭腔,抓着我的力气更大了。“林婉儿那个**!
她把公司掏空了!她联合外人把我们家给搞垮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她开始语无伦次,
眼泪混着昂贵的粉底液往下淌。“林浅……我知道,以前是妈不对,
是妈看不起你……”“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你帮帮他,行不行?
”“他现在……他真的只有你了……”我垂下眼,看着她抓住我的那只手。真是天大的笑话。
那个用一张支票打发我,让我净身出户滚出顾家的人,现在正抓着我的手,求我别走。
“顾夫人。”我伸出另一只手,一根一根地,掰开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冰凉,还在发抖。
“您忘了。”我抽出自己的手腕,上面留下了几道清晰的红痕。“我和顾霆霆,已经离婚了。
”“他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后退一步,与她拉开距离,然后转身走向电梯口。
身后,是她气急败坏的咒骂。“林浅!你这个白眼狼!你不得好死!你会有报应的!
”电梯门打开,我走进去。金属门缓缓合上,将她的声音和那张扭曲的脸,彻底隔绝。报应。
我的报应,三年前就开始了。现在,终于结束了。轮到他们了。……回到家,
客厅的落地灯亮着一圈温暖的光。裴时宴坐在沙发上,膝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
显然是在等我。听见开门声,他合上书,站了起来。“去哪了?”“医院。”我换了鞋,
没打算瞒他,“去看了看顾霆琛。”裴时宴走向我的脚步顿了一下,随即恢复如常,
走到我面前。“他还好吗?”“死不了。”我走到吧台,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水,拧开,
直接灌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压住了心底那点烦躁。“他妈妈也在,
”我放下水瓶,“求我帮忙。”“你怎么回答的?”裴时“宴问。“我拒绝了。
”**在吧台上,转头看向他。“裴时宴,我是不是很冷血?”他走过来,
拿起我放在台面上的水瓶,又取了个玻璃杯,倒了半杯水递给我。他的手指温热,
不经意地碰了碰我的指尖。“不。”他注视着我,目光认真。“你只是在保护自己。
”“浅浅,你不必对任何人感到愧疚。”“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他的话,
驱散了从医院带回来的最后一丝阴霾。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在我最狼狈时出现,
给了我一份体面,一个庇护所的男人。一个念头,在此刻变得无比清晰。“裴时宴。
能够找到一部像《净身出户?转身嫁他千亿死对头!》这样的小说真是我的幸运,它的情节设计精妙绝伦,人物塑造生动有趣,特别是男女主角的爱情线,让人回味无穷。
《净身出户?转身嫁他千亿死对头!》中的裴时宴顾霆琛林浅具有鲜明的个性,让人难以忘记。剧情中的其他角色也各有特色,使人记忆犹新。
裴时宴顾霆琛林浅在《净身出户?转身嫁他千亿死对头!》中的表现令人难以忘记。他独特的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让我深深地被吸引。在后续的剧情中,他的发展让人期待。
作者下无神的《净身出户?转身嫁他千亿死对头!》展现了他老辣的文笔和成熟的故事构思,让人欲罢不能。这是一本值得书虫们强烈推荐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