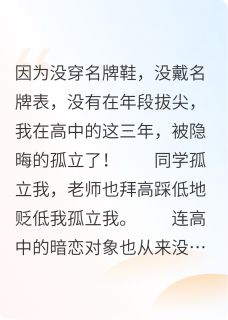我被绑在柱子上,麻绳勒进皮肉里,渗出血珠。眼睁睁看着我哥被按在刑台上,
侯爷举着酒杯,笑着看刽子手落下第一刀。血溅在我脸上,是烫的。奶娘把我塞进菜窖时,
我咬碎了牙。三天后被拖出来,发卖到侯府做丫鬟。夜里给沈云舒洗脚,她踩着我的手背,
问:“你爹的血,是不是比这盆里的水还红?”我盯着她珍珠手链,
那是用我家抄没的珠子穿的。该先扯断它,还是先咬断她的喉咙?1我爹是罪臣。抄家那天,
我被绑在柱子上,眼睁睁看着我哥被一刀刀剐了。奶娘把我塞进菜窖,塞给我半块窝头。
还有半张布告,上面"通敌"两个字被圈得猩红。"记着这印,是靖远侯府的。
"她双眼通红着看着我,指甲掐进我肉里。"窖里黑得像泼了墨,我抱着布告发抖。
外面传来奶娘的惨叫,还有兵卒的笑。我咬着袖子哭,眼泪把布告洇得更皱。
三天后被拖出来,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老太监捏着圣旨念:"罚没入靖远侯府为奴。
"我被俩婆子推上破马车,车轱辘吱呀响。停在侯府门口时,沈云舒早等着了。
穿宝蓝绫罗裙,头上珠钗晃得人眼晕。"你就是姜柔?"她歪头打量我,像看脏东西。
我刚要屈膝,她手里的茶盏"啪"地掉了,碎片溅到我脚边,滚烫得我脚一缩。"晦气。
"她往后退半步,用帕子捂鼻子。"我爹说。"她声音甜得发腻,眼神却淬着冰。
"你爹的血染红了刑场的石头。""你这双沾过他家血的脚,别脏了我家的地。
"周围丫鬟憋着笑,我攥紧袖中的布告,布告边角硌得手心疼。"回大**,奴婢会小心。
"我低着头。"你也配叫奴婢?"她拔高声音。"去柴房待着,明日抄《女诫》,
抄到认清自己身份为止。"翠儿搡我一把:"走快点,别磨蹭!"穿过回廊时,
听见婆子们在假山后嘀咕。"当年姜将军被斩,就是侯爷监的刑。""这丫头活不长,
大**要折腾她呢。"我脚步没停,耳朵却像被堵住了。路过书房,瞥见匾额上的印,
和布告上的残印,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心里一揪,脚步更快了。柴房比猪圈还小,
堆着发霉的干草。翠儿丢个破蒲团:"就睡这儿,卯时叫你。"她摔门出去,
我赶紧摸出布告。借着窗棂的月光,我一遍遍比对那印,越看越心惊,指尖抖得厉害。
外面更夫敲梆子,一下下敲在心上。第二日天没亮,翠儿就踹门进来。
丢给我套粗布衣裳:"赶紧换,去给大**抄书!"书房里熏着檀香,
沈云舒斜倚在贵妃榻上。"笔墨在桌上。"她翻着诗集,眼皮都没抬。"抄《女诫》,十遍。
"我拿起笔,手抖得厉害,第一笔就写歪了,像条蚯蚓,丑得我自己都难堪。
沈云舒"嗤"地笑出声:"草窝里长的就是笨。"我咬着牙往下写,故意写得更丑,
就是要跟她反着来。她看烦了,挥挥手:"去厨房劈柴。""劈够一担才准吃饭。
"斧头沉得像铁块,劈到第五根时,手开始抖,血顺着指缝滴在柴火上,红得发黑。
张妈摘菜时叹:"姑娘,服个软吧。"我没说话,接着劈。沈云舒说,劈不够一担不许吃饭。
肩膀压得生疼,虎口裂了口子,渗着血。天黑时,我拖着柴去见她。她正坐在灯下描眉,
镜子里的影子像画里的人。"放那儿吧。"她头也没抬。"明日去扫花园的落叶。
"我刚要退,她忽然又说:"听说你爹是状元?""怎么教出你这么笨的东西。
"我脚步顿了顿,没回头。有些仇不能说,只能记着。像记着那枚印。回柴房后,
我摸出布告再看,月光照得那残印越发清晰。忽然懂了奶娘的话,活下去不只是活着。
窗外梆子敲了三下,我把布告藏回袖中。明天还要扫落叶,得养足精神。报仇的路长着呢,
我得好好活着。鸡叫头遍时,我就醒了,起身往屋外走去。路过花园,看见落叶铺了一地,
像层厚厚的毯。我拿起扫帚,一下下扫着,心里数着数。一片,两片,
三片……就像数着那些该算的账。2我在侯府的日子,像踩在薄冰上。一步都不敢错。
上个月洒扫时,一片落叶飘进了沈云舒的茶盏她罚我跪在雪地里三个时辰,膝盖冻得青紫。
还有一次,给老夫人捶背时力道重了些。管家婆用藤条抽了我十下,胳膊肿得抬不起来。
听说世子沈逸飞今日回府。那个十八岁就成了探花的少年,朝堂里出了名的清流。
也是我在这深宅里,唯一能抓住的浮木。辰时刚过,我端着茶盘往书房去。手指因为用力,
指节泛白。脚步放得极轻,心却跳得像要撞碎肋骨。书房外,沈云舒的笑声先传了出来。
“哥哥这次回来,可要多陪我几日。”“课业要紧。”沈逸飞的声音响起来,
清润得像玉石相击。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那扇雕花木门。茶盘在手里故意晃了晃。
“哐当”墨砚应声落地,浓黑的墨汁溅上沈逸飞的月白长衫。“放肆!
”沈云舒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我立刻跪下,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奴婢该死。
”眼角的余光里,沈逸飞弯腰去捡墨砚。他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
“无妨。”他开口,语气听不出喜怒。沈云舒却不依不饶,抬脚就往我身上踹。“贱婢!
定是故意的!想攀高枝想疯了!”我咬紧牙关,没躲。预想中的疼痛没落下。
沈逸飞抓住了沈云舒的手腕。“妹妹。”他的声音沉了沉,“不过是打翻东西,何必动气。
”沈云舒挣了挣,没挣开。“哥哥!她是罪臣之女!当年她家被抄,咱家也有份!
”她尖叫着,声音尖利得刺耳,“你护着她?就不怕她报复?”我的心猛地一缩。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的底细。沈逸飞松开手,淡淡道:“她如今是侯府的丫鬟,
按规矩罚月钱便是。”“我不!”沈云舒忽然扬手。清脆的巴掌声在书房响起。
我的脸颊**辣地疼,像是被火烧。“贱婢敢勾引世子,就该打!”她喘着气,
眼睛红得像兔子。我捂着脸抬头,正撞上沈逸飞的目光。他眉头紧锁,
眼底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怒意。“沈云舒!”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喊她,“太过火了!
”沈云舒愣住了,随即哇地哭出来。“哥哥为了个贱婢凶我!我要告诉母亲去!
让母亲撕烂她的嘴!”她跺着脚跑了出去,裙摆扫过门槛时带起一阵风。
书房里只剩我们两人。空气静得可怕,连窗外的鸟鸣都消失了。沈逸飞蹲下身,
递过来一方绣着竹纹的手帕。“来,擦擦。”我没接,重新低下头。“谢世子,奴婢不敢。
”他的手顿在半空,片刻后收了回去。“你叫姜柔?”“是。”“父亲旧案,你可知晓内情?
”我的心猛地提到嗓子眼,后背瞬间沁出冷汗。他果然知道。我攥紧了衣袖,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奴婢不知。”声音稳得连自己都惊讶。沈逸飞沉默了片刻,
书房里只有漏壶滴水的声音。“起来吧,地上凉。”我依言站起,垂着眼不敢看他,
睫毛却控制不住地颤抖。他忽然轻笑一声,打破了沉默。“胆子倒是不小,敢在我面前装傻。
”我浑身一僵,像被施了定身咒。“世子说笑了。”“那日抄家,你藏在假山后,我看见了。
”轰,血液瞬间冲上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我猛地抬头看他。他嘴角噙着笑,
眼神却锐利如刀,仿佛能穿透我的皮囊。“你父亲留的那封信,藏哪儿了?
”我的后背沁出冷汗,浸湿了粗布衣衫。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奴婢……”“放心。
”他打断我,语气忽然温和下来,“我与你父亲,曾有一面之缘。”他站起身,
走到窗边推开半扇窗。风灌进来,吹动他的衣袍。“他是个好官。”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
少年的肩膀已经有了成年人的宽厚。“世子……”“信若在你手上,”他回头看我,
目光温和得像春日阳光,“或许,我能帮你。”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乱了。
他是侯府的世子,是敌人的儿子。却要帮我翻案?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吗?
3沈逸飞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不必急着答复。”他拿起桌上的《史记》,“想通了,
来找我。”我福了福身,退出书房。走到回廊时,正撞见沈云舒带着管家婆过来。她叉着腰,
下巴抬得老高。“就是她!把她拖去柴房,饿三天三夜!”管家婆伸手来抓我的胳膊。
“等等。”沈逸飞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她是我留着伺候笔墨的,谁敢动?”沈云舒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哥哥!
你怎么能……”“下去。”沈逸飞的语气冷了下来。管家婆讪讪地缩回手,
拉着还在跺脚的沈云舒走了。沈云舒走前,狠狠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不知该进还是该退。沈逸飞走到我面前,阳光落在他脸上,
少年的眉眼清澈明亮。“往后,在侯府,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风吹过回廊,
卷起几片落叶。我忽然觉得,这薄冰之下,或许真的藏着暖流。回到杂役房时,
几个丫鬟正凑在一起嚼舌根。见我进来,她们立刻噤声,眼神却像针一样扎过来。
其中一个叫春桃的,曾因偷拿库房的丝线嫁祸给我。若非当时老夫人要抄经祈福,
我怕是早被发卖了。“哟,这不是攀上高枝的姜柔吗?”春桃阴阳怪气地开口。我没理她,
径直走向自己的床铺。那是个靠窗的角落,被褥薄得能摸到棉絮。刚放下手里的空茶盘,
春桃突然撞过来。我的额头磕在床柱上,疼得眼冒金星。“走路不长眼啊?”她恶人先告状。
我捂着额头抬头,看见她袖口露出半块玉佩。那是去年沈云舒丢失的生辰礼,
当时所有下人都被罚跪搜查。原来在她这儿。春桃见我盯着她的袖口,慌忙把胳膊背到身后。
“看什么看!再看挖了你的眼!”我收回目光,默默坐到床沿。有些账,不急着算。
傍晚时分,有人来传话。说世子让我去他的书房伺候晚膳。走到月亮门时,
撞见两个小厮在搬花盆。见我经过,其中一个故意把花盆往我这边挪。
瓷盆边缘擦过我的手背,划出一道血痕。“对不住啊姜柔姑娘。”他假惺惺地道歉,
眼里满是戏谑。这是沈云舒身边最得力的小厮,名叫来福。我盯着渗血的伤口,
忽然想起沈逸飞说的话。“无妨。”我轻轻说,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他们耳中。
来福愣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我敢回话。我没再看他们,径直穿过月亮门。书房里点着安神香,
沈逸飞正坐在灯下看书。听到脚步声,他抬头看过来。目光落在我手背上时,眉头微微蹙起。
“怎么弄的?”“回世子,不小心刮的。”他放下书卷,起身从抽屉里拿出药瓶。“过来。
”我迟疑着走过去,他已经握住了我的手腕。指尖的温度透过粗布传来,烫得我心尖发颤。
“在侯府,不必事事忍让。”他一边涂药一边说,“有我在。”药汁凉丝丝的,
却奇异地压下了灼痛感。窗外的月光漫进来,落在他低垂的眼睫上。我忽然想,
或许真的可以信他一次。4进侯府三个月。我活得像阴沟里的苔藓。见不得光,
还得防着随时被人踩死。二夫人的眼线,从早到晚黏在我身后。走路带风的周嬷嬷,
眼睛像淬了冰的钩子。稍不留神,就能被她挑出错处。父亲的案子,更是碰不得的雷。
前几日问洒扫的老仆,他手里的扫帚都吓掉了脸白得像纸,摇头摇得像拨浪鼓。想查下去,
必须混进人堆里。“管家婆子,后厨缺人吗?”我堵在月亮门口。
她嚼着瓜子斜睨我:“你这细胳膊细腿,劈柴都嫌费劲。”“我能洗碗,能择菜。
”我垂下眼,“只求管顿饭。”她啐了口:“贱骨头,去吧。”后厨油烟重,人也杂。
夜里收拾碗筷时,老仆们爱扎堆唠嗑。这是我唯一能钻的空子。第一晚,
净听他们说谁偷了块肉,谁藏了个馒头。第二晚,有人提到三年前的冬天。“那年腊月,
姜家……”话没说完,就被人捂住了嘴。“活腻了?敢提那茬!”我攥着抹布的手,泛了白。
第三晚,我故意磨蹭到最后,躲在堆柴的角落。寒风从墙缝钻进来,冻得我发抖。
两个烧火的老妈子没走,蹲在灶边烤火。“你还记得不,侯爷当年……”“小声点!
”“怕啥,这时候连耗子都睡了。”另一个压低声音,“我亲眼见的,
侯爷把姜家那个红木箱子,锁进书房暗格里了。”心脏像被狠狠攥住。呼吸一乱,
脚边的柴禾哗啦响了一声。“谁在那儿?”我转身就跑。刚冲过月亮门,迎面撞上个人。
是周嬷嬷。她肥硕的身子挡着路,三角眼瞪得溜圆。“好啊姜柔!深更半夜不回房,
在这儿鬼鬼祟祟做什么?”我后背沁出冷汗。“夫人丢了支蕾丝银钗,”周嬷嬷叉着腰,
“定是你这贼骨头偷的!搜!”两个小丫鬟扑上来。我站着没动。“搜吧。
”她们把我身上摸了个遍,连补丁缝里都翻了。啥都没有。周嬷嬷的脸,青一阵白一阵。
“定是藏起来了!”二夫人的声音突然炸响,她从树后走出来,珠钗乱颤,“在侯府偷东西,
当发卖到最低等的窑子里去,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我抬起头,直视着她。她脸上的粉,
因为生气簌簌往下掉,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像条发怒的老蛇。“夫人。”我的声音很稳。
“若搜不出赃物,便是您凭空污蔑。”二夫人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我的手都在颤:“反了你了!一个贱婢也敢顶嘴?来人,给我往死里打,
打到她招供为止!”“母亲。”沈逸飞的声音插了进来。他从月亮门走进来,
手里捏着支银钗,递到二夫人面前。“云舒妹妹的梳妆盒底层,找到了这个。
”二夫人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不……不可能!是云舒?”“妹妹说,看姜柔不顺眼,
想逗她玩玩。”沈逸飞语气平淡,眼神却扫过周嬷嬷,“让母亲误会了。
”周嬷嬷“噗通”跪了下去,额头直往地上磕。二夫人的脸,红得像要滴血。她死死盯着我,
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算你命大!”她咬着牙,字字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给我滚!再让我在后厨看见你,打断你的腿!”我没动。沈逸飞瞥了我一眼:“还不快走。
”我转身时,听见二夫人在身后尖叫:“废物!连个贱婢都治不了,留你们有何用!
”回到杂役房,我才发现手心全是汗。沈逸飞不知何时跟了来。“为何帮我?”我问他。
他靠在门框上,月光照着他半边脸。“我只是不想母亲被妹妹当枪使。”顿了顿,
他低声道:“别在后厨待了。”“二夫人眼里,你已经是根拔不掉的刺了。”我知道。
今晚这出戏,让她的恨意摆到了明面上。可我不能停。书房暗格。父亲的东西一定在那儿。
我摸了摸袖袋里的半截旧钥匙,那是父亲留给我的,说是能开家里最要紧的箱子。或许,
很快就能用上了。窗外的风,更冷了。但我心里的火,却烧得更旺。
5二夫人的眼线撤了大半。但我知道,这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把戏。
沈逸飞那日留下的《史记》,还压在我枕下。书页里夹着的字条,
“小心暗箭”四个字墨迹已干。他到底是敌是友?我摸出袖中那张皱巴巴的纸,
是前几日在柴房墙根拓下的。几个模糊的刻字,分明是密道入口的标记,
这是我眼下唯一的筹码。“世子在吗?”我站在书房外叩门。沈逸飞开门时,
眼里闪过一丝惊讶。“有事?”他侧身让我进去。“来还书。”我把《史记》递过去。
他接过时,指尖不经意触到我的手,两人都像被烫到似的缩回。“还有这个。
”我将拓纸摊开在桌上。他低头的瞬间,瞳孔骤然收缩。“这是……密道的记号?
”“世子若真想查清当年的事。”“我有能进去的线索。”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沈逸飞沉默了许久。指节捏得发白,指腹摩挲着拓纸边缘。突然,
他转身从书架暗格取出个卷轴。摊开一看,竟是姜家老宅的地图。
“我父亲临终前攥着这图说。”“姜家是被冤枉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下。
原来他早就知道内情。“为何现在才……”“因为一直没找到实证。”他打断我,
“侯爷书房的暗格,我试过三次都没能打开。”我攥紧了拓纸边角。“密道能直通书房内侧。
”“你怎么如此确定?”他挑眉看我。“这是我父亲亲手画的图记。”沈逸飞的眼神亮起来,
像寒夜里燃着的星火。“谁在里面鬼鬼祟祟?”沈云舒的声音突然从门外炸响。她扶着门框,
脸色又惊又怒。“哥哥你竟和这罪女勾结!”我心头一沉,最担心的事还是来了。
沈逸飞猛地挡在我身前。“不关她的事,是我找她来的。”“我这就去告诉父亲!
”沈云舒转身就跑。裙摆扫过门槛,带起一阵风。沈逸飞的拳头在身侧捏得死紧。
“你先回房,这里我来处理。”我站着没动。“侯爷若问起,就说是我胁迫你。
”他回头看我,嘴角竟浮出丝笑意。“姜柔,你当我是怕事的懦夫?
”祠堂的钟声突然急促响起,连敲三下,是府中急召的信号。沈逸飞整了整衣襟。“该来的,
躲不掉。”我看着他走向正厅的背影,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那句话。“这世上,
总有人把公道看得比命重。”正厅的呵斥声隔着庭院传过来。“你可知错?
”侯爷的怒吼震得窗纸发颤。“儿子不知错。”沈逸飞的声音异常平静。
“那罪女的话你也信?她可是奸臣之女!”“父亲,当年姜家旧案疑点重重,难道不该查?
”“住口!”案几被拍得巨响,“沈家绝不能卷进这浑水!否则满门难保!
”“若连公道都不敢求,苟活百年又有何意义?”沈逸飞的声音掷地有声,带着股执拗。
接着是瓷器碎裂的脆响。我躲在回廊柱后偷瞄,看见沈逸飞被两个家丁死死按住。
侯爷指着他,气得浑身发抖。“反了!真是反了!”“把他关进柴房,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沈云舒站在一旁。嘴角勾着掩不住的得意。她的视线扫过来时,
作者矢墨千钧的文笔细腻而出色,《柔中刃》展现了他独特的风格。故事的剧情紧凑,扣人心弦,读完之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令人喜爱的作品,我对作者的才华感到十分钦佩。
《柔中刃》这本书设定新奇,切入点巧妙,文中的主人公沈逸飞沈云舒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作者矢墨千钧通过精心构建的情节,揭示了主角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故事。这是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值得一读。
《柔中刃》的剧情十分精彩。沈逸飞沈云舒的性格特点和剧情发展让人意想不到,令人期待后续的发展。
总之,我对《柔中刃》这本书的点评可以用以下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有趣、真挚动人、精巧结构、环环相扣、新奇设定、细腻文笔、美好感受。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佳作,值得广大读者品味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