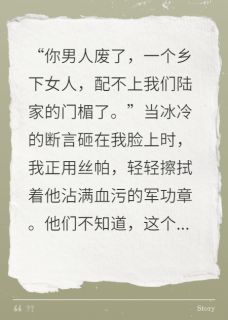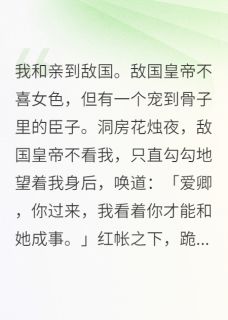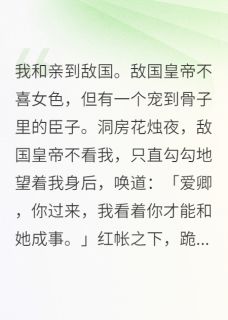新婚夜被休,一纸休书逼她坠入地狱,却不知她本是王血遗脉,翻手掌府,覆手夺权,
令负心人跪地求悔!1新婚夜,她被夫君一纸休书细雪飘得没完,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
冻得人指尖发僵。红烛只剩三分之一,斜斜地挂着泪,快熄了。沈梨音仍坐在喜床边,
手心里捏着那枚圆润的红玉镯,已等了整整三个时辰。她的嫁衣是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绣了一个多月,袖口藏着暗纹,内衬绣着“萧庭渊”三个小字——她以为她嫁的,
是一个能携手一生的夫君。她从来都不贪奢,只想有个名分,有个能喊夫君的男人,
再不被人指着鼻子说是妾女命贱。可这王府的门槛,她是跪着进来的。门吱呀一响,
风雪中有人踏进来,脚步干脆。不是下人,是他——萧庭渊。他穿着素灰袍子,
身上没一丝喜气,眼神冷得像雪地的霜。他不看她,只淡淡扫了一眼她身上的嫁衣。
“沈梨音。”他语气淡漠,“这桩婚事本不该是你的。”沈梨音下意识握紧了玉镯,
脸上的笑意还未散去。“王爷说笑了,臣妾今日拜堂,礼成贴录,已是王妃。”“王妃?
”萧庭渊忽地笑了声,从袖中抽出一张纸,扔到她脚下。“这是休书。”沈梨音怔住。
他道:“你虽是沈家女,可你母出低贱,出身不洁,这王府,不收这样的王妃。
”纸张在风中颤抖,烛火映着那歪歪扭扭的几个字:休沈氏,因其品行不端、德行有亏。
沈梨音没吭声,只是低头将那纸捡起来,捏紧了。“新婚夜就休妻,王爷果然雷厉风行。
”“你若识趣,明日一早便自己打点,搬去南院。”说罢,萧庭渊转身走了,毫不迟疑。
门合上了,风也小了,只剩一地冷清。沈梨音站在喜床边,望着门口良久,才缓缓坐下,
将那纸休书折成一条条细线似的条缝,塞进袖口。烛火熄灭前,她用尽力气笑了一下。
**第二天早晨,王府内院,传话嬷嬷带人来收拾东西,连声招呼都未打,
直接将她的嫁衣、首饰全数取走,只留下那套被泼了茶水的旧衣。“沈氏,请随我们去南院。
”她换了身灰布衣裙,鞋子却还是那双绣着鸳鸯的红鞋,干净得像是与这地界格格不入。
府里的奴仆交头接耳:“不是说她是沈家嫡女么?怎么这么轻贱就被休了?”“哎哟你傻啊,
那是妾女,听说还是被沈大夫人踢出来的野种呢。”“可惜那脸生得好看,
王爷怕是吃完就甩了。”沈梨音没吭声,只低头走着,眼帘垂得低低的,连睫毛都湿了。
她不想争,也不想哭。哭有用么?她娘就是哭死在绣坊的。南院极冷清,
冬日没人愿意来这边伺候,她进门后,房中只点了一炉冷炭,几乎冻死人。
她自己动手收拾屋子,从墙角找出旧被褥,又翻出针线包,一根一根整理绣针。她要活着。
她不能倒。哪怕冷、哪怕饿、哪怕被当作尘埃踢来踢去,她也得活下去。
晚饭是个看起来十五六岁的丫头送来的,名叫阿竹,眼神机灵,说是魏嬷嬷派她来的。
“魏嬷嬷说,姑娘若不想死,就别再等王爷。王爷娶的是苏家**,不是你。
”沈梨音轻笑了一声:“我若想等他,还能坐在这儿吃饭?”阿竹愣了一下:“姑娘不生气?
”“气什么?我本就是妾女,连父亲都不要的人,又何必指望一个陌生男人?
”她夹了一筷子饭,淡声道:“你回去告诉魏嬷嬷,我不死,也不走。我要活得比谁都久,
看他们一个个怎么跪着来求我。”阿竹看着她,忽然红了眼。“姑娘若能活得好,
奴婢愿跟着。”沈梨音终于抬起头,眼中不再有一点柔软。“那你就睁大眼睛看着,
从今天起,我不再求任何人了。”屋外风雪不停,寒冷侵骨,
她却慢慢地在炉火前绣起了第一张帕子。针尖破了指尖,血一滴滴渗进白布,
像极了她此刻的心。**她不知道的是,在王府的另一头,萧庭渊站在书房窗前,
望着那片雪地上孤零零的红鞋印,神色一瞬怔住。可他没转身,只将窗帘拉得更紧。
——沈梨音?他从未想过要娶她。然而谁也没料到,那一纸休书,会换来他此后多年,
跪地求悔的命运。2冷院绣娘,她不肯低头南院的日子,与其说是王府一隅,
不如说像个冷宫。柴房改的屋,屋顶常年漏风,冬雪落得深了,屋角便是厚厚一层霜。
沈梨音披着薄衫,蜷在小炕上,身旁是她绣到半夜的帕子。炉子火灭得早,她舍不得炭,
便只靠两层旧被熬夜。指尖肿了两根,昨日绣那片“连理枝”时被针划出血,红线渗进去,
却愈发逼真。阿竹悄悄进来,捧了一碗热粥,一块薄豆饼藏在袖口里:“姑娘,
嬷嬷叫我送来。那苏家人怕您死了坏了名声,总还得给口吃的。”沈梨音接过粥,抿了一口,
粥里掺了糠,难咽得很。她轻声问:“正妃回府了吗?”“昨晚回的,一身华服,
坐着八人大轿进府,比姑娘您成亲那天排场大多了。”沈梨音却笑了:“也好。
若我还坐在那个位置,只怕要日日受她磋磨,落得更难堪。
”阿竹撇嘴:“可姑娘才是嫁进来的,那位苏**只是躲了病,怎的就能名正言顺回来?
”沈梨音没答,只翻出那块刚绣完的帕子递给阿竹:“你把这个交给魏嬷嬷,
说我想换点炭火和灯油。”阿竹接过去时,眼神变了变。那是一块三寸绣帕,
竟绣了整整两只寒梅,花骨朵含着霜,枝条微颤。更妙的是一行暗纹字,藏在底角绣影之下。
阿竹小声问:“姑娘这手艺,是往常练的?”沈梨音收起针盒,淡道:“绣坊里讨饭的本事。
若没这点东西,只怕早死在那年雪夜。”阿竹顿了一下,忽然眼圈红了。沈梨音不抬头,
继续剪线头:“你告诉魏嬷嬷,我还想要笔墨纸砚。”“绣帕就能换?”阿竹忍不住。
“换不来,那就再绣。”沈梨音的声音平静得像秋水无波:“我不会一直在这屋里,
得动动了。”**魏嬷嬷托人看过帕子后,只说了一句:“这丫头,比她娘还利落。”当夜,
南院就送来了三包上好的松木炭、一盏亮油灯,还有一套干净的棉衣。沈梨音洗了头,
换了衣,坐在炭火旁重新打磨绣架。她要做的,不只是绣帕子,
她要把王府的钱粮账本图样全部复制下来。她从前在沈家短暂学过记账,
后来在绣坊又专做定制图录,如今早就熟得不能再熟。王府这地方,看着规整,
其实漏洞百出。她刚进来的那几日,就发现了:府中二院账本分开记,
内务房明里听苏家人吩咐,暗地却由大夫人旧派把持。每日饭食短斤少两不说,
连她吃的粥里都掺了碎糠。她一一记下。再往深里,
她听说王府外庄送来的田赋粮折数也不对账,文书与实物分出两批,
送上的是四两银子一斤的顶级贡米,可厨房用的却是两文钱的陈粮。她不吭声,
只是一边绣着帕子,一边将所有出入数目画在帛上。那些针线间藏着的,不止是寒梅与飞鹤,
更是沈梨音未来翻身的路。魏嬷嬷第二次来看她时,站在门口看了许久。屋里没有多余装饰,
只有一架香案,一盏油灯,灯下那女子身披青布长衫,乌发散着,针落如风。“沈姑娘。
”魏嬷嬷终于开口,“你可知,你若再这样走下去,便再无回头。”沈梨音抬起头,
眼中一丝温度也无。“我嫁进王府那一刻,便已没得回头。”魏嬷嬷沉默片刻,轻轻点头。
“你母亲当年,也说过同样的话。”沈梨音心头一震。“你还记得她么?”她的声音微颤。
“她是我带进来的。进门头三年,柔顺无比。第四年开始,渐渐懂了府中人情,第五年,
她死了。”魏嬷嬷声音很轻,却沉如铁石,“你若真是她女儿,那你该明白——活下来的,
才有资格算账。”沈梨音轻轻点头。“我不算账,我要掌账。”**这一晚,
沈梨音在炭火边绣了一夜。指尖破了三处,血染了雪白绣布。她却一针不落,一线不颤,
眼中只有一幅图景:王府正厅,众人面前,她穿着亲手绣的锦袍,站在那苏婉宁前,
将她亲手缝过的帕子还给她。不是认输,是让她尝尝什么叫反噬之痛。她不再等王爷回头,
不再信一个男人的怜悯。从今往后,所有人都该明白——她沈梨音,不是来求活路的,
是来取命的。3府宴泼酒,她转身绣出反击冬尽春寒,王府初一设宴,
正妃苏婉宁归府已有五日,终于坐稳中馈之位,开口设宴请府中诸妾及内眷齐聚,名曰迎春,
实则敲山震虎。沈梨音本不该受邀,但魏嬷嬷亲自捧着请帖来到了南院,
言辞恭敬:“姑娘既是成过亲的,名义上仍是王府之人,正妃发了请帖,您不去,便是驳面。
”阿竹气不过:“这分明是设局!前几天才把我们关在南院,如今就请上席?
她分明是想让大家看看您如今落魄的样子!”沈梨音放下针线,轻描淡写道:“不入虎穴,
焉得虎皮?”她换了身清蓝色衣裙,原是绣坊打包时偷藏的一件半成品,底料是旧锦,
却被她重新缝制过,一整幅素白山水自腰间蜿蜒而上,衬得她身姿清瘦挺拔。她不戴首饰,
只在鬓边别了一支细银簪,头也不低,眼也不垂,走进正厅时,众人霎时寂静。
苏婉宁坐在主位,一身金线云锦,比当朝贵妃还雍容,身旁坐着萧庭渊,他淡着脸,
抬眼望了沈梨音一眼,没说话。厅中众人交头接耳:“这不是那位休了的沈氏?
”“居然还有脸来?听说如今睡柴房,靠绣帕子换炭火。”“也真是厚脸皮。
”沈梨音神情未变,只在席前行了一礼:“正妃召我,梨音不敢不来。
”苏婉宁微笑:“妹妹久居南院,怕是孤寂,这些日子也受了冷落,
今日让你与众姐妹叙叙旧。”她话未说完,身侧花婵儿便扬手唤道:“丫鬟,上茶!
”阿竹走上前去端茶,刚迈一步,忽听“哗啦”一声,整杯红茶泼了出去,
直直洒在沈梨音怀里。众人惊呼,花婵儿轻掩红唇:“哎呀,怎么手一滑……沈妹妹,
你这布料怕是便宜货,褪色么?”苏婉宁唇角笑意淡淡,不咸不淡:“婵儿毕竟年幼鲁莽,
妹妹莫怪。”沈梨音低头看着湿透的锦衣,茶水在素白山水上晕出一片不规则痕迹,
像是污渍,更像鲜血。她缓缓将双袖挽起,将那湿漉漉的前襟抖平,
抬头轻声道:“是我自幼穿不得红茶,婵儿妹妹恐怕早就知晓。”花婵儿脸一僵。
沈梨音往前走了两步,走到宴席中央,朝众人略一福身:“衣裳既污,既失体统,
我在这府中也当不起‘王妃’名头,不如众人今日便看个明白——沈梨音,
到底值不值得一纸休书。”她说完,从怀中取出一方白帕,略一甩开,平摊在手中。
帕子一面山水流云,竟是与她裙上图案一脉相承,针法更细,配色更沉稳,
一眼便知出自名手。她扬手递给苏婉宁:“此乃我一夜绣成,赠正妃作赏。愿往后岁月平稳,
莫再以泼茶手段迎宾送客。”众人面面相觑,苏婉宁脸色微变。
那帕子实则绣的是“云锁高台”,针脚翻转之间,山中藏刃,云里有尖,若不细看,
只觉清雅,再细看,却寒意逼人。萧庭渊忽地开口:“此帕出自你手?
”沈梨音淡然道:“正是。”他神色微微一动,却未言语。
苏婉宁强笑着接过:“妹妹手艺倒是进了。”沈梨音回身,
盈盈一礼:“那便不打扰正妃清宴,梨音失陪。”众人眼见她离席,竟无一人敢再笑声,
只有那刺目的红茶痕,在她背影的裙上,晕成一朵梅花,冷冽、凛冽、带刺。**傍晚,
南院炉火炽热,屋内却静悄悄。阿竹端来一盏姜汤,小声问:“姑娘今儿……怎么不怕了?
”沈梨音坐在绣架前,手中丝线未停,只轻声回道:“怕过一次,就不会再怕第二次。
”她将刚开始绣的新布平铺,拈起银线,开始勾勒苏婉宁的画像。眉眼间不多一分不减,
唯独在眼尾处,落下了一针细若游丝的血红。她不再只是那个任人羞辱的替嫁之女。
她在南院寒风中绣下的,不只是花鸟山水,更是她的仇人,她的刀,她的命。下一针落下时,
她唇角一弯:“正妃不喜见血,那我就让她先看一针,再尝一口。”4故人来,
她的心动不再纯粹入春后连绵细雨不断,王府后门通往绣坊的巷子泥泞不堪,
阿竹撑着伞在屋檐下探头,嘴里嘟囔:“姑娘,您不去看看?金三娘那边派人来请您,
说是今日有贵客到。”沈梨音在窗前理着一匹新进的银线,神色平淡:“贵客与我无关。
”阿竹却笑着将一封信放在她绣架上:“那贵客送了这个,还说是‘梨音表妹’。
”她手一顿,针线歪了一分。一纸墨迹,行书洒脱,不带任何官家规矩,却一眼熟稔。
她认得这个笔迹,甚至比认得自己还熟。顾清砚。沈家远房表兄,亦是她幼年时唯一的庇护。
他曾说她是落雪里的一枝梅,他会为她挡尽风寒。后来她娘死了,她被赶出沈家,
他远赴京城,从此再无音信。她以为早忘了他,却没想到,心口竟还会因为这个名字,
起一丝波澜。她收起信,不作声,半晌后才起身换衣:“走吧。
”**金绣坊是京城第一绣坊,背靠金三娘,表面经营绣品,
《弃妃封主,王爷他悔断肠》结构精巧,环环相扣。配角的形象栩栩如生,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身份和情感共鸣。作者一点儿意思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巧妙的安排,展现了多样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转折,使整个故事生动有趣。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
一点儿意思的文笔犀利,故事情节吸引人,让《弃妃封主,王爷他悔断肠》成为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弃妃封主,王爷他悔断肠》这本书展现了作者一点儿意思深厚的情感和艺术才华。他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独特的叙事结构,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故事。主角沈梨音苏婉宁的形象鲜活而真实,她的勇气和智慧令人钦佩。整个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每一个转折都让人意想不到。配角们的存在丰富了故事的层次和张力,他们各自有着引人注目的特点和命运。这是一本令人沉浸其中的佳作,读者会在阅读中体验到无尽的情感和思考的启示。
沈梨音苏婉宁在《弃妃封主,王爷他悔断肠》中的表现令人难以忘记。他独特的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让我深深地被吸引。在后续的剧情中,他的发展让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