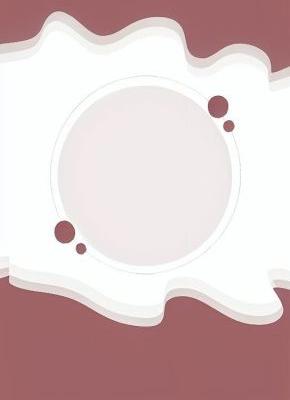那年我正蹲在司棋处的角落里临摹棋谱。听见管事嬷嬷的鞋跟磕在青石板上的脆响。
一巴掌扇得我嘴角淌血:「死丫头,还敢私藏先帝棋谱?」1棋局未终父亲是前朝太傅,
教过三朝皇子下棋。三年前,三千羽林军踏碎了太傅府的朱门,父亲戴着枷锁被押走时,
我分明看见他对着棋盘上未终的棋局,喉间滚出一声「悔」。
如今我成了司棋处最低等的宫女苏瑾,每天的活计是给各宫娘娘磨墨研棋。
管事嬷嬷总说我是「罪臣之女」,分派的活计永远是最累的——可她们不知道,
我临摹的哪里是普通棋谱。那是当今圣上萧彻少年时的手迹,从十三岁到二十七岁,
整整十四年间的棋谱,我临摹了七十二遍。我知道他执黑子时爱走天元,落子极重,
墨痕会在宣纸背面洇出浅浅的圆。用白子时偏爱边角,指尖常沾着松烟墨,
偶尔会在棋盘左下角留下半枚指印。这些隐秘的习惯,
是我用三年时间从故纸堆里扒出来的钥匙。苏家三百口冤魂能不能睁眼,
全看这把钥匙能不能捅开那把锈死的锁。"中秋宫宴要摆棋宴,
"隔壁熨烫棋盒的小翠凑过来,手里还拿着块没吃完的桂花糕,"听说圣上要亲自下场,
跟英国公对弈呢。"中秋,是父亲的生辰,也是当年父亲带萧彻在太傅府的桂树下,
第一次下完一整局棋的日子。那天晚上我没睡,借着茅房窗棂透进来的月光,
把藏在床板下的碎银倒出来数。三个月的月钱,加上变卖母亲留给我的银簪子,
刚好够买通御膳房的小禄子。小禄子收了钱,塞给我一张揉皱的明黄色笺纸。
「圣上喝多了会走九曲回廊,那儿的青苔滑得很,前年就绊倒过两个公公。」
角落里堆着先帝御赐的白玉棋子,我数过,整整一百八十枚,枚枚通透如凝脂。父亲曾说,
这副棋子是太宗皇帝亲手打磨的,棋盘上每一道木纹都藏着兵甲阵图。
当年萧彻第一次赢了父亲,父亲就把这副棋子的「将」子赏了他。我选了枚最薄的白子,
揣在袖袋里。这枚玉子的边缘有道细痕,是我小时候摔在棋盘上磕的,
父亲总说这是「将星有瑕」。如今倒成了最适合碎给人看的。接下来的半个月,
我每天寅时就去九曲回廊候着。寅时的露水最重,能把青石板洇得透湿,
跟雨后的样子差不多。回廊转角有块凸起的青石板,雨后会渗出水珠,
我用草绳量过它的高度,刚好够让一个人「失足」时,能精准地摔在路过者的脚边。
摔碎棋子的角度得反复练习。太轻了惊不动圣驾,
太重了怕伤着自己——我这条命还得留着看仇人伏法。我找了块跟玉子差不多重的石子,
每天在回廊里练上百遍,直到能让石子落地时,既发出清脆的响声,又不会弹得太远。
膝盖上的淤青换了好几茬,最严重的一次肿得像个馒头,我就用艾草煮水敷着,
疼得咬着牙也不敢哼出声。管事嬷嬷见了,只当我是干活不小心摔的,还骂了句「丧门星」。
她不知道,我每摔一次,心里就亮堂一分——父亲教我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原来真要把自己逼到绝境才能懂。那天我蹲在回廊栏杆后,对着月光把棋子抛起来又接住。
玉子冰凉的触感透过掌心传来,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是小禄子,
他脸色惨白地塞给我个油纸包:「苏瑾,快跑!皇后娘娘要清点先帝遗物,
这棋子......"油纸包里是半块桃花酥,是父亲当年总给萧彻备着的。我捏着那酥饼,
忽然想起十三岁的萧彻穿着杏黄蟒纹常服,坐在我院子里的海棠树下,
把最后一块桃花酥分我一半:「苏瑾,等我当了皇帝,就让你爹做国师。」那时的他,
指尖还带着少年人的温热,说话时会有桂花糕的甜香从嘴角飘出来。我把桃花酥塞进怀里,
对着小禄子笑了笑。他不知道,我要的从来不是跑。苏家的冤屈像根毒刺扎在我心里三年,
如今终于找到拔刺的机会,就算拔的时候会剜掉一块肉,我也认了。八月十四的夜里,
我揣着那枚白玉棋子,在九曲回廊练到三更。露水打湿了我的单衣,冷得人直打哆嗦,
可每次听见远处更夫敲梆子,我都觉得父亲在棋盘那端,正等着我落下这关键一子。
月光落在回廊的青苔上,泛着冷幽幽的光。我握紧袖中的玉子,
忽然明白父亲那句「落子无悔」的真意——不是不悔,是没得选。就像现在的我,
明知往前走一步可能粉身碎骨,却连回头的资格都没有。我对着月亮举起棋子,
看玉子映出的寒光刺破夜色。这一局,我赌上苏家满门的性命,
总要让那些藏在棋盘后的鬼魅,见见天光。2玉碎惊龙我攥着那枚白玉棋子站在廊下,
听着远处宫宴的丝竹声,手心的汗把玉子浸得发滑。戌时三刻,小禄子在假山后学了声猫叫。
这是约定的信号——皇帝的銮驾已经过了金水桥。我赶紧往青石板上撒了把细沙,
这是从御花园的松树下筛的,沾了露水后滑得能让人站不住脚。我数着地砖上的裂纹,
心里默算着步数。萧彻走路的步幅是三尺七寸,
这是我从他批阅奏折时起身踱步的距离算出来的。三百六十块地砖,
他该在第三十二块时走到转角。脚步声越来越近,带着龙涎香的气息。我悄悄掀起眼皮,
看见明黄色的袍角从廊柱后露出来,金线绣的龙纹在灯光下闪着冷光。就是现在。
我猛地抬脚,借着细沙的滑劲往前踉跄两步,同时松开了攥着玉子的手。「啊!」
我故意喊得又惊又怯,身子顺势往侧面倒去——这个角度刚好能让我摔在皇帝三步之内,
既不会冲撞龙体,又能保证他看清地上的碎玉。「啪嚓」一声脆响,
白玉棋子在青石板上裂成三瓣。我趴在地上,用眼角的余光瞥见明黄色的袍角停住了。
"拖下去。"萧彻的声音比我想象中冷,像淬了冰的剑锋。三年的帝王生涯,
把当年那个会分我桃花酥的少年磨得只剩威严了。两个禁军立刻架住我的胳膊,
铁钳似的力道捏得我骨头疼。我知道不能慌,父亲教过「棋到险处需造势」,
现在就得把这场戏做足。「陛下饶命!」
「奴婢不是故意的……这是先帝的棋子......"我特意把「先帝」
两个字喊得又高又急,赌他不会对父亲留下的东西无动于衷。果然,脚步声停在了我头顶。
「抬起头来。」我慢慢扬起脸,故意让宫灯的光打在眼角的泪痣上。
这颗痣是母亲用胭脂点的,当年萧彻总说像棋盘上的星位。此刻我睫毛上还挂着泪珠,
想必看起来足够可怜。他的靴子停在离我鼻尖三寸的地方,玄色云纹绣得密不透风。
我看见他弯腰捡起一块碎玉,指尖在那道旧裂痕上摩挲了两下——就是这个动作!
当年他拿到父亲赏的「将」子,也是这样摸着上面的纹路笑。「司棋处的宫女?」
他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打量我。「是……奴婢苏瑾。」我咬着嘴唇,
把早就编好的说辞往外挤,
棋子是奴婢打扫库房时……不小心碰掉的……求陛下恕罪......"我故意加重了语气,
眼角的余光瞥见他捏着碎玉的手指紧了紧。突然,一阵风卷着落叶飘过,廊下的宫灯「吱呀」
晃了晃。我瞅准机会,猛地挣脱禁军的手,膝行两步抱住他的靴筒:「陛下!这棋子有蹊跷!
」这话果然管用。他没让禁军再拖我,反而问:「哦?什么蹊跷?」我心跳得像要撞碎肋骨,
赶紧从怀里掏出那半块桃花酥。油纸被汗浸湿了,酥饼的碎屑沾在我手背上。
……每枚都刻着字......"「这块白子的内侧……刻着『守』字......"「守」
字正好对着天玑星的位置。萧彻沉默了。过了半晌,他忽然蹲下身,
指尖擦过我手背上的酥饼碎屑:「这桃花酥……哪来的?」我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
就知道他不会忘。当年他总说太傅府的桃花酥比御膳房的甜,因为母亲在面里掺了海棠花蜜。
"是,是奴婢捡的..."「在太液池边的柳树下......"太液池边的柳树,
是当年他和父亲对弈时总坐的地方。他捏着碎玉的手指忽然顿住,龙涎香的气息离我更近了。
「你知道『马踏连营』的解法?」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人听见。我的心猛地一跳。
这是当年他输给父亲的那局棋!父亲说这局棋的解法藏着「困龙升天」的玄机。
只教过我和他两个人。「奴婢……奴婢在棋谱上见过......"我故意装作迟疑,
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他袍角的金线在颤抖。「说来听听。」他站起身,声音里终于带了点温度。
我定了定神,把父亲教的口诀往外搬。每说一步,就往他身边挪一寸,
直到能看见他腰间玉佩上的「彻」字。这枚玉佩还是当年母亲亲手编的络子,
如今磨得光滑发亮。「最后一步。」他打断我,目光像探照灯似的盯着我。我深吸一口气,
说出那句藏了三年的话:「帅五进一,弃车保帅。」这是父亲当年在狱中托人带给我的话,
我直到今天才懂其中的深意——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是枚要被舍弃的棋子。
萧彻的喉结动了动,突然转身对禁军说:「带她去养心殿。」两个禁军愣住了,
大概从没见过皇帝把碰瓷的宫女带回寝宫。我也愣了,原以为能保住性命就算成功,
没想到他会给我近一步的机会。"陛下,""这棋子......""捡起来。
"他头也不回,"带去找刘总管,让他看看还能不能拼上。"跟着他穿过月光下的御花园时,
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看见小禄子躲在假山后,冲我比了个「万事大吉」的手势。
夜风掀起他的衣角,露出里面藏着的药包——那是我托他准备的止血散,怕真摔伤了露馅。
养心殿的门槛高得吓人,我故意绊了一下,顺势往旁边歪。萧彻伸手扶了我一把,
他的指尖碰到我手腕时,我能感觉到他在抖。「小心些。」他松开手,
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关切。殿里的地龙烧得很旺,暖得我眼睛发涩。
刘总管捧着个锦盒进来,我赶紧把碎玉拼在里面。三瓣玉子合在一起,正好能看见「守」
字旁边的半个「国」字——这才是父亲要告诉萧彻的真相:有人要动国本。
萧彻盯着锦盒看了半晌,忽然问:「你在司棋处多久了?」「三年零七个月。」我答得飞快,
这是我每天在心里数的日子。他拿起一枚黑子,在棋盘上敲了敲:「会下棋?」「略懂皮毛。
」我垂下眼,看见棋盘角落里刻着个小小的「瑾」字——这是当年我趁他不注意刻的,
没想到他还留着。窗外的月光忽然亮了起来,照得棋盘上的木纹清清楚楚。萧彻落下一子,
声音轻得像叹息:「当年那局棋,你父亲让了我半子。」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啪嗒」
掉在棋盘上,晕开一小片墨迹。原来他什么都知道,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
知道那局棋里藏着的话,知道我今天不是真的碰瓷。"陛下,"我哽咽着,
终于敢抬起头看他,"这三年,
天都在等......等陛下想起太傅府的桃花酥......"他捏着棋子的手停在半空,
月光落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刘忠,"他忽然扬声,
"给苏瑾姑娘取身新衣服,安置在偏殿。"刘总管愣了一下,赶紧应声。我知道,这一步棋,
我赌赢了。但我没看到,在我转身跟着刘总管出去时,萧彻拿起那半块桃花酥,
放在鼻尖轻轻嗅着,指腹反复摩挲着上面的牙印——那是当年他咬出来的形状,
和现在我啃的一模一样。廊外的桂花开得正盛,落在青石板上的碎玉旁边,像撒了把碎金子。
我知道,这盘棋才刚刚开始,但至少,我已经把棋子落在了他的棋盘上。
3棋局暗涌养心殿的偏殿比司棋处的柴房暖和十倍,可我裹着刘总管送来的锦被,
整夜没合眼。窗纸透进第一缕晨光时,
我摸出藏在发髻里的碎瓷片——这是从父亲书房的砚台底抠下来的,背面刻着半个「魏」字,
指向当年构陷苏家的元凶:户部尚书魏庸。「姑娘,该梳洗了。」小太监捧着铜盆进来,
眉眼间带着讨好。我知道这是刘总管的意思。描眉时我故意用了最淡的螺子黛,
把眼角的泪痣遮去大半。父亲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还不是张扬的时候。
铜镜里映出的脸苍白消瘦,倒真像个受了惊吓的宫女。刚走到御书房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瓷器碎裂的脆响。「废物!连个宫女都看不住!」
皇后的声音像淬了冰的银簪,刮得人耳朵疼。我赶紧缩在廊柱后,
看见刘总管捧着个空茶盏跪在地,后脑勺的头发都被冷汗浸湿了。娘娘息怒,
圣上只是让苏瑾姑娘整理棋谱……"整理棋谱?"皇后冷笑一声,
金步摇上的珠串打得"啪啪"响,「哀家看是来分宠的吧!
当年太傅府的狐狸精勾了先帝的眼,如今她女儿又想攀龙附凤?」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原来皇后早就知道我的身份,昨天没立刻动手,不过是在等最佳时机。「让她进来。」
皇后忽然扬声。我深吸一口气,低着头推门进去。御书房的地龙烧得更旺了,
皇后穿着正红绣凤袍坐在榻上,手里把玩着串东珠,每颗珠子都有鸽卵大。
她身后站着四个膀大腰圆的宫女,袖口隐约露出青色的筋络——是练过武的。「抬起头来。」
皇后的声音慢悠悠的,像猫逗老鼠。我依言抬头,故意让她看见我遮去泪痣的眉眼。
奴婢苏瑾,参见皇后娘娘。膝盖刚弯到一半,就被她身边的宫女按住了肩膀。「跪下!」
宫女厉声呵斥,膝盖磕在金砖上,疼得眼前发黑。皇后用脚尖挑起我的下巴,
凤钗的尖儿几乎戳进我眼里:「果然是个狐媚子相,可惜啊......"她忽然笑了,
珠串晃得我眼花,「可惜命贱,只能做个宫女。」我咬着嘴唇不说话,
眼角的余光瞥见博古架上摆着个青玉棋盘——那是父亲亲手雕的,当年送给皇后的生辰礼,
没想到她还留着。「听说你会下棋?」皇后忽然松开脚,指了指桌上的残局,
"给哀家解解这'双马饮泉'。"这局棋是死局,除非弃掉双马才能盘活。
我知道她在试探我,拿起白子轻轻落在位置:「奴婢愚钝,只会舍车保帅。」
皇后的脸色变了变。当年父亲就是用这招赢了她哥哥的兵权,她怎么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
「赏她杯茶。」皇后忽然对身后的宫女使了个眼色。那宫女捧着茶盏走过来,
茶盖碰到杯沿的声音格外刺耳。
我看见她袖口的银镯子闪了一下——那是魏庸府里特有的样式。茶盏刚递到我面前,
就闻到一股淡淡的杏仁味。是牵机药!发作时会让人抽搐如弓,七窍流血而死。
我的心沉了下去。皇后比我想的更急,竟然敢在御书房动手。「谢娘娘赏。」
我双手接过茶盏,指尖故意碰到滚烫的杯壁。「嘶」的一声,手背立刻红了一片。
趁着众人分神的瞬间,我手腕一斜,整杯茶都泼在了自己手背上。「啊!」
我惨叫着倒在地上,故意往皇后的凤袍上滚了半寸。「烫!好烫啊!」手背被茶水浸得冒泡,
钻心的疼让眼泪真的涌了出来。皇后吓得猛地站起,凤袍下摆沾了片茶渍,
她指着我厉声骂道:「混账东西!敢弄脏哀家的衣服!」「娘娘饶命!」我哭喊着,
故意把声音往门外送。「奴婢不是故意的,这茶里......"说到一半突然捂住嘴,
眼神惊恐地看向皇后。这招「欲言又止」是父亲教的,最能勾起人的疑心。果然,
门外传来脚步声,萧彻穿着常服走进来,看见我倒在地上,眉头立刻拧成了疙瘩。
「怎么回事?」他的目光扫过我的伤手,又落在皇后沾了茶渍的袍角上。
皇后的脸瞬间堆起笑:「皇上来了?臣妾正和苏瑾姑娘说笑呢,
没成想她笨手笨脚......"「说笑?」我挣扎着爬起来,手背的水泡已经破了,
脓水混着血水往下滴。「奴婢谢娘娘赐茶,只是这茶......"我故意顿住,
咬着嘴唇看向萧彻,「也许是奴婢不识好歹,
总觉得味道不对......"萧彻的目光落在地上的茶渍上,又瞥了眼皇后身后的宫女。
那宫女的脸白得像纸,手里的茶盘抖个不停。"刘忠,"萧彻忽然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
「把这杯剩下的茶拿去验验。」皇后的笑容僵在脸上,金步摇的珠串「啪嗒」掉了一颗。
"皇上!"她赶紧拉住萧彻的袖子,"不过是杯凉茶,
何必劳师动众......"「皇后是怕了?」萧彻轻轻甩开她的手,
拿起桌上的残局看了看。「这棋你下了三天还没解?」皇后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我知道她根本不会下棋,这残局定是魏庸教她摆的。趁着两人说话的功夫,
我悄悄把一片碎瓷塞进袖袋——刚才泼茶时故意打碎了茶盏,碎片上沾着点茶渍,
正好能拿去给刘总管验。"皇上,"我忽然哭出声,膝行到萧彻脚边。
「奴婢知道自己身份低微,
不该留在养心殿……求皇上让奴婢回司棋处吧......"越是想留下,越要表现得想走,
这是宫里的生存之道。萧彻没说话,只是弯腰拉起我,指尖轻轻碰了碰我手背上的水泡。
「疼吗?」他的声音很轻,像怕吹破了那层皮。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这次是真的疼。
萧彻魏庸在《我在后宫,碰瓷皇帝》中的表现令人难以忘怀。其独特的性格和丰富的剧情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本书。
对于我来说,《我在后宫,碰瓷皇帝》是一部真正值得推荐的佳作。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感人至深,男女主角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感谢前后77的才情,写出了这么好的作品。
《我在后宫,碰瓷皇帝》中的萧彻魏庸具有鲜明的个性,让人难以忘记。剧情中的其他角色也各有特色,使人记忆犹新。
《我在后宫,碰瓷皇帝》这本书让人陶醉其中。作者前后77的文笔细腻流畅,每一个描写都让人感受到他的用心和情感。主角萧彻魏庸的形象生动鲜明,她的坚韧和聪明让人为之倾倒。整个故事紧凑而又扣人心弦,每一个情节都令人意想不到。配角们的存在丰富了故事的内涵和戏剧性,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魅力。这是一本令人沉浸其中的佳作,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不同的情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