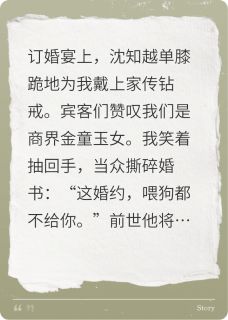“带路!”
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时,牙关咬得生疼,下颌骨都在发酸。谢芸的体温透过薄薄的衣料传来,烫得像块刚从火里捞出来的烙铁——她在发烧,血嫁衣的能量侵蚀已经突破了皮肤屏障,开始灼烧她的五脏六腑。我能感觉到她后颈的皮肤下有细小的硬块在蠕动,那是人脸怪鸟的丝线残留,正像蛆虫般往颈椎里钻。
枭没有废话,转身时战术靴碾过地上的纸人残骸,发出细碎的脆响,像踩碎了一堆干枯的骨头。他的路线刁钻得像条蛇,专往廊柱阴影和供桌死角钻,那些肉眼难辨的能量乱流在他身后半尺处炸开暗紫色的火星,噼啪作响,却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有一次我没跟上他的节奏,裤腿扫过一道能量流,布料瞬间变得像焦炭般酥脆,一股灼烧皮肤的刺痛立刻传了过来。
“跟上我的步频,呼吸调至四秒一吸。”他的声音在颅骨里震动,带着金属摩擦般的质感,“诡墟的空气含灵媒毒素,过量吸入会加剧契约反噬。**妹的体质特殊,毒素会顺着你的接触传导过去。”
我抱着谢芸紧随其后,血嫁衣突然变得重如铅块,每一步都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鞋底仿佛要融化。胸口的鸳鸯烙印突突直跳,那些血色丝线顺着血管往上爬,缠得心脏发紧,每次搏动都带来撕裂般的疼痛。刚冲出祠堂侧门,一股混合着烂肉和粪水的恶臭就撞进鼻腔——那气味不是来自地面的污秽,而是从空气里直接渗出来的,带着活物腐烂时特有的甜腻,熏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回廊尽头的阴影里,三具穿着破烂绸缎宾客服饰的行尸正歪歪扭扭地晃出来。
它们的眼球早烂成了泥,黑洞洞的眼窝对着我们的方向,腐烂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是有痰卡在气管里。最骇人的是它们的关节,每走一步,胳膊就“咔吧”一声往反方向折过去,手肘顶着后背,五指却像蜘蛛腿般灵活地扭曲,指甲缝里还挂着暗红色的肉丝。
“左前方,低威胁。”枭的声音毫无波澜,仿佛在播报天气。他腰间的战术囊“嗤啦”一声破开,金属搭扣弹开的脆响在死寂的回廊里格外清晰。一枚拳头大的金属球被他反手掷出,在空中划出道冰冷的弧线,表面的纹路在昏暗光线下泛着幽幽的蓝光。
“嗡——!”
强光爆开的瞬间,我下意识闭上眼,但那光线还是穿透眼皮,在视网膜上烧出一片惨白。那不是普通的亮,而是带着种尖锐的穿透力,像无数根细针往脑子里扎,太阳穴突突直跳,仿佛有只手在里面搅动。同时炸开的还有高频噪音,不是刺耳的尖啸,而是沉闷地捶打耳膜,震得我胸腔发闷,心脏都跟着错了半拍。
三具行尸突然僵住,腐烂的脸上爆出密密麻麻的血珠——它们没有皮肤的眼睑在疯狂抽搐,像是在承受某种剧痛。其中一具最靠前的行尸,喉咙里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呜咽,腐烂的手爪胡乱抓着自己的脸,指甲刮过颅骨发出“咯吱”的声响,竟硬生生把半块下颌骨都扯了下来,露出里面黑绿色的腐肉和蛆虫。
“穿过去!”枭的身影已经从行尸缝隙里滑了过去,动作快得只剩道黑影,作战服的边缘擦过行尸的躯干,带起一片黑色的粉末,那是尸身风化后的残留物。
我抱着谢芸紧随其后,就在肩膀即将蹭过最右侧那具行尸时,那东西突然猛地转头!它的脖颈以违反骨骼结构的角度拧了一百八十度,颈椎断裂的脆响清晰可闻,腐烂的爪子带着腥风抓向谢芸的后颈——那里的皮肤薄得像张纸,能清晰看见青色的血管,正是人脸怪鸟丝线聚集的地方!
“小心!”
枭的警告和枪声同时响起,但子弹要先穿过行尸的胸腔才能到脖颈,根本来不及!金属破空的锐响和行尸爪子带起的阴风同时扑到面前。
就在这时,血嫁衣突然炸开刺骨的寒意!
不是我在动,是那件衣服活了!领口的撕裂痕猛地张开,露出里面蠕动的、红肉般的内衬,一股怨毒到极致的意念瞬间冲垮我的理智——像被按进滚烫的油锅,皮肤寸寸灼痛;又像脖子被麻绳勒紧,窒息感扼得我发不出声音。百年前那个叫柳红胭的新娘临死前的记忆,如同碎玻璃般扎进我的脑海!
冰冷的花轿、喜婆狰狞的笑脸、金剪刀刺入心口的剧痛、烈火舔舐裙摆时的焦糊味……还有那铺天盖地的怨恨,恨这世道不公,恨这嫁衣缠身,恨所有冷眼旁观的活着的人!
“呃啊——!”
我的右手不受控制地抬起,五根手指变成诡异的青紫色,指甲缝里渗出暗红色的粘液。血嫁衣的袖口无风自动,数道猩红丝线“嗤”地射出去,快得拉出残影,精准地缠上行尸的脖颈和手腕。
那些丝线看着纤细,勒进腐烂皮肉时却发出“咯吱”的声响,像钢丝切过朽木。行尸的动作瞬间定格,空洞的眼窝里渗出黑血,顺着脸颊的沟壑蜿蜒流下。一种源自灵魂层面的窒息感顺着丝线反噬回来——我能清晰“闻”到它临死前的恐惧,那是被乱葬岗野狗分食时的绝望,混合着生前被活活饿死的痛苦,比柳红胭的怨恨更腥、更臭,熏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砰!砰!砰!”
三颗蓝色的子弹几乎贴着我的耳朵飞过,空气被撕裂的锐响震得我耳膜发麻。子弹精准地打爆另外三具行尸的头颅,蓝白色的电浆在碎骨烂肉中炸开,像绽放的死亡之花。枭不知何时已经转身,枪口还冒着青烟,战术目镜的蓝光扫过我缠满红丝的右手,像在看一件失控的仪器,眼神里没有温度。
“能力‘怨咒缠丝’,精神侵蚀度72%。”他的声音冷得像手术刀划开皮肤,“刚才那一秒,你瞳孔扩散了0.3秒,自主意识被压制。再犯一次,你的身体会优先攻击离你最近的活物——也就是**妹。”
我猛地攥紧拳头,红丝像触电般缩回袖口,指尖传来火烧火燎的疼。谢芸在怀里哼了一声,睫毛上挂着的血珠滚落在我手背上,烫得我一哆嗦——那温度比她的体温还高,带着灵媒毒素特有的灼痛感。我低头看她,她的嘴唇已经开始发紫,嘴角溢出细小的血沫,那是内脏被毒素侵蚀的征兆。
“闭嘴。”我咬着牙往前走,后背的冷汗把作战服浸透了,贴在身上黏腻难受。这个人比血嫁衣更可怕——他的枪口永远对准威胁,目光永远盯着数据,仿佛我们不是在逃出生天,而是在完成一场精准的实验。他甚至能计算出我瞳孔扩散的时间,这种精准到可怕的冷静,比任何诡物都更让人心寒。
穿过月亮门时,枭突然矮身,战术靴在青砖上碾出火星,那是靴底的防滑纹与地面剧烈摩擦的结果。他反手将我拽到廊柱后,力道之大让我的肩膀撞在石柱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我的鼻尖差点撞上他的呼吸过滤器,闻到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混杂着硝烟和某种金属的冷香,这是属于TSU成员的独特气味。
“右侧回廊第三块地砖是触发点。”他抬手指了指前方,战术手套的指尖泛着冷光,“上次有个契约者踩上去,被瞬间激活的重力场压成肉泥,灵能波动持续了三天,吸引了半个诡墟的活尸。”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那块地砖和周围的没什么不同,只是边缘泛着极淡的黑紫色,像是被陈年血迹浸泡过。枭已经迈步走了过去,脚尖精准地落在两块地砖的缝隙处,像踩着无形的格子,每一步都分毫不差,仿佛在走一条早已熟记于心的路线。
就在这时,祠堂方向传来一声沉闷的碎裂声,像是某种坚硬的骨骼被生生掰断。高堂之上那具枯骨新郎的下颌骨,终于挣开了电浆网的束缚,一声非人的咆哮穿透了重重阻碍,震得回廊的梁柱都在微微颤抖。
“干扰失效。”枭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急促,战术目镜后的目光扫向远处的大门,“最后五十米,冲出去!”
他突然加速,战术靴踏在地上发出密集的“哒哒”声,像打桩机在敲,每一步都让地面微微震动。我抱着谢芸紧随其后,血嫁衣突然剧烈起伏,胸口的鸳鸯烙印烫得像要烧穿皮肉——柳红胭的本体被彻底激怒了,这件嫁衣不再满足于被动防御,开始主动抽取我的生命力来对抗。
“咯咯咯……我的新娘,想跑去哪呀?”
那个女声直接在颅腔里炸开,带着刺骨的寒意,像是有根冰锥钻进了大脑。回廊两侧的墙壁突然“滋滋”冒出血泡,暗红色的液体顺着砖缝往下淌,在地面汇成细小的溪流,散发着新鲜的铁锈味。那些液体流动的速度极快,还带着诡异的生命力,像无数条细小的血蛇,朝着我们的方向蜿蜒而来。
枭猛地从腰间拽出个漆黑的圆柱,扔向身后时我才看清——那东西表面刻满了银色的符文,像圈着一圈锁链,符文之间流淌着微弱的蓝光,那是用特殊材料绘制的压制符文。
“轰隆!”
爆炸声闷得像闷雷,没有火光,只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黑暗炸开,瞬间吞噬了涌来的血溪。那些黑暗粘稠得像墨汁,里面仿佛有无数手在抓挠,发出指甲刮过玻璃的尖响,听得人头皮发麻。黑暗边缘偶尔闪过一两道惨白的光,像是某些东西在里面挣扎。
“跑!”枭抓住我的后领,把我往前猛拽。他的力量极大,我几乎是被他拖着走,膝盖在地上磕磕绊绊,好几次差点摔倒。怀里的谢芸被颠簸得哼唧了几声,呼吸越来越微弱,这让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快要窒息。
古宅的大门就在眼前,朽坏的门板上还贴着褪色的喜字,红得发黑,被风一吹哗哗作响,像有人在背后摇晃。门外的雾气里,能看到装甲越野车的轮廓,车身覆盖着厚重的装甲,车窗是黑色的防弹玻璃,看不到里面的人。还有几个穿着黑色作战服的人影,手里的枪闪着冷光,枪口都对着大门方向,显然是在警戒。
就在我的脚尖踏出大门的瞬间,身后的黑暗中伸出一只惨白的手,指甲涂着剥落的红蔻丹,带着一股腐朽的脂粉味,直抓谢芸的脚踝!那只手的皮肤像纸一样薄,能清晰看到下面青黑色的血管,手腕上还戴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银镯子,上面刻着“柳”字。
“芸!”
我猛地转身,红丝再次射出。这次我死死咬住舌尖,用疼痛对抗柳红胭的意念——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让我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红丝缠住那只手的刹那,我清晰“看”到了她的脸:柳叶眉,杏核眼,本该是个清秀的姑娘,却被烈火焚去了半张脸,露出焦黑的牙床和扭曲的骨骼。她的眼睛里没有恨,只有一片空洞的绝望,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你逃不掉的……”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又像在笑,凄厉而诡异,“这件嫁衣,会陪你到死……你的妹妹,也会变成和我一样的……祭品……”
“砰!”
大门在我身后重重关上,震起漫天灰尘,也隔绝了柳红胭的声音。枭的手还搭在门闩上,战术目镜的蓝光映着我胸口跳动的血色鸳鸯,像在评估一件刚从泥里捞出来的实验品,眼神里充满了审视。
雨丝突然落下来,混着雾气打在脸上,冷得像冰,让我打了个寒颤。谢芸在怀里动了动,小声喊了句“哥”,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却让我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下来,眼泪差点掉出来。
我低头看着她烧得通红的脸颊,又摸了摸身上这件还在微微起伏的血嫁衣——布料里渗着的墓土味,和柳红胭最后的怨毒一起,钻进我的骨头缝里,像是要在那里生根发芽。
枭已经转身走向越野车,背影在雾气里显得格外孤直,像一柄插在地上的黑色长剑。他的战术靴踩过水洼,发出“啪嗒”声,像在为这场狼狈的逃亡,敲下冰冷的注脚。
而我知道,这只是开始。柳红胭的怨毒,收容所的冰冷,TSU的未知目的,还有身上这件不断啃噬我灵魂的嫁衣……它们会像跗骨之蛆,陪我走完剩下的刑期。
我的第一件寿衣,已经穿好了。但只要能让谢芸活下去,就算穿上第二件、第三件,我也心甘情愿。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在她耳边低语:“芸,别怕,哥带你回家。”
《我成了绝望本身,万物得以喘息》这本书人设有趣,剧情写实,真挚动人。主角谢祀谢芸的形象塑造得十分生动,她的聪明冷静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让人为之折服。作者扣一送鸡仔巧妙地切入故事,设定了一个新奇的背景,并以精巧的结构将各个场景环环相扣,令人过目难忘。文中的配角也出彩,各自拥有独特的身份和共情点,与主角的前后反差使整个故事更加丰富多样。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读者无法自拔地被其抓住,不断追寻下去。
扣一送鸡仔的作品总是令我惊喜。《我成了绝望本身,万物得以喘息》的故事情节特别吸引人,跌宕起伏,让我爱不释手。
渐入佳境的[标签:小说类型]文,《我成了绝望本身,万物得以喘息》一开始让我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但随着故事的推进,它越来越吸引人,我忍不住追着看下去。这部作品展现了作者扣一送鸡仔的扎实文笔和出色的故事构思,是一篇优秀的作品。
《我成了绝望本身,万物得以喘息》这本书巧妙地将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作者扣一送鸡仔通过精湛的笔力,描绘出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主角谢祀谢芸的形象鲜明,她的聪明和冷静为整个故事注入了强大的力量。情节跌宕起伏,每一个转折都让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