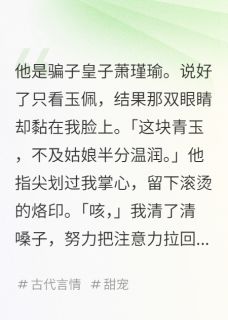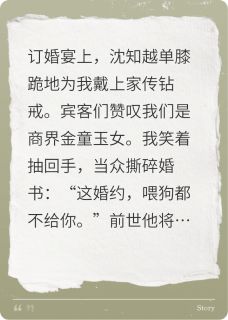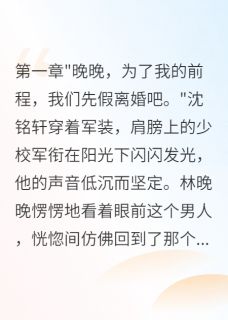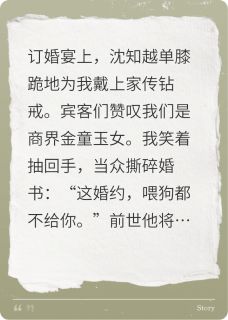我与李雪一同入宫选秀,她规矩我跳脱。后来我生下皇子成了太后,她假死逃出宫做了侠客。
宫墙内我学会忍字头上一把刀,她却策马江湖斩尽不平事。
临终前我攥着她送的玉佩想起她:“阿雪,江南的杏花…开了吗?
”走马灯里我看见十四岁的我们爬上御花园老槐树——她突然推我:“跳啊!外面有自由!
”我纵身跃下,宫墙在身后轰然倒塌。---皇太后江月躺在层层锦绣堆叠的软榻上,
像一件被岁月浸透又被精心包裹的旧物。明黄帐幔沉重地垂落,
隔绝了外间那些细碎、压抑的脚步声和若有似无的啜泣。殿内极静,
只有一盏长明灯在角落的铜鹤灯架上,灯芯偶尔发出细微的“哔啭”声,
映着鹤喙冰冷的反光,是这无边死寂里唯一一点微弱的活气。
空气里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陈旧药味,混杂着名贵熏香竭力想要遮掩衰朽的气息,
沉甸甸地压在人胸口,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滞涩的艰难。她浑浊的目光费力地转动,
最终落在枕畔。那里放着一枚玉佩,玉质早已不复当年的温润,边角磨损得厉害,
色泽黯淡发黄,唯有中间那一点沁入的天然翠色,还固执地透着一丝旧日的鲜活,
如同被遗忘在深秋枝头的一点残绿。她枯瘦的手指动了动,极其缓慢地移过去,
指尖触到那冰凉圆润的玉面,却再也无力将其握紧。那点微弱的凉意,像是一根引线,
猛地刺穿了记忆厚重的茧。“阿雪……”干裂的嘴唇翕动,声音微弱得如同叹息,还未出口,
便已消散在凝滞的空气里,“……江南的杏花……开了吗?”话语在喉间滚动,
带着砂砾般的粗粝。那模糊的尾音,仿佛已耗尽了她仅存的所有力气。她的眼睛缓缓阖上,
又强撑着睁开一条缝隙,视线投向遥远的南方,
徒劳地穿透了层层叠叠的华丽帷幔与森严宫墙,投向一个她一生都未曾抵达的地方。
---景盛元年,春。巨大的朱漆宫门在沉重的“吱呀”声中缓缓开启,
露出后面漫长而肃杀的夹道。高耸的红墙仿佛两道无情的铁幕,
将湛蓝的天空切割成狭窄而压抑的一条。日光吝啬地洒在冰冷的青石路面上,
反射着坚硬的光。一辆辆素帷青篷的马车鱼贯而入,车轮碾过石板路,
发出单调而令人心悸的辘辘声。车里载着的,是各地遴选而来的秀女,
她们是这庞大帝国春日里最新鲜、也最易凋零的点缀。江月缩在车厢角落,
身上簇新的藕荷色细布裙衫被揉得起了褶皱,袖口处不知何时蹭上了一小块灰尘。
她顾不得这些,两只手紧紧扒着小小的车窗边缘,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眼睛瞪得溜圆,
贪婪地捕捉着前方宫门后露出的那一角飞檐斗拱、金瓦红墙。风拂过她额前柔软的碎发,
带来一丝春寒料峭的凉意,却吹不散她眼中那团滚烫的新奇火焰。“快看快看!
那屋檐上的小兽!”她压低了声音,语气里是掩不住的兴奋,
用胳膊肘急切地捅了捅旁边端坐的少女,“雪儿,你见过吗?这么多!
像蹲在屋檐上开会似的!”被她唤作“雪儿”的李雪,
穿着一身裁剪合宜、料子上乘的月白色衣裙,连一丝多余的褶皱也无。她端正地坐着,
脊背挺直如尺,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听到江月的声音,
她只是微微侧过脸,眼神依旧平静地垂落在自己并拢的膝盖上,声音轻而稳:“月儿,坐好。
仪态不可失。”她的声音像初春未化的溪水,带着清冽的平静。江月撇撇嘴,
悻悻地收回身子,却忍不住又飞快地朝外瞥了一眼,嘴里小声咕哝:“规矩规矩,烦死啦!
进了这地方,还不得闷出病来?”她扭了扭有些僵硬的脖子,
目光落在李雪沉静如画的侧脸上,那线条柔和却透着一种近乎严苛的端正。她想起在家时,
偶尔去找她玩,李雪对着铜镜一遍遍练习如何行止有度、如何低眉浅笑的样子。
那时的她只觉得李雪像一幅挂在墙上的美人图,好看是好看,却少了活气。
车轮碾过一道门槛,车身轻轻颠簸了一下。李雪的身体纹丝不动,仿佛钉在了座位上。
江月却猛地一晃,差点栽倒,下意识地一把抓住了李雪的胳膊稳住身形。
李雪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微微一僵,随即放松下来,任由她抓着,另一只手却悄然抬起,
不动声色地拂了拂自己被抓出褶皱的袖口,动作轻柔而迅捷。她抬眼看向江月,
眼神里带着点无可奈何的纵容,轻轻叹了口气:“月儿,你呀……进了宫,
再这样莽撞可不行。一步行差踏错,便是万劫不复。”她的声音压得更低,如同耳语,
却字字清晰。江月看着她眼底那抹深沉的忧虑,
心头那点小小的不以为然忽然被一种莫名的、沉甸甸的东西压住了。她讪讪地松开手,
坐直了身体,也学着李雪的样子,试图把脊背挺得笔直。可那刻意为之的僵硬姿态,
在她身上显得格外别扭。她偷偷瞄了一眼李雪,对方已恢复了那副沉静如水的模样,
仿佛刚才那一瞬间的失态从未发生。宫门的阴影彻底吞没了马车,
也吞没了江月心头刚刚燃起的那点雀跃的星火。---储秀宫的院子方正而空旷,青砖铺地,
光洁得能照出人影。几株新移栽的桃树疏疏落落地立在墙角,枝头的花苞怯怯地打着朵儿,
在肃杀的宫墙下显得格外单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尘土、新木和隐隐脂粉的奇特味道。
新入宫的秀女们按照名册顺序,垂首敛目,排成几列,鸦雀无声。她们统一的浅色宫装,
像一片被风吹得微微起伏的素色花田。教导规矩的嬷嬷姓严,身形瘦削,
一张脸刻板得如同刀劈斧削出来,法令纹深得能夹死苍蝇。她穿着一身深褐色宫装,背着手,
目光鹰隼般扫过每一张年轻的脸庞,眼神锐利得能刮下一层皮。“行!
”严嬷嬷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摩擦般的穿透力,清晰地送到每个人耳中,“步要稳,
身要正,裙裾不动,环佩不鸣!目视前方三尺地,不可斜视,不可旁顾!”她亲自示范。
抬脚,落脚,迈步,转身……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精准、刻板,
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韵律感。衣裙在她身上纹丝不动,只有裙角随着步伐极其轻微地摆动,
幅度精确得如同计算过。“看到了吗?这才是宫里的仪态!”严嬷嬷站定,
目光如锥子般钉在秀女们身上,“你们在家或许有些小性儿,进了这宫门,
就得把那些枝枝蔓蔓统统给我收起来!这里,容不得半点轻狂!”她踱着步子,
走到队伍中间,声音陡然拔高,“若学不会规矩,轻则受罚,重则……哼,
被撵出去还是轻的,怕只怕,连累家人!”队伍里一片死寂,连呼吸声都刻意放轻了。
空气绷紧得如同拉满的弓弦。轮到江月和李雪上前练习行走。李雪深吸一口气,垂着眼帘,
按照严嬷嬷的示范,一步一步稳稳踏出。她的肩膀放松而平直,脖颈的弧度优美,
裙裾的下摆像被无形的线提着,只在她脚踝处漾开极其微小的涟漪。
她的目光专注地落在前方三尺处一块略有磨损的青砖上,神情专注而平静,
仿佛天生就该如此行走。严嬷嬷紧绷的嘴角几不可察地松动了一丝,微微颔首。
下一个是江月。她学着李雪的样子迈步,起初几步还算稳当,可走着走着,
那刻意维持的平衡便开始摇晃。她总觉得别扭,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仿佛手脚都不是自己的。
脚下那双簇新却稍显笨重的宫鞋也成了累赘。一个不留神,左脚绊了右脚的前缘,
身体猛地向前一个趔趄!“哎!”她短促地惊呼出声,双手下意识地在空中乱抓了一下,
才险险稳住身形,没有狼狈地扑倒在地。然而,这小小的失态已足够惊心动魄。
队伍里瞬间响起几道压抑的抽气声。“放肆!”严嬷嬷的厉喝如同鞭子,
狠狠抽在寂静的空气里。她几步跨到江月面前,眼神凌厉得能剜下肉来,“你是哪家的?
如此粗鄙不堪!方才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吗?”她的手指几乎戳到江月的鼻尖,
那深褐色的衣袖带着一股冷硬的檀香味。江月只觉得脸上“轰”地一下着了火,
**辣地烧到了耳根。她死死咬住下唇,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才勉强抑制住那几乎要脱口而出的辩解和委屈。她垂下头,盯着自己绣鞋尖上滚着的珍珠,
那微小的圆润光泽在眼前模糊成一片。她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自己背上,
有怜悯,有嘲讽,更多的是事不关己的冷漠。“站到廊下去!”严嬷嬷的声音冰冷刺骨,
“看着别人怎么走!站到晌午!”江月低着头,一步一步挪到廊下的阴影里。
廊柱冰冷坚硬的触感透过薄薄的衣衫抵着她的后背。她抬起头,
目光越过院中那些规整移动的身影,落在李雪身上。李雪依旧在稳稳地走着,步履从容,
姿态端方,仿佛刚才那场小小的风波与她毫无关系。她的侧脸在春日疏淡的光线下,
平静得像一尊无悲无喜的玉像。那玉像般的沉静里,
江月第一次清晰地尝到了“规矩”二字的分量,沉重得让她几乎喘不过气。
她靠在冰冷的柱子上,阳光被屋檐切割成窄窄的一条,落在脚前,
却照不进她此刻被阴影覆盖的心底。掌心的刺痛还在,提醒着她莽撞的代价。
她用力吸了吸鼻子,把那股酸涩的湿意狠狠憋了回去。
---储秀宫的日子如同一潭表面平静的死水,底下却暗流汹涌。白日里,
一丝不苟的教导:行立坐卧、言谈举止、宫中禁忌、贵人喜好……繁复琐碎如同密织的蛛网。
入夜,小小的通铺房间,十几人挤在一处,呼吸相闻,却各自沉默。
空气里弥漫着年轻身体的气息、劣质脂粉的甜腻,还有挥之不去的、对未来巨大未知的恐惧。
江月越来越沉默。她学会了在走路时盯着自己的脚尖,学会了在嬷嬷训话时垂下眼睑,
学会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收敛起所有不合时宜的表情。
那团曾经在她眼底燃烧的、名为“自由”的火焰,被这深宫无处不在的冷水一点点浇熄,
只剩下压抑的灰烬。只有在深夜,当同屋的呼吸声变得均匀悠长,她才敢在黑暗中,
借着窗外透入的微光,一遍遍摩挲着枕下那枚在宫外时李雪送的玉佩。那冰凉的触感,
是她与那个喧嚣、鲜活的宫外世界唯一的、隐秘的联系。李雪依旧是那个最循规蹈矩的存在。
她的床铺永远是最整洁的,她的仪态永远是最无可挑剔的,
她应对嬷嬷的考校也总是最得体的。她像一株精心修剪过的植物,
完美地嵌合在这储秀宫的框格之中。然而,江月偶尔会在她沉静的眼底,
捕捉到一丝极快掠过的、难以名状的东西。那东西很淡,很轻,
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转瞬即逝,却让江月莫名地感到一丝不安。一次教习间隙,
难得的片刻喘息。两人在储秀宫后一处偏僻角落的廊下避着人。
墙角几丛新发的芭蕉叶子阔大,绿得有些寂寞。江月靠着冰凉的廊柱,
望着头顶被宫墙切割得只剩下一小片的、灰蒙蒙的天空,
声音带着浓重的疲惫和迷茫:“雪儿,你说……我们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就这样……一直学规矩,等着被挑拣?”她伸出手,虚空抓了抓,仿佛想抓住什么,
却只握住了空荡的风。李雪没有立刻回答。她站在芭蕉叶的阴影里,
目光落在远处宫墙高高的鸱吻上,那狰狞的兽首在暮色中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剪影。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声开口,声音飘忽得如同呓语:“月儿,
你想过……墙外面是什么样子吗?”江月一愣,转头看她:“外面?
外面不就是街市、人家……还有,江湖?”她想起以前在茶楼里听过的那些侠客故事,
眼睛里短暂地亮起一点微弱的光,“策马天涯,多自在!
”“自在……”李雪重复着这两个字,唇边忽然弯起一个极浅、极淡的弧度,
带着一种江月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近乎虚幻的向往,“是啊……策马天涯……”她顿了顿,
声音压得更低,低得几乎被风吹散,“听说……江南的杏花,开起来像云霞一样。
”江南的杏花?江月有些茫然,她从未去过江南。但李雪眼中那瞬间闪过的、奇异的光亮,
让她心头莫名地跳了一下。李雪很快收敛了那点异样的情绪,恢复了平日的沉静,
仿佛刚才那瞬间的失神只是江月的错觉。她转回头,看着江月,
眼神又变得柔和而关切:“月儿,别想那么多了。在这地方,想得越多,心越乱。
我们……先熬过眼前吧。”她伸出手,轻轻握了握江月冰凉的手指,
那指尖带着一丝安抚的暖意,却无法真正驱散江月心头的寒意。熬。江月咀嚼着这个字,
只觉得舌尖泛起一片苦涩。原来她们的人生,只剩下一个“熬”字。
她看着李雪平静无波的侧脸,那沉静之下,到底藏着多少她看不懂的暗流?
那关于江南杏花的低语,又意味着什么?江月第一次觉得,
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最懂规矩的李雪,竟也变得有些陌生起来。---日复一日的“熬”,
终究熬出了截然不同的分岔路。李雪在一次考核中被人陷害得罪了当时盛宠的慧妃,
被贬去了浣衣局。江月那张带着几分天然野性、未及完全被规矩打磨掉棱角的脸,
在众多低眉顺眼的秀女中,意外地撞入了帝王偶然一瞥的视线。
她身上那股尚未被完全驯服的生命力,在帝王看惯了温顺的世家美人之后,
成了短暂的新鲜点缀。一次“偶遇”,一次“临幸”,如同投石入水,
在她自己都未曾完全反应过来的惶惑中,命运的巨浪已将她彻底吞没。她成了江贵人。
封号落下的那一刻,江月跪在冰冷坚硬的金砖地上,
听着内侍尖细的宣旨声在空旷的殿宇间回荡,只觉得浑身血液都涌到了头顶,
又在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彻骨的冰凉。她下意识地抬起头,目光越过前面跪伏的人群,
急切地搜寻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她看到了李雪。李雪依旧垂着头,姿势标准得无可挑剔,
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只是在宣旨官声音落下的那个瞬间,
江月似乎捕捉到她交叠在身前的手,几不可察地微微蜷缩了一下,指尖用力得有些发白。
很快,那手又恢复了平静,像两片无波的玉叶。江月搬离了储秀宫那拥挤的通铺,
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华丽而空旷的宫室。雕梁画栋,锦幔绣帷,宫女内侍垂手侍立,
口称“娘娘”。她坐在宽大的紫檀木梳妆台前,看着镜中被华服珠翠包裹的陌生女子,
只觉得那镜中人影模糊而遥远。巨大的惶恐如同冰冷的潮水,夜夜拍打着她的梦境。
秋夏夏羽的《宫墙柳和江南燕》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故事情节紧凑,人性描绘细致,让人期待后续的展开。
秋夏夏羽的《宫墙柳和江南燕》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故事情节紧凑,人性描绘细致,让人期待后续的展开。
秋夏夏羽的《宫墙柳和江南燕》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故事情节紧凑,人性描绘细致,让人期待后续的展开。
《宫墙柳和江南燕》这本书巧妙地将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作者秋夏夏羽通过精湛的笔力,描绘出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主角江月李雪的形象鲜明,她的聪明和冷静为整个故事注入了强大的力量。情节跌宕起伏,每一个转折都让人意者会被情节的发展所吸引,无法自拔。配角们的存在也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张力,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这本书充满了惊喜和感动,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深刻的思考和共鸣。《宫墙柳和江南燕》是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值得推荐给所有热爱[标签:小说类型]小说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