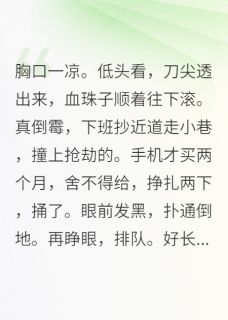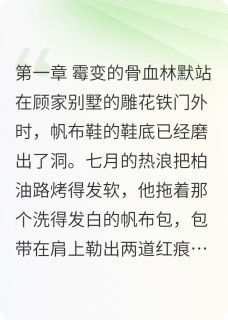我娘是穿越来的,从小教我:“妇女能顶半边天。”“你是女主垫脚石,别搭理男人,
会变得不幸。”丞相替儿子求娶我时,我娘正涮着火锅。她擦擦嘴:“川渝女人,
劳资蜀道山。”皇帝爹疑惑道:“什么意思?
”娘亲微笑说:“意思是他儿子配不上我女儿一根头发丝。”“让他数三声,滚出大殿。
”“否则我亲自送他全家上蜀道——爬山的那种。”1夕阳熔金,泼洒在朱雀大街上,
将青石板染成流动的琥珀。马蹄声碎,敲打着暮归的节奏。我猛一勒缰绳,
身下通体墨黑的骏马“踏雪”前蹄高高扬起,发出一声嘹亮的嘶鸣,鬃毛在晚风中烈烈飞扬,
几乎扫过街边摊贩支起的竹竿。几个正收摊的小贩吓得一缩脖子,
看清是我后又赶忙挤出讨好的笑,深深弯腰行礼。“昭华殿下万安!”我随意挥了挥手,
目光扫过他们堆满廉价胭脂水粉的简陋货架,还有那几匹灰扑扑、一看就粗粝扎手的土布。
心头那股熟悉的、混杂着不屑与烦躁的情绪又涌了上来。这就是京城百姓眼中的“好东西”?
啧。马蹄轻快地继续踏在石板上,哒哒的脆响带着我奔向巍峨的宫门。宫墙的影子越拉越长,
沉甸甸地压过来,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规矩感。每次回宫,这种感觉就如影随形。
唯有想到母亲,想到她那方小小的、总是飘着奇异辛辣香气的“椒房殿”,
心口才仿佛透进一丝自由的风。母亲苏晓晓,一个与这森严宫闱格格不入的存在。
她总说自己是“穿”来的,来自一个叫“现代”的、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地方。那里的女人,
可以像男人一样读书、做官、骑马打仗,甚至……决定自己嫁给谁。“昭华,
”她无数次捏着我的脸,眼神亮得惊人,像淬了火的星子,“记牢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天塌下来,咱娘俩也能给它撑回去一半!”“还有,离那些臭男人远点,
特别是名字听起来文绉绉、长得像小白花的!那都是坑,是女主往上爬的垫脚石!沾上了,
你就等着变得不幸吧!”“女主”是什么?我不太懂。但“不幸”这个词,
在她那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的语气里,显得格外狰狞可怕。她的教导如同烙印,
深深刻在我骨子里。所以,当那个什么礼部侍郎家的公子,在春日宴上拿着把破扇子,
念着酸掉牙的情诗,还自以为风流倜傥地朝我抛媚眼时,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差点把刚吃的御膳房新做的玫瑰酥吐出来。垫脚石?不幸?母亲的话瞬间在耳边炸响。
我当场冷下脸,一句“挡路了”,让那自以为是的“风流才子”脸色由红转白再转青,
活像个调色盘。从此,“昭华公主脾气古怪、眼高于顶”的名声,算是彻底坐实了。挺好,
清净。穿过一道道森严的宫门,守卫铠甲碰撞的铿锵声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冷硬。终于,
熟悉的、霸道而奇异的香气钻入鼻腔——热辣、滚烫,带着花椒的酥麻和牛油的厚重,
强势地盖过了宫中惯有的沉水香和龙涎香的味道。是母亲的小厨房又在鼓捣她的“火锅”了!
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下来,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我一夹马腹,“踏雪”撒开四蹄,
朝着椒房殿的方向疾驰而去。椒房殿内,灯火通明,却毫无宫室该有的端方持重。
一张特制的、中间挖了洞的紫檀大圆桌占据主位,桌下炭火正旺,架着一口赤铜大锅。
锅里红浪翻滚,密密麻麻的花椒粒和干辣椒在牛油汤底中载沉载浮,
浓烈霸道的辛香几乎凝成实质的白雾,弥漫了整个空间。“娘!”我扬声喊道,
随手解下沾了尘土的披风丢给迎上来的宫女。桌边那人闻声抬头。
她穿着件样式古怪却异常利落的窄袖胡服改良袍子,
墨黑的长发只用一根朴素的乌木簪子松松挽起,几缕碎发垂在光洁的额角。
岁月似乎格外优待她,脸上并无太多深宫妇人常见的刻痕与暮气,那双眼睛尤其明亮,
此刻映着锅中沸腾的红油,跳跃着火焰般的光彩。“回来啦?”苏晓晓——我的母亲,
大夏朝的贵妃娘娘,正麻利地从翻滚的红汤里捞起一片薄得透光的毛肚,手腕一抖,
七上八下,动作熟稔得像个积年的老庖厨。“快,洗手去!刚涮好的千层肚,
再晚一秒就老了,暴殄天物!”她一边说,一边将那颤巍巍、裹满红油的毛肚塞进嘴里,
满足地眯起眼,发出含糊的喟叹,“嗯……巴适!”我净了手,坐到她对面。桌上琳琅满目,
摆满了宫人们见所未见的食材:鲜红的鸭血方方正正,嫩滑的脑花盛在白瓷小碗里,
鹅肠、黄喉、郡肝码放得整整齐齐,
绿的豌豆尖、脆生生的藕片、吸饱了汤汁的冻豆腐……与殿外那庄严肃穆、等级森严的皇宫,
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今天骑射练得如何?”母亲又夹起一片肥牛,
在沸腾的锅中心三涮两涮,肉片瞬间蜷曲变色,
蘸上她秘制的、加了蒜泥、香菜和大量小米辣的油碟,一口吞下,
辣得她鼻尖渗出细小的汗珠,却畅快无比。“尚可。”我学着她的样子,
笨拙地捞起一块鸭血,“就是靶场那几个教习,迂腐得很,总说什么‘公主金枝玉叶,
能开半石弓已是难得,不必强求准头’,烦人。”鸭血入口即化,
滚烫鲜辣的味道直冲天灵盖,我忍不住吸了口气。“哼,”母亲嗤笑一声,
端起手边冰镇的果子露灌了一大口,冰凉的甜意中和了舌尖的灼烧,“别理那些老古董。
咱女人力气是小点,但准头靠的是眼力、手稳和脑子!练!给我狠狠地练!
以后谁再敢在你面前放这种屁,你就拿箭指着他的鼻子问,敢不敢跟你比一场!”她顿了顿,
眼神变得促狭,“哦,对了,今天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垫脚石’又往你跟前凑?
娘教你的‘防狼簪’用法,练熟了没?”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娘!没有!
您女儿我‘凶名在外’,哪个垫脚石敢来触霉头?”那根特制的簪子,顶端磨得极尖,
尾部还藏了个精巧的机关,据说能喷出特制的辣椒粉,是母亲亲自画图设计,
让内务府最顶尖的工匠打造的“防身利器”。虽然一次也没用过,但揣在袖中,
确实多了几分底气。我们正吃得酣畅淋漓,额头冒汗,
殿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而小心的脚步声。椒房殿的大太监李德全,
一个被母亲“川味”熏陶得也能吃两口辣的老内侍,躬着身子,脚步轻得像猫,
几乎是溜着边儿蹭了进来。“娘娘,殿下,”李德全的声音压得极低,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前头……承乾殿那边,似乎……出事了。
”母亲正夹着一片藕准备下锅,闻言动作一顿,眼皮都没抬:“哦?天塌了还是地陷了?
陛下龙体欠安?”语气漫不经心,仿佛在问“外面下雨了吗”。“不……不是,
”李德全咽了口唾沫,声音更低,“是……谢丞相,带着几位重臣,
正在殿前……恳求陛下赐婚。”“赐婚?”我握着筷子的手一紧,
心头莫名掠过一丝不祥的阴云。这深宫之中,
能劳动丞相亲自出马求赐婚的对象……屈指可数。李德全的头垂得更低了,
声音细若蚊呐:“是……是为他家大公子谢玉衡,求娶……求娶昭华殿下您。”2“哐当!
”我手中的银筷失手掉在镶螺钿的桌面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几滴红油溅出来,
落在月白的衣袖上,晕开刺目的痕迹。谢玉衡?
那个以“芝兰玉树”、“温润君子”闻名京城,被无数闺阁女子视为梦中佳婿的丞相嫡长子?
一股强烈的恶心感猛地窜上喉头,比刚才吃到那颗爆开的花椒还要猛烈百倍。垫脚石!
巨大的、镶金嵌玉、无数人仰望的垫脚石!母亲的话如同惊雷,瞬间在我脑海中炸响。
“呵……”一声极轻的冷笑从我身旁传来。我猛地转头,母亲苏晓晓不知何时已放下了筷子。
她脸上方才涮火锅时的惬意和红晕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淬了冰的平静。
那双总是跳跃着火焰般光彩的眼睛,此刻幽深得像两口古井,
所有的情绪都被强行压到了最底处,只余下表面一层寒潭般的冷光。
她慢条斯理地拿起一方素白的丝帕,极其仔细地擦拭着每一根手指,动作轻柔得近乎诡异,
仿佛在擦拭一件稀世珍宝,连指甲缝里的红油都不放过。那专注的神情,
与方才大快朵颐的模样判若两人。殿内只剩下铜锅中汤底持续翻滚的“咕嘟”声,
单调而压抑。李德全大气不敢出,头几乎埋进了胸口。“谢安石……”母亲终于擦完了手,
将丝帕随意丢在桌上,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火锅的喧嚣,
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冷硬质感,“好大的手笔,好厚的脸皮。”她缓缓站起身,
没有看李德全,目光投向殿外沉沉暮色笼罩下的宫阙剪影,唇角勾起一抹极淡、极冷的弧度。
“李德全。”“奴……奴才在!”“去承乾殿。告诉陛下,”她的声音没有丝毫起伏,
平静得可怕,“本宫稍后便到。请陛下……务必等我一等。”李德全如蒙大赦,
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殿门在他身后无声地合拢,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也仿佛将这殿内压抑的寒意锁得更紧。殿内只剩下我和母亲。方才还令人垂涎的火锅香气,
此刻闻起来却有些滞涩。我看着母亲挺直的背影,那背影单薄,
却像一柄收入鞘中的绝世利刃,鞘身朴素,却散发着无声的威压。“娘……”我开口,
声音有些发涩。母亲没有回头,只是轻轻抬起手,止住了我的话。她走到窗边,
推开一扇雕花木窗。暮春微凉的夜风带着御花园里草木的气息涌入,
稍稍吹散了殿内浓重的辛香,却吹不散那股无形的凝重。“昭华,”她终于开口,
声音在夜风中显得格外清晰,“怕吗?”我立刻挺直了脊背,走到她身边,与她并肩而立,
望向远处承乾殿隐约可见的灯火:“不怕!垫脚石而已!沾上才会不幸!”母亲侧过头,
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极其复杂,有欣慰,有心疼,更深处,
翻涌着一种我无法完全理解的、近乎燃烧的愤怒和决绝。她伸出手,
冰凉的手指轻轻拂过我的鬓角,将我一丝被风吹乱的发丝拢到耳后。那指尖的凉意,
却奇异地让我躁动不安的心沉静下来。“好孩子。”她收回手,
目光重新投向那片象征着至高权力的灯火,“记住娘的话。这世上,没有任何人,
能替我们做决定。尤其是决定我们该嫁给谁,该成为谁的附属品。”她的声音不高,
却字字如铁,砸在椒房殿光滑的金砖地上。“他们以为这是施恩?是攀附?
”母亲唇角的冷笑加深,眼中寒芒乍现,“谢安石这只老狐狸,打得好算盘。
想用我女儿当梯子,把他谢家再往上拱一步?呵……”她顿了顿,转过身,面向我,
眼神锐利如刀,仿佛要剖开一切虚妄。“昭华,你可知那谢玉衡,温润君子名声在外,
后院却已有两房‘红颜知己’,皆是清倌出身,美其名曰‘知音’?”她语带讥诮,
“他母亲,谢丞相的正室夫人,当年亦是名门闺秀,嫁入谢府后,主持中馈,生儿育女,
结果呢?谢安石转头就纳了四房年轻貌美的妾室,其中一个还是她当年的陪嫁丫鬟!去年,
那夫人郁郁而终,你猜谢安石做了什么?不过半年,又抬了一个十五岁的商户女做贵妾!
所谓的名门规矩,不过是套在女人脖子上的枷锁!”我听得心头一阵阵发冷。这些秘闻,
深锁闺阁的我从未听闻。京城中人人称颂的谢家父子,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竟是如此不堪!
“还有,”母亲的声音冷得像冰,“你以为谢安石只是看中你公主的身份?他更看中的,
是我椒房殿!看中陛下对我这个‘异类’的几分容忍!
看中我那些‘离经叛道’却能生财的点子!他想把我女儿娶回去,
连带着把我也绑上他谢家的战车!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她深吸一口气,
胸膛微微起伏,似乎在强行压下那股滔天的怒意。再开口时,声音已恢复了几分平静,
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昭华,你记住。你的婚事,只能是锦上添花,
绝不能是雪中送炭,更不能是别人棋盘上的筹码!要嫁,也必得是你自己千挑万选,
心甘情愿,且那人能与你并肩而立,而非让你仰其鼻息!”她的话,如同滚烫的烙印,
深深印刻在我心上。那些关于“垫脚石”的警告,在此刻变得无比清晰、具体而残酷。
“走吧。”母亲最后整理了一下那身利落的胡服袍子,挺直了背脊,整个人如同出鞘的利剑,
锋芒毕露,“去会会那位‘位高权重’的谢丞相。”“娘,等等!”我急忙拉住她的衣袖,
眼中是不加掩饰的担忧,“父皇他……”母亲脚步一顿,回头看我,眼中的冰寒融化了些许,
染上一丝复杂难言的暖意,还有一丝……了然的决绝。“放心。”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力道不大,却带着奇异的安定力量,“你父皇……他或许有他的考量,但这一次,娘不会退。
一步都不会。”她的手心温热,眼神却锐利如鹰隼,直刺向承乾殿的方向。3“川渝女人,
劳资蜀道山!”她几乎是无声地,用只有我能听清的家乡话低语了一句,随即转身,
大步流星地朝殿外走去,步伐坚定,带着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我立刻跟上,
椒房殿厚重的殿门在我们身后缓缓开启,承乾殿那辉煌的灯火和隐隐传来的议论声,
如同巨大的漩涡,瞬间将我们吞噬。辛辣的火锅香气被抛在身后,前方,
是冰冷的权谋与一场避无可避的风暴。承乾殿内,灯火通明,亮如白昼。
蟠龙金柱在烛火映照下反射着冰冷坚硬的光泽,巨大的盘龙藻井高高在上,
俯视着殿中的芸芸众生。空气里弥漫着龙涎香沉郁厚重的气息,
将椒房殿带来的最后一丝辛辣彻底掩盖,只剩下一种令人窒息的庄严肃穆。御座之上,
皇帝李晟——我的父皇,身着明黄常服,斜倚在宽大的龙椅中。他年过五旬,
面容依稀可见年轻时的俊朗,
但眉宇间沉积着挥之不去的倦怠与一种深沉的、难以捉摸的暮气。此刻,他右手支着额角,
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光滑的紫檀扶手,目光低垂,看着御案上一份摊开的奏折,眉头微锁,
仿佛被什么难题困扰。对于殿中凝重的气氛,他似乎并未过多在意,或者说,早已习惯。
殿中央,以谢安石为首,几位身着紫袍的重臣肃然而立。谢安石,当朝丞相,已过花甲之年,
须发半白,面容清癯,保养得宜,一身深紫仙鹤补子官袍衬得他气度儒雅雍容。
他微微躬着身,姿态放得极低,双手捧着一份明黄的奏疏,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回荡在空旷的大殿里,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恳切与忧国忧民。“……陛下明鉴。
昭华殿下金枝玉叶,贤淑端方,实乃我大夏明珠。犬子玉衡,虽愚钝,然仰慕殿下风仪久矣,
常言若能得配殿下,乃三生之幸。老臣亦深知门第或有不足,然拳拳之心,天地可表。
”他顿了顿,抬起眼,目光诚恳地望向御座,“如今北境虽安,然西陲不稳,
南疆亦有土司反复。陛下春秋正盛,然储位关乎国本,宜早定乾坤,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若昭华殿下下嫁寒门,一则恐委屈金枝,二则……恐于国本稳固,亦非万全之策啊。
《劳资蜀道山,丞相算哪座山?》的框架设置得非常出色,作者一支幽默笔的文笔也十分出众。不同于想象力构架的情节,这本书以淡淡的细水长流的温馨隽永打动读者。读完后,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深刻的感受,让人产生了一种想要再次阅读的冲动。
一支幽默笔的作品总是让人眼前一亮。在《劳资蜀道山,丞相算哪座山?》中,他展现出了极高的文笔技巧和深厚的人性洞察力。
作者一支幽默笔的《劳资蜀道山,丞相算哪座山?》令人沉醉其中,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意想不到的转折让人难以预测。男女主角的形象独特而深刻,使整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真心希望作者能关注到这个评论,期待更多精彩的情节!
《劳资蜀道山,丞相算哪座山?》这本书充满了智慧与勇气。作者一支幽默笔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主角苏晓晓昭华的成长历程。她在面对困境时展现出坚韧和聪明,激励着读者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整个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每一个转折都令人意想不到。配角们的存在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趣味和戏剧性,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性格和魅力。这是一部令人充满期待和感动的佳作,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