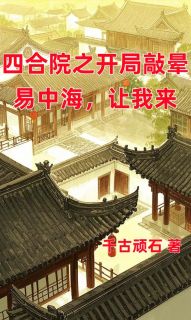顾辞雪怀了她养弟的孩子。
顾家晚宴,她搂着顾临川,理直气壮命令我:
“我家小川嘴馋了,要吃你亲手做的做红烧竹笋。”
“他现在是顾家嫡孙的爸爸,地位尊贵,你搬去佣人房,方便听吩咐。”
我一声不吭,将寥寥几件衣物收拾好,提包离开。
老佣人劝她挽留我,顾辞雪轻蔑一笑:
“这招他都用了多少次了?哪次不是一天就死皮赖脸回来舔我。”
宾客们看向我,目光全是鄙夷。
顾辞雪的好姐妹甚至开起赌局,押注一个稀有皮爱马仕赌我12小时就回家。
在哄笑声中,远远传来直升机的轰鸣。
这次,我不会回头了。
1
刚踏出顾家大门,一股猛力拽住我的手腕。
回头看见顾辞雪冷硬的面孔:
“留下你的红绳,小川心慌,大师说要用带血的物件来镇。”
她指着我烈士父母留下的唯一贴身物件。
染着他们鲜血的红手绳。
顾辞雪见我不动,不耐烦皱眉:
“一千万,行了吧?你不要贪得无厌。”
我低下头,竭力掩住即将滑落的泪,以及唇边的苦笑。
贪得无厌。
这就是我奉献身心的十年婚姻,换回来的四个字。
可我却不得不接受。
否则就会像上个月我拒绝给顾临川的爱犬哭丧一样,被自己妻子赶出家门,裹着半尺白布在寒风中守灵三天三夜。
事后,她让助理打给我五百万,说是我给狗披麻戴孝的辛苦费。
既然钱不得不收,我又何苦再给理由他们作践我?
我摘下红绳,顺从递给顾临川。
顾辞雪满意点头,掐住我下巴:
“算你识相,许叙白。”
“看在你是我名义丈夫的份上,孩子姓顾,也可以喊你一声爸......”
话音未完,顾临川尖叫出声。
血红的手绳内露出针尖的寒光,扎在他手腕上。
“辞雪姐姐,红绳里藏了针!”
女人瞬间暴怒,捏着我的手一甩,顺势落下响亮的耳光。
“**!竟然在东西上动手脚害小川!”
我被掴倒,撞翻身后香槟车,倒在一地玻璃渣中,鲜血横流。
她看不见血泊中的我,眼里只有养弟手腕上几不可见的血滴。
她紧张地用手帕捂住伤口,暴躁怒吼家庭医生。
众人看向我目光里的鄙夷更甚,嗤笑出声。
不仅他们,连我自己都笑出声来。
只是这笑里,忍不住带了泪。
昨晚我被顾临川逼着吞下整颗鸡蛋,过敏诱发哮喘,顾辞雪眼神都没给我一个。
我痛苦得抓着地毯要药,她一脚把我踹向墙角。
“这是小川最喜欢的地毯,弄断一根线我让你拿命赔。”
此刻,我趴在被刮烂的地毯上,笑声怎么也止不住。
围观的宾客眼神惊恐看着我,下意识后缩。
我挣扎着站起来,想去拉行李箱。
顾辞雪一脚踢翻箱子,踩住我被玻璃扎穿的手指,伤**裂,溅出一股血。
“我允许你走了么?”
下一秒,我像狗一样被他扯着衣领拖到顾临川面前。
破损的双膝在地面拖出两条长长的血痕。
但顾辞雪眼里只有委屈的养弟。
“怎么?还要我教你怎么做?”
冷硬的话语将我从愣神中扎醒。
习惯成自然,我端正地跪在顾临川身前,额头撞向地面。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三下沉重的闷声撞击后,额头红肿盖过了往日磕头留下的青紫。
我想不起来了,什么时候开始,磕头认错成了日常。
顾临川说菜好油,我要磕头。
顾临川不喜欢我穿蓝色,我要磕头。
顾临川看到了我们的结婚照不高兴,我要磕头。
但这次,顾临川依然不满意。
我木然地看着眼神挑衅的顾临川。
抬起手掌,左右开弓狠狠给了自己十个耳光。
脸颊**辣肿起,我侧头仰视顾辞雪,语气平静:
“顾总和顾少爷,高兴了吗?”
顾辞雪气笑了:
“许叙白你装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搞小动作,等爸妈回来告状!”
说完他嫌恶撞开我,扶顾临川回房。
我挣扎站起,走向后山。
听见后山轰隆的直升机声,螺旋桨翼从视线里出现,心上涌起狂喜。
突然,口鼻被捂住,**的气味袭来。
我失去意识,陷入昏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