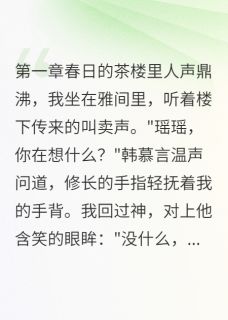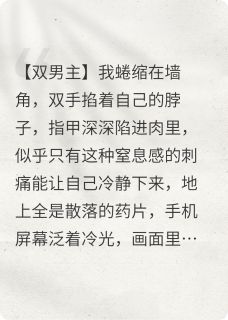2
谢挽风将我拖进房,拖出长长一道血线。
“看看你干的好事!”
他眼底猩红,众目睽睽下撕开我的衣襟,命人取来匕首。
那妇科圣手不忍地劝阻:“这位姑娘才淋了雨,寒气入体。”
“若此时取其心头肉入药,恐伤元气。”
“况且这只是民间传闻,并无真凭实据。”
“将军慎重啊!”
“不必再劝。”谢挽风死死按住我,“哪怕仅有一丝可能,也要保住灵儿腹中的孩子!”
他将匕首刺进我心口,却因为我拼命挣扎迟迟剜不下血肉。
“老实点,赫连喜。”
“谢挽风!”我拼命躲闪,“那是你的孩子,要救用你自己的命救,凭什么伤害我?”
“凭什么?”谢挽风声若寒冰,“你心思恶毒,竟在平安符做手脚,倒要问我凭什么?”
他将匕首又狠狠刺进一寸,“赫连喜,本将是在给你机会,为谢粼积德!”
“否则有这样一个阴毒的母亲,将来死后怕是都要下地狱!”
为粼儿积德?
我止住了挣扎,怔怔地想。
前些日子我连夜噩梦,梦到粼儿出事,梦到谢挽风提刀将我母子二人逼上刑场,又梦到我死后粼儿一个人孤零零在世间游荡。
我怕极了,才央求谢挽风放我出府,跪行九千九百九十九阶求来平安符。
可回到将军府,粼儿竟然死了。
是我的错,我应该把粼儿紧紧抱在怀里,不离开半步。
我闭上眼,任谢挽风动作。
谢挽风见此,皱了皱眉头,张张嘴想要说什么。
最终却也只是转动匕首,生生剜下我心口一大块血肉。
我咬紧牙关,喉间都泛起血腥味。
男人少见的语带怜惜,“阿喜,再忍忍,只要灵儿腹中孩子无事,便让谢粼入谢家宗谱。”
可是他已经死了。
我偏过头,不想再看他一眼。
心口血流如注,大夫正要给我包扎,榻上突然传来阮灵的低声**。
“将军,灵儿好疼。”
谢挽风立马将大夫拎去阮灵榻前,要求他为阮灵诊治。
大夫面带难色地告诉谢挽风,不及时包扎我很可能会失血过多死掉。
只片刻的犹豫,谢挽风冷声道:
“你是我请来为灵儿保胎的,不要多事。”
“可是......”
我打断大夫的劝阻。
“没事,你去吧。我可以走了吗?”
后半句话,我问的是谢挽风。
他脸上那点子犹豫立即消失,他皱眉冷斥道:
“灵儿的身体好起来之前,你哪里都不许去。”
他草草用纱布按住我心口,叫来管家,把我关进柴房。
柴房里,管家一脸怜悯地帮我解开绳子,而后勾起我的下巴。
“都说丹贡女子性子烈,我看倒是未必。”
“若是赫连夫人肯伺候小的,小的便帮您在将军面前美言几句,如何?”
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意思,我恶狠狠一口咬上他的虎口。
男人吃痛,当即甩了我一巴掌,啐骂两句锁上了柴房门。
整整一天,我再没吃到过一粒米。
膝盖和心口处的伤引起高热,烧的我昏昏沉沉,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草原的鹰。
我曾经也像它一样,自由自在。
来到这里,却被折损双翼,打断双腿,困在这方寸之地。
烈马似的性子也被磨平了。
幸好,幸好我马上就可以离开这地狱般的地方。
夜晚,柴房门被一脚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