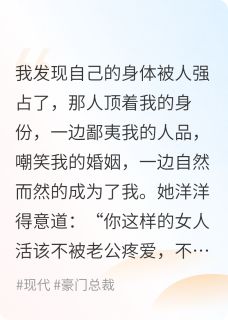心总是往府外飘,人便也放纵地往府外去。
我在醉仙居酒楼对面的茶馆徘徊了几日,也没瞧见那人的身影。
大概,刻意去见的人总是见不到的。
回府路上,我瞧见了一直瘸腿的小猫。
它后腿大约刚被马车碾过,露出一节白骨,地上有一滩不大的血迹。
它靠着墙躺在地上,对路过的人投去希冀的目光,又一次次失望。
我小心翼翼地抱起它,飞奔着去了最近的医馆。
一进门,那写药方的代笔小厮恰好抬眸,我们四目相接,是他。
他还记得我,笑得和煦:“是你啊,来医馆做甚,是你病了,还是家中有人病了?”
我被他的笑晃了心神,像枯涸已久的水井,突然涌入大方甘泉。
我努力掩饰心中的雀跃,抱着猫猫,走得他面前:“是它。”
医馆的学徒正在给猫猫包扎,我轻抚猫猫的脑袋安慰它,眼睛却总不自觉往正在写药方的他身上看。
他停笔时也会往我们这边看,若是一个不留神被他抓住我正在看他,他眼里的笑意便会更浓些。
我在医馆里磨磨蹭蹭,待到了医馆关门。
他却以为我全然是因为担心小猫,非常善解人意:“你若是不放心,便将猫儿放在医馆,我来照顾它。”
说不清楚是真为小猫好,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我将小猫寄养在医馆,留足了银钱。
我更有了借口日日去见他,出门前总是满怀期待,离别时总是满心惆怅。
他是一个顶好的人,连猫猫都喜欢粘他。
我每次去,猫猫总窝在他怀里睡觉。
明明碍着他写字了,他也不恼。
见我来,他便停下笔,将猫猫抱给我,那双眼睛清亮清亮的,和他名字——言清——一样干净,更讨人喜欢了。
待到猫猫痊愈那日,我才知道他本不住医馆,为了夜里留在医馆代我照顾猫猫,他每日工钱减半。
我心生愧疚,要补偿他,他也不客气地收了那些银两。
猫猫似乎察觉到离别的情绪,怎么也不愿意从他怀里出来。
他有些好笑,揶揄我:“这猫不会是你拐来的吧,怎的赖着我,不愿跟你走?”
我有些恼,这猫猫花着我的银子,却如此拆我的台,便一股脑将遇到猫猫的始末道出,似要他来评评理,这猫猫好不知恩。
他听了哈哈大笑:“猫可不知道何为衣食父母,倒是让我白占了便宜。”
他将猫猫放到地上:“让它自己来选择去处吧。”
最后,猫猫扭着猫步,一步三回头地看我,却跟着他回了家。
言清说:“你若是想它了,随时可以过来。”
他给了我一把,他家里的钥匙。
钥匙在手里十分滚烫,我的脸也红了,再也藏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