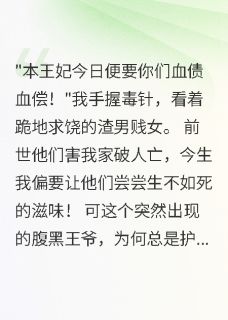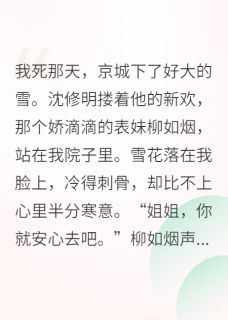听闻此话,现场喧嚣骤起,气氛紧绷。
宁母虽对宁砺棠多年寒心,此刻见女儿孤零零一人,仍忍不住起身,冷声道,
“今日是镇国公府的婚仪,还是市井泼皮的闹剧?宁家嫡女,哪里能被你们这样轻辱!”
话还没有说完,便有人嗤笑,
“哟,夫人好大的架子!大喜之日,热闹些有何不可?既入了国公府,便是府上人,咱们闹一闹,也是给她添‘福气’!”
另一人高声附和,
“就是!规矩礼教平日压得人喘不过气,今日松快些,夫人何必扫兴?莫非瞧不起咱们这些大族世家,不配与你商贾宁家同乐?”
宁母一时哑口无言。
那人顿了顿,讥讽更甚,
“再说了,若连这点玩笑都受不住,日后如何在国公府立足?咱们这可是在帮她‘历练’呢!”
宁母闻言,只觉眼前一黑,身形踉跄,幸得宁父及时扶住,才未倒下。
宁母暗地里扯了扯宁父的衣袖,示意他向国公爷说情。
宁父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正欲起身,却见高堂之上的国公爷已先一步开口。
“诸位放心!”
镇国公笑容满面,声如洪钟,
“既是小儿的婚礼,大家尽管尽兴,热闹些才好!”
说罢,他侧过头,对脸色铁青的宁家父母故作郑重道,
“亲家不必忧心,若小儿要有半分失礼之处,老夫定会命人将砺棠‘请’出笼子,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宁父闻言,喉头一哽。
若要失礼,哪里还来得及?这分明就没把他宁家女当一回事。
心中明了,却不敢多言。
宁家不过是世人最看不起的商贾,哪敢与正一品的国公爷争辩?
即便心如刀绞,也只能强忍苦涩。
此时,宁砺棠已被几个膀大腰圆的小厮半推半搡地押进了笼子。
宁母见状,心如刀割,泪水无声滑落,却只能死死攥住帕子,撇开头不忍再看。
宁心兰听闻,按住盖头摸索着连忙上前几步,
装出一副焦急模样,蹙眉轻叹,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姐姐怎会受这般委屈,这可如何是好…”
宁母强忍抽泣,轻轻拉过宁心兰的手,欣慰道,
“你是个好的,以后在镇国公府,你姐姐还得由你多照扶照扶。”
宁心兰语气温柔似水,
“母亲放心,到时哪怕姐姐不领情,打我骂我,我也定当尽力帮扶姐姐。”
宁母再一次欣慰地点头。
然而她不知,盖头之下的宁心兰却是唇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快意。
宁砺棠啊宁砺棠,你也有今日!
那边,宁砺棠被推进笼子,小厮便迅速落了锁。
席间众人屏息凝神,目光齐刷刷投向笼中,或猥琐窃笑,或满眼期待,或好奇张望。
笼内,家猪不安地踱步,蹄子踩在青砖上,“踏踏”作响,衬得气氛愈发诡异。
笼子虽宽敞,容纳两人一猪后仍有余地,却让宁砺棠感到逼仄压抑。
景颢魃仍旧是原先跪地的姿势,一动不动。
唯一不一样的是,他抬起头来看向了她。
那双眼睛漆黑如墨,漠然冰冷,像一把滚烫的钝刀,无声地在宁砺棠的脸上划割。
宁砺棠手臂上的汗毛一根根炸了起来,后背已然被冷汗浸湿。
直觉告诉她,他是“危险”,却又强撑着与他对视。
他银色长发披散,半边面容如玉雕琢,眉目如画。
搭配一席喜服,似九天谪仙坠入凡尘,又似一幅残缺的古卷,
美得惊心动魄,却透着难以言喻的破碎与孤寂。
而隐于发间的另一半脸,隐约可见烧伤……
当宁砺棠的视线刚移动向他的另一侧脸。
景颢魃的眼神骤然转冷,如同野兽领地受侵,透着森然警告。
同时,他的呼吸陡然粗重,喉间发出如兽类般低沉的嘶鸣,
似乎下一秒便会扑上来,咬断她的喉咙。
宁砺棠心头一紧,下意识护住脖颈,步步后退,
直至背脊抵上冰冷的木笼,才屏住呼吸,不敢再动分毫。
宁砺棠不知,景颢魃却在她退后的瞬间,微微偏过头,将烧伤的半边脸隐入发间。
她若见了那状似恶鬼的半边脸,定会如旁人一般惊叫着逃开。
所以,他不想她看。
如果她非要看,他会考虑与其面对她恐惧自己的模样,不如先杀了她。
那江湖人见景颢魃毫无动静,眉头微皱。
却仍强作镇定,扬声对众人道,
“诸位放心,我这虎狼之药乃世间极品,三秒起效,从未失手。景公子不过是在强忍,好戏还在后头!”
众人闻言,眼中期待更甚,纷纷翘首以盼。
可一盏茶、三盏茶、五盏茶过去,景颢魃依旧纹丝不动。
“这怪物油盐不进,真是无趣!”
有人嗤笑一声,兴致索然地摇头。
然而,距离最近的宁砺棠却看得真切。
景颢魃浑身颤抖,脖颈间青筋暴起,如藤蔓般蜿蜒爬升。
显然药效已发,他却硬生生扛了下来。
等她再细看时,瞳眸猛然一颤,像是被什么狠狠击中,连呼吸都窒了一瞬。
只见景颢魃为抵药效,五指成勾,竟朝身上伤口狠狠抓去,以痛楚强压欲望。
他身上的伤口本就深可见骨,此刻竟被他生生撕裂,血肉模糊。
痛楚稍一麻木,他便毫不犹豫地换一处新伤,指尖狠戳,甚至搅动。
宁砺棠站在几步之外,清晰听见皮肉撕裂的声响,却自始至终未闻景颢魃哼过一声。
但他的目光始终死死锁住宁砺棠,仿佛她是他维持理智的唯一执念,近乎偏执。
宁砺棠蹙眉,对他这般极度的隐忍既心生佩服,
同时,心底对他恐惧的峰值直接置顶,对待自己都如此残忍。
好在回忆前世,他与宁心兰成婚之后便从未归家,间接说明她熬过新婚夜就算通关。
但前世新婚夜,宁心兰还是差点死在这怪物手上,
那日,宁心兰浑身是血地逃出婚房,甚至废了一只手。
惊悸过后,疑惑涌上心头,致使她的眉越拧越紧。
他明明强大到足以杀光在场所有辱他之人,为何宁愿自伤,也不肯反击?
景颢魃似察觉她眉间微蹙,误以为嫌恶,
心中陡然涌起一股陌生的苦涩。
他不懂这情绪从何而来,
却知是因她而起。
那个从小女孩长成女子的她。
那个曾经总是微笑着看她,现在不止忘记他还嫌弃他。
他背过身去,再不让她瞧见自己的脸。
这种陌生的感觉令他厌恶,或许……
只有杀了她,才能彻底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