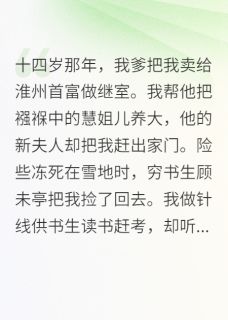
十四岁那年,我爹把我卖给淮州首富做继室。我帮他把襁褓中的慧姐儿养大,
他的新夫人却把我赶出家门。险些冻死在雪地时,穷书生顾未亭把我捡了回去。
我做针线供书生读书赶考,却听闻他中了探花,娶了公主。
慧姐儿气鼓鼓地嘟囔:「娘亲怎么总遇不到好人。」
我笑着捏捏她的小脸:「你秀才叔父又没娶我,怎么不是好人呢?」
破旧的木门夹杂着风雪被推倒,来人气冲冲:「谁说我没娶?」1我第一次见慧姐儿时,
她还是个满月大的女婴。蜡黄的小脸皱巴巴的,瘦瘦小小的一只。我那时也才十四岁,
父亲嗜赌成性,欠下淮州首富江宵的巨债,竟要把我卖给江家做这女娃的继母。
江宵本不想娶我,他母亲却见我逗弄慧姐儿的样子纯良,才答应了我爹。成婚那日,
江宵说我太小了,实在下不去手。于是我成了不用侍奉夫婿,
只用给慧姐儿换尿戒子的首富夫人。我娘生弟弟时我才八岁,爹娘下地干活,
我便在家照顾弟弟,照顾婴儿得心应手。江家老太太见我对慧姐儿无微不至,又没什么心眼,
对我十分满意,盼着我再长大些,给江宵生个儿子。一转眼慧姐儿三岁了,我也十七了。
打从我及笄起,老夫人就撺掇着江宵同我圆房。可大概是因为做名义夫妻久了,
我俩大眼瞪小眼,谁也迈不出第一步。老夫人戳着他的头说他没用,
末了还补上一句:「瞧你这没出息的,连媳妇都圆不了房,夫妻恩爱是假,
你心里惦记着已故夫人,这府里谁不知道?」江宵面子上过不去,灌了许多酒来我房里,
慧姐儿还在我怀里睡着。他把我拉到凉榻上就要亲我,我却只顾着推他胸膛:「小声些,
莫吵醒了慧姐儿。」他把我按倒,不耐烦地摆手:「知道了,你专心些。」
可他喝得实在太多了,这一晚竟没能成事。慧姐儿第二日杵着下巴问我:「娘亲,
你和爹爹昨夜在做什么呀?」江宵正好路过,我俩对视一眼,尴尬得想钻地缝。当天晚上,
江宵就让慧姐儿搬回自己屋子去睡。我和江宵磨蹭着吃完了老夫人送来的酒菜,
两人脸都红起来,我轻声打趣他:「夫君也不是头一回了,怎还这般害羞?」
他瞪我一眼:「蠢材,祖母给的酒菜里有**!」往日疼我的老夫人,这回差点害死我。
江宵太久没有行事,一朝开荤,那一夜我险些晕过去两回。第二天请安时,
老夫人看着我眼眶青黑,慧姐儿咬着软饼子鼓着脸,终于松了口气。
慧姐儿却还追着问我:「娘亲眼睛怎么乌青,爹爹昨夜打你了?」我与江宵互相看了一眼,
又尴尬了。圆房之前,江宵像个兄长,我带慧姐儿在府中小池塘捉鱼,
他会在一旁给我们递甜瓜。我们的风筝落在树上,他会爬树给我们取回来。
我们爬屋顶看星星,他就给我们扶梯子。圆房以后,他突然不许我做这些了。我知道,
他是想要个儿子。可我大概因为幼时养得不好,哪怕在江府养尊处优这么些年,一年过去,
还是没能怀上孩子。我觉得对不起他,他对我很好,我却不能替他生个儿子。
江宵知道我的心事,总是温声哄我:「阿梨别难过,我们还年轻,来日方长。」夫妻恩爱,
来日方长,我一直都是这么以为的。可男人竟是说变就变。江宵回来得越来越晚,
即便回来了,也大都在他自己的屋子睡。慧姐儿又搬回了我屋里。中秋节那日,
江宵吃过团圆饭便出了门。慧姐儿闹着要去放花灯,我便带她去了淮河畔。月影灯红,
远处一艘画舫上是两个人旖旎的身影。我抹了一把眼眶的泪,想抱慧姐儿走,
小姑娘却指着那画舫大声问我:「娘亲,那是不是爹爹?」周围的人看过来,
霎时明白了画舫上的人是谁。指指点点的议论声四起,我用衣袖挡住慧姐儿的脸,
逃也似的离开了河畔。首富江宵中秋夜会女子被正室和长女抓了现行。
淮州的大街小巷茶余饭后都在说这事,我半月没带慧姐儿出门。
慧姐儿问我:「爹爹不是很喜欢娘亲吗?为何不陪娘亲放灯,却抱着那个姐姐?」
原来孩子都以为他很喜欢我,在这之前,我也这么以为。丑闻传到老夫人那里,
她训斥我:「都是因为你生不出儿子,否则他何至于此。」那一刻我才明白,
老夫人对我所有的好,都不是因为真心喜欢我。可我从未说过不许他纳妾。
没过几日我便明白了,他想要的不是妾。那日我哄睡了慧姐儿,他突然来了。温存到半夜,
我热汗淋漓,想起来开窗透透气。他忽然说:「我打算娶陈县令的女儿为妻。」
窗外的风灌进来,我打了个寒噤,从头凉到了脚底。娶妻?那我算什么?
我淡淡应了他一声:「好,和离书还是休书,你给我一样便好。」
他却疑惑:「我何时说要与你和离?」「她入府为平妻,你本就不擅管家,
往后就让她替你分担。」我是乡野赌徒的女儿,如何能与县官老爷的女儿平起平坐。
即便我愿意,那陈**也定不会愿意的。可我没想到,他们竟情深至此。七日后,
江宵将人娶进了门。因是平妻,我不便观礼,但慧姐儿回来后同我说:「娘亲,
爹爹的新娘是那日画舫上的姐姐。」她不高兴地嘟囔:「爹爹让我叫她母亲,
我明明已经有娘亲了。」我替她擦汗的手一顿,却也只能对她说:「新娘子也是你的娘亲,
慧姐儿要听爹爹的话。」我原以为只要我忍让,日子便能过下去。可第二天午饭时,
新夫人坐在了我的位子上,对我道:「沈氏,夫君念旧情,才让你与我平起平坐,
但往后我才是江府主母,在府中你只算是妾。」我看了看老夫人和江宵,他们神色淡淡,
算是默许了。我站起身应道:「我知道了,主母。」妾是没资格上桌的,
我只能站在一边给慧姐儿布菜。慧姐儿憋着嘴就要哭,我哄她:「慧姐儿乖,娘亲不饿,
一会儿再吃。」没料我刚说完,新夫人就撂了筷子:「祖母,夫君,
这府中的规矩只怕得教教,我如今过了门,怎么还娘亲娘亲的摆不正自己的身份呢!」
我一愣,看向江宵,他瞥了我一眼,训斥慧姐儿:「你忘了昨日爹爹怎么跟你说的,
今后你只能喊她姨娘。」原来慧姐儿昨日只说了半句。他从未凶过孩子,今日新夫人才过门,
就惹哭了慧姐儿。往日对慧姐儿百般疼爱的老夫人冷眼旁观。我抱着慧姐儿离开了偏厅。
在江府生活了四年,惊觉这里并不是我的家。2我再也没有领着慧姐儿放风筝捉鱼。
主母要我带着她搬到偏院住,主屋的金银细软什么都没让带走。府中的人好似将我们忘了,
茶水糕点再也没有过,饭菜也是跟下人的一样。慧姐儿如今四岁了,已经懂得许多道理。
她陪我吃着冷饭冷菜,穿往年的旧衣服,有时会问我:「娘亲,为什么爹爹不来看我们,
也不给我们送新衣裳?」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孩子,只能说:「爹爹有很多事要忙,
等闲下来便会来了。」后来她不再问了,似乎知道了爹爹不会闲下来的。因为主母有了身孕。
看样子,是画舫那日便有了。我曾疑惑,即便是厌了我,也不该如此对待慧姐儿,
原来是这样。我与慧姐儿在偏院住到了入冬,炭火迟迟没有送来。我可以捱着,
但慧姐儿毕竟是江府的长女。于是我去见了主母,想问问能不能送些炭火过去。
主母的屋子里烧得暖烘烘的,小几上摆着各色糕点。听了我的请求,
她冷冷一笑:「一个乡野来的女人,一个死人留下的女儿,也配用炭火么。」
她泼了我一杯茶,把我赶了出来。恰巧江宵来了,我抱住他的腿,
希望他能念着情分替我们说句话。他蹲下来,用手替我抹掉脸上的茶渍:「回去吧,
一会儿我让人送炭过去。」他掀开门帘进去,我却听到他柔声问主母:「阿柔,
今日孩儿可有闹你?」傍晚终于有人送了炭来,是呛人的黑炭,从不在屋里烧的。
我在院中点了炭,将被子烘得暖暖的再拿进屋里给慧姐儿披上。慧姐儿窝在我怀里,
有些难过:「娘亲,我是不是要有小弟弟了?」我摸摸她的头发说:「是啊,
等母亲生了小弟弟,你多去她跟前走动,哄哄弟弟玩儿,母亲便会喜欢你,
兴许会把你带在身边。」她小小的脸上挂着倔强:「她才不是我母亲,我只有娘亲。」
她忽然往我怀里钻了钻:「其实我知道,你也不是我亲娘。」我愣住了,
从她在襁褓中就是我亲手带的,守着乳母喂奶,给她换尿戒子,给她洗澡穿衣。
瘦瘦小小的婴儿,带到如今,府中从未有人提过她的生母。
我笑着问她:「慧姐儿不喜欢娘亲了吗?」小丫头摇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是,
我最喜欢娘亲,我不是你生的,你还对我这样好。」我疑惑:「是谁同你说你不是我生的?」
「有一回我去爹爹书房玩,看到他藏起来的画像,他说那是我的亲娘。」
慧姐儿想了想说:「爹爹说,他最喜欢的便是我的亲娘。」头一次,
我对江宵故去的第一个夫人有些好奇。3到了腊月,听送饭的小丫鬟说,江宵想纳妾,
主母同他闹了一场,差点掉了孩子。我猜测大概是因为主母怀有身孕不能同寝。
可慧姐儿的生母亡故后,我进门那三年,江宵夜夜都在自己屋里睡,又是怎么忍过来的?
想起慧姐儿说的话,我想是因为他当时还念着发妻。年少的感情最是美好,那人去了,
后面的人都成了将就。江宵从前或许也是个痴情的男子,可他如今也成了个世俗的男人,
看他对慧姐儿的态度便知。他的深情和良心都跟着慧姐儿的娘一起走了。江宵与主母闹,
我与慧姐儿遭殃。近来没人给我们送炭火,连吃食也断了。我带着慧姐儿去找江宵,
得知他出了远门,老夫人早已不管事了,便只能去见主母。主母没有让我们进门,
只是说我们事多,若觉得江府不好,便出去自谋生路。她让身边的嬷嬷把我们撵出了门。
寒冬腊月,我与慧姐儿穿着薄棉的衣裳,无处可去。我带她往城外走,那里有一间破庙,
至少能挡住风雪。可慧姐儿着了寒,还没走到城外便发了惊热。我抱着她在雪地里跑,
想去找大夫。可那雪太深了,我抱着慧姐儿根本走不快。有人路过,看见是我,都啧啧叹息,
却没有一人愿意帮我。我抱着高热的慧姐儿在雪地里哭。很多年前,我也是这么抱着弟弟,
看着弟弟一点点没了气息。我爹染上赌瘾,娘跑了,留下我和弟弟。我爹要把弟弟卖了,
却发现他得了天花,就让我把他丢掉。我看着慧姐儿通红的脸,恨死了江宵,
就像幼时恨我爹一样。慧姐儿摸摸我的脸:「娘亲,我看到我的亲娘了,跟画上一模一样。」
我慌了,大声地喊她:「慧姐儿!你看看娘亲,那不是你娘,我才是,你不许跟她走!」
她的额头越来越烫,再也不回应我。我也再也流不出泪,
只能抱着她默念:「慧姐儿不怕不怕啊,你同你的亲娘去吧,娘亲一定回江府,让他们偿命!
」恍惚间耳畔传来一个声音:「夫人?」我欣喜地抬头,看到的却不是江宵,
是一个陌生男子,披着蓑衣斗笠来到我们身边。他从我怀里抱起慧姐儿,问我:「还能走么?
」我点头,起身时却一个踉跄,我的腿已经冻得麻木了。那人皱了皱眉,
将慧姐儿单手扛在肩上,另一只手搀着我,稳稳地往前走。他的家就几步远,
他将我扶进屋子,扯了被子给我盖住腿,用毯子裹住慧姐儿转身出去了。等他们回来,
慧姐儿已经退了高热,在他怀中酣睡。我接过孩子,差点落泪。他脱了蓑衣和斗笠,
坐下喝了杯热茶才问我:「你是江府的……主母?」4我苦笑,
如今淮州还有谁不知道我离下堂妻只差一纸休书。他看了我怀中的慧姐儿一眼,
微微叹了口气:「你们怎么……」心酸往事,我不想再提,但慧姐儿尚在病中,
我只能求他:「郎君能否收容我们几日,待我找了生计,就带慧姐儿走。」他抿抿唇,
扫视了一圈屋子,目光最终落在角落的空地上:「我这里也就这么大,若你不在意,
我便在那里搭张床睡,用布帘子隔开。」遇到好人了,我与慧姐儿总算不用再受冻。
他说他叫顾未亭,是个秀才,家中父母双亡,自己在郊外的军营给军士写家书,挣些散钱,
如今还没有凑够上京参加秋闱的盘缠。夜里慧姐儿又发了热,一直说胡话。我给她喂水,
又拧了帕子给她擦身上,折腾到半夜也不见退。我怕吵着顾未亭休息,只能压着嗓子哭。
他还是听到了,起身披了衣服出去,捧了团雪回来:「用帕子包着雪,给她擦额上和脖子。」
见我不解地看着他,他憨厚地笑笑:「今天带慧姐儿去扎针时大夫教我的,
退烧的药材太贵了,我没带那么多钱。」慧姐儿的烧终于退了,我俩都睡不着,
便守在床边说话。我有些愧疚:「我一个妇人带着孩子住在你家,只怕你来日不好说亲的。」
他无所谓地笑笑:「日行一善,又无逾矩,若对方计较,那也是不能结亲的。」
我又说:「何况本就无人愿意嫁我这一无所有的秀才,你不必自责。」
我眼下只能说些好话报答他:「来日你必定高中,到时候定能娶个公主。」他失笑:「好,
借你吉言。」5我不好在城中找活计,怕遇上江府的人。
顾未亭便帮我在军营里寻了个缝缝补补的活。他又担心我是女子,出入军营不便,
每日将要缝补的衣裳带回来,等我缝补好了他又送回军营去。我与慧姐儿就这么住了下来。
如今我与顾未亭都能挣些散钱,但我与慧姐儿吃的并不多,正月过后,
我又在小院中开了地种菜。男人不会持家,从我来后,顾未亭便把钱交给我管。两个月下来,
竟也有了盈余。我又养了些母鸡,等下了蛋可以进城去卖。我盘算着等中秋时,
便能攒到银两给顾未亭上京赶考了。慧姐儿很喜欢顾未亭,像个小尾巴,整日里「叔父叔父」
地喊。有一日顾未亭带她去军营玩,回来时,我听到慧姐儿喊他「爹爹」。我吓了一跳,
忙对她说:「不能这么喊,让人听到了,你叔父可如何说亲呢!」
慧姐儿小声道:「我们每日一同吃饭睡觉,他还会带我去雪地里捉兔子,
从前爹爹不就是这样么。」我被她「一同睡觉」说得脸红,
忙跟顾未亭道歉:「你别听小孩子瞎说,我一定让她再不那么喊了。」
顾未亭帮我叠缝补好的衣裳,烛光下看不清神色,只听他说:「小孩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