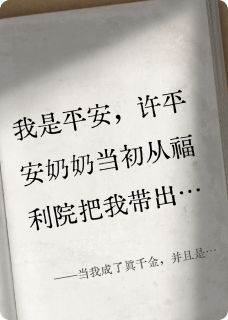第一章:梨园初遇春日的风掠过宫墙,卷起一阵雪白的梨花雨。柳如眉提着沉甸甸的药箱,
低头快步穿过御花园的九曲回廊。她刚刚为太子妃施完针,
指尖还残留着艾草燃烧后的苦涩香气。"脚步放轻些,惊了贵人你可担待不起。
"引路的老嬷嬷回头瞪了她一眼。柳如眉将头垂得更低,
青石板上的花瓣被她匆匆的脚步碾碎,渗出几丝清甜的汁液。这是她入宫第三个月,
太医院最低等的医女,连走路的声响都要被挑剔。转过一道爬满紫藤的月洞门,
前方忽然传来朗朗的读书声。柳如眉本能地往道旁避让,却不慎踩到湿滑的花瓣,
药箱脱手而出——一双手稳稳接住了坠落的药箱。"《本草纲目》?
"清越的男声在头顶响起,"你是医女?"柳如眉慌忙跪伏在地,
额头几乎贴到冰冷的石板上。"奴婢参见太子殿下。""起来说话。"那人虚扶了一下,
"药箱里的书都翻旧了,你常读?"柳如眉这才敢微微抬眼。
太子赵景恒一袭月白锦袍立于梨树下,玉冠束发,眉目如画。
他手中正捧着她那本做了密密麻麻批注的《本草纲目》,
阳光透过花枝在他俊逸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回殿下,奴婢...略通皮毛。
"赵景恒翻到折角的一页,"三七止血,须用新根,你说'陈年者反增淤血',
太医院那些老头子可不这么认为。"柳如眉心头一跳。这是她父亲生前的独到见解,
她冒险写在批注里,没想到被太子一眼识破。"奴婢...家父曾...""你父亲是大夫?
"太子目光如炬。柳如眉咽下了后半句话。十年前父亲被处死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
血染红了太医院的青砖地。"只是...乡野郎中。"她声音细如蚊呐。
一片梨花落在太子手中的书页上。他轻轻拂去,忽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柳如眉。""柳如眉..."太子将这名字在唇齿间细细品味,
"可是取自'柳叶眉间发,桃花脸上生'?"柳如眉惊讶地抬眼,正对上太子含笑的眸子。
那一瞬间,她仿佛看见了星辰大海——这深宫之中,竟有人能道出她名字的出处。
"殿下博学,正是此意。"她忘了规矩,唇角不自觉扬起一丝笑意。
老嬷嬷在后面狠狠扯她衣袖。太子却浑不在意,将书放回药箱,
"本宫近日研读《黄帝内经》,有些疑难不解。太医院那些老学究,
开口闭口都是'古法不可违'。"他顿了顿,"明日午时,来东宫书房。"柳如眉呆立原地,
直到太子的背影消失在花径尽头,才发觉手心已沁出细密的汗珠。"贱婢好大的胆子!
"老嬷嬷一巴掌扇在她脸上,"谁准你直视太子?谁准你妄议医理?"柳如眉跪着承受责打,
却忍不住望向太子离去的方向。风又起了,满树梨花纷纷扬扬,像一场不合时宜的春雪。
回到下等医女聚居的耳房,柳如眉从枕下摸出一方褪色的绣帕。
那是她唯一从家里带出来的物件,帕角绣着一株柳树,是母亲生前最后一针。
十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夜晚,她躲在药柜里,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拖走,
母亲哭晕在地再没醒来。"柳丫头,发什么呆?"同屋的李医女推门进来,
"听说你今天见到太子了?"柳如眉慌忙收起绣帕,"只是...碰巧...""小心些吧。
"李医女压低声音,"崔太子妃最恨年轻医女接近太子,上月刚打死一个送药的。
"烛火噼啪作响,柳如眉摩挲着药箱上的刻痕。父亲临终前的话言犹在耳:"如眉,
医术可救人,亦可杀人。这深宫里的病,大多不是用药能治的..."次日午时,
柳如眉战战兢兢地站在东宫书房外。两个带刀侍卫审视着她粗布衣裙上补丁,眼中满是轻蔑。
"进来。"太子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推开门,满室书香扑面而来。赵景恒正伏案疾书,
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案几上摊开的正是那本《柳氏医案》——父亲毕生心血,世间仅存三册。"殿下怎会有此书?
"话一出口柳如眉就后悔了。太子笔锋一顿,墨汁在宣纸上晕开一片。"偶然得之。
"他抬头直视柳如眉,"听闻柳太医医术冠绝天下,可惜..."柳如眉心跳如鼓。
太子知道她的身世?这是试探还是..."你会针灸?"太子突然转了话题。
"家父在世时曾悉心教导。"赵景恒揉了揉太阳穴,"本宫近日头痛难忍,
太医院开的药苦得反胃。"柳如眉犹豫片刻,轻声道:"若殿下不嫌,奴婢可一试。
"得到首肯后,她取出随身携带的银针。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礼物,
针尾刻着细小的柳叶纹。站在太子身后,她能闻到他发间淡淡的龙涎香,
混合着墨与纸的清冽气息。"请殿下放松。"她深吸一口气,
指尖轻轻按在赵景恒的太阳穴上。这是她第一次触碰这位尊贵的男子,他的皮肤温热,
肌理紧致,却在穴位处绷着不自然的硬结。银针精准刺入,赵景恒微微皱眉。"会有些酸胀,
请殿下忍耐。"柳如眉声音轻柔如春风。她转动针尾,感受着气机的流动。父亲说过,
最高明的针灸师能通过银针感知病人的情绪。此刻,
她感受到的是深重的疲惫与孤独——这竟与她自己如出一辙。三针过后,
赵景恒长舒一口气:"妙手。比太医院那些老头子强多了。""还需再施三次,方可根治。
""那便每日此时过来。"太子语气不容拒绝,"带上你的《本草纲目》。"离开东宫时,
柳如眉在转角处撞见一个华服妇人。崔太子妃冷冷扫视着她,
目光如刀般刮过她朴素的衣裙和手中的药箱。"区区医女,也配进太子书房?
"太子妃的声音像淬了毒的蜜,"小心针扎错了地方,要了你的小命。"柳如眉深深福礼,
却在低头时看见太子妃腕间露出一截狰狞的疤痕——那是长期服用某种毒药留下的痕迹。
她心头一震,忽然明白了太子头痛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
太医院首座徐太医站在远处的楼阁上,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他转身对阴影中的人影低语:"去禀报丞相,柳元之女...入宫了。
"第二章:银针定情夜雨敲窗,东宫的烛火在风中摇曳。柳如眉跪坐在偏殿的矮案前,
指尖轻轻翻动着《本草纲目》的泛黄书页。窗外雷声隐隐,她拢了拢单薄的衣衫,
思绪却飘回白日里太子那双含笑的眼睛。“柳姑娘。”门外传来内侍恭敬的声音,
“殿下传您过去。”她一怔,连忙合上书卷:“这么晚了?”“殿下突发高热,
太医院的人束手无策。”柳如眉心头一紧,顾不得多想,抓起药箱便随内侍匆匆穿过回廊。
雨丝斜斜地打在她的衣袖上,寒意渗入肌肤,却抵不过她胸腔里那颗越跳越快的心。
东宫内殿,灯火通明。赵景恒躺在床榻上,面色潮红,额上覆着一层细密的冷汗。
几位太医围在床前,低声争论着用药,却无人敢贸然施针。“殿下!”柳如眉快步上前,
顾不得行礼,直接伸手搭上他的脉搏。脉象沉而急促,指尖触及的肌肤滚烫如火。
“寒邪入体,郁而化热。”她蹙眉,迅速从药箱中取出银针包,“需立刻放血泄热,
否则热毒攻心,恐有性命之忧。”“放肆!”太医院首座徐太医厉声呵斥,“殿下千金之躯,
岂容你胡乱施针?”柳如眉指尖微颤,却仍坚持道:“殿下高热不退,再耽搁下去,
只会加重病情。”床榻上的赵景恒微微睁开眼,目光涣散,却在看到她时稍稍聚焦。
“……让她……试试……”他嗓音沙哑,艰难地抬了抬手。柳如眉深吸一口气,
指尖捏着银针,轻轻刺入赵景恒的合谷穴。针尖刺破肌肤的瞬间,他的手指微微蜷缩,
却并未抽回。她稳住心神,又在他曲池、大椎等穴位上施针,动作又快又准,
每一针都恰到好处地引动气机。殿内静得落针可闻,只有烛火偶尔爆出一声轻响。三针过后,
赵景恒的呼吸渐渐平稳,高热也退了几分。柳如眉额上沁出细汗,却不敢松懈,
又取出特制的药粉,用温水化开,小心翼翼地喂他服下。“殿下,再忍忍。”她低声道,
指尖不经意间擦过他的唇,两人皆是一怔。赵景恒的目光落在她脸上,昏黄的烛光下,
她的眉眼如画,眸中盛着毫不掩饰的担忧。他忽然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腕。“殿……殿下?
”柳如眉一惊,下意识想抽回手,却被他握得更紧。“别走。”他声音低哑,
带着病中的虚弱,却不容拒绝。她怔住,心跳如擂鼓。三日过去,赵景恒的病情终于好转。
柳如眉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他榻前,熬药、施针、换药,连眼都未曾好好合过。
直到第四日清晨,太医诊脉后终于露出笑容:“殿下热毒已清,只需静养几日便可痊愈。
”柳如眉长舒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眼前一阵发黑,险些栽倒。
一双手稳稳扶住了她的肩膀。“你也该休息了。”赵景恒不知何时已坐起身,
眸色深沉地看着她苍白的脸色。她慌忙退后一步,低头行礼:“殿下无碍,奴婢便放心了。
”他沉默片刻,忽然道:“你救了本宫的命。”柳如眉摇头:“奴婢只是尽了本分。
”“本分?”他轻笑一声,“太医院那些人,可没一个敢像你这样冒险。”她抿唇不语,
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银针包上的纹路。赵景恒的目光落在她手上,
忽然道:“这银针……是家传的?”柳如眉指尖一顿,低声道:“是家父留下的。
”“你父亲……”他似是想问什么,却终究没再继续,只是淡淡道,“从今日起,
你留在东宫,做本宫的专属医女。”她猛地抬头:“殿下?”“怎么,不愿意?”“不,
奴婢只是……”她声音渐低,“怕不合规矩。”赵景恒唇角微扬:“在这东宫,本宫的话,
就是规矩。”消息很快传遍宫廷。一个低等医女被破格提拔为太子专属医女,
还赐居紫竹院——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事。柳如眉搬入紫竹院那日,李医女拉着她的手,
既羡慕又担忧:“柳丫头,你可要小心些,崔太子妃那边……”她苦笑:“我知道。
”可即便知道前路艰险,她仍忍不住心生欢喜。东宫的书房里,赵景恒批阅奏折时,
她便在角落的矮几前研读医书,偶尔他抬头问一句药理,她便轻声回答。有时他倦了,
她便煮一盏安神茶,两人隔着袅袅茶香,竟也能聊上许久。一日午后,她正低头整理药材,
赵景恒忽然走到她身旁,伸手捻起一味草药。“这是什么?”“当归。”她答道,
“补血活络的。”他指尖摩挲着药草,忽然道:“听说……当归的寓意,是‘应当归来’?
”柳如眉一怔,耳尖微微发热:“民间……是有这样的说法。”赵景恒垂眸看她,
忽然轻笑:“那日后若有人赠你当归,你可要记得回来。”她心跳漏了一拍,
抬头正对上他的眼睛。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过咫尺,呼吸交错间,药香弥漫。柳如眉慌忙低头,
却听见他低声道:“如眉,留在本宫身边。”不是命令,而是请求。窗外的风吹动书页,
沙沙作响,却掩不住胸腔里那颗剧烈跳动的心。然而,宫墙之内,暗流涌动。
太医院首座徐太医站在丞相苏远山面前,低声道:“大人,那柳如眉……恐怕不简单。
”苏远山眯起眼:“哦?”“她用的针法,属下从未见过,但……”他压低声音,
“很像十年前柳元的手法。”苏远山指尖一顿,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柳元的女儿?
”“属下不敢确定,但……”“查。”苏远山冷冷道,“若她真是柳元之女,绝不能留。
”与此同时,崔太子妃的寝宫内,一盏茶被狠狠摔在地上。“贱婢!”她咬牙切齿,
“区区医女,也敢勾引太子!”身旁的心腹宫女低声道:“娘娘,
要不要……”崔太子妃冷笑:“不急,本宫倒要看看,她能得意到几时。”窗外,暮色沉沉,
一场风暴正在酝酿。而紫竹院内,柳如眉浑然不知危险将至,只是低头绣着一方锦帕,
帕角一株梨花,悄然绽放。第三章:锦帕传情夏至宫宴,蝉鸣聒噪。
柳如眉站在最末席的角落,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中的银针包。
这是她成为太子专属医女后第一次参加宫廷宴席,可身份所限,
她只能与最低等的宫女们挤在一处,连面前的果盘都比旁人少了一半。“听说就是她,
用银针救了太子殿下?”“长得也不怎么样嘛,
太子殿下怎么会……”细碎的议论声飘入耳中,柳如眉低头抿了一口清酒,
喉间泛起一丝苦涩。忽然,殿内一阵骚动。太子赵景恒一袭月白锦袍踏入殿中,
身姿挺拔如松,眉目间带着与生俱来的矜贵。众臣纷纷行礼,他却径直走向御前,
向皇帝请安后,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末席。柳如眉慌忙低头,
却仍感觉到那道视线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今日宴饮,不必拘礼。”皇帝含笑抬手,
示意众人入座。乐声起,舞姬们翩跹而至,水袖翻飞间,
柳如眉的目光却总忍不住瞥向主位——赵景恒正与几位大臣交谈,神色淡然,偶尔举杯浅酌,
一派从容。“柳医女。”一名宫女忽然走到她身旁,低声道,“太子妃娘娘请您过去。
”柳如眉心头一跳,抬眼望去,只见崔太子妃端坐在太子身侧,妆容精致,
唇边噙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柳如眉缓步上前,恭敬行礼:“奴婢参见太子妃娘娘。
”崔太子妃垂眸看她,指尖轻轻敲着案几:“听闻你医术精湛,
连太医院的老先生们都自愧不如?”“娘娘谬赞,奴婢只是略通皮毛。”“是吗?
”崔太子妃忽然伸手,端起一盏热茶,“本宫近日手腕酸痛,你既会针灸,
不如也替本宫看看?”话音未落,她手一歪,滚烫的茶水径直朝柳如眉泼来!
柳如眉本能地侧身一避,却仍被溅湿了衣袖。灼热的痛感瞬间从手臂蔓延,她咬唇忍住痛呼,
却听见周围一片惊呼——“殿下!”赵景恒不知何时已离席,大步走到她身旁,
一把扣住她的手腕。被烫伤的肌肤红肿一片,在素白的衣袖映衬下格外刺目。
他的眼神骤然冷了下来。“太子妃。”他声音不高,却字字如冰,“手抖得这么厉害,
可是病了?”崔太子妃脸色微变:“臣妾只是……”“既然病了,就该好好休养。
”赵景恒打断她,转头对柳如眉道,“随本宫来。”众目睽睽之下,他拉着柳如眉离席,
留下一殿哗然。偏殿内,赵景恒亲自取了药膏,轻轻涂在柳如眉的伤处。“疼吗?”他问。
柳如眉摇头,却在他指尖碰到伤处时忍不住轻颤。赵景恒动作一顿,抬眼看她:“逞强。
”她抿唇不语,心跳却因他的靠近而乱了节拍。他的眉目近在咫尺,
长睫垂下时投下一片阴影,鼻息拂过她的手腕,微热,微痒。“殿下不该这样。”她低声道,
“奴婢不值得您……”“值不值得,本宫说了算。”他打断她,语气不容置疑。药膏清凉,
渐渐缓解了灼痛。柳如眉垂眸看着自己的手腕被他握在掌心,
忽然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深宫之中,最危险的不是刀剑,而是人心。”她悄悄抬眼,
却正对上赵景恒深邃的目光。那一瞬,她恍惚觉得,自己似乎坠入了更危险的深渊。
夜深人静,柳如眉回到紫竹院,才发现案几上多了一个锦盒。打开一看,
竟是一枚雕着并蒂莲的白玉玉佩,玉质温润,在烛光下流转着柔和的光泽。
玉佩下压着一张字笺,上面只有一行小字——“赠如眉,愿君心似莲,不染尘泥。
”笔迹清峻,是赵景恒的手笔。柳如眉怔怔地看着玉佩,胸口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意。
她摩挲着玉上的纹路,忽然想起什么,从枕下取出一方素白锦帕。
这是她偷偷绣了许久的——帕角一株梨花,花瓣细密,花蕊处还缀了一粒小小的珍珠,
宛如晨露。她提笔,在帕角题下一行小诗:“深宫寂寂月如霜,谁解银针度夜长。
愿作君心枝上雪,不教尘埃落华裳。”墨迹干透后,她将锦帕折好,
交给一直暗中帮衬她的宫女小桃:“明日……悄悄送到东宫。”小桃会意,
抿嘴一笑:“姑娘放心。”翌日清晨,柳如眉刚推开房门,
便看见崔太子妃的心腹嬷嬷立在院中,面色阴沉。“柳医女,太子妃娘娘召见。
”柳如眉心头一紧,下意识摸了摸袖中的银针,这才跟着嬷嬷去了太子妃寝宫。
殿内熏香浓烈,崔太子妃斜倚在软榻上,指尖把玩着一只玉杯。“跪下。”她懒懒道。
柳如眉跪伏在地,额头抵着冰冷的地砖。“听说,你昨夜给太子送了东西?”崔太子妃冷笑,
“一方绣帕?还题了诗?”柳如眉浑身一僵——小桃被发现了?“贱婢!
”一只茶杯狠狠砸在她肩头,热茶浸透了衣衫,“你以为攀上太子就能飞上枝头?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柳如眉咬牙不语,肩头的灼痛却比不上心中的寒意。
崔太子妃起身,居高临下地睨着她:“本宫今日就让你明白,这深宫里,谁才是主子。
”她拍了拍手,两名粗使嬷嬷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架起柳如眉——“拖去慎刑司,杖二十。
”慎刑司的板子落在身上时,柳如眉死死咬住唇,不肯发出一声痛呼。父亲说过,
太医的女儿,骨子里该有傲气。打到第十板时,她已意识模糊,
却恍惚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侍卫们慌乱的阻拦声——“殿下!您不能进去!
”“滚开!”赵景恒的声音如同惊雷炸响。下一瞬,刑杖声戛然而止。柳如眉艰难地抬眼,
朦胧视线中,只见赵景恒一身朝服未换,显然是刚下朝便赶了过来。他脸色铁青,
眼中翻涌着滔天怒意,一把推开行刑的嬷嬷,将她打横抱起。“殿下……”她气若游丝,
“奴婢……脏了您的衣裳……”赵景恒手臂收紧,声音沙哑:“闭嘴。
”他抱着她大步离开慎刑司,所过之处,宫人纷纷跪伏,无人敢抬头。柳如眉靠在他胸前,
听见他心跳如鼓,一声声震着她的耳膜。恍惚间,她似乎听见他说——“如眉,
本宫绝不会再让你受委屈。”紫竹院内,太医们进进出出,煎药的气息弥漫了整个院子。
赵景恒坐在床畔,亲自喂柳如眉喝药。“殿下……”她轻声问,
“那方锦帕……”“本宫收到了。”他淡淡道,“诗写得很好。”柳如眉耳尖微热,
却见他忽然从袖中取出那方锦帕——只是原本素白的帕子,如今沾了一角血迹。
“慎刑司的人弄脏了它。”赵景恒眸色阴沉,“本宫已命人杖毙了那两个嬷嬷。
”柳如眉心头一震。“至于崔氏——”他冷笑一声,“她父亲是兵部尚书,
本宫暂时动不得她。但迟早有一日……”话未说完,柳如眉却已明白他的意思。
她轻轻握住他的手指:“殿下,不必为奴婢树敌。”赵景恒反手将她指尖拢入掌心,
一字一句道:“如眉,在这深宫里,你是唯一让本宫觉得真实的人。”窗外,夏雨骤至,
打落了满庭梨花。第四章:宫墙密约秋日的风卷着枯叶扫过宫墙,柳如眉站在紫竹院的廊下,
指尖轻轻抚过腰间的并蒂莲玉佩。距离那日慎刑司的杖刑已过去半月,她的伤渐渐痊愈,
可宫中的暗流却愈发汹涌。崔太子妃被禁足,朝臣们议论纷纷,
连带着她这个“祸水”也成了众矢之的。“姑娘,风大了,回屋吧。”小桃捧着药碗走来,
眼里满是担忧。柳如眉摇头,目光落在远处巍峨的宫门上——那里,
一队铁甲侍卫正策马而入,马蹄声如雷,惊起一群寒鸦。“出什么事了?
”小桃压低声音:“北境八百里加急军报,说是戎族破了雁门关,
陛下急召太子殿下和诸位将军议事。”柳如眉心头一紧,指尖无意识地攥紧了玉佩。
三更时分,东宫的书房仍亮着灯。柳如眉端着安神茶站在门外,
听见里面传来激烈的争论——“殿下,此去凶险,您乃国之储君,岂可亲征?
”“雁门关一破,戎族铁骑可直逼京城!本宫不去,谁去?”赵景恒的声音冷如寒铁。
茶杯在她手中微微发颤,几滴热茶溅在手背上,她却浑然不觉。门忽然开了。
几位将军鱼贯而出,见到她时皆是一怔,随即低头匆匆离去。最后出来的徐太医瞥了她一眼,
目光阴沉如毒蛇。柳如眉垂眸行礼,待众人走远,才轻轻推门而入。书房内,
赵景恒背对着门站在沙盘前,烛火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孤寂而锋利。“殿下。”她轻唤。
他转身,眉宇间的肃杀之气在看到她时稍稍缓和:“这么晚,怎么还不休息?
”“听说您要出征……”她将茶放在案上,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赵景恒沉默片刻,
忽然伸手抚上她的脸颊:“担心本宫?”他的掌心粗粝温热,带着常年握剑留下的薄茧。
柳如眉睫毛轻颤,却不敢躲开,只低声道:“殿下万金之躯……”“嘘。
”他指尖抵住她的唇,“这里没有太子,也没有医女。”烛火噼啪一声,爆出一朵灯花。
五日后,大军开拔在即。整个皇城笼罩在肃杀之中,连秋日的阳光都显得惨淡。
柳如眉站在太医院的高台上,望着远处校场上黑压压的军队。赵景恒一身玄甲,
立于万军之前,如出鞘的利剑。“姑娘,该去送药了。”小桃在身后提醒。
柳如眉深吸一口气,拎着药箱走向东宫——这是她最后一次为太子请脉。可刚到宫门,
她就被侍卫拦下:“殿下有令,今日不见任何人。”她怔在原地,
却见太子的贴身内侍匆匆走来,塞给她一个锦盒:“殿下让交给姑娘的。
”盒中是一支白玉簪,簪头雕成梨花模样,花蕊处嵌着一粒明珠,
在阳光下流转着柔和的光晕。“殿下还说……”内侍压低声音,“今夜子时,御花园老地方。
”月上中天,御花园的梨树下,一道颀长的身影负手而立。柳如眉裹着素色斗篷,
脚步轻得像猫。可还未靠近,赵景恒便转过身来,玄色披风在风中猎猎作响。“来了?
”他唇角微扬。她刚要行礼,却被他一把拉入怀中。
清冷的龙涎香混着铁锈般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战甲的味道。“殿下,
这不合规矩……”她慌乱地推拒。“规矩?”赵景恒低笑,“本宫明日就要上战场了,
还管什么规矩?”他的手臂如铁箍般收紧,下颌抵在她发顶,声音忽然哑了下来:“如眉,
等我回来。”柳如眉鼻尖一酸,从袖中取出一个绣着梨花的香囊,
轻轻塞进他手中:“里面……有奴婢的一缕头发。”赵景恒打开香囊,只见青丝如墨,
缠绕着一片干枯的梨花瓣。他眸色一暗,忽然拔下她发间的木簪,
将那支白玉梨花簪插入她的发髻。“以此为誓。”他低头,在她耳边轻语,“待我凯旋,
必不负卿。”他的呼吸灼热,烫得她耳尖发红。夜风卷着落叶从两人之间穿过,
却吹不散那纠缠的气息。远处传来更鼓声,子时已过。赵景恒松开她,
从怀中取出一块令牌:“我不在时,若有人为难你,持此令可直入御前。”令牌冰凉沉重,
正面刻着“如朕亲临”四个大字。柳如眉手一抖,险些将它摔在地上——这是天子御令,
见令如见君!“殿下,这太贵重了,奴婢……”“收好。”他打断她,语气不容置疑,
“还有,离崔氏和苏远山远些。”“苏丞相?”她一愣,“为何……”话音未落,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殿下!”太子的亲卫跪在十步开外,声音紧绷,“陛下急召,
说是戎族使者到了,要求和亲!”赵景恒脸色骤变。柳如眉心头猛地一沉——和亲?
太子尚未娶正妃,若戎族要的是皇室公主……“你先回去。”赵景恒匆匆替她系好斗篷,
指尖在她颈后微微一滞,“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别做傻事。”他的眼神太过复杂,
柳如眉还未来得及细想,他已转身大步离去,玄色披风很快融入夜色。三日后,
一道圣旨震惊朝野——戎族退兵的条件,竟是要大周太子迎娶丞相苏远山之女苏玉瑶为正妃!
“听说那苏**才貌双全,自幼爱慕太子,苏丞相这才……”“嘘,慎言!
你没看太子接旨时的脸色,简直要杀人!”流言如野火般蔓延。柳如眉站在紫竹院的梨树下,
手中的剪刀悬在半空,迟迟未落下——她本想剪一枝梨花晒干,寄去边疆。可现在,
还有必要吗?“姑娘!”小桃慌慌张张跑来,“太子殿下闯了御书房,当庭抗旨,
被陛下罚跪在宫门外已两个时辰了!”剪刀当啷一声落地。柳如眉拎起裙摆就往外跑,
却在宫道转角猛地刹住脚步——不远处,赵景恒笔直地跪在青石板上,玄甲未卸,
背上还缚着荆条。秋雨淅沥,冲刷着他脸上的血痕,可他的背脊依旧挺得笔直,
如一把宁折不弯的剑。御书房的门紧闭着,里面传来皇帝暴怒的呵斥声。她躲在廊柱后,
指甲深深掐入掌心。一滴雨水顺着他的下颌滑落,砸在地上,也砸在她心里。当夜,
柳如眉被一队陌生侍卫“请”到了冷宫。“奉皇后懿旨,柳氏医术精湛,特命照料静太妃。
”为首的嬷嬷面无表情道。静太妃——先帝晚年最宠爱的妃子,因谋害皇嗣被废,
如今疯疯癫癫地关在冷宫最深处。小桃急得直哭:“姑娘,这分明是要您的命啊!
那静太妃发起疯来,前个月刚咬死一个宫女……”柳如眉却异常平静,
只是摸了摸发间的白玉簪:“帮我收好它。”冷宫的大门在身后轰然关闭,
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黑暗中,
传来一阵似哭似笑的声音——“嘻嘻……又来一个送死的……”第五章:赐婚风波冷宫的夜,
比柳如眉想象中更冷。风从腐朽的窗棂缝隙钻进来,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她蜷缩在角落的草席上,听着远处疯癫的静太妃时而尖叫,时而痴笑,
指甲在木门上抓挠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药……给我药……”沙哑的女声忽然贴近耳边。
柳如眉猛地睁眼,一张惨白的脸几乎贴到她面前——静太妃披头散发,浑浊的眼球凸出,
枯瘦如爪的手指掐住她的肩膀:“你是来毒死我的对不对?对不对!”“娘娘!
”柳如眉强忍恐惧,握住老人颤抖的手腕,“奴婢是来给您治病的。
”指尖下的脉搏紊乱急促,瞳孔扩散,
嘴角还有未干的白沫——这是长期服用某种毒药的症状!
静太妃突然诡异地笑了:“你也是太医的女儿?十年前……那个柳太医,
也说过一样的话……”柳如眉浑身血液瞬间凝固:“您认识家父?”老太妃却猛地推开她,
踉跄后退:“滚!你们都想害我!他和苏远山是一伙的!一伙的!”苏远山?!
柳如眉还未来得及追问,老太妃已尖叫着冲回内室,将瓶瓶罐罐砸得粉碎。她怔在原地,
脑海中回荡着那句“他和苏远山是一伙的”——父亲明明是因拒绝与叛党合谋才被处死,
怎么会……天刚蒙蒙亮,冷宫大门突然被推开。“柳姑娘!”小桃红着眼扑进来,
“太子殿下今早闯了早朝,当众拒婚,陛下气得摔了玉玺!
”柳如眉手中的药碗哐当落地:“他疯了?!”“殿下说……宁可削爵流放,
也绝不娶苏家女。”小桃哭道,“现在被关在宗人府,
连崔家都上书求情了……”柳如眉指尖深深掐进掌心。崔家求情?
那个恨不得她死的崔太子妃?不,这绝不是好心——崔氏父亲是兵部尚书,
与丞相苏远山明争暗斗多年,如今太子拒婚打的是苏家的脸,崔家自然乐见其成!“姑娘,
还有更糟的……”小桃颤声道,“苏丞相向陛下进言,说您魅惑储君,应当处死!
”一阵天旋地转,柳如眉扶住墙壁才没倒下。她早该想到的。
从赵景恒为她挡下杖刑那一刻起,她就成了众矢之的。如今太子拒婚,
苏远山岂会放过这个“祸水”?“小桃。”她突然抓住宫女的手,
“帮我找一样东西——十年前太医院的旧档,尤其是关于静太妃的!”三日后,
一道圣旨降到冷宫。“陛下有令,柳氏即刻押往大理寺候审!”柳如眉被粗暴地拖出冷宫时,
静太妃突然扑上来,
将一本发黄的册子塞进她衣襟:“给你父亲……报仇……”册子很快被侍卫搜出,
却在看清封面时变了脸色——《承平十二年太医院实录》。“晦气!”侍卫将册子扔在地上,
“疯婆子的破烂!”柳如眉趁机踩住书角,借着跌倒的动作将它重新藏入袖中。
大理寺的牢房阴冷潮湿。她蜷缩在角落,借着铁窗透入的月光,
颤抖着翻开那本残破的医案——“……静嫔脉象沉涩,
疑为水银之毒……苏大人命改用安乐散……”“……柳太医抗命,
言安乐散乃慢性剧毒……”“……苏大人怒,以抗旨罪押柳太医入诏狱……”字迹潦草,
像是有人匆匆记录后又试图涂抹。最后一页还粘着半张残破的纸,
上面是父亲熟悉的笔迹:“苏远山与崔贵妃合谋毒杀静嫔腹中龙子,嫁祸皇后。
吾今拒配毒药,必死无疑。如眉吾儿,若你侥幸得活,切记——”后面的字被血迹浸透,
再也无法辨认。泪水砸在纸上,晕开了陈年的血渍。十年了,
她终于知道父亲为何而死——不是因为谋反,而是因为不肯同流合污!“柳如眉,你可知罪?
”大理寺公堂上,苏远山一袭紫袍端坐主位,阴鸷的目光如毒蛇般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