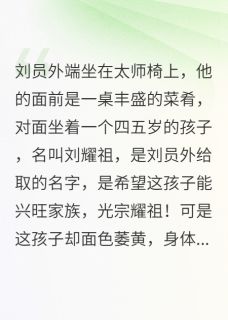推开家门时,阳光正斜斜地穿过客厅。
我站在玄关,恍惚间又听见小凯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
“妈妈,能陪我出去跑跑吗?”
手指抚过楼梯扶手,上面还留着儿子小时候用蜡笔画的歪歪扭扭的刻度。
每道痕迹都记录着他的成长:五岁、六岁、七岁……最后一道停在十岁的位置,比去年高了整整六厘米。
小姑子从厨房端出两杯热可可,杯子是小凯最喜欢的恐龙图案。
“都按你说的收拾好了。”她轻声说,“他的房间……一点都没动。”
推开儿童房的蓝色木门,床头的夜光星星还在天花板上闪着微光。
书桌上摊开的作业本里夹着张纸条,铅笔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爸爸答应周末带我去新开的恐龙博物馆”。
三天后,我们在城郊的向日葵墓园为小凯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祖母执意要亲自捧骨灰盒,她枯瘦的手指死死扣住汉白玉盒子,指节都泛了白。
“孩子,沈家欠你的……”老太太颤抖着将一抔土撒入墓穴,突然抓住我的手腕,“那对狗男女在牢里也不会好过。我刚收到消息,徐暖暖查出乳腺癌晚期,沈凌飞在监狱被人打断了三根肋骨。”
我轻轻抽回手,把儿子最珍视的球鞋放进墓穴。
照片上的他穿着红色队服,笑容比身后的晚霞还要灿烂。
从墓地回来的路上,律师打来电话说捐赠手续已经办妥。
后视镜里,小姑子突然红了眼眶:“嫂子,那可是三十八亿……”
“买不回他一次呼吸。”我转动方向盘拐上去法院的路,“现在去签离婚协议。”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反复确认:“您确定放弃所有财产分割?”
钢笔在纸上划出沙沙声时,我想起今早监狱的来电,沈凌飞绝食的第七天,狱医说他的胃已经出现穿孔。
倒也算偿命了。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