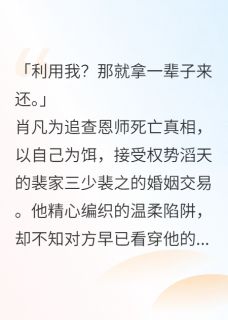赵候年近四十,身材依旧魁梧,比之怀恩多了几分不敢让人靠近的霸气。
我拿着软尺在他健壮的身子上衡量,他敛下眸子低头看我,仿佛透过我在看什么人。
“何姑娘是哪里人士?家中父母贵庚?”
“我乃平洲人,父亲早逝,娘亲于一年前病逝。”
我小心回复,赵候叹息一声,我的手却正好摸到其放松下来的肌肉。
“父亲、母亲。”
闻声而来的赵怀恩,挨着李朝颜坐下,神色自若。
夫人不曾应他,面色冷淡,唯有扭头看自家侄女时脸上才浮现出几分笑意。
一股诡异的气氛在亭中弥漫,我依次为李朝颜和赵怀恩量尺寸。
“还有三月,何娘子可不要着急,仔细些。毕竟这婚服,女子一生只能穿一次。”
李朝颜眉飞色舞,我低头应道。
待到赵怀恩时,我的手刻意加重力道。
他以为我在发泄醋意,嘴角微扬。
耐心些,我压住心头的激动。
转身离去时抬起手腕,暼了一眼赵怀恩,默默擦拭着眼角的泪珠。
距离婚期还有半月时,我向侯府送去了三件衣服。
赵候的外袍,赵怀恩的婚服以及一件绣满经文的缦衣。
夫人收到衣物时勃然大怒,几个气势汹汹的丫鬟婆子奉命将我押入她的院中。
夫人脸色阴沉可怖,堪堪将我打了十九大板,才甩手让人离开。
如今这院内只有我和她二人。
“你屡次三番的提起我儿,究竟有何图谋?”
夫人捻着佛珠,皮笑肉不笑,俨如一尊佛像。
院外奴仆笑我拍马屁拍到蹄子上,如今死路一条。
她打了我十九下才松口,分明是接收到了我的消息。
“他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大雪天,母亲喊了一天一夜才将他安然带来这世间。瑞雪兆丰年。娘亲唤他瑞瑞,期望他吉祥,好运。”
我趴在板凳上,面色惨白,朝着那火盆里的将要燃尽的缦衣缓缓开口。
那缦衣的外层绣的是金刚经,寓意夫人长乐无忧,断除苦难。
而内衬则绣着百喻经,杀子成担。
古时有一愚父失子打算搬家,时人劝其搬尸,一劳永逸。
恶父嫌尸重,遂杀一子,以担挑之。
赵尤自幼体格健壮,却死在了剿匪路上。
夫人吃斋念佛多年,如何不理解其中的讥讽。
此刻却是粗喘着气,一脸错愕。
她死咬着唇,一行清泪缓缓而下,视线在那点星火上停留。
那个表情俨然是让我继续说。
“若是真的吉祥好运,他如今也该十九了吧。”
我深深的看了一眼候夫人,她捏紧了佛珠身子一晃,手撑在我的背上保持清醒。
我们靠得很近,近到我能听见她口里喃喃唤着吾儿。
“死在生父手中,算是好运吗?”
我抬起头,满怀恨意的对上她的眸子。
四目相对,那个柔弱的、清冷的侯夫人变了。
“继续打!”
侯夫人咬牙切齿的下令,板子如雨点般落下,猛烈却又轻柔。
“住手!你这毒妇!”
一声暴喝,我望着那道身影当即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