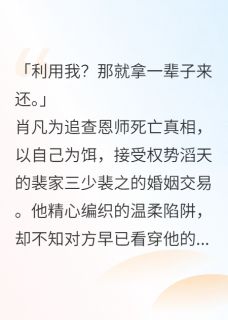1深秋的傍晚,城市被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暮色之中,寒风裹挟着枯叶在街道上肆意飞舞。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手中紧攥着那张冰冷的裁员通知书,
仿佛那是一道无法逾越的深渊。曾经以为安稳的工作,在这一刻化为泡影,
未来的生活瞬间变得模糊而迷茫。回到家中,我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
目光空洞地望着天花板。房间里寂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
每一声都像是在敲打我的心脏。我满心的焦虑与不甘,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排解。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许久未联系的牌友老周发来的消息:“今晚麻将局,三缺一,来不来?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回复了“来”。或许是想要逃避现实的残酷,
或许是渴望在牌桌上找到一丝慰藉,我鬼使神差地选择了用麻将填补内心的空虚。从此,
我一头扎进了麻将的世界,每天不是在麻将馆,就是在去麻将馆的路上。
2麻将馆的白炽灯管在头顶滋滋作响,我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推开玻璃门。
潮湿的梅雨气息裹挟着檀香瞬间扑面而来,
柜台后老板养的绿毛鹦鹉扑棱着翅膀用扬州话怪叫:"幺鸡!幺鸡!
"这畜生倒学得一口地道牌语。正要寻常坐的西南角,忽见窗边绿丝绒帘幕轻晃。
斜射的夕照里,穿月白旗袍的女子正用象牙烟嘴轻叩桌沿,翡翠镯子碰着青瓷茶盏,
发出清越的碎玉声。她耳后别着支鎏金点翠蜻蜓簪,随转头的动作振翅欲飞。
"阿弟要来凑搭子伐?"吴侬软语带着苏州评弹的尾韵,
她眼波掠过我攥着保温杯的手——那里还留着前日被开水烫出的水泡。
我认出这是上海虹口区老克勒们惯用的嵌宝麻将桌,嵌着玳瑁的牌垛在暮色里泛着幽光。
林婉——她递来的名片带着晚香玉的熏香——葱白指尖在牌面上摆出个"万"字阵列。
当穿豹纹短裙的李红晃着满胳膊银镯推门而入时,我注意到她左耳垂缺了半枚,
像是被什么利器削去一角。最后到的王丽抱着竹编暖手炉,金丝眼镜腿上缠着褪色的红线,
倒像个女学生。牌局初启时,李红用川普抱怨着天气:"龟儿子天气燥得很,
九万(久弯)都晒成麻花啰。"王丽扶眼镜时小指在镜框连敲三下,
我看见林婉不动声色地将刚摸的五万换成了九万。她们说的"弯弯话"里掺着川湘口音,
后来才知这是她们自创的密码:把"幺鸡"叫作"小凤凰","白板"唤作"玉扣子",
数字牌则用"天牌(九)""地牌(八)"之类的古彩叫法。六圈过后,空调突然发出蜂鸣。
李红叼着细烟起身调试,胸前的十字架银链在牌垛上方晃出光斑。
当那束反光扫过第三列第七张牌时,王丽突然用宜兴话轻叹:"今朝东风忒杀瘾。
"林婉涂着暗红甲油的尾指立即勾起耳后碎发——这是要换东南西北风的暗号。
果然下一轮王丽就碰走了我盯了半天的东风。最精妙的是她们的手势阵。
李红每次摸牌前都会用重庆话数数:"一个(1)、双(2)、三(3)..."看似随意,
实则尾音轻重对应花色。当她拖着长音说"七个(7)筒"时,
王丽立刻将暖手炉转了九十度——这是要七筒的信号。林婉则会用苏州码子记账,
在账本边缘画些奇怪的符号,后来才知那是用"〡〢〣〤"的旧式计数法标注各家余牌。
第十圈开牌时,翡翠镯子的震动频率突然加快。林婉抚牌的动作像在弹奏古筝,
甲尖每次触到牌背,镯子里的磁珠便发出蜂鸟振翅般的嗡鸣。
当李红甩出二条喊"打雀儿"时,王丽忽然将青瓷杯推到桌沿,
杯底与檀木摩擦的"吱嘎"声竟与镯子共鸣出某种旋律。"碰。"林婉推倒两张牌时,
银戒与镯子相撞迸出蓝火。
我分明看见她收进的红中背面有细如发丝的烫痕——那本该是五圈前沉在牌河底的绝张。
空调风口突然转向,绿绒桌布上波动的阴影恰好遮住她换牌的动作。又三圈后,
李红借口撵烟灰,用Zippo火机燎过某张牌角。
受热的塑胶牌面浮现出暗红花纹——这是最新型的温控显影麻将,
在红外监控下会组成北斗七星阵列。她假装咳嗽,吐出的烟圈在空中划出"三六九"的轨迹,
王丽见状立刻将暖手炉的铜盖旋开半圈。**始于林婉哼起《秦淮景》的瞬间。
吴语唱词里藏着"四六成对,三九连环"的切口,
王丽手机里流淌的琵琶声掩盖了微型接收器的电流声。我右耳突然刺痛,
像有银针在耳膜上绣花——法医后来在耳道里找到纳米级震片,正是次声波干扰器的杰作。
当我的清一色即将告成时,李红突然用川剧腔调大喝:"杠上花儿开!
"四张西风拍桌的力道激起茶汤涟漪,林婉从杠尾摸牌的刹那,翡翠镯子裂开细缝,
露出内藏的磁吸装置。那张烫手的八筒在空中划出诡异的弧线,
仿佛被无形丝线牵引着落入她的牌列。终局时刻,
王丽"失手"打翻的麦芽糖浆在桌布蜿蜒成蛇形。趁我擦拭之际,
林婉尾戒上的金刚石在牌面刻下暗纹。待糖渍拭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