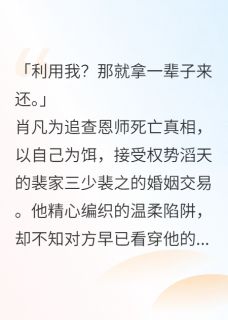闺女上小学那年,我带队去德国考察。在法兰克福的钢铁厂里,
金发碧眼的工程师听说我来自中国,惊讶地瞪大眼睛:“女士也能搞冶金?
”我调试着新设备,头也不抬:“在中国,女人能顶半边天。”回国那天,
白明远带着闺女来接机。小丫头举着纸花蹦蹦跳跳:“娘娘!我数学考了满分!
”我蹲下来亲了她一口:“真棒!比你爸强。
”白明远委屈地撇嘴:“我当年物理也不差好吧?”闺女十二岁那年,我带她回了趟老家。
县钢厂已经扩建了三倍,高耸的烟囱冒着白烟。厂长换成了小杨,
她拉着闺女的手直夸:“真俊!跟你娘当年一样俊!”我们去了趟村里。老宅还在,
母亲坐在枣树下乘凉,头发全白了。闺女甜甜地喊“姥姥”,乐得母亲直往她手里塞红枣。
“娘,**后来怎么样了?”我随口问道。母亲摇摇头:“死了。从劳改农场回来没两年,
喝醉酒掉河里了。”我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去灶台烧水。闺女跟进来帮忙,
小脸被火光映得通红:“娘娘,姥姥说的**是谁啊?”我摸了摸她的头,“不重要的人。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转眼间,闺女的高考成绩放榜了。闺女考上了北大,
白明远喝得酩酊大醉,抱着相册又哭又笑:“我闺女有出息!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