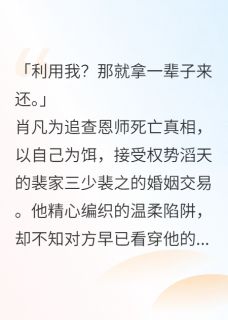清晨那场闹剧总算是落下了帷幕,贾张氏一路骂骂咧咧地回到了自家那狭小昏暗的屋子。刚一进屋,她就迫不及待地把棒梗拽到跟前,浑浊的眼珠子滴溜一转,开始眉飞色舞地讲述起自己心中那点算计,当然,只字未提那个“偷”字。
“棒梗呀!”贾张氏故意扯着嗓子,声音里透着一股让人起腻的亲昵,“你瞅瞅,咱这天天清汤寡水的,都快把身子熬坏了。今儿个,咱就别去学校遭那份罪了,奶奶想法子给你弄肉吃,咋样?”一提到“肉”字,贾张氏忍不住吧唧了几下嘴,似乎那香喷喷的肉已经到嘴边了。
棒梗本就不是个爱学习的主儿,在学校里那成绩,简直是一塌糊涂,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早就消磨光了他对上学的那点热情。此刻一听奶奶这话,眼睛瞬间亮得跟灯泡似的,这可正合他心意啊!去学校?那多没劲,哪有吃肉来得痛快。
“奶奶,我可太想吃肉了,学校我是真不想去。”棒梗一边说着,一边挠了挠头,可没一会儿,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眉头又皱成了个疙瘩,撇着嘴嘟囔道,“但是不去学校得请假呀,老师要是发现我无故旷课,回头不得狠狠收拾我?奶奶,你可得帮我请假啊。”
贾张氏一听,拍着胸脯保证:“你这小兔崽子,放一百个心!奶奶自有办法,就凭奶奶这张嘴,三言两语还糊弄不过去个老师?你就等着吃肉吧,啥事儿都没有!”说完,还得意地笑了起来,脸上的褶子更深了,仿佛已经看到了美味的肉食摆满一桌,全然不顾这背后隐藏的风险与是非。
而棒梗呢,一想到马上就能吃到肉,也跟着傻乐起来,压根没去细想奶奶这反常提议背后的猫腻,只满心欢喜地盼着那顿美餐,至于学业、规矩,早就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切都如同贾张氏那精明的所预料的一般,顺顺当当。今儿个早上,贾张氏一步三晃地去给棒梗请假,那过程顺利得就跟抹了油似的,老师连问都没多问几句,就点头应下了。
贾张氏心里那叫一个得意,扭着腰肢往家走,路上还不忘跟棒梗念叨:“棒梗呀,你跟奶奶说说,你那老师叫啥名儿?”棒梗眼珠子滴溜一转,挠挠头,也没多想,脆生生地回道:“我老师叫冉秋叶,那可老有文化了,上课讲的故事、道理,我们都听得入迷,同学们都特别喜欢她。”
一听这话,贾张氏撇了撇嘴,脸上瞬间堆满了鄙视,那褶子都快能夹死苍蝇了,她扯着嗓子就开腔了:“棒梗呐,你可得记住了,以后娶媳妇,千万不能找老师。你瞅瞅,太有文化的女人,脑子都学傻了。就说你这老师,瘦得跟个麻秆似的,风一吹都能刮跑咯,哪能干得了家里的家务活呀!天天就知道捧着书本,往后保不齐就变成跟院里那三大爷闫老抠似的,一毛不拔,整天算计,这日子还能有个热乎气儿?咱可不能往那坑里跳。”
棒梗眨巴眨巴眼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贾张氏瞧着孙儿这模样,满意地哼了一声,那股子掌控一切的劲儿,仿佛这世上的事儿,都得按她的想法来才成。
贾张氏带着棒梗,一路骂骂咧咧地回到了四合院。刚迈进家门,棒梗那小眼珠子就滴溜乱转,瞅了一圈,小鼻子一吸溜,满心期待地问道:“奶奶,您今儿个早上不是拍着胸脯保证,说今天能让我吃上肉吗?肉在哪儿呢,我咋瞅了半天,连根肉丝都没见着呀?”
贾张氏眼珠子一转,脸上瞬间堆满了怨毒,拉着棒梗坐到炕沿边,唾沫星子横飞地开了腔:“棒梗呀,你可不知道,这院里的死绝户傻柱,昨晚干的事儿那叫一个缺德冒烟!你被人冤枉抓鸡的时候,他不但不仗义,帮你顶个罪,还跟那许大茂穿一条裤子,俩人狼狈为奸,硬生生地讹诈咱们贾家的钱。你说,他们是不是坏到骨子里了,可恶至极啊!”
一提到这,贾张氏就气得直喘粗气,胸脯剧烈起伏,她顺了顺气,接着撺掇:“趁着现在院里没啥人走动,你麻溜儿地跑去傻柱家,瞅瞅有啥能吃的。我估摸着,昨晚他们吃香喝辣的,那鸡肉铁定没吃完。你手脚麻利些,拿回来咱祖孙俩也开开荤。”
棒梗被这么一激,小脸涨得通红,握紧了小拳头,咬牙切齿地应和道:“奶奶您说得太对了!傻柱就是个混账玩意儿,平日里还老惦记着娶我妈,想让我改姓何,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纯粹就是白日做梦!我现在就去,把他家能吃的都给搜罗回来,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咱贾家。”
说罢,棒梗蹭地一下跳下炕,像只小猎豹似的,风风火火地冲出门去,直奔傻柱家,那劲头,仿佛要把傻柱家给“打劫”一空,才解心头之恨。贾张氏看着棒梗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阴狠的笑,靠在炕头,就等着孙儿满载而归。
往日那个缺心眼的原主傻柱,听从一大爷的话从不锁门,导致棒梗进自己家就和逛大街一样。可现如今这何雨柱,早不是过去那个任人拿捏的主儿了。昨儿个,他特地去集市上精挑细选了一把锃亮的铁锁,那眼神透着股子精明劲儿,跟以前傻愣愣的模样判若两人。早上出门上班前,还特意给妹妹雨水千叮咛万嘱咐,让她走的时候务必锁好门,别给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可乘之机。
这边厢,棒梗被贾张氏撺掇得热血上头,满心想着去傻柱家“打秋风”,把好吃的都搜刮回来。他那小脑袋瓜里还全是过去的惯性思维,闷着头撒腿就往何雨柱家冲,脚下像生了风似的。到了门口,他瞅都没瞅一眼,抬手撩起门帘就要往里闯,哪知道“砰”的一声巨响,就跟炸雷似的,他结结实实地撞在了门上。那新换的门锁纹丝不动,棒梗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击力反弹回去,像个破布袋似的,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重重地摔在地上。这一下摔得可不轻,棒梗只觉得浑身骨头都要散架了,脑袋“嗡嗡”直响,疼得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哭声撕心裂肺,响彻整个四合院。
院里几个没工作、正坐在门口择菜唠嗑的妇人,听到这动静,手里的活儿一扔,赶忙起身,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瞧热闹。她们一边跑,一边互相打听:“这是咋啦?谁家孩子哭得这么惨?”一时间,院子里叽叽喳喳,乱成了一锅粥。
再说贾张氏,这会儿正美滋滋地坐在家里炕头,闭着眼,嘴角流着哈喇子,脑海里全是香喷喷的鸡肉,幻想着棒梗一会儿抱回一堆吃食,她该先撕哪条鸡腿。突然,那刺耳的哭声钻进耳朵,她一个激灵,像是被人从美梦里硬生生拽了出来,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好。也顾不上穿鞋,趿拉着就往外跑,边跑边喊:“我的大乖孙呐,这是咋回事哟!”那声音里满是焦急与慌张,跟刚才算计傻柱时的阴狠模样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