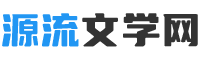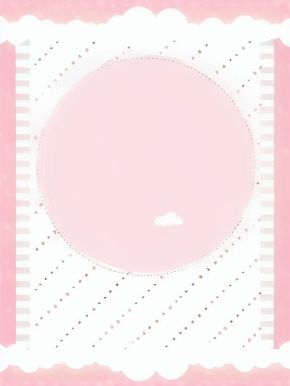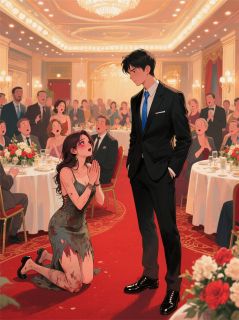1离婚日,他的失常冰冷的离婚协议,静静躺在昂贵的红木办公桌上。李清月垂眸,
拿起桌上的派克钢笔。笔尖划过纸张,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如同他们三年婚姻的无声落幕。
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李清月。字迹清秀,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果决。整个过程,
她平静得像是在签署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眼神甚至没有一丝波澜。协议被推到陈景深面前。
他今天穿着一身炭灰色的手工西装,衬得他愈发挺拔冷峻。男人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
此刻却罕见地没有立刻拿起笔。他的目光,第一次如此专注地凝视着对面的女人。
李清月穿着一件素雅的米白色连衣裙,未施粉黛的脸庞干净清丽。她瘦了些,
下巴的线条更清晰了。陈景深喉结微动。他没有去看那份刺眼的协议,
反而问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今晚……”他的声音略带沙哑,似乎有些不确定。
“……还回来做饭吗?”话音落下,空气都仿佛凝滞了几秒。李清月抬起眼,眸光平静无波,
甚至带着一丝礼貌的疏离。“陈先生,我已经搬出去了。”她的声音很轻,
却清晰地提醒着他。“我们的契约,今天正式结束。”契约。是的,契约。陈景深的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闪过三年前的画面。那时,陈老爷子病重,以家族继承权施压,
催他尽快完婚稳定后方。而他,陈景深,天之骄子,商界精英,
为了扫清事业道路上的最后一点家族障碍,
选择了最“省心”的联姻对象——家世普通、安静温顺的李清月。
他记得当时李清月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裙子,站在他面前,低着头,
声音细弱却坚定:“我答应,但我有条件,我需要一笔钱。”后来他才知道,
她是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家庭,为了支付弟弟高昂的学费。或许,还有一丝深埋心底,
连她自己都未曾细究的,对少年时期那个惊鸿一瞥的陈景深的朦胧好感。婚后的三年,
如同一潭静水。李清月将别墅打理得井井有条,默默扮演着一个完美妻子的角色。
她知道他的口味,他的习惯,甚至他每一条领带的摆放位置。而他,陈景深,
习惯了她的存在,习惯了她的付出,却将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视而不见。他的心中,
似乎永远盘踞着一个“张晚晴”的影子。那个早逝的、才华横溢的商业对手之女,
成了他逃避现实情感、标榜深情的完美借口。他甚至从未深思过,那份对张晚晴的“怀念”,
究竟是爱,还是对自己未竟事业蓝图的一种遗憾投射。思绪被拉回。陈景深拿起笔,
笔尖在签名处悬停了数秒。最终,他还是落笔,签下了“陈景深”三个字。力透纸背。
签完字的瞬间,一股莫名的空虚和难以言喻的烦躁,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攫住了他的心脏。
像是习惯了的某个重要器官,突然被剥离。李清月看着他签完,微微颔首,
拿起属于自己的那份协议。她站起身。“陈先生,再见。”没有多余的告别,
没有丝毫的留恋。她转身,一步一步,走向门口。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而决绝。
陈景深看着她的背影,那个曾经无数次在晨曦中为他准备早餐、在深夜灯下等他归家的背影。
这一次,她没有回头。门开了,又轻轻合上。办公室里,只剩下陈景深一人,
和那份冰冷的离婚协议。以及,心底那股越来越清晰的,陌生的慌乱。
2空荡的别墅与“月光集”的新生李清月离开后的第一个清晨,
陈景深是被胃部熟悉的绞痛唤醒的。偌大的别墅空寂得如同一个巨大的回音室。
阳光穿透落地窗,却驱散不了房间里的丝丝冷清。他习惯性地走向厨房,想给自己弄杯咖啡。
那台昂贵的咖啡机静静地立在那里,面板上的指示灯闪烁着复杂的光芒。陈景深伸出手,
指尖在冰凉的金属按键上悬停了数秒。他皱眉。这东西,怎么用?平日里,
李清月总会在他下楼前就准备好一切。一杯温度恰好的黑咖啡,一份搭配得宜的早餐。现在,
厨房里只有冰冷的台面和沉默的电器。他放弃了咖啡,转身上楼去衣帽间。
一整排熨烫平整的衬衫和西裤。他随手拿起一条领带,
却怎么也系不出李清月平日里为他打理的那般妥帖。镜中的男人,英俊依旧,
眉宇间却染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狼狈和烦躁。胃部的疼痛一阵阵袭来,
提醒着他昨晚应酬后的空腹和今晨被忽略的早餐。陈景深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李清月。
那个在他生活中近乎透明,被他视作理所当然的女人。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背景板。
她是这个家曾经的温度,是他规律生活的隐形支柱。而现在,这个支柱,被他亲手推倒了。
与此同时,城南一间临街的店铺内,却是另一番景象。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门,
洒在一室的鲜花绿植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芬芳。李清月穿着简单的棉布长裙,
头发随意地挽起,几缕碎发垂在颊边,平添了几分柔和。
她正和合伙人苏蔓认真讨论着花艺工作室“月光集”的开业细节。“清月,
这批荷兰空运过来的郁金香品相真好,你看这个‘夜皇后’,颜色太正了!
”苏蔓指着一捧深紫色的郁金香,语气兴奋。李清月俯身细看,指尖轻轻拂过花瓣,
眼底是专注而温柔的光。“嗯,确实不错。搭配一些浅色的玛格丽特,或者白色风信子,
效果应该会很好。”她的声音轻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专业。讨论工作时,
她眉眼间闪烁着一种陈景深从未见过的神采。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投入,
让她整个人都散发着令人舒适的活力。她的笑容明媚,
不再是过去三年里那种带着些许疏离和礼貌的浅笑。那是真正轻松愉悦的,
不带任何负担的笑容。几天后。陈景深的黑色宾利停在了“月光集”不远处的街角。
他告诉司机,自己下来考察一下附近的商铺。一个拙劣的借口。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
他只是……鬼使神差地,想来看看。隔着一条马路,
他看见了那间招牌雅致的花店——“月光集”。三个字,娟秀中带着风骨,
像极了李清月那个人。然后,他看见了李清月。她正站在店门口,微微侧着身,
似乎在调整一块新挂上的木质迎客牌。午后的阳光温柔地笼罩着她,
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微风吹拂起她的裙摆和发梢。
那一瞬间,陈景深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不轻不重地撞了一下。李清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不经意地朝他这个方向瞥了一眼。目光平静,没有停留。然后,她转过身,
和一个从店里走出来的年轻女孩笑着说了些什么,两人一起走进了店内。陈景深站在原地,
看着那扇玻璃门在他眼前合上,隔绝了那个身影。心中涌起一股复杂难言的情绪。有惊讶。
她似乎……变了。变得更加鲜活,更加耀眼。也有一种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失落。
以及一丝被彻底忽略后,隐秘的恼怒。她甚至没有认出他的车。或者,认出来了,
也毫不在意。陈景深握紧了方向盘,指节微微泛白。他第一次尝到了,
什么叫作真正的“无关紧要”。
3笨拙的试探与无声的较量“月光集”花艺工作室的门被推开时,
李清月正低头修剪一束刚到的肯尼亚红玫瑰。风铃轻响。她抬头,看清来人,
动作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陈景深。他怎么会来这里?男人一身剪裁合体的高定西装,
身姿挺拔,气质一如既往的清冷矜贵,与这间温馨雅致的花店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陈先生?
”李清月放下手中的花剪,语气平静无波,仿佛面对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访客。
陈景深目光扫过店内,最终落在她身上,声音低沉:“李**,我代表陈氏集团,
来洽谈长期花艺布置合作。”他递出一张名片,动作间带着不容置喙的商界精英气场。
李清月接过,指尖触碰到微凉的烫金字体。陈氏集团需要花艺布置,这不奇怪。
但需要他陈景深亲自对接,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请坐。”李清月引他到待客区,
倒了杯温水,“陈氏集团的合作意向,我们‘月光集’非常荣幸。
不知陈先生对花艺风格和预算有何具体要求?”她公事公办,将个人情绪掩藏得极好。
陈景深端起水杯,却没有喝,目光似有若无地停留在她清瘦却挺直的背影上。
“我们集团总部大楼,以及旗下几家酒店,都需要定期更换鲜花。”他开口,语气平稳,
“要求是,格调高雅,符合各场所定位,花材必须是顶级。”听起来倒是专业。
李清月点头:“这些‘月光集’都能满足。我们会根据不同场所出具详细的设计方案和报价。
”“嗯。”陈景深应了一声,随即话锋一转,“我个人对花艺也有些浅薄的见解。
”他开始提出一些要求。比如,总裁办公室需要一种“既能体现权威又不失亲和力,
最好带着一丝禅意”的花。又比如,酒店大堂的花艺要“大气磅礴,
但细节处又要体现极致的温柔,能让人联想到星空与大海”。李清月静静听着,心中了然。
这些要求,看似高端,实则空泛,甚至有些自相矛盾。
一个常年沉浸在商业数字和冰冷合约里的人,突然对花艺有了如此“深刻”的见解,
其意图不言而喻。她没有点破,只微笑着一一记录,
然后以专业的口吻回应:“陈先生的想法很有启发性。关于总裁办公室,
或许可以考虑东方禅意风格的兰花或松柏盆景,搭配简约线条的花器。至于酒店大堂,
我们可以尝试用大量白色系和蓝色系花材,通过构建视觉焦点和层次感来营造您所说的意境。
”她巧妙地将他那些“外行”的要求,转化为切实可行的专业方案。
陈景深看着她侃侃而谈的样子,眼神深邃。她似乎完全没受到他们过去关系的影响,
专注而迷人。这种专注,他曾经在她为他打理家事时见过,
却从未像此刻这般清晰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力量。“方案细节,后续让我的助理和你对接。
”陈景深最终说道,起身准备离开,似乎此行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
李清月也随之起身:“好的,期待与陈氏的合作。”她送他到门口,没有多余的寒暄。
陈景深离开后不久,李清月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请问是李清月**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温柔的女声。“我是,请问您是?”“我是张心怡,张晚晴的妹妹。
”李清月握着手机的力道紧了几分。张晚晴。这个名字,曾是她婚姻里一道无形的阴影。
“张**,你好。”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冒昧打扰,
”张心怡的语气带着一丝歉意,“我刚从国外回来,整理姐姐遗物时,
发现一些她生前很珍视的东西,似乎……与陈景深先生有关。我想,或许应该让陈先生知道。
”她的声音轻柔,带着一种不谙世事的纯真。“我冒昧联系了陈先生,他似乎很忙。
听闻李**曾是陈太太,也是姐姐生前的好友,所以想问问您,是否方便代为转达,或者,
您是否知道陈先生何时有空?”李清月沉默了几秒。张心怡的言谈举止,
甚至某些细微的停顿和尾音,都刻意地带着几分张晚晴的影子。这让她心中警铃微作。
“抱歉,张**,我和陈先生已经离婚了。”李清月淡然道,“他的行程,我并不清楚。
如果你有重要的事,建议还是直接联系他的助理。”“啊……这样吗?
”张心怡的语气透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失落和惊讶,“对不起,是我冒失了。那……打扰您了。
”挂断电话,李清月看着窗外,眸色微沉。张心怡在这个时候出现,绝非偶然。
她这是想通过自己,重新勾起陈景深对张晚晴的“怀念”,还是有别的图谋?另一边,
陈景深坐在回公司的车上,脑海中不断回放着李清月在花店里的样子。她比以前更清瘦了些,
但眉宇间的独立与自信却愈发耀眼。那种疏离感,像一根细密的针,轻轻刺着他的心口。
这时,助理秦川汇报:“陈总,张晚晴**的妹妹张心怡女士刚刚来电,
说有张**的遗物想交给您。”陈景深蹙眉。张心怡?他对这个名字有些模糊的印象,
似乎是个娇弱文静的女孩。“知道了。”他淡淡应道,
心中却因“张晚晴遗物”几个字泛起一丝涟漪。或许,他最近对李清月异样的关注,
只是因为张心怡的出现,勾起了他对故人的追忆和某种情感投射。他这样告诉自己,
试图将那份莫名的烦躁归因于此。几天后,“月光集”工作室接到了一份匿名举报,
称其使用的花材以次充好,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很快便找上了门。
一时间,刚刚起步的“月光集”陷入了小小的风波。李清月得到消息时,
正在和一个重要的供应商洽谈下一季的合作。她没有慌乱,冷静地安排合伙人先稳住员工,
自己则立刻赶回工作室配合调查。她调出所有批次花材的进货单、原产地证明以及质检报告,
条理清晰地向调查人员一一说明。同时,她也联系了几位长期合作的酒店采购负责人,
请他们出具了对“月光集”花材品质的客观评价。陈景深是在一个行业会议的间隙,
偶然从旁人口中听到“月光集”出事的消息。他心中一紧,立刻让秦川去打探具体情况。
“是被人恶意举报了,说花材有问题。”秦川很快回报,“李**正在处理。
”陈景深眉峰紧锁。他下意识地想动用自己的人脉去压下这件事,
或者至少查清是谁在背后捣鬼。然而,他的电话还没拨出去,秦川又补充了一句:“陈总,
李**那边似乎已经快解决了。她提供了非常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花材的品质,
监管部门的人初步判断是恶意举报,正在追查举报源头。而且,
好几家五星级酒店都公开力挺‘月光集’,说她们的花艺品质是业内顶尖的。
”陈景深握着手机的动作顿住了。他设想过李清月可能会焦头烂额,可能会需要帮助。
却没想到,她如此迅速而有效地化解了危机。一股难以言喻的挫败感,
夹杂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骄傲,在他心中升起。他发现,自己对李清月的了解,
似乎还停留在那个温婉居家、默默付出的“陈太太”印象上。
而如今这个独立、果决、能在商场风波中冷静应对的李清月,让他感到陌生,
也让他……对她的能力有了全新的认知。同时,也有一丝无力感。他想帮忙,却发现,
她似乎并不需要。或者说,她已经强大到可以自己撑起一片天。
4“白月光”的滤镜与现实的刺痛陈景深试图用张心怡的存在,
来填补李清月离开后那份莫名的躁动。他努力在张心怡精心模仿的举手投足间,
寻找张晚晴的影子。然而,那份刻意的相似,反而像一根细针,
时不时刺破他自我构建的麻醉。张心怡会学着张晚晴微微歪头,眼中带着三分笑意七分思索。
可陈景深看到的,却只有模仿的痕迹,僵硬且缺乏灵魂。
他甚至会带张心怡去一些他和张晚晴曾经讨论过商业项目的地方。他期望能重温旧梦,
以此证明自己对李清月的异样情绪,不过是对故人的某种延续性怀念。清冷的墓园。
陈景深独自站在张晚晴的墓碑前。风吹过,松柏低鸣。他努力回忆,
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与张晚晴浓情蜜意的画面。奇怪的是,浮现的尽是些零碎的片段。
多是两人在会议室争论商业蓝图,或是在某个项目庆功宴上遥遥举杯。那些画面清晰,
却冰冷,缺乏男女之间的温情脉脉。他第一次隐约意识到,他对张晚晴的所谓“深情”,
或许更像是一种执念。一种对年少时期未能实现的理想化符号的固守。
一种对自己未竟事业蓝图的遗憾投射。而非纯粹、炙热的爱恋。这个认知让他感到一丝慌乱,
仿佛一直以来坚信的某种东西,正在悄然崩塌。与此同时,李清月的生活,
正以一种他从未想象过的姿态,绚烂绽放。她的花艺工作室“月光集”声名鹊起。
社交媒体上,偶尔能刷到她和朋友们在花艺课上巧笑倩兮的照片。照片里的她,
穿着素雅的棉布裙,发髻松散,脸上是发自内心的、轻松明媚的笑容。那种笑容,
是陈景深在三年的婚姻生活中,极少见到的。
她不再是那个只围绕着他的厨房和书房打转的女人。她有了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光芒。陈景深滑动着手机屏幕,指尖有些发凉。心中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愈发浓烈。像是被人抢走了珍藏的宝贝,又像是自己亲手丢弃的明珠,如今在别处熠熠生辉,
刺得他眼睛生疼。某日,陈景深在自己空荡的书房里,
无意间拉开了一个许久未曾动过的抽屉。里面静静躺着一本李清月常看的旧书。
书页有些泛黄,页角微微卷起。他随手翻开,一张手绘的简易食谱掉了出来。
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他胃不好时宜吃的几种粥品,旁边还有些可爱的简笔画,
标注着注意事项。字迹温柔,带着她特有的细致。那一瞬间,
陈景深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他想起李清月无数个清晨在厨房忙碌的背影。
想起她端上来的、总是温度刚好的养胃粥。想起她在他应酬晚归时,
沙发旁永远亮着的那盏小灯,以及温在保温壶里的蜂蜜水。
这些曾被他视作理所当然、甚至有些不耐烦的日常,此刻却像潮水般涌来,
带着令人窒息的暖意和悔意。再对比张心怡那些刻意模仿张晚晴的“完美”举止,
显得那么苍白而虚假。李清月的真实、鲜活,以及那些被他忽略的点点滴滴,反而在此刻,
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狠狠刺痛了他的心。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李清月的好,
不是张晚晴的影子,而是她独有的,无可替代的温暖。一股强烈的冲动驱使着他。
陈景深拿起手机,拨通了李清月的电话。他用谈合作项目的名义,约她晚上一起吃饭。
语气尽量显得平淡,公事公办,藏起了内心的波澜。电话那头,李清月的声音平静无波,
带着礼貌的疏离:“陈总,谢谢您的邀请。”停顿了片刻。“不过今晚花店有个重要的预约,
恐怕走不开,下次吧。”她的婉拒干脆利落,不带一丝犹豫。陈景深握着电话,
听着里面传来的忙音,久久没有放下。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被拒绝的滋味。
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坚决。一种他从未在她身上体会过的,冰冷的界限感。
挫败感像冰冷的潮水,瞬间将他淹没。他第一次意识到,李清月,是真的不打算回头了。
而他,似乎也第一次,有了想要追回什么的念头。
5张心怡的“局”与陈景深的动摇夜色渐浓。张心怡坐在陈景深办公室的会客沙发上,
姿态娴雅,眉眼间带着几分与张晚晴相似的忧郁。她手中捧着一杯温水,轻声道:“景深哥,
这是姐姐生前一直想推动的一个山区儿童艺术教育的慈善项目,
我整理遗物时才发现这份详细的计划书。”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仿佛每一次提及姐姐,都牵动着未愈合的伤口。“她说,希望那些孩子也能有机会接触到美,
用艺术点亮他们的人生。”陈景深看着她,眼神复杂。张心怡的出现,像一把钥匙,
轻易打开了他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她偶尔的蹙眉,说话时微微偏头的习惯,
甚至是对某种花草的偏爱,都与张晚晴惊人地相似。这种相似,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慰藉,
也让他对张心怡提出的请求,难以轻易拒绝。“这个项目,听起来不错。”陈景深沉吟片刻,
“需要陈氏提供什么支持?”张心怡眼中闪过一丝微光,快得让人无法捕捉。
“姐姐原本希望,能从陈氏旗下的文创基金里申请一部分启动资金,并且,她还提到过,
希望您能担任这个项目的名誉顾问……”她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试探和期盼:“毕竟,
您是她生前最信任也最钦佩的人。”这话,像羽毛一样轻轻搔刮着陈景深的心。
他确实对张晚晴怀有愧疚,那份未能共同实现的商业蓝图,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都是他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张心怡巧妙地利用着这份愧疚感,
将自己与姐姐的遗愿捆绑在一起,试图在陈氏集团这棵大树上,找到一个可以倚靠的位置,
甚至获取更实际的资源。她表现得体,从不直接索取,
而是将一切都归结于“完成姐姐的梦想”。有时,她甚至会主动联系李清月,
送上一些据说是张晚晴生前喜爱的小点心,或者几句轻描淡写的关心,
言语间尽是对“姐姐故友之妻”的友善。那份滴水不漏的周到,
反而让李清月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此刻的陈景深,
尚未察觉到这“温柔陷阱”背后的深意,只觉得张心怡的出现,
似乎填补了他生活中因李清月离开而产生的某种空洞。然而,平静的水面下,暗流已然涌动。
陈氏集团一个重要的海外文旅投资项目,近期突然遭遇了不明阻力,合作方态度暧昧,
一些关键环节也莫名卡顿。项目负责人焦头烂额,却查不出具体原因。这日,
李清月带着新培育的“晨曦微露”系列主题花束,
前往该项目位于市中心的临时推广展厅进行布置。这是“月光集”接下的一笔大订单。
休息间隙,她无意间听到两个项目组员的低声交谈。
“……听说又是那个叫‘启明创投’的在暗中搞鬼,
他们最近一直在接触我们的欧洲合作方……”“启明创投?没怎么听过啊,哪来的程咬金?
”“背后好像有张家的影子,就是……张晚晴那个张家……”李清月端着水杯的手微微一顿。
张家?启明创投?她对商业运作并非一窍不通,父亲当年经商时,她耳濡目染,
也曾翻阅过不少商业案例。“启明创投”这个名字,她隐约有些印象,
似乎与几年前张氏企业试图转型时,接触过的一些不太光彩的海外资本有关联。
而张心怡最近频繁出入陈氏,言谈间对陈氏的某些内部事务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心”。
一个念头在她脑中闪过。她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回到工作室后,思虑再三。最终,
她用一个不常用的邮箱,给陈景深的私人助理发了一封匿名邮件。邮件内容很简单,
只有一句话:“警惕启明创投,及其与张氏的潜在关联,或对贵司海外项目不利。
”没有署名,没有多余的解释。她只是凭着一丝商业直觉,
和一种不愿看到无辜者因阴谋受损的底线。陈景深的助理收到邮件时,起初并未在意。
这类匿名的“提醒”或“爆料”,他们偶尔也会收到,大多是捕风捉影。
但当他习惯性地将“启明创投”这个名字输入内部风险监控系统时,
一条不起眼的记录跳了出来。那是张心怡近期以“了解姐姐生前投资意向”为由,
向法务部咨询过的一个小型海外基金,而那个基金,与“启明创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