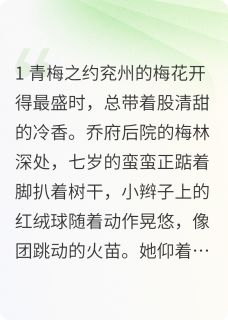第一章:暗夜重逢月光像一柄淬毒的薄刃,将总裁办公室切割成明暗交错的牢笼。
莫羽的匕首刺入檀木门的瞬间,熟悉的雪松香裹着威士忌的余韵扑面而来。
这味道与记忆里泛黄的画面重叠——十五岁那年漏雨的阁楼上,
少年用浸过药水的纱布为她包扎伤口,霉味里就掺着这样清冽的松香。
"这次打算刺左肩还是右肋?"低沉的嗓音惊碎了月光。莫羽的瞳孔在银质面具后骤然收缩,
匕首悬停在男人喉结三寸处。冷亦寒倚坐在真皮转椅上,鎏金钢笔仍在合同末尾游走,
仿佛抵在颈间的不是凶器而是情人指尖。他抬手解开三颗黑丝衬衫纽扣,
苍白的胸膛赫然陈列着七道刀疤。最靠近心脏的那道新月状伤痕泛着淡粉色,
在月光下如同未愈的吻痕。"你留下的记号比董事会印章更清晰。"冷亦寒的指腹抚过疤痕,
丝绸般的嗓音裹着危险的笑意,"需要我提醒吗?去年圣诞夜在游轮,
你刺偏了0.**分;上个月慈善晚宴,那把餐刀..."莫羽的刀尖突然下压,
在男人锁骨刻出血线。鲜血顺着银刃蜿蜒,在黑色衬衫上绽开暗红的花。
她的呼吸却比刀锋更先紊乱——那晃动的铂金链坠上,竟系着半枚生锈的银铃。
二十年前的暴雨夜在视网膜炸裂。五岁的她蜷缩在孤儿院储物间,
怀里女婴的襁褓上就系着这对铃铛。当醉酒的院长提着皮带踹门时,
她把其中半枚塞进妹妹襁褓:"小暖乖,姐姐引开坏人就来接你。
"此刻那半枚铃铛正在冷亦寒颈间轻颤,锈迹斑斑的裂口处还沾着奶渍。"小暖在哪里?
"刀刃割破空气的尖啸戛然而止。冷亦寒握住她颤抖的手腕,将匕首转向自己心口。
这个动作太过熟稔,仿佛演练过千百次。莫羽的泪水先于理智坠落,
砸在男人手背溅成细碎的光。"在你成为幽灵的第三年。"冷亦寒的拇指摩挲她腕间旧伤,
那里有被铁链磨出的环形疤痕,"我把她的骨灰撒在蓝楹树下——你们总爱在那里数花瓣。
"记忆如暴雨倾盆。莫羽看见十八岁的自己从燃烧的别墅窗口坠落,
冷亦寒在火场徒手扒开滚烫的瓦砾。浓烟中传来婴儿微弱的啼哭,
那是她最后一次听见妹妹的声音。"你骗我!"匕首深深没入檀木桌面。莫羽扯下面具,
狰狞的烧伤从左眼蜿蜒至下颌,像朵枯萎在雪地的红梅,"那天你明明抱着她逃出来了!
"冷亦寒忽然起身,松香混着血腥味将她困在办公桌与胸膛之间。
他的指尖抚过她扭曲的疤痕,如同触碰易碎的瓷器:"你坠楼时压断了三根肋骨,
却用最后力气把我推出火场。"温热的呼吸拂过她结痂的眼睑,
"等我砸开地窖的门...小暖的襁褓已经凉了。"窗外惊雷乍响。
莫羽的耳畔轰鸣着记忆里的爆裂声,
那夜火舌舔舐房梁的噼啪与此刻雨打玻璃的脆响重叠成命运的交响。
冷亦寒的唇擦过她颤抖的睫毛,声音轻得像叹息:"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辨认那些冒牌货吗?
她们的眼睛太干净,不像你..."他突然扯开衬衫,心口纹着与她面具相同的荆棘图腾。
蜿蜒的黑刺间点缀着蓝楹花瓣,正是她当年最爱的式样。"每收购一家逼死莫氏集团的企业,
我就添一道疤。"冷亦寒抓着她手指划过那些凸起的伤痕,"泰森化工的氰化物,
华荣地产的钢筋,还有你父亲吞下的那瓶安眠药..."莫羽的指甲深深陷入他胸肌,
直到鲜血染红指尖。十二岁那晚的场景在脑海闪回:父亲的书房弥漫着苦杏仁味,
母亲的白旗袍浸在血泊里,而窗外飘着那年第一场雪。"为什么纵容我刺杀?
"她嘶哑的质问混着血腥气,"明明可以让我死在那场爆炸里!
"冷亦寒的吻落在她残缺的耳垂,那里缺了一小块软骨,
是当年为他挡下铁棍的印记:"只有刀锋抵住咽喉时,
你才会像现在这样..."他的犬齿轻轻厮磨那道旧伤,"...完整地属于我。
"雨声渐密。莫羽忽然嗅到若有似无的奶香,与冷亦寒身上的雪松香纠缠成致命的毒。
她的视线掠过男人肩头,浑身血液瞬间凝固——办公桌上的相框里,
穿碎花裙的小女孩正抱着半枚银铃甜笑。那是五岁的小暖。
"你居然留着..."她踉跄后退,腰际撞上红木陈列架。青瓷花瓶应声碎裂,
瓷片划破脚踝也浑然不觉,
"你怎么敢...怎么敢把她的照片..."冷亦寒的身影笼罩上来,
阴影中他的眼眸如同淬火的刀:"我每天对着这张照片签署收购协议。
"他捏住她下巴强迫抬头,"看着仇人的企业在破产文件上签字时,
我总会想起你父亲被抬出书房的样子——"响亮的耳光截断话语。莫羽的手掌**辣地疼,
却不及心口撕裂的万分之一。冷亦寒偏着头轻笑,血丝从嘴角渗出,
为他冷峻的面容添了分妖异的艳色。"这巴掌比上个月那枪更疼。"他舔去唇间血珠,
突然将她压倒在散落的文件上,"要继续吗?
莫氏集团最后1%的股权**书就在这里..."苍白的手指挑开她衣领,
"用你的身体来换?"纸页在纠缠间簌簌作响。莫羽的利齿咬破他肩头,咸腥在口腔漫开时,
二十年前的画面突然闪现:阁楼漏雨的深夜,发烧的少年将最后半块馒头塞给她,
自己啃着结冰的窗棂。她为他偷药被吊打时,他整夜跪在雨里哀求。
"为什么..."她的哽咽淹没在男人唇间。这个吻血腥而暴烈,
像是要把七年的思念与恨意都嚼碎了咽下。冷亦寒的手掌贴着她后腰的旧伤,
那里有被烙铁烫出的"莫"字——曾经显赫的家族徽记,如今只剩屈辱的烙印。
警报声骤然撕裂雨幕。冷亦寒抱着她滚进保险柜后的暗门时,子弹穿透防弹玻璃,
将小暖的照片击得粉碎。莫羽下意识伸手去抓相框残片,却被男人紧扣在怀中。"别回头。
"他的唇贴着她耳际震颤,"就像当年在火场,你让我别回头那样。
"暗门在身后闭合的刹那,
莫羽看见自己映在钢化玻璃上的倒影——面具碎裂的杀手泪流满面,
而暴君般的男人正温柔拭去她颊边血迹。雨滴顺着玻璃蜿蜒而下,
将两个交叠的身影扭曲成二十年前雨夜相拥的孩童。在散发着雪松香的黑暗里,
冷亦寒突然轻笑:"知道为什么我的香水十年未换吗?"他握着她持刀的手按在自己心口,
"每次你刺杀失败,都能循着味道找到回家的路。"惊雷炸响。莫羽的匕首当啷落地,
如同十七岁那晚坠在火场的银铃。第二章:铃铛往事暴雨鞭笞着孤儿院的铁皮屋顶,
十五岁的莫羽蜷缩在漏风的阁楼角落。怀里的小暖正在发高烧,
滚烫的额头贴着她锁骨处的胎记,像块灼红的炭。冷亦寒跪在霉烂的木板地上,
正用牙齿撕扯从护士站偷来的纱布。"再忍忍。"少年沾着血迹的手掌覆住她脚踝的铁链,
那里被镣铐磨得血肉模糊,"等攒够买钳子的钱,我们就..."楼下的惨叫声截断话语。
莫羽把小暖塞进冷亦寒怀里,抓起生锈的镰刀冲向楼梯口。潮湿的裙摆扫过少年苍白的脸,
他嗅到熟悉的血腥味混着茉莉香——那是莫羽每天清晨在洗衣房偷肥皂搓出来的味道。
阁楼门下透出的光影里,醉醺醺的院长正拎着皮带抽打偷面包的哑女。莫羽的指甲掐进掌心,
直到血腥味盖过茉莉香。这是本月第三次,冷亦寒的旧伤未愈,小暖的奶粉罐也快见底。
"老畜生!"她故意踢翻铁皮桶。当院长通红的醉眼瞪过来时,
莫羽转身冲向暴雨倾盆的庭院。铁链拖过积水的声音像条垂死的蛇,
身后传来皮带破空的呼啸。雨水模糊了视线。莫羽在泥泞中狂奔,脚踝的伤口泡得发白。
她记得冷亦寒教过的路线:绕过枯井,翻过西墙缺口,在槐树下第三个砖缝里藏着半块刀片。
只要割断铁链,就能去码头偷渡船的货箱。皮带抽在脊背的瞬间,莫羽摸到了冰凉的砖缝。
指尖触到的不止是刀片,还有枚闪着微光的银铃铛。这是上个月货轮水手掉落的,
她曾隔着铁丝网看他们往海里撒纸钱。"小贱种!"院长的皮鞋碾住她手腕。
莫羽用最后力气将铃铛塞进嘴里,铁锈味混着雨水吞入喉管。皮带扣砸在太阳穴时,
她听见遥远的雷鸣中夹杂着冷亦寒的嘶吼。再次醒来时,月光正从阁楼天窗漏进来。
冷亦寒的脸在阴影里模糊不清,唯有脖颈处新鲜的鞭痕泛着血光。他正在用牙齿撕扯床单,
给昏迷的小暖当尿布。"张嘴。"少年沾着药粉的手指抵住她唇缝。莫羽尝到熟悉的苦味,
是冷亦寒每周去教堂偷的止血药。当他的指尖触到她碎裂的臼齿时,
有什么冰凉的东西滑入掌心。是那枚沾着血丝的银铃铛。"我在槐树下找到的。
"冷亦寒的呼吸喷在她结痂的耳后,"等逃出去,找铁匠打成两半。
"他撕下衬衫最后一块干净布料,将铃铛系在小暖的襁褓上,"你一半,妹妹一半。
"莫羽攥紧铃铛,尖锐的棱角刺破掌心。月光下冷亦寒的睫毛投下蝶翼般的阴影,
正在用舌尖润湿干裂的奶粉勺。这个总把食物让给她们的少年,肩胛骨已经瘦得凸出衬衫。
惊雷炸响的刹那,阁楼门突然被踹开。莫羽本能地扑向小暖,却被冷亦寒猛地推开。
院长举着煤油灯的身影在门框摇晃,酒气熏得人作呕。"原来藏在这儿。
"皮带扣擦过冷亦寒的颧骨,血珠溅在小暖的襁褓上,"上次就是你偷的药?
"莫羽的指甲深深掐进木地板。她看着冷亦寒被拖出阁楼,
少年回头时用口型无声地说:"藏好铃铛。"整夜的雨声里,鞭打声与闷哼声在走廊回荡。
小暖的哭声渐渐微弱,莫羽将铃铛含在口中,铁锈味混着奶腥味在舌尖漫开。
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乌云时,她摸到冷亦寒爬回阁楼的血迹——蜿蜒如一条猩红的河。
"他们发现西墙的洞了。"少年溃烂的指尖碰了碰她脚踝,"明天巡警要来检查,
院长要把小暖..."他剧烈咳嗽起来,血沫染红胸前的绷带。莫羽突然扯断颈间的红绳。
那是母亲留给她的翡翠观音,此刻却成了最讽刺的装饰。她把红绳缠在冷亦寒手腕,
将铃铛塞进他掌心:"带小暖去码头,穿蓝条纹的水手每周三会在酒馆招工。""那你呢?
"冷亦寒的瞳孔在晨光中收缩成针尖。莫羽正在用煤灰涂抹小暖的胎记,
动作轻柔得像在描眉:"我去引开巡警,老地方汇合。"她没说的是,
今早在洗衣房偷听到院长要把小暖卖给南洋商人。也没说自己在厨房偷了把剔骨刀,
此刻正贴着大腿绑着。正午的烈日烤着庭院。莫羽故意踢翻巡警的茶盏,
滚水泼在对方锃亮的皮靴上。当警棍挥来时,她露出脖颈的淤青,
用最甜美的声音哭诉:"长官,地窖里还有更多孩子..."尖利的哨声刺破寂静。
莫羽在混乱中冲向锅炉房,身后传来院长气急败坏的咒骂。
她记得冷亦寒教过的:掀开第三块地砖,穿过下水道就能到码头。
铁链却在此刻缠住了排水管。莫羽发狠地拽动脚踝,皮肉撕裂的声音混着警笛格外清晰。
当熟悉的雪松香突然靠近时,她几乎以为是幻觉。"走!"冷亦寒满手是血地抱着小暖,
襁褓上系着的半枚铃铛叮当作响。莫羽看见他额头新鲜的伤口,那是砸破地窖锁头的代价。
爆炸声在身后炸响。莫羽回头时,锅炉房的浓烟已经吞噬半个天空。
冷亦寒的手掌贴着她后腰的胎记,
滚烫得像块烙铁:"院长点燃了煤油..."他们跌跌撞撞跑进码头时,
夕阳正把海水染成血色。莫羽将翡翠观音塞给醉醺醺的水手,换来两张皱巴巴的船票。
冷亦寒突然扯断红绳,将其中半枚铃铛系在她脚链上:"等安顿下来,
我找铁匠..."汽笛声淹没了承诺。莫羽把小暖塞进他怀里,
突然转身冲向浓烟滚滚的孤儿院。她听见冷亦寒在身后嘶吼,听见小暖的哭声混着铃铛脆响,
听见自己的心跳震耳欲聋。火舌舔舐着主楼的雕花玻璃,莫羽在浓烟中摸索到院长办公室。
保险柜里躺着孩子们的卖身契,还有她父亲公司破产的证明文件。当燃烧的房梁砸下时,
她最后看见的是窗外飘落的雪——那是冷亦寒说过要带她看的初雪。
剧痛从后背蔓延开的瞬间,莫羽摸到脚踝的半枚铃铛。铁链终于断裂,
清脆的声响如同那年阁楼上,冷亦寒为她偷来的第一颗水果糖落地时的动静。在意识消散前,
她仿佛听见少年绝望的呼喊穿透火海。那声音后来常在梦里回荡,直到七年后重逢时,
化作总裁办公室里的雪松香,缠绕着半枚生锈的银铃。第三章,
雨夜残章暴雨将墓园的石碑冲刷成苍白的骨殖。莫羽的黑色风衣吸饱了雨水,
沉甸甸地坠在肩头。冷亦寒的伞始终悬在她头顶三寸,
仿佛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七年前那场火海的距离。"你每年都来?"她的靴尖碾碎一截枯枝。
墓碑上没有名字,只有被岁月侵蚀的蓝楹花纹,与冷亦寒婚戒上的雕花如出一辙。
男人伸手拂去碑顶落叶,露出底部暗格:"这里埋着你最爱的诗集。
"羊皮封面在雨水中卷曲,夹着的蓝楹花瓣早已碳化成蝶翼般的薄片,
"每收购一家仇人的企业,就撕一页当祭品。"莫羽的指尖刚触及书页,
记忆便如电流般贯穿全身。十八岁生日那夜,她正是在这本《恶之花》里藏了把餐刀,
趁院长醉酒时割断了他的喉咙。火舌蹿上丝绸窗帘时,冷亦寒抱着小暖撞开房门,
脸上还沾着厨房的面粉。"为什么骗我这是空棺?"她突然掐住他手腕,
力道大得伞骨发出悲鸣。冷亦寒的白衬衫紧贴胸膛,
隐约露出心口荆棘纹身的轮廓:"当年火场只找到你的发卡。"他掀起石碑,
露出下层暗格里的银质发夹,"我亲手埋的。"惊雷劈裂天际。莫羽踉跄后退,
后背撞上蓝楹树粗糙的树干。雨水顺着枝桠浇进衣领,
却浇不灭视网膜上燃烧的画面——冷亦寒跪在焦黑的废墟里,十指血肉模糊地扒拉着瓦砾,
怀中襁褓早已没了声息。"那些刺杀..."她的匕首抵住他咽喉,却抖得划不破雨幕,
"都是你安排好的?"冷亦寒忽然扯开衬衫,雨水顺着肌理流进腰腹间的疤痕。
最深处那道十字形伤口泛着青紫,正是她上个月在游艇派对上留下的。
"泰森化工董事长死前告诉我,当年往你父亲酒杯下毒的是他妻子。
"他抓住她持刀的手按向心口,"现在那女人正在公海喂鱼。"记忆在暴雨中错位。
莫羽看见十二岁的自己蜷缩在洗衣房,冷亦寒正用偷来的酒精为她清洗鞭伤。
月光从气窗漏进来,照见他后腰新鲜的烙伤——那是为她偷退烧药受的刑。
"你总是这样..."刀尖刺破皮肤的瞬间,她尝到唇间咸涩的雨水,
"自以为是地替我复仇..."冷亦寒的吻突然落下,混着血腥与雨水的咸腥。
这个吻比火更烫,比刀更利,撕开她七年未愈的痂。莫羽的匕首深深扎进树干,
蓝楹花簌簌落在交缠的发间。"当年你为我偷药挨打时,
我就发誓..."他的犬齿厮磨她耳垂的旧伤,"要让你亲手斩断所有锁链。
"闪电劈亮墓园,莫羽在冷亦寒瞳孔里看见自己狰狞的面具裂痕。那些所谓的刺杀目标,
竟全是参与过莫氏集团破产案的豺狼。华荣地产的太子爷溺死在自家泳池时,
手中攥着她故意留下的蓝楹花瓣;泰森化工的女主人被鲨鱼撕碎前,
手机里最后一条短信是冷亦寒发的坐标。"你监视我?"她扯开他湿透的衬衫,
荆棘纹身在雨水中泛着诡异的青蓝。
冷亦寒的指腹按上她锁骨处的条形码——那是杀手组织的标记:"每次你任务失败,
地下诊所都会多具无名尸。"他忽然含住她渗血的指尖,"那些替你顶罪的替身,
眼睛都没你十分之一亮。"莫羽的膝盖重重磕上墓碑。记忆如开闸的洪流,
她看见冷亦寒在停尸间为无名尸合上双眼,将蓝楹花瓣塞进他们僵冷的手心。
那些苍白的脸庞逐渐重叠,变成小暖青紫的遗容。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她的嘶吼破碎在雨声中。冷亦寒的掌心贴上她后颈,
那里有被电流灼伤的疤痕:"你被他们抓回去改造时,我正跪在拍卖会现场。
"他的唇擦过她颤抖的眼睑,"用莫氏祖宅换了张进入黑暗的门票。"雷鸣在云层翻滚。
莫羽突然扯下面具,残缺的左脸暴露在暴雨中。
冷亦寒的瞳孔骤然收缩——那道从眉骨撕裂至下颌的伤疤,竟与孤儿院火灾那夜,
他隔着火场看到的焦黑身影完全重合。"现在满意了?
"她抓住他的手按在凹凸不平的皮肤上,"你精心饲养的怪物..."话音戛然而止。
冷亦寒的衬衫在撕扯中敞开,心脏位置赫然纹着枚银铃铛。铃舌是根断箭,正刺穿蓝楹花蕊。
莫羽的指尖触到纹身下的凸起,那是颗嵌在皮下的微型胶囊。"当年火场找到的。
"他划开皮肤取出胶囊,透明舱体内躺着半枚带血的乳牙,"你换牙时非要埋在蓝楹树下,
说等长成新娘就挖出来当婚戒。"记忆在雨中显影。七岁的她举着沾血的乳牙,
冷亦寒在树下挖坑时被碎瓷片割破手指。两个孩子的血混在泥土里,
渗入树根长成今日满枝的蓝楹。"现在它是你的了。"冷亦寒将胶囊系在她颈间,
铁锈味的吻落在伤疤上,"连同我腐烂的余生一起。"警笛声刺破雨幕。
莫羽条件反射地摸向腿侧枪套,却被冷亦寒扣住手腕:"是来扫墓的警察。
"他的拇指摩挲她腕间旧伤,"今年清明特别热闹,你父亲当年的秘书今早刚被保释。
"暴雨冲刷着墓碑上的蓝楹花纹,
莫羽忽然看清那根本不是雕刻——是用无数针孔拼成的摩斯密码。
当她用沾血的指尖抚过凹陷,那些尘封的账目与契约在脑海中自动解码。
原来冷氏集团这些年收购的不止是仇敌,还有所有能指证幕后黑手的证据。
"你从来...没问过我愿不愿意..."她的哽咽被雷声碾碎。
冷亦寒的唇贴上她跳动的太阳穴,声音轻得像叹息:"就像你当年没问我要不要独自逃生。
"积雨云裂开缝隙,月光如银针刺穿夜幕。莫羽在冷亦寒眼中看见自己支离破碎的倒影,
正与他心口的铃铛纹身重叠成诡异的图腾。当警车探照灯扫过墓园时,她突然咬住他喉结,
在血腥味中尝到了咸涩的雨水,与记忆深处那个血火交织的夜晚如出一辙。
冷亦寒的白衬衫在纠缠中彻底敞开,
月光照亮心口新鲜的刀伤——那是她三小时前在晚宴上留下的。
此刻鲜血正顺着肌理流进蓝楹花纹,将银铃染成赤色。
"你的心跳..."莫羽的掌心突然僵住,"为什么有两组频率?"暴雨在此时达到顶点。
冷亦寒握住她探向心脏的手,嘴角扬起破碎的笑意:"当年为你挡下的那颗子弹,
从来就没取出来过。"第四章,蓝楹之约暮色将蓝楹树染成紫雾时,
莫羽的匕首正抵着冷亦寒的咽喉。花瓣落在染血的刀锋上,像极了二十年前那个雪夜,
她为他偷来的第一支绢花。"你连这里都买下来了?"她环视着杂草丛生的庭院。
坍塌的围墙外隐约可见新建的购物中心,唯有这株蓝楹树被玻璃罩精心保护,
树下石碑刻着"莫氏故宅"。冷亦寒的指腹擦过刀刃,
血珠渗入树根处的泥土:"每月十五号,我都在这里等。"他的西装裤沾满草屑,
仿佛还是那个蜷缩在树洞里的少年,"等你来杀我,或者…"雷鸣在云层深处翻滚。
莫羽突然扯开他衬衫,那道横贯胸腹的刀疤正在渗血——正是上周拍卖会上她亲手划开的。
绷带下赫然露出泛黄的纸页,正是《恶之花》缺失的篇章。"用仇人的血当墨水?
"她撕下浸血的纸张,波德莱尔的诗句混着腥甜扑面而来。冷亦寒忽然握住她手腕,
将伤口按在树干刻痕处。年轮沟壑间歪斜的"寒&羽"二字,正与她掌纹严丝合缝。
暴雨倾盆而下。莫羽的视网膜闪过白光,
十六岁生日的场景在雷声中重现:冷亦寒用碎瓷片刻下他们的名字,
鲜血顺着树皮流进她新买的布鞋。那天他说等蓝楹花开满九十九次,就带她去看海。
"你数过吗?"她的指甲抠进树皮,"这些年花开过多少次?"玻璃罩内忽然亮起暖黄灯光。
冷亦寒转动树根处的铜铃,暗格弹出一本皮质账簿。泛黄的纸页间夹着干枯的蓝楹花,
每朵都标注着日期与坐标:"从你假死那年开始,每次收购仇家的企业,就埋一朵在树下。
"莫羽的指尖抚过1998年4月7日的记录。那日正是父亲头七,
冷亦寒在暴雨中收购了泰森化工第一间实验室。压花旁的血指印尚未褪色,
仿佛还能嗅到少年指尖的铁锈味。"当年火灾不是意外。"冷亦寒突然扯开领带,
露出锁骨下方的烙印——竟是莫氏集团的徽章,"你父亲发现了神经药物配方,
那些人要灭口前…"他的喉结滚了滚,"我偷听到通话,但来不及…"惊雷劈裂夜空。
莫羽的匕首深深扎进树干,刀柄上的银铃发出凄厉颤音。
她终于看清那些"刺杀任务"的真相:游轮上的军火商曾向院长贩卖孤儿,
慈善晚宴的贵妇是药物实验的资助者。"为什么现在才说?"她的拳头砸在玻璃罩上,
裂纹如蛛网蔓延。冷亦寒从背后环住她颤抖的肩,
血腥气混着雪松香浸透呼吸:"等我把最后一个仇人埋在树下…"他的唇擦过她耳际旧伤,
"就能干干净净地死在你手里。"暴雨冲刷着玻璃裂痕,莫羽在倒影中看见十八岁的自己。
那夜她本要带冷亦寒私奔,却在码头看见父亲秘书与院长交易。当子弹穿透父亲太阳穴时,
冷亦寒正抱着发烧的小暖躲在货箱里。"你看护小暖那晚…"她突然转身揪住他衣领,
"为什么给她喂安眠药?"冷亦寒的瞳孔在闪电中收缩成深渊:"你听见了?
"他的白衬衫被树杈勾破,露出腰间陈年针孔,"那些人来搜查前,
我只能…"喉结艰难地滚动,"…让她暂时安静。"莫羽的耳光响彻庭院。冷亦寒偏着头笑,
血丝顺着下颌滴在蓝楹花上:"这巴掌比当年在阁楼挨的鞭子疼多了。"他忽然扯开衬衫,
心口纹身下竟藏着圆形疤痕,"你父亲中弹那晚,这颗子弹本该是我的。"记忆如洪水决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