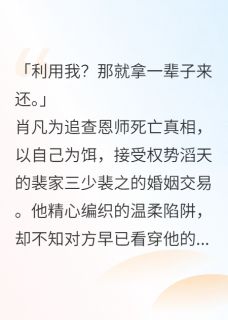1井边残梅映旧梦暮色如墨,缓缓浸透将军府祠堂的飞檐。
顾清婉的膝盖重重磕在青石板上,刺骨的寒意顺着筋骨攀爬,却不及心口传来的万分之一痛。
祠堂内檀香氤氲,烟雾缭绕间,她捧着母亲牌位的手,止不住地剧烈颤抖。依族规,
冬至祭祖这般庄重仪式,向来由嫡女为故去主母上香。可当她捧着鎏金香炉踏入祠堂,
眼前景象如同一记重锤——苏挽月正亲昵地扶着王氏安坐主位,
继母王氏的金丝牡丹裙不经意扫过供桌,庶妹苏挽月腕间翡翠镯子在昏暗光线下晃得人目眩。
“阿姐来得晚了。”苏挽月垂眸,指尖优雅地替王氏理着袖口,话里却藏着刺,“母亲说,
您总记挂着太子殿下,许是忘了今日祭祖的规矩?”王氏端起茶盏轻抿,
丹蔻染就的指甲敲了敲案几,语气满是轻蔑:“婉婉自小被她娘惯坏了,哪里懂得持家守礼?
你娘虽是镇北将军之女,可如今……这将军府的主母,是我。”顾清婉喉间发紧,
往事如潮水翻涌。她清晰记得母亲临终前,那虚弱却坚定地攥着她的手,
声声叮嘱“婉婉一定要好好活着……”可此刻,面对这尖酸话语,
她竟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萧承煜就站在祠堂门口,玄色太子蟒袍裹着寒气,
目光扫过她时,冰冷得如同看待无关紧要的尘埃。“太子殿下。”苏挽月突然娇软地唤道,
“阿姐定是急着给姨母上香,才忘了时辰。”说着,便扶着王氏起身,“娘我们去偏厅用茶,
不扰阿姐尽孝。”王氏的裙裾擦过顾清婉发顶,
她听见那女人压低声音的轻笑:“到底是没了娘的孩子,连争宠都笨手笨脚。
”祠堂门“吱呀”合上的刹那,顾清婉手里的香“啪”地掉在地上。三柱香滚进供桌底下,
落进积年的香灰里。她蹲下去捡,指甲缝里沾满灰尘,指尖突然触到供桌下一块松动的砖。
再探,竟摸到个硬邦邦的陶瓮——是那年她和萧承煜埋下的“岁寒盟”。
瓮口红绸早已褪成灰白,顾清婉颤抖着掀开,里面躺着半卷红梅笺。纸角被井边的风卷起,
露出两行斑驳字迹:“待红梅再开,便娶阿婉。”记忆如决堤洪水,
十二岁那年光景汹涌而来。那时她与十五岁的萧承煜,蹲在枯井旁小心翼翼埋下陶瓮。
他说等明年梅花开,就带她去看雪后初晴的宫墙;他说等做了太子,
就用最红的喜轿抬她进门;他说阿婉是他最珍贵的……“阿姐。”顾清婉猛地抬头,
苏挽月不知何时已站在井边,手中端着茶盏,眉眼温婉:“我见你在祠堂里闷得慌,
特意煮了桂圆茶。”她将茶盏放在井沿,帕子不经意扫过顾清婉手背,“阿姐别难过,
太子哥哥心里……还是有你的。”顾清婉死死盯着茶盏里浮着的桂圆,
水面上几星极细粉末在月光下泛着可疑银光。她想起三日前,萧承煜捏着苏挽月诗稿,
满眼欣赏地说“月儿的字比你温婉”;想起昨日,他替苏挽月披斗篷时,
温柔呢喃“月儿比你善解人意”。那些话语如利刃,在她心上反复剜割。她端起茶盏,
一饮而尽,苦涩在喉间蔓延,却不及心中万分之一。苏挽月指甲掐进掌心,
眼中闪过诧异:“阿姐?”“茶很甜。”顾清婉将空盏递回,指腹擦过帕子上绣的并蒂莲,
那刺目图案似在嘲讽她的天真,“替我谢过妹妹。”夜风呼啸,卷起她的裙角。
枯井里传来幽咽风声,像极了那年萧承煜替她折梅时,梅枝在风中摇晃的声响。
她攥紧怀里陶瓮,转身往偏院走去。那里只有一盏孤灯、一张旧床,和母亲留下的半幅绣绷,
是她在这冰冷世界里仅存的温暖角落。走到院门口时,墙外传来细微脚步声,
轻得像极了萧承煜从前翻她院子的动静。顾清婉驻足,手指无意识摩挲着陶瓮上的红绸,
心中涌起一丝期待,又害怕那只是幻想。风掀起她额前碎发,院外脚步声骤停。她屏住呼吸,
心提到了嗓子眼。有人轻轻叩了叩院墙,那声音像在敲一扇久未开启的门,
也敲在她的心坎上。院外叩墙声又响两声,顾清婉攥陶瓮的手骤然收紧。
她记得萧承煜惯会翻墙头——十二岁那年她在后院练箭,他从墙外来,发顶沾着玉兰,
笑说“阿婉射偏了”,被她用箭尖戳破袖口。门闩“咔嗒”一声开了,
月光下立着个穿玄色劲装的人,腰间银鱼牌昭示着太子府暗卫身份。他递来个檀木匣,
匣面雕着并蒂莲:“太子殿下说,当年的同心佩该物归原主。”顾清婉指尖刚触到匣盖,
暗卫突然侧耳。远处马蹄声传来,他猛地收回手:“苏姑娘的马车往御街去了。”话音未落,
人已翻上墙头,玄色衣摆扫过她发梢,只留檀木匣“咚”地砸在青石板上。她蹲下身捡起,
匣盖摔开,金丝同心佩滚出——那是十五岁生辰,萧承煜亲手所编,
说要将“阿婉的名字刻在我心口”。可此刻佩上沾着的茉莉脂粉香,
分明是苏挽月惯用的味道,如同一把盐,撒在她溃烂的伤口上。第二日卯时,
宫报传至将军府。“太子殿下携苏姑娘赏梅,于御花园红梅树下共饮青梅酒。
”传话小丫鬟偷瞄顾清婉脸色,“那树……是当年您和太子殿下埋‘岁寒盟’的那棵。
”顾清婉手中茶盏“咔嚓”裂开细纹,滚烫茶水溅在手上,她却浑然不觉。
她想起埋陶瓮那日,萧承煜说“等梅树长到两人高,我便娶你”。如今梅树枝桠早扫着宫墙,
树下依偎的身影,却早已换了人。未时三刻,顾怀远的贴身护卫敲响偏院门。
将军府正厅炭火烧得炽烈,顾清婉却感受不到丝毫暖意,额角沁出的细汗,
是因心中的焦虑与不安。父亲将退婚书拍在案上,墨迹未干:“王氏有了龙嗣,
商户那边要苏挽月做太子侧妃。”他指节叩着泛黄的将军令,
“你娘临终前攥着这东西说‘阿婉是将军府嫡女’,可嫡女要护着将军府的根基。
”顾清婉望着那方将军令,母亲最后一次抱她时,也是这般攥着它,说“婉婉要像这令旗,
立得直,站得稳”。可如今令旗蒙尘,恰似她的婚事,恰似她的阿煜哥哥,
一切都已面目全非。“女儿不退。”她声音发颤,却无比坚定。顾怀远拍案而起,
怒目圆睁:“你当太子殿下为何送同心佩?不过是堵你的嘴!
苏挽月的诗稿在御书房摆了半月,你娘的陪嫁庄子早被太子划给商户——你早就是弃子!
”顾清婉怀里陶瓮硌得肋骨生疼,她抱起它往外跑,雪粒打在脸上,像母亲教她骑射时,
马背上呼啸而过的风。御花园红梅开得正艳,红得似火,却暖不了顾清婉的心。
她在梅树下驻足,眼前景象如同一把钢刀,剜着她的心。萧承煜立在树前,手中捏着红梅,
苏挽月仰头娇笑,发间金步摇晃得人眼晕。那场景与十二年前如出一辙——那时他也是这般,
折了梅要簪她发间,说“阿婉戴红梅最好看”。“阿煜哥哥。”顾清婉开口,
声音被风雪撕成碎片。萧承煜转头,他身后的苏挽月突然踉跄,扑进他怀里,
娇嗔:“这梅枝扎人。”他低头替她理乱发,指尖掠过她耳后,
声音轻柔似叹息:“月儿怕疼,我替你挑最软的。”顾清婉指甲深深掐进陶瓮,
仿佛这样能减轻心中的剧痛。她往前走,雪地里碎冰硌得脚疼,每一步都似踏在刀尖上。
萧承煜手抬起,红梅即将落进苏挽月发间的刹那,她拼尽全力喊:“那是我和你的梅树!
”苏挽月猛地回头,眼中闪过得意。顾清婉脚步顿住——她在萧承煜眼中看到的,
只有不耐烦,像看待一个无理取闹的孩童,那眼神,彻底浇灭了她最后的希望。
“阿姐来凑什么热闹?”苏挽月笑着,话语满是嘲讽,“太子哥哥说要替我簪梅,
你当年……不也求过他?”顾清婉脚下一滑,扑向井沿去扶,陶瓮“砰”地摔在地上,
红梅笺散落一地。金丝同心佩从她袖中滑落,“叮咚”坠入井底,那清脆声响,
恰似她心碎的声音。“盯紧顾家嫡女。”萧承煜的声音清晰传来,
“她若怀了龙种……”后面的话被风雪卷走,却如重锤,将顾清婉砸入无尽深渊。
她跪在雪地里,捡起一张红梅笺。“待红梅再开,便娶阿婉”的字迹被雪水晕开,
像十二岁那年,萧承煜替她挡落石时,染在她裙角的血,那抹血色,
成了她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她捂住嘴咳嗽,指缝间渗出温热液体,落在雪地上,
红得像那支没簪成的红梅,也像她渐渐流逝的生机。2药香浸透旧帕顾清婉跪在雪地里,
指缝间血珠不断滴落,宛如红梅被揉碎,染红了这冰冷的雪地。她眼前发黑,耳边嗡嗡作响,
栽倒之际,手仍死死抓着半张晕开的红梅笺,仿佛那是她与往昔唯一的羁绊。
偏院土炕烧得温热,顾清婉却感受不到一丝暖意。迷迷糊糊间,她听见脚步声,
沈太医的药箱“咔嗒”开启,指尖搭上她脉搏的瞬间,她的身体微微颤抖。
“顾姑娘这是……”沈太医声音发紧,带着惊讶,“喜脉。”“可算盼到了。
”王氏的声音从门口飘来,语气中藏着不易察觉的恶意,“沈大人,按我交代的开。
”顾清婉睫毛颤动,闭着眼,听着沈太医磨墨声,
闻着药罐中飘出的异常苦腥——这味道与她喝过的安胎药截然不同。深夜,万籁俱寂。
顾清婉攥着药碗立于井边,井水结着薄冰,她用碗沿敲碎,冰碴扎得手生疼。
药汤“哗啦”倒入井中,药粉沉底时,水面突然映出一道身影。是萧承煜。
他身着玄色暗纹锦袍,翻墙而入。窗纸上映出他翻找的影子,妆匣、枕头,
最后从被褥下抽出张纸——正是太医院张老医正开的安胎方。顾清婉指甲掐进掌心,
钻心的疼痛让她清醒。原来他早已知晓,原来他此来,不过是为药方,而非看她。那一刻,
她的心彻底坠入冰窖。次日晌午,窗棂轻响。顾清婉掀开棉帘,见半卷密函卡在砖缝,
边角沾着新泥。展开一看,是萧承昭的字迹:“苏家祖坟风水局,实则藏王氏与沈医正密信。
苏挽月以‘克母’为由,命沈医正往你茶中掺慢性毒药,三月后必咳血不止,太子见你病弱,
自然生厌。”她浑身发冷,手中茶盏“啪”地坠地碎裂。蹲下身,
她颤抖着将密函塞进腰间同心佩暗格——那是萧承煜十二岁所赠,
他曾说“里面能藏要紧东西”,如今却藏着这般残酷真相。傍晚,苏挽月提着红泥小炉前来。
“阿姐病着,我熬了参汤。”她掀开盖子,白雾中眉眼温柔,可那温柔下,
藏着毒蛇般的恶意,“趁热喝。”顾清婉接过碗,苏挽月的手突然碰向她腕间红绳,
“这绳子旧了,我替阿姐换条新的。”话音未落,红绳“啪”地断裂,坠子滚入床底。
“我的红绳!”顾清婉追出,回廊风大,她看见萧承煜背对着她,手中捏着那截染血红绳。
他指节发白,声音冰冷如淬毒:“谁敢动你物件?”顾清婉脚步顿住,
昨夜井边的场景、他翻找的手,一一在脑海闪过,喉咙发紧,竟说不出话。“阿婉?
”萧承煜走近,抬手欲碰她脸,那动作似还带着往昔温柔,却让她只觉讽刺。她后退一步,
撞在廊柱上,躲开了他的触碰。他的手悬在半空,前院突然传来喧哗。“大人!
朝堂送来急报,说有匿名奏章……”下人的声音被风卷走。萧承煜拧眉,将红绳塞进她手里,
“等我。”可顾清婉明白,这不过是敷衍之词。她攥着红绳立于风中,
听见“将军府”“私通北境”等字眼,如冰锥刺入耳朵。雪又纷纷扬扬落下,落在同心佩上,
暗格里的密函被捂得温热,可她的心,却愈发寒凉。偏院雪未停,
顾清婉攥着红绳的手冻得发僵时,暗卫破门而入。“太子宣顾姑娘即刻上殿。
”刀鞘撞在门框上的钝响,仿佛预示着一场风暴的降临。金銮殿内地龙烧得人发闷,
顾清婉却通体冰凉。她跪在前朝青砖上,
听见萧承昭冰冷如冰锥的声音:“匿名奏章指将军府私通北境,皇兄当真不知?
”萧承煜端坐龙椅,玄色朝服泛着冷光,威严表象下,是对她的怀疑与冷漠。他突然甩袖,
一卷染着朱砂的纸页“啪”地拍在顾清婉脚边:“顾家嫡女竟勾结外敌?
”墨迹未干的“北境密信”在她眼前展开,顾清婉指尖颤抖——那分明是沈太医的仿冒字迹,
她曾在王氏房里见过类似药方。“不是我!”她抬头,却撞进萧承煜淬毒般的眼神,
那眼神让她感到无比陌生与恐惧。“搜。”他冷冷吐出一个字,便将她推向绝望深渊。
暗卫的手探入她袖中时,顾清婉想起昨夜井边的风。
她原以为藏在同心佩暗格里的密函能证清白,此刻才惊觉——苏挽月扯断红绳那日,
有人早已动了她的袖袋。伪造的密信被抛上御案,萧承煜捏着信角,指节泛白:“顾清婉,
你还有何话?”她张了张嘴,喉间像塞了团雪,满心的委屈与不甘,却无法言说。
殿外的雪落在她发间,恍惚间,她又看见十二岁的萧承煜,举着同心佩说“阿婉的东西,
我替你守”,可如今,他却亲手将她推入万劫不复之地。当夜,顾清婉翻墙逃出偏院。
她裹着萧承煜旧年所赠狐裘,蹲在枯井后的老槐树上。月光洒落,照见苏挽月扶着沈太医,
鞋尖踢着井边碎瓷——那是她前夜倒药汤的碗。“三日后上元灯会。
”苏挽月声音甜腻得发腻,“让太子亲眼见她癫狂,到时候……凤印就是我的。
”沈太医搓着手:“那慢性毒药掺在茶里三月,她早该咳血了,怎的还……”“笨。
”苏挽月轻笑,“我让丫鬟每日往她粥里加半钱朱砂,
胎儿早烂在肚子里了——她以为喝的是安胎药?”顾清婉指甲掐进树皮,心中剧痛难忍。
她想起昨夜熬的药,苦腥中混着甜腻朱砂味——原来从一开始,沈太医开的就是堕胎药。
第二日,顾清婉翻出压箱底的安胎药粉。那是张老医正偷偷塞给她的,说“若信不过太医院,
便用这个”。她捏着药粉立于厨房外,见苏挽月侍女端着莲子羹经过,故意撞翻醋坛。
“哎呀!”侍女蹲下擦地,顾清婉迅速将药粉撒进羹里。3血染凤仪牌上元夜,灯市如昼,
人声鼎沸。顾清婉身着素白裙裾,宛如一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百合,静静伫立在桥边。
她的目光,死死锁定在远处那道熟悉的身影上——苏挽月身着金丝绣就的崭新华服,
步履摇曳生姿,在人群中仿若闪耀的星辰,而陪伴在她身旁的,
正是顾清婉曾日夜思念的萧承煜。顾清婉缓缓端起手中的莲子羹,那碗中褐红色的汤汁,
在灯火的映照下,宛如凝固的鲜血。她的手微微颤抖,心中百感交集,有恨,有怨,
更有深深的不甘。最终,她轻轻一松手,“哗啦”一声,莲子羹如一道诡异的血瀑,
尽数泼洒在苏挽月的裙裾之上,瞬间染出一片狰狞的“血花”。“阿姐!
”苏挽月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呼,踉跄着连连后退,那双美目瞬间蓄满了委屈的泪水,
模样楚楚可怜,不知情的人见了,定会心生怜惜。人群顿时如沸水般骚动起来,
纷纷围拢过来,好奇地张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顾清婉的目光越过嘈杂的人群,
与萧承煜那道冰冷的视线撞了个正着。此刻的他,身着玄色华服,
腰间那枚曾经属于她的同心佩坠子在灯光下若隐若现,刺痛着她的双眼。她喉咙发紧,
满心想要呼喊“阿煜哥哥”,诉说自己的冤屈与痛苦,可话到嘴边,
却被萧承煜那冷硬如铁的声音生生打断:“顾清婉,你当这是将军府后院?
”“我……”顾清婉向前迈出一步,想要解释,喉间却突然涌上一阵腥甜。
暗红的血珠不受控制地从她口中溢出,重重地溅落在雪地上,与那洒落的药粉混在一起,
形成一幅凄惨而又诡异的画面——那是她昨夜呕出的、带着胎气的血,是她失去孩子的证明。
萧承煜的瞳孔骤然紧缩,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他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然而,
就在他即将触碰到顾清婉的瞬间,苏挽月却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哭哭啼啼地拽住他的袖子,
娇声说道:“太子哥哥,阿姐她……她定是被北境的邪术迷了心。
”萧承煜伸出的手猛地顿在半空,原本急切的眼神逐渐变得冰冷。
顾清婉望着他那逐渐冷下去的目光,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破灭。她突然弯下腰,
一阵剧烈的腹痛从下腹如汹涌的潮水般涌来,仿佛有无数把利刃在绞动着她的五脏六腑。
她强撑着扶住井边的石栏,指缝间渗出的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入井中,
在水面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宛如她破碎的心境。林嬷嬷从人群中拼命挤了出来,
眼含热泪地扶住她的腰,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姑娘……你这是……”顾清婉咬着嘴唇,
缓缓摇头,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井水里倒映着她惨白如纸的脸庞,
以及远处萧承煜被苏挽月拉走的背影,那背影渐行渐远,仿佛要带走她生命中所有的光。
她听见林嬷嬷带着哭腔的声音混着周围嘈杂的人声,
如同隔了一层毛玻璃般模糊不清:“快……快回偏院……”雪,越下越大,
纷纷扬扬地落在她的发间,落在井里,也落在她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顾清婉扶着井栏,
慢慢地蹲下身来。就在这时,
她突然听见肚子里传来一阵细微的动静——那不该是三个月大的胎儿能发出的动静。
她的手紧紧攥着同心佩,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心中满是苦涩与绝望。
井边的灯笼在寒风中被吹得不停地摇晃,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身上,
映出她裙角渗出的暗红血迹,宛如一朵在寒冬中凋零的红梅,凄美而又悲凉。
顾清婉的指甲深深抠进井边的石缝里,每一下都仿佛要将自己的痛苦与不甘宣泄出来。
腹痛如汹涌的潮水,一波比一波更猛烈,好似有熊熊燃烧的火舌,裹挟着锋利的刀刃,
在她的腹中肆意翻搅,疼得她几近昏厥。林嬷嬷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扶着顾清婉的胳膊也跟着直打颤,
声音里满是惊恐与绝望:“姑娘……血止不住……保不住了……”顾清婉紧咬着嘴唇,
直到尝到了铁锈般的血腥味。下身的热流汹涌而出,伴随着黏腻的疼痛,
仿佛要将她的生命一同带走。突然,林嬷嬷发出一声尖锐的尖叫:“头……露头了!
”顾清婉只觉眼前一黑,意识开始模糊。她隐约感觉到有一团小拳头大小的东西滑了出来,
浑身裹着血污,却没有发出一声啼哭。林嬷嬷颤抖着伸手去探孩子的鼻息,
手却猛地缩了回来,
声音里充满了悲痛:“没气了……是个女娃……”顾清婉强撑着最后一丝意识,
盯着那小小的身子,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夺眶而出,砸落在雪地上。
她的手依然紧紧攥着同心佩,暗格里的密函早已被体温焐软。她颤抖着解下玉佩,
用染血的帕子小心翼翼地裹住女娃,塞进空心的玉坠里——那是当年萧承煜亲手雕琢的,
说好了要用来装他们婚书的。“阿姐……你疯了?”林嬷嬷想要阻拦,却被顾清婉用力推开。
顾清婉扯下裙角,用尽全身力气咬破指尖,鲜血如珠般滴落。
她颤抖着在帕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勿寻太子”。就在这时,井壁突然簌簌地落下灰尘。
顾清婉艰难地抬起头,只见青苔裂开了一条细缝,
露出半截陶瓮——是御花园里那口承载着她和萧承煜美好回忆的陶瓮!当年,
他们满怀期待地埋下“岁寒盟”,约定等红梅再开就娶她。如今,陶瓮上的红漆早已褪去,
刻着“阿煜阿婉”的四个字,也被青苔遮盖了一半。顾清婉伸出手,缓缓地摸向陶瓮,
冰冷的井水漫过她的脚踝,寒意瞬间蔓延全身。然而,她却突然笑了起来,泪水和着血珠,
一滴一滴地掉落在瓮上:“原来你藏在这里……”与此同时,御书房内,
朱砂印狠狠地砸在诏书上,“废后”两个字如同一记重锤,刺痛着萧承煜的双眼。
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井边那滩触目惊心的血迹,仿佛红梅被无情地踩烂,
刺痛着他的内心。苏挽月娇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陛下英明,顾氏善妒,
早该……”“善妒?”萧承煜突然猛地转身,如同一头暴怒的狮子,掐住苏挽月的脖子。
苏挽月的脸瞬间涨成了紫茄色,她拼命地用指甲抓挠萧承煜的手背,
声音里充满了恐惧:“你……你发什么疯?”“她肚子里的孩子。
”萧承煜的拇指用力碾着她的喉结,眼中燃烧着熊熊的怒火,“你动的手?
”苏挽月却突然笑了起来,泪水从她的眼中涌出:“不过是碗堕胎药……她这种女人,
留着孩子也是祸……”“咔嚓”一声脆响,萧承煜毫不犹豫地掐断了她的气管,
将她狠狠地甩在地上。太监们吓得纷纷跪地,浑身颤抖着,大气都不敢出。
只见萧承煜拎起苏挽月的脚,一路拖着她出了殿门。“扔井里。
”他的声音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井底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苏挽月的头重重地撞在陶瓮上,碎片四处飞溅。萧承煜探出身子,想要去够什么,
一片锋利的陶片瞬间划开了他的手背,鲜血如注,一滴一滴地落进井里,
与顾清婉的血混在了一起,仿佛在诉说着这一场悲剧的惨烈。
“报——”卫队长焦急地跪在殿外,大声禀报道,“镇北将军世子萧承昭,带三千亲卫闯宫,
说要救顾氏。”萧承煜缓缓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眼神中充满了疯狂与决绝。他抓起案上的剑,
冷冷地说道:“通敌。”箭雨如蝗虫般落下,萧承昭的剑还未来得及挥出,便被无情地射倒。
他的怀里掉出一个东西——那是一枚梅枝书签,上面还染着鲜血,
正是当年萧承煜亲手折了送给顾清婉的。顾清婉静静地蹲在井底,
看着井口的光被阴影一点点遮住。当兄长的尸体被无情地拖走时,那枚书签也滚到了井边,
渐渐地被雪覆盖了一半。她伸出手,想要抓住那最后的一丝回忆,然而,
冰冷的井水却漫到了她的腰间。“姑娘!”林嬷嬷趴在井口,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陛下说……说要见你!”顾清婉紧紧攥着裹着孩子的同心佩,心中满是悲凉。
井壁的陶瓮裂开了一道缝隙,露出半卷发黄的纸——那是她当年写下的“岁寒盟”,
上面“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却又显得那么讽刺。
远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林嬷嬷突然止住了哭声。
顾清婉听见王氏那尖细如针的声音传来:“陛下,李尚书说……这井里的人,
该劝降了……”萧承煜的剑出鞘声在寂静中格外响亮。顾清婉缓缓闭上了眼睛,
任由冰冷的井水漫过头顶。在最后一刻,她摸到了陶瓮里的纸,
上面自己的字迹依然清晰:“阿煜哥哥,我等你娶我。
”王氏的指甲深深地掐进李尚书的胳膊,她望着井底翻涌的黑水,喉结动了动,
说道:“陛下,顾氏通敌,您若肯降她为庶人……”“通敌?”萧承煜的剑从鞘中滑出半寸,
寒光扫过王氏鬓边的珠花,眼中满是杀意。李尚书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额头重重地撞在青石板上:“老臣愿为顾氏说项,将军府……”“说项?
”萧承煜的剑尖挑起李尚书的官袍,露出里面绣着的商队暗纹,“你可知罪?
”他想起三日前户部呈上来的账本——商户往敌国运的粮草,正是李尚书批的印。
王氏惊恐地后退半步,却撞在了井栏上。萧承煜的剑更快,瞬间刺穿了李尚书的心口,
又毫不留情地挑断了王氏的喉管。鲜血如喷泉般溅在井壁上,顺着青苔缓缓往下流淌,
最后落进顾清婉方才躺过的水洼里,染红了那一片冰冷的水域。“搜她。
”萧承煜甩了甩剑上的血,冷冷地对发抖的太监说道。当苏挽月的尸身被拖过来时,
裙摆上还沾着井底的泥污。太监粗暴地撕开染血的缎面,
内衬上金线绣的“王氏”二字格外刺眼,刺得萧承煜眯起了眼睛。他突然疯狂地笑了起来,
笑声在宫墙上回荡,惊飞了一群乌鸦:“好个替姐探病,
好个孤女投亲……原来克母的是你们!”井底传来一阵水声,顾清婉扶着井壁,
缓缓浮了上来。她的头发湿漉漉地黏在脸上,怀里的同心佩被井水浸得透凉。
她望着井边横七竖八的尸体,又看了看萧承煜那沾满鲜血的手,张了张嘴,
轻声唤道:“阿煜……”萧承煜缓缓转身,手中的凤印被他捏得“咔咔”作响。
“你死了才好。”他的声音冰冷而又绝望,指缝间渗出的鲜血,将碎瓷片扎进肉里,
“省得我……”话音未落,他突然踉跄了一下,
右手死死地捂住心口——那里正是顾清婉跳井前,用**刺进他掌心的位置。
当时她写下“勿寻太子”,血珠渗进他的皮肤,此刻竟像有根毒针在狠狠地扎着,痛入骨髓。
顾清婉想要伸手去扶他,可手刚碰到他的衣袖,就被萧承煜狠狠甩开。他后退两步,
撞在了烧得只剩半面墙的凤仪宫上。他死死盯着顾清婉怀里的同心佩,
突然想起那日她被废后时,也是这样紧紧攥着玉坠,雪落在她的睫毛上,美得让人心碎,
却又那么遥不可及。“烧。”他眼神空洞地对卫队长说道,“把凤仪宫烧了。
”火把被扔了进去,苏挽月的尸身也被无情地拖进了火海,顾清婉的牌位同样未能幸免。
萧承煜静静地站在火前,从灰烬中扒出半卷红梅书笺——那是当年他折梅簪在她发间时,
她写下的“愿逐晨霞伴君老”。火光照得他眼尾发红,他对着虚空,失魂落魄地笑了起来,
声音轻得如同梦呓:“阿婉,我烧了凤仪宫,烧了苏挽月,
烧了李尚书……你可愿……再与我埋一次陶瓮?”夜更深了,崔嬷嬷裹着灰布斗篷,
蜷缩在凤仪宫的废墟外。她望着余烬中忽明忽暗的火光,
摸了摸怀里的药瓶——那是顾清婉跳井前,她没来得及递上的安胎药。一阵风卷起灰尘,
扑在她的脸上。崔嬷嬷眯起眼睛,看见焦土上有个东西在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她蹲下身,
用枯枝轻轻地拨了拨——半块同心佩,上面染着鲜血,刻着“阿煜”二字,
还沾着没烧尽的帕子边角。她刚要伸手去拾,远处突然传来巡夜的脚步声。
崔嬷嬷慌忙攥紧帕子,缩进残墙后,心跳如擂鼓,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暗角里,
半块玉佩上的血渍在月光下泛着暗红,隐约能看见另一面刻着“阿婉”。
)4青苔藏骨未亡人崔嬷嬷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巡夜的脚步声碾碎焦土,
每一下都像是踩在她的心上。她蜷缩在残墙后,枯枝扎得手背生疼,却不敢发出一丝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