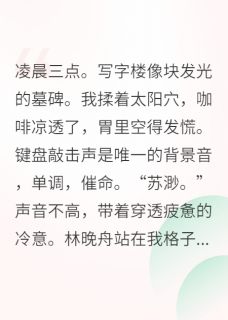我叫沈青梧,曾是京城最让人艳羡的侯夫人。如今,指尖抚过这只描金牡丹香炉冰凉的炉壁,
只觉得讽刺。这香炉,是我那好夫君秦砚之,在我生辰那日,亲手捧到我面前的。“青梧,
”他那时眼神温柔得能溺死人,执起我的手,语气是十二万分的真诚,
“这‘暖情香’是我费尽心思寻来的海外珍品,安神助眠最好不过。你为**持中馈,
殚精竭虑,我只愿你夜夜安枕无忧。”他轻吻我的指尖,誓言犹在耳畔回响,
“此生唯你一人,绝不负卿。”呵,绝不负卿?三年前,
他秦砚之不过是个家徒四壁、空有几分才学的寒门举子。是我沈家,
看中他当时那点清朗风骨,我爹散尽半数家财,为他疏通关节,打点考官。他高中探花,
御前得脸,一步步青云直上,直至封了这忠勇侯,哪一步离得开我沈家的鼎力支持?
我沈青梧的嫁妆,更是填补了他侯府初立时的无数窟窿!可这爵位刚稳当,
他那远房的“好表妹”柳含烟就“恰巧”父母双亡,来京城投奔了。
秦砚之牵着那弱柳扶风的柳含烟到我面前,眼底是我从未见过的怜惜:“青梧,含烟命苦,
以后你就是她的亲姐姐。她孤身一人,我们定要好好照拂。”他握着我的手,言辞恳切,
“她已与吏部侍郎之子赵珩定亲,待她出嫁,我们便是她唯一的娘家人了。”我那时,
竟还信了他这副情深义重的模样。想着他念旧情,是好事。我沈家嫡女的气度,
自然要善待这孤女。可秦砚之的“照拂”,却越来越离谱。“青梧,含烟年纪小,
没见过什么世面,你那些新打的头面,匀几件给她戴着玩玩?免得去赵家被人小瞧了去。
”“这匹流光锦是贡品吧?含烟皮肤白,穿着定好看,你做了那么多新衣,这匹就给她吧?
”“含烟身子弱,库房里那支百年老参,炖了给她补补?”一件件,一桩桩。我的东西,
我的嫁妆,只要柳含烟多看一眼,秦砚之便软语温言地来讨要。我稍有迟疑,
他便蹙眉叹息:“青梧,你素来大方,怎地对自家表妹如此计较?她孤苦伶仃,
我们不多疼她些,谁疼她?”那语气,仿佛我才是那个刻薄寡恩的外人。更令人心寒的是,
柳含烟的胃口越来越大。有一次,柳含烟“突发奇想”,
说想要我院子里那株我精心培育了五年、刚刚开花的稀世绿牡丹。那是我从江南重金求来,
视若珍宝。秦砚之竟也开口:“青梧,含烟喜欢得紧,你素来爱花,再寻一株便是了。
这株就挪去她院里赏玩几日。”我强忍着怒火拒绝,秦砚之竟沉了脸:“你身为侯府主母,
连一盆花都舍不得给妹妹?心胸未免太过狭隘!”最终,那盆绿牡丹还是被强行抬走,
放在柳含烟窗下。没过几日,便因照料不当枯萎了。柳含烟只是撇撇嘴:“哎呀,
这花儿真娇气,没福分。”秦砚之却反过来安慰她,对我枯萎的珍宝视而不见。柳含烟呢?
在我面前,永远是那副怯生生、感激涕零的模样:“多谢表嫂,含烟真是几世修来的福气,
能有您这样好的嫂嫂照拂。”可背过身去,那眼神里的得意与轻蔑,却像针一样扎人。
更让我恶心的是,她竟敢在无人时,用帕子掩着嘴,低低笑道:“表嫂这正室的头面衣裳,
穿在我身上,倒比表嫂更合衬几分呢。表哥也是这么说的……”她故意拖长了调子,
眼中是淬毒的得意。而秦砚之,自柳含烟来后,对我越发“体贴”却也越发疏离。
每日公务“繁忙”,回府便道疲惫,十次有九次宿在书房。偶尔宿在正房,也是心不在焉,
草草了事,再无半分新婚时的温存。甚至当我主动亲近,他会不着痕迹地避开,
皱眉道:“青梧,你如今是侯夫人,当持重些。含烟还在府里,莫要让她觉得我们轻浮。
”他开始挑剔我。说我管家太过严苛,不如含烟“懂得体恤下人”;说我妆容太过庄重,
不如含烟“清水芙蓉天然去雕饰”;甚至有一次,他看着我精心准备的晚膳,竟说:“青梧,
你这手艺比起含烟在老家学的江南小菜,还是差了些火候和心思。”那语气里的嫌弃,
毫不掩饰。更让我心冷的是,他开始明里暗里暗示我“无出”。在婆婆面前,
他会叹气:“母亲,儿子不孝,至今未能让您抱上嫡孙。”目光却若有似无地扫过我。
婆婆看我的眼神也日渐不满。可明明,他夜夜“宿在书房”或早早将我“安睡”,
我如何能有孕?他将不育的责任,悄无声息地推到了我身上!每每留宿正房,
必定亲手燃起那“暖情香”,温柔地哄我喝下他端来的安神汤。起初我只道他体贴。
直到有一夜,那安神汤味道似乎淡了些,我睡得并不沉,半夜被窗外隐约的调笑声惊醒。
鬼使神差,我披衣起身,循声走到西暖阁窗外。那虚掩的窗缝里透出的烛光,
和里面不堪入耳的交欢声,还有柳含烟那娇媚入骨的“表哥……你比那赵木头强多了……”,
以及秦砚之满足的低吼……柳含烟娇喘着问:“表哥,
你说要是沈青梧那个不下蛋的母鸡知道了我们的事,会不会气死啊?”秦砚之嗤笑一声,
声音带着情欲的沙哑和不屑:“知道又如何?她沈家如今还能奈我何?我已是忠勇侯!
离了她沈家,我照样稳坐这位置!她若识相,就乖乖当她的摆设夫人,
否则……”他声音陡然转冷,“有的是法子让她‘病逝’!到时候,这侯府的一切,
还有沈家剩下那点家底,还不都是我们的?含烟,你再给我生个儿子,这爵位,
将来就是我儿子的!
烟得意地娇笑:“那表哥可要快些…人家可不想顶着赵家未婚妻的名头太久…等赵家退了婚,
你就休了那黄脸婆,风风光光娶我进门!”原来如此!什么安神香!什么安神汤!全是**!
全是为了迷晕我,好方便他们这对狗男女苟合!他夜夜宿在书房?分明是宿在这西暖阁,
宿在柳含烟的床上!而他竟让我,他的正妻,把他偷情的表妹当亲妹妹照顾,
还把自己的衣服首饰送给她穿戴?!滔天的怒火和灭顶的羞辱几乎将我焚烧殆尽!
我死死咬住嘴唇,尝到了血腥味,才没让自己尖叫出声。我踉跄着回到冰冷的床上,
睁眼到天明。看着枕边空无一人,看着那袅袅余烟的香炉,心,一寸寸冷成了寒铁。哭闹?
寻死?那是懦夫所为。我沈青梧,沈家嫡女,不是任人欺辱的菟丝花!秦砚之,柳含烟,
你们加诸我身的屈辱,我要你们百倍偿还!我要你们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
我强压下所有情绪,面上依旧是那个温婉大度的侯夫人。暗中,我以“心悸难眠”为由,
重金寻访名医,不仅确认了自己身体康健,更将那“暖情香”和安神汤的残渣秘密送去检验。
结果不出所料——香是致人昏睡的“梦甜乡”,汤里加了助眠的曼陀罗汁。
好一个“安神助眠”!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那位医术高超的老大夫,
在仔细诊脉和询问了我的日常饮食后,面色凝重地告诉我:“夫人,
您体内有长期服用微量‘寒食散’的迹象。此药性极寒,久服会严重损伤胞宫,
导致……终身难孕!”如同五雷轰顶!我瞬间想起了每日晨起,
秦砚之都会亲手端给我的那碗他声称是“宫中秘方、滋补养颜”的燕窝羹!原来如此!
他不仅要迷晕我方便偷情,更要彻底绝了我的子嗣!好让柳含烟的儿子名正言顺地继承一切!
这算计,何其歹毒!滔天的恨意几乎将我吞噬!秦砚之,柳含烟,你们不仅要我的尊严,
要我的钱财,还要断我的血脉,谋我的性命!此仇不报,我沈青梧誓不为人!
我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证据。柳含烟每次穿戴我的衣物首饰去秦砚之书房“送点心”,
我都“恰好”让心腹丫鬟看见。她与秦砚之在花园“偶遇”时的眉来眼去,
我也“无心”让洒扫的婆子瞧个正着。这些风言风语,最终都会成为压垮他们的稻草之一。
最重要的,是赵家。吏部侍郎之子赵珩,清贵孤高,最重礼法规矩,眼里容不得沙子。
我精心挑选了一个赵珩陪同母亲上香的日子,“偶遇”在寺庙后山。“赵公子安好。
”我微微颔首,眉宇间带着恰到好处的忧虑。“侯夫人。”赵珩回礼,目光清正,
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柳含烟即将成为他的妻子,而我,
是柳含烟在京城唯一的“娘家人”。“赵公子,”我轻轻叹了口气,欲言又止,
“含烟妹妹近日……似有些心事,夜不安寝,
常于府中西暖阁礼佛至深夜……我与侯爷劝过几次,总不见效。她心思重,又孤身在此,
我这做嫂嫂的,实在忧心她嫁入贵府后,若还如此郁结,恐……”我顿了顿,
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忧虑,“而且,
含烟妹妹似乎……对侯府库房里一些逾制的东西,格外感兴趣。我曾委婉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