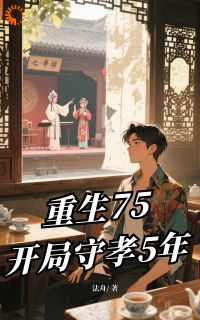第十年了。北风卷着哨音,刀子似的刮过雁回关斑驳的城墙,扬起陈年的沙尘。
城楼垛口上干枯的蒿草,在风里簌簌地抖。苏雁回裹紧了身上半旧的靛青色棉袍,
还是觉得那股子寒气无孔不入,顺着骨头缝往里钻。
她站在自家那间小小的“雁归茶肆”门口,木头门槛已被磨得溜光发亮。她微微仰着头,
目光像是生了根,牢牢钉在关城西面最高、也最空寂的那座箭楼上。灰蒙蒙的天幕下,
一大群黑点由远及近,排成巨大而熟悉的“人”字,带着穿透寒风的嘹亮鸣叫,
正顽强地向着北方,向着关外那片广袤而寒冷的故乡飞去。雁阵掠过城楼上方,
翅膀拍打空气的声音清晰可闻,卷起的风拂乱了苏雁回鬓边几缕早已花白的发丝。
大雁北飞了。十个寒暑,整整十次。每一次雁群归来,翅膀划破长空的声音,
都像一把钝刀子,在她心口上缓慢地、反复地磨着。最初几年,那声音是滚烫的,
带着灼人的希望,烧得她眼眶发热,浑身血液都往头顶涌。她总会早早爬上城楼,
挤在那些同样翘首期盼的妇人堆里,踮着脚,脖子伸得老长,
目光贪婪地扫过每一个从关外涌入的人流,搜寻那张刻进骨血里的面孔。每一次城门洞开,
马蹄踏着烟尘奔来,她的心都会提到嗓子眼,又随着一张张陌生面孔的出现,
沉沉地摔回冰冷的腔子里。一次,又一次。后来,希望渐渐被风沙磨蚀掉了锋利的棱角,
变得沉重而麻木。她不再爬上城楼,只是倚在茶肆的门框边,像此刻这般,
静静地望着那空无一人的箭楼垛口。那是他走时最后挥手的地方。那地方太高,太荒凉,
除了偶尔停驻几只昏鸦,再无人迹。仿佛一个巨大的、沉默的伤口,
刻在雁回关沧桑的额头上。雁声渐远,终至消失。天空重新变得空茫,只剩下呼啸的风。
箭楼的垛口依旧空着,像一个无言的嘲笑。苏雁回缓缓垂下眼睫,
遮住了眼底最后一丝微弱的光。十年了。连大雁都记得归期,他呢?心底有个角落,
冰封了十年,此刻又被这如期而至的雁鸣和如期而至的空荡,狠狠凿了一下,
裂开细微的纹路,渗出细密的、无声的疼。她拢了拢鬓边被风吹乱的灰白发丝,转身,
掀开厚重的蓝布棉门帘,弯腰走进了自家这间小小的茶肆。门帘落下,
隔绝了关外粗粝的风沙,也隔绝了那片空寂的天空。茶肆里光线有些暗,
弥漫着柴火、劣质茶叶和关外汉子身上汗味、牲口味混杂的气息。几张粗糙的木桌条凳,
坐了三两拨客人。有穿着肮脏羊皮袄、靴子上沾满泥雪的赶脚行商,
正就着粗瓷碗里浑浊的茶水啃着干硬的馍;也有几个本地闲汉,围着一小碟咸豆,
唾沫横飞地争论着今年的皮毛价钱。“掌柜的,添水!”一个满脸络腮胡的行商粗着嗓子喊。
苏雁回脸上没什么表情,只低低应了一声“来了”,便提着粗陶大茶壶走过去。
热水注入粗瓷碗,热气腾腾地模糊了那行商胡子拉碴的脸。她动作麻利,
却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疏离和疲惫。十年的光阴,不仅染白了她的鬓角,
也在她眼角刻下细密的纹路,更在她周身沉淀下一种洗不掉的暮气,
像这茶肆里经年不散的烟火气。就在这时,棉布门帘又被掀开了。
一股更猛烈的寒气裹着雪沫子涌了进来,吹得炉膛里的火苗都矮了一截。
一个高大的身影堵住了门口的光线。茶肆里嘈杂的声音瞬间低了下去。所有人的目光,
有意无意地都瞟向了门口。来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肘部和膝盖都打着深色补丁的旧棉袄,
棉袄外面套着一件同样破旧、看不出原色的羊皮坎肩。肩上背着一个瘪塌塌的粗布行囊。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头上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旧毡帽,帽檐的阴影,
几乎完全遮住了他的左半边脸。阴影下,隐约可见一道深色的、扭曲的布条横亘而过,
严严实实地覆盖着左眼的位置。露出的右眼,眼皮有些浮肿,眼白浑浊带着浓重的血丝,
目光沉沉的,像蒙着一层关外终年不化的冻土,没有任何温度地扫过茶肆里简陋的桌椅和人。
他沉默地走到最角落、最避风的一张桌子旁坐下,那张桌子紧挨着泥坯垒的灶台,
是茶肆里光线最暗、也最不起眼的位置。他坐下时,动作有些僵硬,似乎右腿不大灵便。
那个瘪塌塌的行囊被他放在脚边。伙计阿旺,一个十六七岁、脸上还带着稚气和怯懦的少年,
立刻皱了皱鼻子,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嫌恶。他磨蹭了一下,
才不情不愿地拎着茶壶走过去,粗声粗气地问:“喝点啥?”独眼男人没有立刻回答。
他微微抬了抬下巴,视线似乎落在了灶台上那个烧得发黑的粗陶大茶壶上,
又似乎什么也没看。半晌,才从喉咙深处挤出两个沙哑干涩的字,
像是生锈的铁片在摩擦:“山茶。”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
让角落里那几个闲汉都停止了争论,朝这边望了一眼。“山茶?”阿旺愣了一下,
随即撇撇嘴,嘟囔道,“苦得很,没人喝那玩意儿。”雁回关地处边陲,
商旅往来求的是解乏暖身,喝的多是粗粝的砖茶沫子,要么就是兑了盐巴和奶的酥油茶。
本地山崖上长着一种叶子极厚、味道奇苦的野生茶树,寻常百姓嫌它刮油水,苦涩难咽,
只有实在没嚼谷的穷苦人偶尔采来熬煮,权当个水味。苏雁回心善,
每年采茶季也会收一点晒干备着,但一年到头也卖不出几壶。独眼男人没再说话,
只是从怀里摸索出两枚边缘磨得发亮的旧铜钱,轻轻放在油腻的桌面上。铜钱碰撞,
发出细微的轻响。阿旺看着他放在桌上那两枚可怜的铜钱,再看看他那身破烂和骇人的独眼,
脸上的嫌恶更浓了。他一把抓过铜钱,没好气地说了句“等着”,转身走到灶台边。
他没有去拿装山茶叶的旧竹罐,反而从角落一个落满灰尘的破陶罐里,
胡乱抓了一把颜色发黑、碎末居多的陈年茶渣——那是平时扫地扫出来的、准备倒掉的废物。
他把这些碎渣扔进一个豁了口的粗陶碗里,提起滚水,粗暴地冲了下去。
深褐色的茶水瞬间溢满了碗沿。阿旺端着这碗浑浊不堪、散发着霉味的“茶”,
重重地顿在独眼男人面前,茶水溅出来几滴,落在破旧的桌面上。“喏,你的苦茶!
”他语气带着明显的轻蔑和不耐烦。独眼男人的目光,落在那碗冒着可疑热气的浑浊液体上。
那只完好的右眼,瞳孔似乎微微缩了一下,但脸上依旧是那副冻土般的漠然。他没有碰碗,
也没有看阿旺,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像一块扎根在角落里的顽石。
阿旺被他这无声的反应弄得有些发毛,更觉得晦气,生怕这瘟神坐久了影响生意。
他左右看看,见苏雁回正背对着这边给另一桌添水,便飞快地端起那碗滚烫的“茶”,
几步走到门口,“哗啦”一声,狠狠泼在门外的冻土地上。冒着热气的深褐色水渍,
在冰冷的泥地上迅速洇开一小片污迹,又被寒风卷起的尘土迅速覆盖。“喝完了!赶紧走人!
”阿旺故意大声说着,像是在宣告某种胜利,把空碗随手往旁边的水盆里一丢,
发出哐当一声响,然后叉着腰,挑衅似的瞪着角落里的男人。茶肆里短暂的安静被打破,
行商们继续啃馍,闲汉们继续争论,只是偶尔投向角落的目光,多了几分看戏的意味。
独眼男人依旧沉默。他像是没有听见阿旺的叫嚣,也没有看到那碗被泼掉的茶。
他那只浑浊的右眼,缓缓抬起,越过阿旺,越过几张桌子,
落在了苏雁回微微佝偻着背、正低头给客人添水的侧影上。那目光极其复杂,
像压抑着千钧重物,又像深潭底下翻涌着看不见的暗流,只一瞬,便又沉沉地垂了下去,
重新盯着自己放在膝上、指节粗大变形的手。那双手,布满新旧交叠的疤痕和厚厚的老茧,
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他枯坐了约莫一盏茶的功夫,那沉默像是有实质的重量,
沉甸甸地压在那个角落。然后,他动作迟缓地站起身,
依旧有些僵硬地拖着那条不太灵便的腿,没有再看任何人,像一道沉默的影子,
掀开厚重的棉布门帘,再次融入了门外呼啸的寒风和漫天卷起的黄沙里。阿旺看着他消失,
才长长地吁了口气,仿佛送走了什么不洁的东西,赶紧拿起抹布,用力擦拭那张桌子,
仿佛要擦掉那人留下的所有痕迹。苏雁回添完水,直起身,
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门口地上那片迅速干涸的深褐色水渍,
又掠过角落那张刚被阿旺用力擦拭过的空桌。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握着粗陶壶柄的手指,
微微收紧了些,指节泛出一点青白。她转身回到灶台后,拿起一块抹布,
默默地擦拭着灶台上溅出的水渍。炉膛里的火光映着她沉默的侧脸,
鬓角的白发在跳跃的光影里格外刺眼。日子像雁回关外冻硬的土地,板结、冷硬,日复一日。
自那日之后,那个独眼的男人,
竟成了“雁归茶肆”每日里一道固定的、令人不快却又挥之不去的风景。
他总是赶在午后最清冷、客人最稀疏的时候来。带着一身关外风沙的寒气,
沉默地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蓝布棉门帘,径直走向最角落、最靠近灶台的那张桌子。坐下,
放下一两枚磨得发亮的铜钱。不用开口,
阿旺便知道他要什么——那碗最苦、也最贱的野山茶。阿旺的嫌恶与日俱增。
他认定这是个晦气的瘟神,是个来讨债的鬼。每次端上那碗用茶渣碎末胡乱冲成的“山茶”,
他的动作都带着一股发泄般的力道,碗底撞击桌面发出刺耳的声响。独眼男人从不碰那碗茶,
只是沉默地坐着,像一尊没有生命的泥塑。他那只完好的右眼,目光大部分时间低垂着,
落在自己那双布满伤痕的粗糙大手上,偶尔会抬起,越过嘈杂的茶肆,
落在苏雁回忙碌的身影上。那目光沉甸甸的,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专注和深藏的痛楚,
每一次都只停留极短的瞬间,便飞快地移开,仿佛怕被灼伤。坐够一盏茶的功夫,
他便起身离开。而阿旺,也必定会在他转身后,
立刻冲过去端起那碗几乎没动过的、已经温凉的苦茶,快步走到门口,
带着一种混合了厌恶和莫名恐惧的狠劲,“哗啦”一声泼在门外冻硬的土地上。
那深褐色的水渍,成了茶肆门口一个污浊而短暂的标记,很快被风沙或行人踩踏得无影无踪。
茶肆里的常客,从最初的侧目,到后来的习以为常,甚至带上了几分戏谑的麻木。
有人私下里给那独眼男人起了个绰号——“哑茶鬼”。这绰号带着边城特有的粗粝和刻薄,
在几个闲汉的挤眉弄眼中迅速传开。“瞧,哑茶鬼又来了!”“啧啧,天天来,
点一碗泼一碗,图个啥?”“晦气!阿旺泼得好!这种人就该离远点!
”“听说他那眼珠子是被狼掏了,身上一股子死人气…”议论声不高,却像嗡嗡的苍蝇,
在茶肆油腻的空气里盘旋。苏雁回有时在灶台后揉面,有时在给客人续水,
那些话语碎片不可避免地钻进她的耳朵。她从不参与,也从不制止,
甚至连眉头都很少皱一下。她只是沉默地做着手里的活计,动作依旧麻利,
神情却像结了冰的湖面,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唯有在阿旺又一次重重地将那碗劣茶顿在男人桌上,或者端着空碗走向门口泼水时,
她握着茶壶或抹布的手指,会不易察觉地蜷缩一下,指节绷得发白。日子一天天滑过。
雁群早已远去无踪,关外的风一日冷过一日。
独眼男人成了茶肆里一道固定却令人窒息的布景。他沉默地来,沉默地坐,
沉默地承受着阿旺的轻慢和旁人的指点,再沉默地离开。
只有那只偶尔抬起、望向苏雁回的右眼,泄露着某种被死死压抑的、汹涌的痛苦。而苏雁回,
仿佛彻底将他视作了空气,目光从未在他身上有过片刻的停留。她的世界,
似乎只剩下灶膛里跳跃的火苗,粗陶壶里翻滚的开水,
以及年复一年等待后沉淀下来的、无边无际的枯寂。这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席卷了雁回关。狂风裹挟着鹅毛大雪,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混沌,
几步之外便看不清人影。风刮在脸上,像裹了沙砾的鞭子抽打。这样的天气,
连最勤快的行商也缩在客栈里烤火,整条街都陷入了死寂,只有风雪凄厉的咆哮。
“雁归茶肆”里,炉火烧得旺旺的,驱散着门缝窗隙钻进来的寒气。阿旺裹着件破棉袄,
缩在炉膛边的小板凳上打盹,脑袋一点一点。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
苏雁回坐在靠窗的条凳上,手里拿着一件缝补了一半的旧棉衣。针线在她指间穿梭,
动作熟练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窗外是呼啸的风雪,窗棂被吹得咯咯作响。风声里,
似乎夹杂着一点别的、极其微弱的声音。像是沉重的脚步,在厚厚的积雪里跋涉,
又像是风卷起了什么重物。苏雁回缝补的动作顿住了。她侧耳听了听,
目光投向被风雪拍打的门帘。那声音很模糊,断断续续,很快又被更大的风声淹没。
也许是错觉吧。这样的鬼天气,连野狗都不会出来。她低下头,继续手中的针线。
“吱呀——”厚重的蓝布棉门帘,被一股大力猛地推开,挟裹进一团冰冷的雪雾。狂风灌入,
吹得炉火一阵乱晃,火星噼啪四溅。阿旺被惊得一个激灵,从小凳上跳了起来,
睡眼惺忪地看向门口。风雪中,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几乎是跌撞着闯了进来。
他身上的破旧棉袄和羊皮坎肩被雪浸透了大半,沉甸甸地往下坠着水。
毡帽上、肩膀上积了厚厚一层雪,连那道遮着左眼的布条边缘都沾满了雪沫。
他那只露在外面的右眼,眼睫毛上结着细小的冰晶,眼白里的血丝红得吓人,
脸色是一种不正常的青灰。他站在门口,带进一股刺骨的寒气,
沉重的呼吸在冰冷的空气中凝成白雾。他似乎想往前走,但右腿僵硬得更厉害了,
身体晃了一下,才勉强稳住,一步步挪向他那个角落的老位置。每一步,
湿透的裤腿和破靴都在肮脏的地面上留下一个深色的水印。阿旺看清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