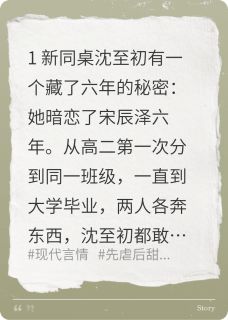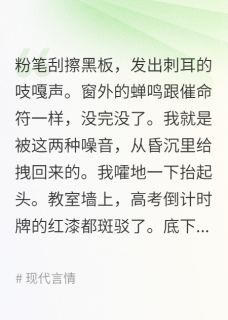第一章:生日宴与认亲宴尖锐的失重感仿佛还撕扯着每一寸神经,
骨骼在坚硬地面碎裂的闷响犹在耳边。林晚猛地睁开眼,肺里灌入的不是冰冷污浊的夜风,
而是甜腻得发齁的香槟与昂贵香水混杂的空气。眩晕感潮水般退去,眼前不是冰冷的水泥地,
而是流光溢彩的水晶吊灯,折射着宴会厅里衣香鬓影的浮华景象。身下是丝绒椅面的触感,
耳边是觥筹交错的喧闹。她低头,指尖死死掐进掌心,
红的月牙印——不是二十八岁生日宴那夜被推下露台前、江如烟指甲掐在她腕上留下的血痕,
而是她自己用力过度的证明。她重生了。回到了十八岁这场盛大而虚伪的认亲宴。命运,
给了她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个将仇敌亲手碾入地狱的剧本。“晚晚,发什么呆呀?来,
尝尝这个,厨房刚做的鱼子酱。”一只保养得宜的手伸过来,指尖捏着一枚精致的银匙,
上面堆着黑珍珠般的鱼子酱。是苏曼,她血缘上的母亲,
前世在她被江如烟一步步逼向深渊时,永远站在“养女”那边的母亲。林晚抬眼,
撞进苏曼含着笑意的眼底。那笑意,浮在表面,深处是审视,是衡量,
是评估一件失而复得的物品是否值回票价。林晚胃里一阵翻搅。她记得,前世苏曼就是这样,
用看似温柔的举动,不动声色地将她推向孤立无援的境地。她甚至记得,自己死后,
苏曼是如何轻描淡写地对媒体说“亲生女儿性格太孤僻,想不开”。“谢谢妈,我不饿。
”林晚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初来乍到的怯懦,完美复刻了前世的自己。她垂下眼睫,
掩住眸底翻涌的刻骨恨意。指腹在礼服宽大的裙摆褶皱间摸索,
触碰到一个冰凉坚硬的小瓶子,被她用体温焐得微热——氰化物,
她提前准备好的、为江如烟准备的“生日贺礼”。毒药冰冷的触感从指尖蔓延,
刺醒了她被香槟**神经。视线越过人群,精准地捕捉到那个身影。江如烟。
她穿着和林晚同款不同色的定制礼服,站在巨大的落地窗边,
像一只误入金丝笼的、惶惑不安的白鸟。暖黄的灯光落在她精心打理过的卷发上,
映出柔美的轮廓。她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白瓷碟,
上面盛着一小块淋着鲜红草莓酱的奶油蛋糕。那鲜红的色泽,刺得林晚眼球生疼,
世死亡时刻、那同样淋着草莓酱的“最后晚餐”重叠在一起——江如烟就是用这样一块蛋糕,
骗她吃下了掺着安眠药的“和解点心”,然后在寂静无人的露台上,将她推了下去。
“姐姐……”一个怯生生的、带着细微颤抖的声音在身侧响起。林晚猛地回神,
心脏骤然紧缩。江如烟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她面前,低着头,长长的睫毛不安地颤动着,
像是受惊的蝶翼。她双手捧着那块小小的草莓蛋糕,几乎要举到林晚眼前,
白瓷碟的边缘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姐姐…饿吗?”江如烟的声音更低了,
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讨好,“这个…很甜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周遭的喧嚣瞬间被抽离,
只剩下眼前这块小小的蛋糕和江如烟那张无辜的脸。
林晚的指尖在裙摆下猛地攥紧了那个冰冷的玻璃瓶,指节用力到发白。毒药就在手边,
仇人就站在眼前,带着与前世一模一样的“死亡邀请”。只要一个动作,她就能结束这一切,
让江如烟也尝尝毒药灼烧喉咙的滋味!杀意,像冰冷的毒蛇,缠绕上她的心脏,
吐着猩红的信子。她几乎要控制不住伸出手。就在这时,江如烟因为紧张,微微侧了下头。
她柔顺的发丝被这个动作带开,一小截白皙的后颈暴露在宴会厅明亮的光线下。
林晚的瞳孔骤然收缩!就在那截后颈的皮肤上,靠近发际线的地方,
清晰地浮现着一串幽蓝色的、非自然的数字:**73%**。那数字像是某种电子纹身,
又像是从皮肤下透出的诡异光晕,在柔和的灯光下,散发着冰冷而不祥的气息。
它静静地悬浮在那里,像一个无声的倒计时,一个指向未知深渊的坐标。林晚伸向毒药的手,
僵在了裙摆的褶皱里。冰冷的玻璃瓶硌着她的掌心,寒意顺着血脉蔓延,
却浇不灭心头那团骤然被点燃的、混杂着惊疑与更浓烈杀意的烈火。这是什么?标记?诅咒?
还是……某种她无法理解的警示?江如烟似乎察觉到了林晚目光的凝滞,困惑地抬起了头,
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里盛满了茫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她捧着蛋糕的手,又往前送了送,
那鲜红的草莓酱几乎要滴落下来。“姐姐?”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林晚的目光死死钉在那串冰冷的“73%”上,又缓缓移回江如烟那张写满纯良无害的脸上。
前世坠楼时耳边江如烟那句带着恶意**的“姐姐走好”,
与眼前这句怯生生的“姐姐饿吗”,在脑海中疯狂撕扯。裙下的毒药瓶,冰冷刺骨。
颈后的蓝字,诡异莫名。复仇的剧本,在她重生的第一刻,就走向了无法预料的崩坏。
林晚强迫自己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伸手,却不是去接那蛋糕,
而是看似不经意地、带着一点排斥和紧张,轻轻推开了江如烟的手臂。动作很轻,
却足以让江如烟趔趄了一下,手中的蛋糕碟子差点脱手。“我不吃甜食。”林晚的声音很冷,
带着重生者无法完全掩饰的疏离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她不再看江如烟瞬间苍白下去的脸和泛红的眼圈,视线越过她,
落在她身后不远处、一个被随意放在休息区沙发上的粉色手账本上。
那本子封面上印着幼稚的卡通兔子。一个荒谬的念头,带着刺骨的寒意,
猛地攫住了林晚的心神——那本子,前世她见过!在江如烟的房间里,
就放在她堆满名牌包包的梳妆台上!那时她只当是假千金装嫩的又一个道具。
可现在……林晚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起来,擂鼓一般撞击着肋骨。她几乎是下意识地,
趁着江如烟失魂落魄地低头看着差点洒掉的蛋糕,苏曼又被几位贵妇拉去寒暄的瞬间,
脚步虚浮地走向那个沙发。指尖触碰到那柔软的皮质封面时,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决绝。
翻开。内页是少女娟秀的字迹,密密麻麻。
些记录着“今天钢琴课好难”、“新裙子好漂亮”、“妈妈好像更喜欢姐姐了”的琐碎日常,
心脏却在不断下沉。没有她预想中的恶毒诅咒,
只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卑微的讨好和小心翼翼的惶恐。直到她近乎绝望地翻到最后一页。
呼吸,在那一刻彻底停滞。那一页没有文字,只有一幅用彩色铅笔认真描绘的画。
画面构图清晰得残忍——一个穿着长裙的女孩,从高高的、布满繁复雕花的露台上,
向下坠落。风卷起了她的裙摆和长发,背景是城市遥远而冰冷的灯火。画风甚至称得上稚拙,
却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极速下坠的失重感和……绝望。画中坠楼女孩的脸,
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勾勒,但那五官轮廓,分明就是前世的她!林晚!而在画面的最下方,
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小字,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刻上去的,
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执拗:保护姐姐。
第二章:天使的烫伤与恶魔的笔记冰冷的毒药瓶硌着掌心,
那刺骨的寒意却远不及林晚心头的万分之一。她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宴会厅的喧嚣,
将那幅坠楼画和“保护姐姐”的字眼,连同江如烟颈后诡异的“73%”,
一同锁进了翻腾的脑海深处。重生的狂喜早已被冰冷的疑虑和更深的恨意取代。这算什么?
命运开的恶劣玩笑?还是江如烟更高明的伪装?那串蓝色的数字,像一个无声的嘲讽,
悬在她复仇的道路上,闪烁着不祥的光。她回到了“属于”她的、在江家宽敞却冰冷的客房。
指尖划过昂贵丝绒窗帘,触感细腻,却让她想起前世坠楼时,粗糙水泥地摩擦皮肤的剧痛。
目光落在梳妆台上——那里安静地躺着一个不起眼的纸袋,
是她重生后第一时间准备的“必需品”。不是珠宝,不是华服。
是几瓶不同种类的强效泻药和一瓶低浓度的工业清洁剂。毒药太过极端,也容易暴露,
她要的是让江如烟在“意外”和“病痛”中,一点点品尝她前世所受的屈辱和折磨。
慢性毒杀,钝刀子割肉,才更解恨。晚餐是家庭小聚。长条餐桌铺着雪白桌布,
银质餐具闪闪发光。苏曼坐在主位,笑容温婉得体,细心地为丈夫江正宏布菜,
偶尔看向林晚的眼神,带着一种审视的满意,仿佛在看一件终于归位的收藏品。而江如烟,
则缩在离林晚最远的角落,像个透明的影子,低着头,小口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连咀嚼都小心翼翼。林晚的目光如同冰冷的探针,反复扫描着江如烟。颈后的发丝垂落,
遮住了那个诡异的蓝字。她的每一个细微动作——睫毛的颤动,手指捏紧筷子的力度,
甚至吞咽时喉结的滚动——都被林晚纳入眼底,试图从中找出伪装的破绽。
佣人端上来一盅热气腾腾的虫草花胶汤,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
汤盅恰好放在林晚和江如烟之间。机会!一个冰冷而清晰的念头瞬间攫住了林晚。不是毒药,
但足够让这位娇生惯养的假千金当众出丑,痛苦难堪。她的指尖在桌下微微蜷缩,
计算着角度和力度。就在佣人转身的刹那,林晚“无意”地抬肘,动作幅度不大,
却精准地撞向了汤盅的底部!“小心!”惊呼声几乎同时响起。
滚烫的汤水眼看就要泼向林晚的手臂和胸前的衣料。电光火石之间,一道白影猛地扑了过来!
是江如烟!她几乎是本能地伸出双手,不是去推开汤盅,而是徒劳地、用那双纤细白皙的手,
直接捧向了倾倒的滚烫容器!“嗤啦——”皮肉接触滚烫瓷器的声音令人头皮发麻。
滚烫的汤汁飞溅,大部分淋在了江如烟的手背和小臂上,瞬间红了一大片,
迅速鼓起骇人的水泡。只有零星几点溅在林晚的袖口,留下微不足道的湿痕。“啊!
”江如烟痛得浑身一颤,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大颗大颗的冷汗从额角渗出。
她捧着迅速红肿起泡的双手,像捧着什么易碎的、却已破碎的珍宝,身体因剧痛而微微佝偻。
“如烟!”苏曼猛地站起身,脸上满是惊怒,
但林晚敏锐地捕捉到她眼底一闪而过的……不耐烦?
仿佛江如烟的受伤是一件麻烦的、打乱她计划的意外。
“姐姐…对不起…”江如烟的声音带着剧烈的痛楚和无法抑制的哭腔,
她甚至不敢看自己惨不忍睹的手,反而惊恐地望向林晚,泪水在通红的眼眶里打转,
“是…是如烟没端稳…差点烫到姐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她语无伦次地道歉,
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制造灾难的罪魁祸首。剧烈的疼痛让她身体都在发抖,可她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为“差点”烫到林晚而道歉?甚至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林晚僵在原地。
预想中江如烟的尖叫、指责、或者苏曼借机发难的情景都没有出现。
只有眼前这双迅速红肿溃烂的手,
和江如烟那双盛满了恐惧、痛苦和……一种近乎卑微的、祈求原谅的眼神。那眼神太纯粹,
纯粹得让林晚精心构筑的恨意堡垒,都产生了一丝动摇的裂痕。“快!叫医生!
”江正宏终于反应过来,沉声命令。佣人们乱作一团。家庭医生很快赶来,
为江如烟处理伤口。上药时的剧痛让她忍不住痛呼出声,泪水无声地滑落,
但她死死咬着下唇,不敢哭得太大声,只是偶尔泄露出一两声压抑的抽泣,像受伤的小动物。
林晚站在稍远的地方,冷眼旁观。她看着医生用剪刀剪开江如烟被汤汁黏住的袖口,
露出底下触目惊心的烫伤。看着消毒药水涂抹上去时,
江如烟疼得浑身痉挛却依然死死攥着拳头,指甲深深陷进完好的掌心肉里,
留下更深的月牙痕。她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不是因为同情江如烟,
而是因为这完全超出预期的反应,让她精心准备的“复仇第一步”显得如此卑劣和……可笑。
更重要的是,江如烟的行为,与她颈后的“73%”恶念进度条,形成了何等刺眼的悖论!
为什么?她到底在演什么戏?博取同情?还是……那个数字,并非她理解的“恶念”?
混乱中,苏曼走到林晚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语气带着一种刻意的安抚:“晚晚吓坏了吧?别怕,如烟这孩子就是毛手毛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