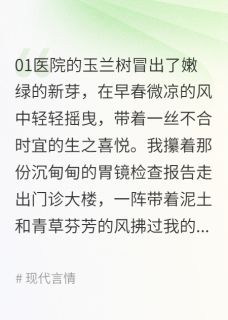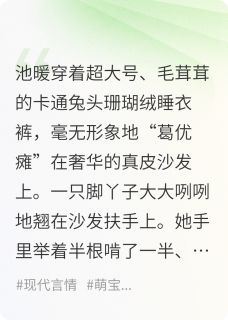
“邵晋!帮兄弟一把!江湖救急!”池云冰的声音隔着手机听筒都震得邵晋耳膜嗡嗡响,
带着一种“你不答应我就从天而降砸你家地板”的焦躁。邵晋面无表情地把手机拿远了些,
另一只手稳稳地握着方向盘,正堵在晚高峰的车河里,寸步难行。
窗外是连绵不绝的汽车尾灯,红得刺眼,空气黏稠闷热,让人心烦。“说。”邵晋言简意赅,
语气里透着“有屁快放,我很忙”的意味。“我妹!池暖!”池云冰的声音拔高了一个八度,
“她毕业了,刚在你们市找到工作!人生地不熟的,我这当哥的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邵晋心里咯噔一下,升起一股极其不妙的预感。
他几乎是立刻就猜到了池云冰接下来要放什么屁。果然——“让她住你那儿!就住一阵!
找到合适的房子立刻搬!兄弟,我就信得过你!你可是我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兄弟!
你为人正派,我放一百二十个心!真的!”邵晋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
他眼前不受控制地闪过一个模糊的影子——池暖,池云冰那个小他好几岁的妹妹。印象里,
最后一次见面好像还是她高考结束的暑假,穿着素净的棉布裙子,
安安静静地坐在池家客厅的角落看书,阳光洒在她柔软的发顶上,
像个不谙世事、极易受惊的小兔子。池云冰这个妹控,
更是把她形容得如同温室里最娇嫩的花朵,碰一下都可能碎掉。“不行。
”邵晋斩钉截铁地拒绝,声音冷得像冰渣,“绝对不行。池云冰,你脑子被门挤了?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像话吗?传出去对她名声不好,对我也不合适。
”他试图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帮她找房子没问题,付三个月房租也行,但住一起,
免谈。”“哎呀!邵晋!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池云冰在电话那头急得跳脚,
背景音里似乎还有机场广播的杂音,“我对你放一百个心!你的人品,我拿项上人头担保!
再说我家暖暖,那真是从小乖到大!特别懂事,特别安静,胆子小得跟兔子似的!你放心,
她绝对绝对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她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
她就是需要一个安全点的地方过渡一下,顶多一个月!一个月后她没找到房子,
我亲自飞过来把她拎走!”池云冰的保证如同连珠炮,
把他妹妹形容得像个不食人间烟火、完美无瑕的瓷娃娃。邵晋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收紧,
骨节泛白。他太了解池云冰了,这家伙一旦认定的事情,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尤其事关他那个宝贝妹妹。堵车的长龙终于松动了一点,邵晋烦躁地松开刹车,
车子缓缓向前挪动。“池云冰,这不是放不放心的问题,是原则问题。
”邵晋试图做最后的挣扎,语气严肃,“**妹成年了,是个大姑娘。我们非亲非故,
住一起算怎么回事?”“怎么非亲非故了?你是我兄弟,就是我妹的哥!长兄如父懂不懂?
她现在就是需要长辈照看一下!”池云冰开始胡搅蛮缠,“邵晋!邵大哥!邵祖宗!
算我求你!暖暖她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在陌生的城市,天都快黑了,
我这边航班马上起飞关机了!地址发你了!拜托了兄弟!回头请你吃满汉全席!
她真的很乖的!真的!比珍珠还真!”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登机催促广播,
紧接着是池云冰最后一句带着破音的“拜托了兄弟!她真的很乖!”,然后“嘟”的一声,
忙音响起。世界瞬间清静了。邵晋握着手机,听着那单调的忙音,
只觉得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太阳穴突突地疼。他把手机狠狠拍在副驾驶座位上,
目光阴沉地盯着前方再次停滞的车流。
车厢里只剩下空调单调的送风声和他自己压抑的呼吸声。池云冰这**!先斩后奏!
他烦躁地抓了把头发,目光瞥向副驾座位上那可怜的手机。屏幕还亮着,
一条新信息提示嚣张地躺在通知栏里。是池云冰发来的地址,
外加一个巨大的、谄媚的笑脸表情。邵晋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吐出,
试图把胸腔里那股想揍人的冲动压下去。算了,看在多年兄弟情分上。他认命地打方向盘,
车子艰难地挤出主路,朝着那个陌生的地址驶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池暖,
但愿你真的像你哥说的那样“很乖”。否则……否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邵晋头疼地想,
一个“胆子小得跟兔子似的”女孩,他能拿她怎么样?凶一下估计都能哭给他看。
城市的霓虹灯开始次第亮起,车窗外光影流转。邵晋按照导航,
将车停在一个略显老旧的居民小区门口。路灯昏黄,勉强照亮楼栋斑驳的入口。他下车,
环顾四周,目光很快锁定在单元门旁那个小小的身影上。
一个巨大的、看起来能把人装进去的行李箱立在地上。旁边,
一个穿着米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安静地站着,微微低着头,
路灯的光晕柔和地勾勒出她纤弱的轮廓和垂落的柔软发丝。她双手规规矩矩地交叠放在身前,
整个人显得异常乖巧、安静,甚至……有点可怜兮兮的味道。
像一只被遗弃在陌生街角、不知所措的小动物。正是池暖。
和记忆里那个安静看书的女孩形象重叠了。邵晋心里那点因为被强塞麻烦而升起的烦躁,
瞬间被一种莫名的、类似“欺负弱小”的负罪感取代。他硬着头皮,清了清嗓子,朝她走去。
听到脚步声,池暖抬起头。那一瞬间,邵晋感觉自己的脚步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路灯的光清晰地映照出她的脸。皮肤很白,带着点长途跋涉后的疲惫,但那双眼睛……很大,
很亮,像浸润在清澈溪水里的黑色琉璃。此刻,那对琉璃里清晰地映着不安和怯生生的依赖,
长而密的睫毛像蝶翼般微微颤动。她的嘴唇小巧,微微抿着,看到邵晋走近,
立刻努力地弯起一个弧度,露出一个乖巧又带着点讨好意味的笑容。“邵晋…哥哥?
”她的声音细细软软的,带着一丝不确定和小心翼翼,像羽毛轻轻搔过耳膜,“哥哥说,
要麻烦您一段时间了…真的…真的不好意思。”她说着,还微微鞠了个躬,姿态放得极低,
十足的谦逊和歉意。这副模样,简直把“我很乖,我很懂事,我绝不添麻烦”写在了脸上,
生动得无可挑剔。邵晋心里最后那点抗拒,在她这怯生生、湿漉漉的眼神注视下,
像阳光下的薄冰一样迅速融化、瓦解。池云冰那家伙虽然**,
但关于他妹妹“很乖”的描述,似乎……暂时看起来,没怎么夸张?“嗯。”邵晋应了一声,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冷硬,他伸手去拉那个巨大的行李箱,“走吧。
”“谢谢邵晋哥哥!”池暖的声音立刻轻快了一点点,带着感激,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
像个听话的小尾巴。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轻微又有些笨拙的“哒、哒”声。
邵晋走在前面,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心里默默叹了口气。算了,
就当照顾一个需要临时庇护的小妹妹吧。他提醒自己:保持距离,谨守分寸,一个月,
最多一个月。他打开了单元门,示意池暖先进。池暖小声道谢,侧身进去时,
发梢不经意间擦过邵晋的手臂,留下一缕极淡的、混合着洗发水和阳光味道的馨香。
邵晋的手指在冰冷的门把手上无意识地收紧了一瞬。池暖低着头,
嘴角的弧度在昏暗的楼道阴影里,极其轻微地、难以察觉地加深了一点点。
邵晋的公寓是典型的单身精英风格——冷色调,极简,一丝不苟。
宽敞的客厅连着开放式厨房,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璀璨的城市夜景。
一切都干净、规整、充满秩序感,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空气里常年弥漫着淡淡的薄荷香薰和书籍纸张的味道。池暖拉着她那个巨大的行李箱,
小心翼翼地踏进玄关,仿佛踏入了一个由精密仪器构成的陌生空间。
她那双小鹿般清澈的眼睛里充满了恰到好处的新奇和一丝被震慑住的拘谨,
地砖、线条冷硬的黑色皮质沙发、以及占据了一整面墙、码放得如同军队列阵般整齐的书柜。
“好…好干净啊。”她轻声感叹,声音里带着点怯生生的羡慕,
手指不自在地绞着连衣裙的衣角,“邵晋哥哥,你平时一定很爱整洁。
邵晋弯腰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全新的、标签都还没撕的男士拖鞋——这是他接到池云冰电话后,
在楼下便利店唯一能买到的最大号应急品——放在她脚边。“嗯。”他言简意赅,
指了指客厅旁边一扇关着的门,“那是次卧,以后你住那。卫生间在走廊尽头。
厨房的东西你可以用,用完清理干净。”“嗯嗯!”池暖用力点头,
换上那双对她来说过于宽大的拖鞋,像踩在两只小船上,走路发出啪嗒啪嗒的滑稽声响。
她拖着行李箱,有些笨拙地走向次卧,开门前还不忘回头,
露出一个无比乖巧的笑容:“邵晋哥哥,我一定不会弄乱你东西的!我会很小心很小心的!
”邵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几不可闻地又叹了口气。他走到开放厨房的中岛台边,
打开冰箱,拿出冰水灌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滑入喉咙,
稍微浇熄了些许被强行打乱生活节奏的烦躁。他需要冷静,
需要适应这个突然闯入的、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麻烦”。然而,他“平静”的生活,
从第二天清晨开始,就以一种极其“温和”的方式,被彻底打破了。清晨六点半,
邵晋的生物钟准时将他唤醒。他习惯性地洗漱完毕,换上运动服,准备进行雷打不动的晨跑。
刚推开卧室门,一股浓郁的、绝对不属于他厨房的焦糊味就霸道地钻进了他的鼻孔。
邵晋眉头瞬间拧紧,快步走向厨房。只见开放式厨房的操作台前,
一个小小的身影正手忙脚乱。池暖穿着她那件米白色的睡裙,
外面套着一件明显大了好几号的、属于邵晋的深灰色围裙,
长长的带子在身后系了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她一手拿着锅铲,
一手慌乱地想去关电磁炉的开关,小脸皱成一团,额角还沾着一点可疑的白色粉末,
那双大眼睛里蓄满了惊慌失措的水汽,眼看就要决堤。锅里,
一团黑乎乎、黏糊糊的不明物质正冒着绝望的青烟。“邵…邵晋哥哥!”听到脚步声,
池暖猛地回头,像看到了救星,声音带着哭腔,可怜极了,
…我想学着给你做早饭的…可是…可是这个煎蛋…它…它自己就变成这样了…呜呜…对不起!
我太笨了!”她说着,眼眶真的红了,泪水在里面打转,要落不落,
配合着鼻尖和脸颊上蹭到的面粉黑灰,效果加倍。邵晋看着那锅“碳基生命体”,
再看看眼前这个狼狈不堪、泫然欲泣的“罪魁祸首”,责备的话瞬间堵在了喉咙里。
他快步上前,一把关掉电磁炉,动作利落地将那个惨不忍睹的煎蛋铲进垃圾桶,
打开抽油烟机开到最大档。“没事。”他声音有点干涩,尽量放平缓,“别做了,出去吃吧。
”“可是…可是我想帮忙…”池暖低着头,手指无措地绞着围裙的边缘,声音细若蚊呐,
“哥哥总说我什么都不会…我不想当累赘…”邵晋看着她头顶柔软的发旋,
那点因为厨房被“轰炸”而升起的火气,彻底被一种“欺负弱小”的无奈取代。
他揉了揉突突直跳的太阳穴:“不是你的问题。我的锅…比较难用。
”这个借口他自己都觉得离谱。“真的吗?”池暖立刻抬起头,
湿漉漉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一丝希望的光,“那…那邵晋哥哥,你能教我吗?就…就最简单的,
煮个面?我保证这次认真学!”她的眼神充满了虔诚的求知欲,
仿佛邵晋是米其林三星大厨。
邵晋:“……”他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名为“池暖”的柔软陷阱里。于是,
清晨宝贵的晨跑时间,变成了邵氏厨房速成班。
再下面条”、“如何判断面条是否煮熟”、“如何打一个完整的荷包蛋(而不是蛋花汤)”。
池暖像个最认真的小学生,亦步亦趋地站在他身边,
拿着个小本子(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的),时不时记上两笔,
嘴里还念念有词:“水开…下面…煮三分钟…关小火…轻轻放蛋…”她靠得很近,
身上带着刚起床的温热气息和一丝甜甜的奶香(大概是某种沐浴露),
发梢偶尔会蹭到邵晋的手臂。邵晋全程身体僵硬,目不斜视地盯着锅里的面条,
仿佛在研究什么高精尖课题。他必须集中全部意志力,
才能忽略身边这个过分“好学”又过分“靠近”的小麻烦。
当一碗勉强及格(主要归功于邵晋的及时补救)的阳春面终于端上桌时,
邵晋感觉自己像打了一场硬仗,后背都微微出汗了。“哇!成功了!”池暖看着自己那碗面,
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成就感,她双手捧起碗,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小心翼翼地吹了吹,
然后献宝似的递到邵晋面前,“邵晋哥哥,你尝尝!第一碗给你!
”邵晋看着那碗清汤寡水、飘着几根蔫蔫青菜的面,又看看女孩期待又忐忑的眼神,
拒绝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他拿起筷子,挑了一小撮送入口中。味道…平平无奇,甚至有点淡。
“嗯,还行。”他给出了一个极其保守的评价。但这足以让池暖开心得像只偷到油的小老鼠,
眉眼弯弯,脸颊上的小酒窝都露了出来。“太好了!我会煮面了!谢谢邵晋哥哥!
”她心满意足地开始小口小口吃自己那碗。邵晋默默吃着自己的面,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这丫头,也太容易满足了吧?一碗面就高兴成这样?池云冰那家伙,
平时到底是怎么养妹妹的?一股莫名的责任感,悄然滋生。厨房风波只是序曲。当天傍晚,
邵晋正在书房处理一份紧急邮件。客厅里传来池暖压低声音的惊呼,
紧接着是玻璃碎裂的清脆响声。邵晋心里一沉,立刻起身出去。客厅里,
池暖手足无措地站在饮水机旁边,
下是一滩水渍和几片锋利的玻璃碎片——他那个价值不菲的、设计感极强的玻璃水杯的残骸。
她手里还捏着半张湿透的纸巾,显然是想去擦,又不知从何下手。看到邵晋出来,
她的脸瞬间变得煞白,大眼睛里迅速弥漫开恐惧和自责的雾气,嘴唇哆嗦着:“对…对不起!
邵晋哥哥!
我…我就是想帮你倒杯水…我…我手滑了…我不是故意的…呜呜…这个杯子是不是很贵?
我…我赔给你…”她的声音带着哭腔,身体都在微微发抖,像一片在寒风中打颤的叶子,
仿佛下一秒就要因为恐惧和内疚而晕厥过去。邵晋看着地上的狼藉,
再看看女孩吓得魂不附体的模样,那点因为杯子被打碎的郁闷瞬间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无奈和一种…奇异的保护欲。他快步走过去,避开地上的碎片和水渍,
语气尽量放得平缓:“别动!小心扎到脚。”他把她轻轻往旁边安全地带拉了拉,
“一个杯子而已,碎了就碎了。人没事就好。”“可是…”池暖还想说什么,
眼泪已经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砸在光洁的地砖上。“没什么可是的。
”邵晋打断她,声音带着一种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温和,“去拿扫帚和簸箕,我教你清理。
以后小心点。”池暖吸了吸鼻子,用力点头,飞快地跑去拿工具,
背影仓惶又带着点如释重负的庆幸。邵晋看着她纤细的背影,认命地弯腰,
开始徒手捡拾一些大的玻璃碎片。指尖触到冰凉尖锐的玻璃,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丫头,是水做的吗?眼泪说来就来。而背对着他,
正笨拙地拿着扫帚的池暖,嘴角却几不可察地、极快地向上弯了一下。那弧度极浅,
转瞬即逝,快得如同幻觉。只有她自己知道,刚才那“手滑”的角度,可是精心计算过的,
完美避开了所有可能伤到自己的危险区域。效果,满分。同居生活的日常,
就在这种“邵晋哥哥,这个我不会…”的无限循环中推进。“邵晋哥哥,
洗衣机…它好像把衣服都缠在一起了…怎么办呀?
”邵晋黑着脸从滚筒里解救出她那件被绞成麻花的蕾丝睡衣。“邵晋哥哥,
这个…这个文件怎么打印双面呀?我点了好多下都没反应…它是不是坏了?
”邵晋耐着性子教她操作那台他用了三年从没出过问题的打印机。“邵晋哥哥,
阳台那盆绿绿的小树…叶子黄了!它是不是渴死了?我明明每天都给它浇水的!
”邵晋看着那盆因为浇水过多而根部腐烂、奄奄一息的昂贵小叶紫檀盆景,额角青筋暴跳。
邵晋感觉自己仿佛一夜之间多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他的时间、空间、甚至神经,
都在被这个看起来纯良无害、实则处处“笨拙”的女孩无声无息地侵占。
他引以为傲的秩序感和私人领地,正在被一种名为“池暖”的柔软力量缓慢而坚定地瓦解。
他会在加班到深夜回家时,看到客厅留着一盏暖黄色的小夜灯,
旁边的保温杯上贴着粉色的便利贴,上面是娟秀的字迹:“邵晋哥哥,辛苦了,
喝点温水哦~”旁边还画着一个拙劣的、歪歪扭扭的笑脸。他会在周末清晨,
被一阵极其轻微、但坚持不懈的吸尘器嗡嗡声吵醒,推开门,
看到那个小小的身影正极其认真、极其缓慢地推着吸尘器,一寸寸地清理着客厅的地毯,
那专注的模样,像是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他会在某个疲惫的傍晚,
闻到厨房飘出不同于焦糊味的、真正属于食物的香气,虽然味道依旧平平,
看到餐桌上摆着两盘卖相勉强及格的家常菜,
带着点小忐忑和小期待的眼神:“邵晋哥哥…我…我今天照着手机学的…你…你要不要尝尝?
”每一次,邵晋心里的那点因为被打扰而升起的烦躁,
总会被她那些笨拙却无比用心的举动悄然抚平,甚至…滋生出一点点暖意。
他开始习惯家里多了一个人,习惯了那声软软的“邵晋哥哥”,
习惯了在玄关看到那双歪歪扭扭摆放的女士拖鞋,习惯了空气里除了薄荷香薰外,
偶尔飘荡的、属于女孩的淡淡甜香。他甚至在某个加班的深夜,
鬼使神差地点开了一个之前从不关注的“新手厨房必备”购物链接,
默默下单了一套据说“防滑防烫傻瓜式操作”的锅具。邵晋没有意识到,
他坚硬外壳上那道名为“池暖”的裂缝,正在无声无息地扩大。他更不会知道,
在他看不见的角度,比如他深夜在书房工作时,那个应该“早早睡下”的次卧门缝里,
会有一双亮得惊人的眼睛,正透过缝隙,静静地、专注地凝视着他伏案工作的背影,
嘴角噙着一丝计划通行的、志在必得的微笑。猎物,正在习惯猎人的存在。而猎人,
正耐心地等待着那个足以让猎物彻底放下所有防备、一击致命的完美时机。
日历无声地翻过一页又一页,池暖在邵晋公寓的“临时寄居”生活,
已经平稳(至少表面如此)地运行了一个多月。邵晋原本如精密仪器般运转的世界,
似乎真的渐渐适应了这颗“小行星”的引力扰动。习惯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当他发现自己开始下意识地在超市的生鲜区多拿一份她爱喝的酸奶,
或者在加班时顺手给她发条“晚归,勿等”的信息时,邵晋才惊觉,某些界限正变得模糊。
这天晚上,邵晋有个推不掉的应酬。合作方热情似火,酒过三巡,
气氛热烈得如同煮沸的开水。邵晋素来克制,但架不住对方轮番上阵,白的红的轮番轰炸。
饶是他酒量尚可,结束时也脚步虚浮,眼前发花,被司机老张半搀半扶地塞进了车里。
“邵总,送您回家?”老张透过后视镜,看着后座揉着额角、脸色泛红的老板。
“嗯…”邵晋含糊地应了一声,胃里翻江倒海,太阳穴突突地跳着疼。
他只想快点回到那个安静、熟悉的空间,把自己扔进沙发或者床上。
车子在深夜寂静的街道上平稳行驶。城市的霓虹透过车窗,
在邵晋有些迷蒙的视野里拉长成模糊的光带。他闭着眼,
努力对抗着酒精带来的眩晕和不适感。
脑子里不受控制地闪过一些零碎片段:池云冰拍胸脯保证“我妹超乖”的脸,
池暖第一次拖着行李箱站在路灯下的纤弱身影,
、打碎的玻璃杯、被绞成麻花的睡衣、贴在保温杯上的粉色便利贴……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
带着一种奇异的、柔软的暖意,竟奇异地冲淡了些许身体的不适。原来,
那个曾经觉得是巨**烦的存在,如今竟成了他潜意识里“舒适区”的一部分。终于,
车子停在了熟悉的地下停车场。邵晋谢过老张,自己扶着冰冷的墙壁,
步履有些踉跄地走向电梯。金属门在眼前闭合,镜面映出他此刻有些狼狈的样子:领带松垮,
衬衫领口解开两颗,脸上带着明显的醉意。他烦躁地扯了扯领带,深吸一口气,
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清醒一点。不能让那丫头看到自己这副样子,省得她又“大惊小怪”,
用那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他,好像他下一秒就要倒毙街头似的。电梯平稳上行,
发出轻微的嗡鸣。数字跳动,最终定格在他家所在的楼层。“叮——”电梯门缓缓滑开。
邵晋扶着冰凉的金属门框,踏出电梯。走廊里感应灯应声而亮,
柔和的光线铺满通往家门的短短路径。他掏出钥匙,**锁孔,转动。“咔哒。”门开了。
一股浓郁霸道的、混合着孜然辣椒面油脂香气的味道,如同实质的拳头,
猛地轰击在邵晋被酒精**感官上!这味道,
与他公寓里常年萦绕的薄荷清冽、书籍墨香格格不入,
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和一种…放肆的欢愉。邵晋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味冲击得一个趔趄,
差点没站稳。他扶着玄关的墙壁,混沌的大脑艰难地处理着眼前的景象——客厅里,
电视正播放着一部热闹的综艺节目,音量被调得很低,只有嘻嘻哈哈的背景音。而客厅中央,
那组线条冷硬、价值不菲的深灰色真皮沙发上,正大喇喇地坐着一个身影。
不是池暖平时那副小白兔的样子。她穿着一套印着巨大卡通兔头的、毛茸茸的珊瑚绒睡衣裤,
盘着腿,一只脚丫子还极其不雅地踩在沙发扶手上。
她整个人以一种极其放松、极其慵懒、甚至可以说有点“葛优瘫”的姿势陷在沙发里。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手里正举着半根色泽红亮、油光闪闪的鸭脖子,
啃得那叫一个投入忘我、酣畅淋漓!嘴角沾着明显的辣椒粒和酱汁,
腮帮子因为用力咀嚼而鼓鼓囊囊。面前的茶几上,摊开着一个油渍麻花的快餐盒,
面堆着小山似的鸭脖骨头和几个空了的啤酒易拉罐(邵晋发誓自己冰箱里绝对没有这种东西!
)。客厅的灯光只开了沙发上方一盏暖黄的射灯,正好将她笼罩其中。她一边啃着鸭脖,
一边眼睛盯着电视屏幕,
时不时还跟着里面的笑点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极其惬意的“啧”声,
甚至还舒服地晃了晃踩在扶手上的那只脚丫子。
整个画面充满了强烈的反差和一种…邵晋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野性的真实感。
邵晋僵在玄关的阴影里,酒意瞬间被这极具冲击力的场景惊飞了大半。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喝太多出现了幻觉,或者走错了家门?
喟叹的人…真的是那个整天眨巴着无辜大眼、说话细声细气、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的池暖?
!他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瞳孔因为震惊而微微放大。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只有电视里综艺节目的罐头笑声和池暖啃噬鸭脖的“咔嚓”声,
在寂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也许是玄关处过于死寂的气氛终于引起了池暖的警觉。
她啃鸭脖的动作猛地一顿,像是某种小动物突然嗅到了天敌的气息。
她极其缓慢地、带着点难以置信的僵硬,扭过头,朝玄关的方向看来。四目相对。
空气瞬间冻结。池暖那双在暖黄灯光下依旧显得很大很亮的眼睛,
在看清门口那个高大身影的瞬间,瞳孔骤然紧缩!那里面清晰地倒映出邵晋的身影,
以及一种被当场抓包、魂飞魄散的巨大惊恐!她嘴里的鸭脖“啪嗒”一声掉在睡衣裤上,
留下一个油亮的污渍。时间,停滞了绝对不超过半秒。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池暖脸上的表情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瞬间抹去,然后以光速重新描绘!
那副慵懒、肆意、带着点小得意的神情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邵晋无比熟悉的——惊慌失措、泫然欲泣、无辜又委屈的小白兔表情!
她几乎是弹射般从沙发上跳起来,手忙脚乱地把踩在扶手上的脚丫子放下,
试图把掉在腿上的鸭脖捡起来又觉得不妥,最后只是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那双大眼睛迅速弥漫开浓重的水雾,长长的睫毛如同沾了露水的蝶翼,剧烈地颤抖着。
她的嘴唇哆嗦着,声音带着明显的哭腔和剧烈的颤抖,
瞬间切换成那副能融化钢铁的软糯腔调:“邵…邵晋哥哥!你…你回来啦!
”她像是被吓坏了,声音都变了调,带着浓重的鼻音,目光慌乱地扫过茶几上的狼藉,
语无伦次地解释,“这个…这个鸭脖…是…是对门的邻居阿姨!
她…她晚上做多了…非…非要送给我尝尝!我…我推辞不过…就…就…”她的解释苍白无力,
逻辑混乱,充满了欲盖弥彰的味道。一边说着,
豆大的泪珠已经不受控制地、争先恐后地从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滚落下来,
顺着白皙的脸颊滑落,在下巴处汇聚,然后滴落在印着卡通兔头的睡衣前襟上,
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那模样,委屈得像是被全世界冤枉了。邵晋依旧站在玄关的阴影里,
高大的身影带着一种沉沉的压迫感。他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酒精带来的眩晕感早已被眼前这出荒诞至极的“变脸”驱散得一干二净。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她,那双深邃的眼眸如同寒潭,平静无波,却深不见底,
仿佛能穿透她所有的伪装,直抵核心。他的目光,极其缓慢地,
从她泪痕交错、写满无辜和惊吓的小脸,下移到她那件沾了油渍和泪痕的卡通睡衣,
掠过茶几上那堆小山似的鸭脖骨头和空啤酒罐,最终,
定格在她因为慌乱解释而微微张开的、油光红亮的嘴角。那里,一粒小小的、鲜红的辣椒籽,
正无比醒目地粘在她柔软的唇瓣上,像一枚无声却无比刺眼的罪证。
客厅里只剩下电视里不合时宜的综艺罐头笑声,以及池暖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邵晋终于动了。他缓缓地、一步一步地从玄关的阴影里走出来,踏进客厅的光晕下。
他的步伐很稳,带着一种奇异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皮鞋踩在光洁的地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