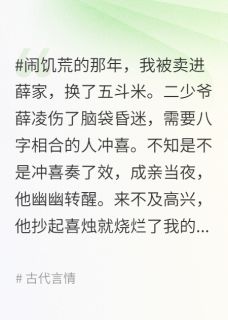
#闹饥荒的那年,我被卖进薛家,换了五斗米。二少爷薛凌伤了脑袋昏迷,
需要八字相合的人冲喜。不知是不是冲喜奏了效,成亲当夜,他幽幽转醒。来不及高兴,
他抄起喜烛就烧烂了我的嫁衣。他怨我趁虚而入,拆散了他和小青梅,恬不知耻。此后三年,
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挑剔。后来,王府的人找到我,说我是流落在外的小郡主。
离开薛家那天,嬷嬷问我,要不要等进京赶考的薛凌回来。我摆摆手说:“不必了。”反正,
我不过是他五斗米换来的妻。1.上好的三净羊毫笔掷在我身上,
在素色的衣裙上沁出一团乌黑的墨点。薛凌气急败坏地看着我,
声音冷得让我心头一颤:“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来书房打扰我。”“敲门声这么大,
害我下笔不稳,好好的一幅画被你给毁了。”铺开的宣纸上,是一幅美人图。美人身姿婀娜,
五官还未画出,只露出一双眼睛,眼尾处落下凌乱的一笔,像极了泪珠。我垂下头,
低声解释:“是母亲让我来的,她说你今日咳嗽,所以我煮了梨羹。”“她说,她说,
母亲说什么便是什么,你难道就没有自己的主意吗?”我紧紧咬着下唇,不让眼泪落下来。
名义上,我是薛凌的妻,可阖府的人都知道,我不过当初是用五斗米换来给他冲喜的。
入府那天,薛老爷子便说了,二少爷活,我活,二少爷死,我死。
一个连命攥在别人手里的无根浮萍,哪里有反驳的权利。
薛凌平日里最看不惯我这副软弱可欺的样子,很快,他厌烦地摆了摆手,示意我出去。
回廊转角处,几个婢女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捂嘴轻笑,
毫不避讳地议论:“每次进书房都要惹少爷生气,要不是八字好,哪轮得到她做这正妻。
”“嘘,小声点,老爷生前特意嘱咐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动她的位置,
就当府里多养一个闲人罢了。”“唉,可怜少爷一翩翩公子,到头来,
竟娶了这样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我毫不在意地理了理衣服,绕过回廊,向院子外面走去。
一声惊雷骤然划破天际,淅淅沥沥的雨滴砸在身上。我想起三年前,成亲那日,
也是落了这样一场雨。2.那时薛凌在一声惊雷中醒来,茫然地看着满室红烛,
又看了看坐在床边,穿着嫁衣的我。不等我开口,他很快明白过来。愤怒,焦急,羞恼。
众多情绪在他眼中翻滚,他踉跄着起身,抄起床头燃着的龙凤喜烛,狠狠砸在我脚边。“滚,
你不是我的妻,我要娶的人是玉瑶,你滚,你滚啊。”金色的火苗瞬间点燃了我的衣裙,
灼热的气息烫的我忍不住惊呼出声。薛凌愣在原地,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幸而守夜的婢女及时赶到,帮我扑灭了火,又派人通知了薛老爷和薛夫人。
众人都沉浸在二少爷醒来的喜悦中,无人注意我残破的嫁衣下,被烧伤的小腿。
满府红绸高悬,雨声淅沥。我蜷缩在廊下,忍着灼痛,将破烂的嫁衣紧紧裹在身上,
仍冷得打颤。屋内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伴着薛夫人一连声地劝慰和安抚。昏昏沉沉间,
我再也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再次醒来时,小腿已经被包扎好,轻轻一动,
便是撕裂般的疼。苦涩的药味顺着窗户飘进来,
伴着薛凌略带歉意的声音:“我哪里知道她连躲都不躲,我又不是故意的。”“你爹说了,
此女八字旺你,如今你能醒来,便是承了她的因,万不能对她太差,以免损了福报。
”薛凌沉声道:“可是,我喜欢的是玉瑶。
”薛夫人恨铁不成钢:“那周玉瑶在你昏迷第三日便与别人定亲了,偏你还心心念念。
”良久,她叹了口气:“罢了,你若实在不喜欢她,五年后,娘便做主替你休妻,
府里养她五年,也算还了这份果了。”3.我冒着雨走进薛夫人的院子,
胸前的磨团洇染出大片的黑色,狼狈又可怜。像往常一样,薛夫人皱了皱眉,又叹了叹气,
让婢女取了一只玉镯塞进我手里,便挥挥手打发我走。回到偏院,我将玉镯仔细收在匣子中,
里面大大小小的首饰已攒了满满一匣,倘若换成银子,想必足够我日后买一间铺子了。
翌日一早,薛凌身边的长随实安带了一名妇人来见我,
笑着道:“二少爷说昨日不慎弄脏了夫人的衣裙,特命小的带了锦绣阁的裁缝娘子,
说给夫人做几身新衣裳。”我乖顺点头:“替我谢过二少爷。
”裁缝娘子仔仔细细的帮我量了尺寸,临走时笑眯眯的称赞:“夫人这身段样貌,
竟比上京城的世家贵女还要好上几分呢。”“届时穿上我们锦绣阁的碧绡月纹裙,
定然是恍若神仙妃子。”几日后,新衣送来了,流光溢彩的月纹蜀锦裙外,
罩着浅碧色的绡纱,果然观之不俗。我穿上它,梳好妆,在垂花门处等着薛凌。
女子欢快地笑声由远及近,薛凌手里拿着一只风筝走过来,身旁跟着表妹兰琦。他看着我,
有一瞬间愣神,瞳孔微缩。“嫂嫂好。”兰琦冲我行礼,
然后对着薛凌眨眨眼:“嫂嫂今日好漂亮啊,竟让我想起玉瑶姐姐。”“昔日,
她最爱穿这碧色衣裙了。”薛凌冷了脸,沉声道:“东施效颦,俗不可耐。”说完,
拂袖而去。兰琦故作歉意地捂嘴:“哎呀,嫂嫂,我又说错话了,你不会怪我吧?”我苦笑,
摇摇头:“没事的,既然他不喜欢,往后我就**了。”正好,拿去卖钱。这几年,
我想尽一切办法攒钱。一半给了绣坊的女掌柜,让她教我识字算账,一半偷偷买了笔墨书册。
夜里,我练字读书,直至辰时才歇下,从不间断。白天,我拿起绣花针,忍气吞声,
从不与人争辩。4.薛凌过来时,我正在绣一方帕子。近来,这种绣了诗书的帕子格外好卖,
一方能多卖十文钱。他斜斜倚在门框上,瞟了绣棚一眼,念出上面的字:“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破天荒地,他勾了勾唇,心情颇好地与我多说了几句话:“倒也不急,
还有一个月我才进京参加春闱,足够时间准备了。”“护膝,外袍,腰带,不拘几件,
只要是深色的便好。”我轻轻点头,这些,自会有专人为他准备妥当。临走时,
薛凌将一支白玉兰花簪子扔进我怀里:“送你的,正好配你那套碧色的衣裙。
”我将簪子收好,放进匣子里。那套衣裙被我当掉了,用它换了十本书。已经读过书的我,
早已明白东施效颦的意思。最后一方帕子绣好后,我将绣品悉数装进篮子里,准备拿给绣坊。
快到门口时,却不知被谁从后面撞倒,数十方帕子散落一地。兰琦小心翼翼地扶起我,
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无事。”我拍拍灰尘,低头去捡帕子。
“呀,这些帕子好精致啊。”兰琦惊喜喊道:“上面还绣了诗词呢?嫂嫂是要送给表兄吗?
”我淡淡回她:“不是,是要拿去卖掉的。”“卖掉?”薛凌从我身后走过来,
一把夺过兰琦手中的帕子,那上面正绣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声音冷冽,
脸色沉沉:“怎么?薛府是缺你钱了吗?”我咬住唇不语。薛府在衣食上并不曾短缺我,
可也不曾给过我月例。小厨房的下人不待见我,就连来了葵水想喝一碗姜枣茶,
都要自己掏钱来买。初来时,我身无分文,只能日日绣帕子拼命攒钱。这些,
薛凌都不曾知道。他只知道每次我在他那里受了委屈后,薛夫人都会赏我首饰,
他的母亲待我宽厚。他定然在想:宋阿陶很好哄的,那么他有时说话刻薄些,也不算什么。
5.“呵。”薛凌冷笑一声,松手,帕子轻轻落到地上。他伸出脚,
簇新的靴子踩上我还没来得及捡起的帕子,狠狠碾着。“少给**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怎么,
薛府养不起你了吗?你是在打我的脸吗?”“不过是一方帕子,我才不稀罕。
”素白的帕子被踩进泥里,只剩满目脏污。薛凌一把推开我,转身上了马车。
我猝不及防地跌入一旁的花丛,花枝上的刺扎入手臂,划出一道长长的血痕。
实安急地直拍腿:“少爷以为这帕子是你为他参加春闱准备的呢,这几日一直盼着,你竟然,
竟然,唉!”他叹着气跑远了。兰琦斜睨我一眼,讥诮地笑着:“嫂嫂还真是,
让人刮目相看呢。”“贱民的女儿,果然是骨子里都带着一股穷酸气。”我狼狈地爬起后,
捂住流血的伤口,忍不住落下泪来。天色渐渐暗,不知在门槛上坐着哭了多久。最后,
我胡乱地抹了一把脸,捡了几方还能修补的帕子放回篮子里。从前,为了讨好薛凌,
我不是没送过他这些东西。他不喜欢**近,我便用目光偷偷丈量他的尺寸,
再暗暗记下他喜欢的颜色。靴子,外袍,腰带,每一样我都下了十足十的功夫。
哪怕十个手指都生了冻疮,房间里冷得连针都捏不住,我还是靠着烛火,
给他做了一顶狐裘帽。可是每一次都能被他挑出毛病。不是针脚太密了,就是颜色太深了,
亦或是,鞋子太合脚,而他偏偏喜欢穿大一点的。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随手赏给下人。
一颗炙热的心,始终捂不化这冬日的寒冰,连带这颗心,也终于冷了下来。
我抱着篮子走回院子,夜风很凉,月光将我的影子拉的又细又长。孤寂,又萧索。
6.薛凌一连几日都没有再见我,直到他进京赶考的这一天。长亭外,
薛夫人带着众人送了又送,仍不舍地拉着他的手,抹着眼泪。“我儿这次若能高中,等回来,
娘必然为你娶一房你心仪的妻室,好为薛家开枝散叶。”薛凌看了我一眼,耳尖泛红。
却似乎又想到什么,只一瞬便冷了脸,赌气般的撇过头去。他说:“旦凭母亲做主。
”薛夫人若有所思地笑笑,将身后含羞带怯的兰琦往前推了推:“不是有话要对你表兄说吗?
”兰琦红着脸,将一个荷包塞到薛凌手里:“祝表哥一举登科,金榜题名,琦儿,
琦儿等着你回来。”薛凌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将荷包收进怀中:“表妹有心了。
”“不像某些人,不曾送我只言片语,一针一线。”我尴尬地站在那里,
带着众人嘲笑、审视的目光,目送薛凌上了马车。成亲三年多,我仍是处子之身。
用一个少夫人的虚名换来三年安稳的日子。我暗暗告诉自己:宋阿陶,你还是赚了。回府时,
远远看见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薛府门前。马车上,坐着一名年轻矜贵的公子,
身后是一排婢女和侍卫。“这位是荣亲王世子。
”手持佩剑的侍卫向薛夫人介绍:“世子有要事相商,可否过府一叙。”7.直到穿上华服,
被一群婢女伺候着梳妆打扮,戴上满头珠翠,我仍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事。
荣亲王世子秦煜竟是我一母同胞的兄长,而我,是十四年前走失被拐,流落民间的郡主。
我生怕这是一场梦,梦醒后,我仍是那个只能低眉敛目地宋阿陶。可是手上的红色胎记,
与秦煜无比相似的眉眼,无一不在提醒我,这是事实。我和薛凌的关系,
原本也没有去官署备案,只是薛老爷临终前执意让我上了族谱。如今,
在族谱上将我的名字划去,我和薛凌,便算两清了。薛府在祈州也算名门贵族,
但是与荣亲王府比,还是不值一提。薛夫人本就不喜我,如今能卖荣亲王一份人情,
自然是痛快答应。只用了两日,秦煜带来的婢女便为我收拾好了箱笼。
看着从我房间里抬出的一箱箱书籍,秦煜的眸子里有一闪而过的欣赏:“你竟然识字?
”我笑的乖巧又温婉:“跟着绣坊的女掌柜学了三年识字算账,
平日里也会看些书来打发时间。”“毕竟,‘读书取适心,名誉非可攀’。”秦煜笑了笑,
第一次向我展露出属于兄长的亲昵:“我秦煜的妹妹,果然是在崖底也能发光的珍珠。
”“等见到母亲,她定然也会喜欢你的。”这一刻,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我长舒一口气,
无比庆幸这三年来的挑灯夜读。你看,哪怕是骨肉至亲,在家族的利益面前也会小心思忖,
认真考量。倘若今日的我如同乡野村妇般无知无礼,恐怕很难以郡主的身份顺利回京。
抚摸着那个装满首饰的小小的匣子。曾经我谨小慎微地一点点攒下这些东西,
小心的谋划着自己的未来,将他们当做安身立命之本。那些苦涩难捱的日子,终究成了过往。
启程前一夜,一直照顾我的老嬷嬷问我,要不要等进京赶考的薛凌回来再走。
“我能看得出来,二少爷心里是有你的,只是他自小被骄纵长大,做事难免随性了些。
”心里有我吗?我不清楚,亦不想再去深思。反正,我不过是他五斗米换来的妻。
如今缘分已尽,自然是一别两宽,各生欢喜。8.马车行了十日,我来到了荣亲王府。
在路上,王府的嬷嬷已教了我规矩,面对神色各异的众人,我礼数周到,一一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