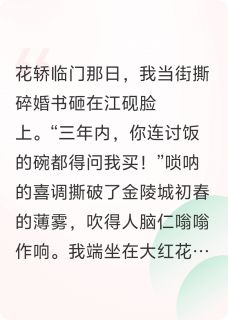
花轿临门那日,我当街撕碎婚书砸在江砚脸上。“三年内,你连讨饭的碗都得问我买!
”唢呐的喜调撕破了金陵城初春的薄雾,吹得人脑仁嗡嗡作响。我端坐在大红花轿里,
指尖冰冷,隔着厚重绣金的轿帘,
也能描摹出外面那场“盛况”——江家为了迎娶我这个“卑贱商女”,排场做得十足十,
锣鼓喧天,红绸铺地,生怕全城不知道他江家娶了新妇,更不知道他江家娶这新妇,
图的是我沈家泼天的钱。花轿稳稳停在江府那气派得过分的朱漆大门前。喧闹声浪里,
我清晰捕捉到那一声熟悉的、带着惯常倨傲的轻笑。江砚。轿帘被喜婆殷勤掀开,
刺眼的天光涌进来。我没等那套“跨火盆”的吉利话出口,自己一弯腰,走了出去。
沉重的凤冠压得脖子生疼,我抬手,在满街看客、江家亲朋错愕的注视下,
一把将它扯了下来。金凤钗、珠翠流苏叮叮当当滚落一地。死寂瞬间吞噬了所有吹打。
江砚就站在几步外的台阶上,一身大红喜服衬得他面如冠玉,只是那双眼里的鄙夷和算计,
像淬了毒的针,扎得人生疼。他显然没料到这一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眉头拧起,
带着一丝被冒犯的愠怒:“沈娇,你发什么疯?吉时已到,还不快……”我向前一步,
直接踩过那顶价值不菲的凤冠,绣鞋碾在细碎的珍珠上。伸手入怀,
掏出那份鲜红刺目的婚书。指尖用力,刺啦——清晰的撕裂声在寂静中格外惊心。一片,
又一片。鲜红的碎纸如同被揉碎的残花,被我扬手,狠狠砸向江砚那张俊美却虚伪的脸。
碎纸纷纷扬扬,沾了他满身满脸。“江砚,”我的声音不大,却像冰锥,穿透了所有喧嚣,
钉在每个人耳中,“这亲,不结了。”江砚下意识抹开脸上的纸屑,
白皙的脸上被纸角划出一道细小的红痕,狼狈又滑稽。他先是愕然,
随即是滔天的怒火烧红了眼:“沈娇!你这贱妇!敢在今日、在我江府门前撒野?!
你沈家还想不想在金陵立足了?!”他身后的江家亲眷也反应过来,纷纷怒斥:“反了!
简直反了!”“商贾贱户之女,果然毫无教养!”“快把她绑起来!送官!
”我无视那些聒噪的苍蝇,只盯着江砚,盯着他那双因暴怒而微微发红的眼睛,一字一顿,
清晰无比:“从今日起,你我恩断义绝。但我把话撂在这里——”我微微扬起下巴,
唇角勾起一个冰冷的弧度,目光扫过他,扫过他身后那巍峨却早已蛀空的江府门楼,
最后落回他脸上,带着淬毒的预言:“三年之内,我要你江砚,跪在我沈娇面前摇尾乞怜!
你连讨饭的破碗——都得问我买!”死寂。比刚才更彻底的死寂。连唢呐手都忘了喘气。
江砚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荒诞的笑话,脸上那点狼狈被一种极致的轻蔑取代。他嗤笑出声,
肩膀耸动,笑声越来越大,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鄙夷:“哈哈哈!沈娇,你是不是被气疯了?
还是你们这些满身铜臭的商贾,就只会做这等痴心妄想的白日梦?讨饭?
问你这卑贱商女买碗?”他上前一步,居高临下,眼神像在打量一件肮脏的货物,
声音淬着冰碴:“你沈家是有些浮财,可在我江家百年清贵门楣面前,算什么东西?你沈娇,
又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我面前口出狂言?”那“卑贱商女”四个字,被他咬得极重,
像淬毒的鞭子。我看着他,看着他眼中那份深入骨髓的、对商贾的轻蔑。
这轻蔑曾是我沈家主动捧上金山银山也未能融化的冰山一角。心口像是被那冰碴子反复碾过,
尖锐的痛楚之后,是燎原的冰冷恨意。“我算什么东西?”我轻轻重复,声音里听不出喜怒,
只有一片死寂的寒潭,“江砚,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我不再看他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
也不理会身后炸了锅的议论和江家人的咆哮叫骂,猛地转身。沉重的嫁衣外袍被我一把扯下,
随手抛在地上,露出里面一身素净却利落的月白衣裙。
我径直走向停在街角、毫不起眼的一辆青布马车。“**!
”陪嫁的大丫鬟阿萝早已吓得脸色惨白,此刻才反应过来,带着哭腔追上来。“回府。
”我钻进马车,声音平静无波,只有指尖在袖中掐得死紧。车帘落下,
隔绝了外面江砚暴怒的吼声和江府门前那一片狼藉的红。马车启动,
平稳地驶离这片令人窒息的喧嚣。阿萝坐在我对面,惊魂未定,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们…我们真的…”“阿萝,”我打断她,
目光透过晃动的车帘缝隙,看向外面飞速倒退的街景,
那喧嚣的红渐渐被寻常的灰瓦白墙取代,“不是‘我们’回去。是我回沈府。你,
”我看向她,眼神不容置疑,“立刻去淮安。拿着我的印信,找盐场大掌柜。告诉他,
我沈娇的话:从今日起,沈家名下所有盐船、盐引、盐仓,全部停摆。一粒盐,都不准再出。
”阿萝猛地睁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停…停盐?!**,那可是我们沈家几代人的根基!
这…这江南的盐价…”“就是要它乱。”我唇角那点冰冷的弧度更深了,
带着玉石俱焚的决绝,“乱到天翻地覆,乱到…有些人该跳出来了。按我说的做,立刻去!
”阿萝看着我眼中那从未有过的、近乎疯狂的冷厉,所有劝说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她用力点头,接过我递出的贴身印信,马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下,她跳下车,
迅速消失在人群中。车轮继续滚动,载着我驶向沈府。心口的冰冷恨意并未消散,
反而沉淀下去,化为一股支撑我走下去的、更坚韧的力量。江砚,你说我卑贱?
你说我痴心妄想?好,很好。我们就看看,你这清贵门楣的江家少爷,
离了“卑贱商女”的银子,离了这“铜臭”撑起的排场,到底能清贵几日!---三个月。
金陵城上空仿佛被无形的阴云笼罩,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源头,是盐。
往日里车水马龙、喧嚣鼎沸的盐市码头,如今一片死寂。
几艘挂着沈家旗号的大船静静泊在岸边,船舱紧闭,像沉默的巨兽。
岸上囤积如山的盐包被苦力们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盐引贩子们聚在角落,个个愁眉苦脸,
唉声叹气。“疯了!沈家那位大**真是疯了!三个月一粒盐不放,
这江南的盐价…是要涨到天上去啊!”“谁说不是!我家铺子都快断炊了!客人都堵着门骂!
”“听说扬州那边,盐价已经翻了三番!再这么下去,怕是要出乱子啊!
”“沈家到底图什么?金山银山不赚,这不是自断臂膀吗?”“图什么?嘿嘿,
”一个消息灵通些的压低声音,朝江府方向努努嘴,“还不是花轿前撕婚书那档子事儿?
江家少爷那声‘卑贱商女’骂得痛快,沈家这位姑奶奶,是要把天捅个窟窿来报仇呢!
”议论声嗡嗡作响,像一群焦躁的苍蝇。江府。曾经门庭若市,
如今也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萧条。书房里,江砚烦躁地踱着步,
昂贵的锦缎靴子踩在光洁如镜的金砖上,发出空洞的回响。他面前摊着几本账册,墨迹淋漓,
全是刺眼的赤字。“少爷!少爷!”管家江福连滚爬爬地冲进来,脸色灰败如土,
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完了…全完了!盐价…盐价崩了!”江砚猛地停步,
瞳孔骤缩:“崩了?不是一直在涨吗?说清楚!”江福噗通一声跪在地上,
老泪纵横:“涨…涨到头了呀少爷!沈家…沈家那妖妇!她…她今天突然放风出来,
说…说淮北发现特大盐矿!储量惊人!还…还拿出了勘探图!就在半个时辰前,
消息刚传到码头,那盐价…那盐价就像雪崩一样往下砸啊!”江砚如遭雷击,身体晃了晃,
一把抓住桌角才勉强站稳:“放屁!淮北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哪来的盐矿?!
定是沈娇那**造谣!快!快把我们高价收来的盐引抛出去!趁现在还有人接盘!
”“抛…抛不掉啊少爷!”江福哭嚎着,头磕在地上砰砰响,“消息一出来,
盐引就成了烫手的山芋!谁还敢接?都在疯狂往外抛!市面上的盐引价格,
已经…已经跌破了我们当初收购价的三成!而且还在往下掉!
我们…我们收的那些盐引…全砸手里了!全是废纸啊!”江砚只觉得一股腥甜涌上喉咙,
眼前阵阵发黑。沈娇!又是沈娇!这三个字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理智。
他想起自己为了囤积居奇、趁着盐价暴涨大捞一笔,不仅将江家能动用的现银全部投入,
更是以江家祖宅、名下最值钱的田庄铺面作为抵押,向几家钱庄借了巨款,
才吃下市面上近四成的盐引!那是江家几代人攒下的根基!“少爷!还有…还有更糟的!
”江福的声音带着绝望的哭腔,“永通钱庄、利丰钱庄…好几家的管事都堵在前厅了!
说…说我们抵押的祖宅地契和田庄铺面的契约…到期了!要…要收走抵债!
他们…他们拿出了契约文书,上面盖着少爷您的私印!白纸黑字啊少爷!”“什么?!
”江砚眼前彻底一黑,踉跄着后退,撞在沉重的紫檀木书架上,
震得上面一个前朝官窑花瓶摇摇晃晃,“噗”地掉下来,摔得粉碎。
碎片溅到他昂贵的靴子上,他浑然不觉。抵押?地契?他什么时候签过这种文书?!
电光火石间,一个模糊的片段闪过脑海。那是盐价刚开始疯涨、他被暴利冲昏头脑的时候。
沈娇撕婚书后,沈家虽然彻底断了往来,但他私下里通过一个“可靠”的掮客,
搭上了几家背景深厚、愿意提供大额借贷的钱庄。签契约那晚,他志得意满,
在对方巧舌如簧的吹捧和几杯黄汤下肚后,似乎…似乎确实在几份厚厚的文书上盖了私印,
签了名字……难道……难道那些文书里夹带了抵押祖产的契约?!
冷汗瞬间浸透了江砚的后背。他被设计了!被沈娇那个**一步步引入了死局!
囤盐引的钱是借的,抵押的是祖产!如今盐引变成废纸,债主上门逼债,祖产即将不保!
“**!毒妇!沈娇!我要杀了你!”江砚双目赤红,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
发出凄厉的咆哮。巨大的恐惧和愤怒彻底冲垮了他的理智。他猛地转身,冲出书房,
像一阵狂风般卷向后院粮仓。沉重的粮仓大门被他狠狠踹开。
里面囤积着江家最后的应急存粮。江砚眼中全是疯狂的血丝,他冲进去,
对着码放整齐的粮缸拳打脚踢。“毒妇!都是你!都是你害的!”他嘶吼着,
用尽全身力气踹向一个半人高的青瓷大缸。“哐当——哗啦——!”大缸应声而倒,
碎裂开来。金黄的稻米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汹涌而出,流淌了一地,淹没了江砚的靴子。
他站在米堆里,胸口剧烈起伏,昂贵的锦袍上沾满了灰尘和米粒,头发散乱,
脸上是扭曲的恨意和一种濒临崩溃的绝望。哪里还有半分昔日金陵贵公子的倨傲风采?
就在这时,一个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女声,清晰地穿透了他粗重的喘息和粮仓里的混乱,
在门口响起:“江少爷,好大的火气。踹倒了粮缸,是打算今晚就喝西北风了么?
”江砚猛地抬头,血红的眼睛死死盯住门口。阳光从门口斜射进来,
勾勒出一个纤秀却挺拔的身影。沈娇穿着一身素净的月白襦裙,外罩一件烟青色的薄纱半臂,
发髻简单挽起,只斜插一支素银簪子。脸上脂粉未施,却眉目如画,眼神清亮,
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冰冷和……一丝淡淡的嘲讽。她就那样闲适地站在那里,
与粮仓内的一片狼藉和江砚的疯狂狼狈,形成了刺眼的对比。她身后,
跟着几个面无表情、身材健硕的沈家护院。其中一个护院手中,正拿着一卷深蓝色的契纸,
慢条斯理地展开。江砚的目光死死钉在那卷契纸上,熟悉的朱砂印泥颜色刺得他眼球剧痛!
那是他江家祖宅的地契!此刻,正被沈娇的人,像展示战利品一样拿在手里!“沈!娇!
”这两个字几乎是从江砚的牙缝里挤出来,带着刻骨的恨意和噬血的疯狂,“你竟然敢来?!
你害得我江家还不够惨?!”“害?”沈娇轻轻挑眉,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她莲步轻移,踩着地上散落的米粒,姿态从容地走进粮仓,目光扫过满地狼藉,
最后落回江砚那张因愤怒和恐惧而扭曲的脸上。“江少爷此言差矣。盐市买卖,明码标价,
有涨有跌,本是常事。你贪心不足,妄图囤积居奇,甚至不惜抵押祖产借贷豪赌,
如今赌输了,怎能怪到旁人头上?”她走到江砚面前几步远停下,目光平静无波,
声音却清晰地敲打在江砚濒临崩溃的神经上:“这地契,还有你抵押出去的田庄、铺面文书,
如今都在我沈家名下。永通、利丰那几家钱庄,不过是帮我沈家走个过场罢了。江砚,
”她微微俯身,靠近他,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如刀,“你江家的百年根基,现在,
是我的了。”“你——!”江砚气得浑身发抖,目眦欲裂,几乎要扑上去掐死眼前这个女人。
但他刚一动,沈娇身后的护院便齐齐上前一步,眼神锐利如鹰,
无形的压力瞬间将他钉在原地。沈娇直起身,好整以暇地理了理衣袖,
从袖中抽出那张象征着江家最后一点体面的祖宅地契,在江砚眼前轻轻晃了晃。
深蓝色的纸张在昏暗的粮仓里,像一张催命的符。“看着这些米,
”沈娇的目光落在地上流淌的金黄稻谷上,语气带着一丝施舍般的怜悯,“怪可惜的。
这样吧,江少爷。”她顿了顿,目光重新落回江砚惨白的脸上,
唇角勾起一个极淡、却冰冷刺骨的弧度:“你现在,就在这里,给我磕一个头。
”她伸出纤细的手指,点了点脚下沾满灰尘和米粒的地面。“磕一个响头,
我就赏你一口饭吃。如何?”---粮仓里死寂得可怕。空气凝滞,
只剩下江砚粗重得如同破风箱般的喘息声,还有他自己狂乱的心跳,在耳边擂鼓般轰鸣。
他死死盯着沈娇,那张曾经让他惊艳、如今却只余下刻骨恨意的脸。
她眼中那毫不掩饰的冰冷、嘲讽,还有那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像滚烫的烙铁,
狠狠烫在他的尊严上。磕头?在这满地狼藉、米粮混杂的肮脏地面上,
给这个他曾经鄙夷到骨子里的“卑贱商女”磕头?只为了换一口饭吃?!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沈娇!”江砚从牙缝里挤出嘶吼,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沫,“你休想!我就算是饿死!
从这里跳下去!也绝不会向你摇尾乞怜!你等着!我江家还没完!
我还有……”“你还有什么?”沈娇平静地打断他,眼神像冰水,
瞬间浇熄了他最后一点虚张声势的火焰,“你江家值钱的产业,如今都在我手里。
你江砚的名字,在金陵各大钱庄已是死账,无人再敢借贷一文。你指望谁?
指望你那群只会锦上添花、如今早已避你如蛇蝎的‘清贵’亲朋?
还是指望……”她的声音微微一顿,带着一丝玩味的探究,目光似乎穿透了粮仓的墙壁,
望向府邸深处某个方向。
你那位缠绵病榻多年、却依旧死死攥着江家最大一份产业——城西万顷桑田和织造坊的叔父,
江承恩?”江砚的瞳孔骤然收缩!像被最隐秘的毒针刺中!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板窜上头顶!
她怎么会知道?!她怎么敢提?!叔父江承恩,是江家上一代硕果仅存的长辈。为人刚直,
最重礼法门风。当年父亲早逝,江砚年幼,江家曾一度风雨飘摇,是这位叔父力挽狂澜,
稳住了局面。虽然后来因身体原因退居幕后,将家主之位交给了江砚,
但他手中那份由祖父亲自分给他、并立下严苛遗嘱“非病重垂危或自愿,
不得转赠或分割”的桑田织造产业,始终是江家最厚实的一块底牌,
也是江砚心中最大的隐忧和……觊觎。叔父缠绵病榻多年,据名医所言,已是油尽灯枯,
全靠名贵药材吊着命。江砚一直隐忍,只等那一刻。只要叔父一死,
那份庞大的产业自然顺理成章落入他这个唯一的嫡亲侄儿手中!那是他翻盘的最后希望!
是他江砚重新立于人上的资本!沈娇此刻点破,是何用意?!难道她连叔父都……不!
不可能!沈娇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叔父身边都是江家忠仆!她一定是虚张声势!
江砚强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色厉内荏地吼道:“住口!我叔父的事,轮不到你这外人置喙!
沈娇,你今日羞辱于我,这笔账,我江砚记下了!他日必当百倍奉还!滚!
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江府!”“滚?”沈娇轻笑出声,那笑声在空旷的粮仓里显得格外清脆,
也格外刺耳。“该滚的,恐怕很快就是你了,江少爷。这宅子,如今姓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