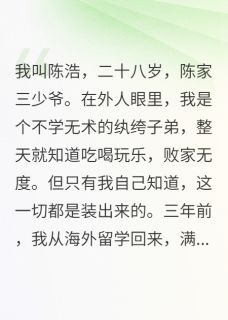结婚领证那天,我媳妇揣着我给的半个月工资,一夜没回家。我急得满头是汗,
生怕她一个乡下姑娘在城里出事,发动全厂工友找了一宿,差点要去派出所报案。
结果第二天,却在供销社门口撞见她,挽着一个油头粉面的“倒爷”,
嘴上抹着我从没见过的鲜亮口红。那倒爷嘴角还沾着一点,
指着我对她说:“这就是你那穷鬼丈夫?一个月36块死工资,能给你买什么?
”我媳妇立刻甩开我的手,劈头盖脸地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和李哥谈生意呢,
他路子广,能帮咱家搞到彩电票,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李哥是能人,思想比你活络,
我跟他学点本事怎么了?你一个臭劳工还想管我?”“赶紧给我滚回去,别耽误我过好日子!
再纠缠不清,我就跟你离婚!”我笑了,“那就离。”1苏兰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嘴唇翕动半天,一个字也没挤出来。她大概以为我会像从前那样,低头认错,求她回家。
我准备转身离开,她却突然拨开人群冲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周建国,你犯什么浑?
”“我说离婚是气话,你听不出来?当初在村里死活要带我进城,现在跟我拿乔?
”“你就不怕我真走了,再也没人给你洗衣做饭?”她眉头皱成一个疙瘩,
像看一个不懂事的愣头青,眼里全是烦躁和不耐。我低头清晰地看到,
苏兰锁骨那块藏着一小片红痕,像是被人用力嘬出来的。
再联想到她刚才说跟着李哥学本事的说辞,我胸口堵得慌。从认识到领证,
苏兰从不许我在她脖子上留下印子。她说厂里人多嘴杂,叫人看见了丢人。现在,
她却任由另一个男人在她身上留下这么扎眼的痕迹。或许是我的视线太过锋利。
苏兰心虚地拢了拢衣领,声音拔高八度:“蚊子咬的!城里蚊子毒,你大清早找茬是不是!
”“我晚点就会回去。”都快入冬了,哪来的毒蚊子?她连撒谎都懒得动脑筋。
我闭上干涩的眼,把火气压进喉咙:“苏兰,我没开玩笑,我们离婚。”信任这东西,
碎一次就再也拼不起来。之前她拿我的工资去给李哥买“的确良”衬衫,我只当她是仗义,
帮衬朋友。她夜里偷偷去舞厅,我也信了她是去学点新东西,开阔眼界。
我不愿用厂里那些长舌妇的脏话去想我的妻子。可她却在我发动全厂兄弟找她一夜后,
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苏兰一怔,刚要反驳,身后的李哥却忽然嗤笑一声。“哎哟,
小兰,你男人不识货啊。”他懒洋洋地开口,故意把手搭在苏兰肩上。苏兰的脸瞬间涨红,
身体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不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看不出这其中的龌龊。
怒火烧到头顶,我猛地甩开她的手。她踉跄一步,撞翻了旁边卖鸡蛋的货摊,
噼里啪啦碎了一地。李哥尖叫着跳开,苏兰慌乱地看着我。我头也不回地挤出人群,
到了厂里就拨通了工友黑子的电话:“麻烦帮我给我哥周海捎个口信。”“对,我要离婚了,
让他帮我问问林晓燕。”挂了电话,我蹲在供销社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许久都站不起来。
或许我和苏兰,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我不该把一个一心想飞上枝头的麻雀,
当成能和我同甘共苦的燕子。苏兰是苏兰,她永远不可能是林晓燕。
我更不该妄想一个长得有几分相似的影子,能代替我心里的那个她。想起三年前,
在村口第一次见苏兰的场景,喉咙里泛起一阵苦涩。2当初我只是个刚转正的工厂技术员,
每月拿着固定工资,心里却装着还不完的人情债。初恋林晓燕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临走前,
她父亲找到了我。他没说一句话,只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拍在我面前。通知书对现在的我来说,
只是一张褪色的旧纸。可对那时的我来说,它是我和林晓燕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托人给她带去了一双新皮鞋,然后断了联系。后来回乡探亲,
在河边救了落水的苏兰。她当时诧异地看着我:“你不是海河哥的弟弟吗?在城里当工人,
一个月得挣不少钱吧?”她羡慕地看着我,“不像我们,
一辈子刨土疙瘩……”或许是那份羡慕满足了我的虚荣,又或许是别的。
我笑着摇了摇头:“城里也就那样,你要是想去,我可以帮你。”她眼睛瞬间亮了,
随即漾开一个纯朴的笑容。苏兰的笑容太像我记忆里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
所以我明知苏兰主动跟我回城必有她的盘算。但还是没能抵住,后来日子长了,
我也真心实意想跟她过日子。我总觉得,既然把人带出来了,就得对她负责。
所以苏兰想要的一切,只要我能给,从不吝啬。她说娘家弟弟要娶媳妇,彩礼不够,
我就把攒了半年的奖金都给了她。可她却隔三差五跟李哥混在一起,
回来晚了就拿“学做生意”当借口。一旦我多问一句,她就立刻翻脸:“李哥路子广,
认识的人多,我不跟他学着点,难道跟你一样在工厂里熬死一辈子?你懂个屁!
”口袋里的传呼机震动起来,是黑子发来的消息,告诉我深圳那边已经联系好了。刚想回信,
却发现宿舍门被人一脚踹开。一进去就看见苏兰正指着我的床铺,
对一群工友唾沫横飞:“别看他平时装得人模人样,其实根本不行,我们结婚这么久,
他一次都没碰过我!”配上她那副梨花带雨、受尽委屈的模样。我的宿舍里,
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和领导,现在下面已经窃窃私语,指指点点。
还有些平时不对付的工友,高声问我是不是真的“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
我顿时血冲头顶。这时,李哥也耀武扬威地打来电话,因为是宿管大爷拿来的,我没法不接。
他小人得志的嗓音从听筒里钻出来:“周建国,听说你不行啊?怪不得小兰要跟着我。
男人没本事守不住老婆,就别怪别人下手。”“对了,
小兰用你的名义在我这拿了五百块钱做本钱,你一个劳模,不会想赖账吧?”我没怒,
反而笑了,我现在是真的佩服苏兰和李哥的**。他们不仅败坏我的名声,
还合起伙来算计我的钱。我冷笑一声,挂断电话,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离婚两个字说得清清楚楚。把苏兰和她那堆不属于这里的东西一起扔出宿舍后,
我锁上了门。结果电话又响了。是当铺的张老板。电话接通后,听见他说:“周师傅吗?
你前两天让我留意的‘上海’手表,今天有个女的拿来当了,我看着像你爹那块,
就给你提个醒。”全身的血都凉了,我感觉自己掉进了三九天的冰窟窿里。
不敢相信地又问了一遍:“你说什么?”3对面重述了一遍。可我依旧听得不真切,
耳朵里全是嗡嗡的轰鸣。父亲走得早,这块表是他省吃俭用大半辈子买下的,临终前交给我,
说以后传给我的儿子。这是我最珍视的东西,我一直锁在箱底,从未跟苏兰提过。
我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当铺张老板叹了口气,挂断电话。我疯了一样冲向当铺。死当,
一百块。我颤抖着手,看着当票上那熟悉的字迹和红手印。脑子乱成一锅粥,
传呼机又收到一条新留言:【敢把我东西扔出来,你长本事了。
】【你忘了你在竞争车间主任吗?立刻把你的存折给我,不然我就去纪委告你乱搞男女关系,
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我死死盯着那行字,恨不得把苏兰的骨头一根根捏碎。
我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她所谓的“娘家”,只因为她说女人管钱,家里才能兴旺。
我本以为苏兰只是贪财,爱慕虚荣。却没想到她居然连我父亲的遗物都敢动,
还用我的前途来威胁我!我咬着牙,赤红着眼关掉传呼机。既然她要毁了我的一切,
那我就让她辛苦钻营的东西全部化为泡影。一封牛皮纸信封被宿管大爷递到我手里。打开,
里面掉出一张去往深圳的单程火车票和一份盖着红章的录用通知书。
信纸上只有一句话:【我们等你。】我将通知书叠好,贴身放着,
亲自提笔写下回信:【半个月后到。】我独自一人坐车回到乡下老家,给父亲上坟。
做完这一切,我又把自己这些年获得的所有奖状,一张张在坟前烧掉。跪在父亲的墓碑前,
我发誓,一定会让苏兰亲眼看着她所追求的一切,是何等可笑的泡影!直到一个星期后,
没等到我摇尾乞怜的苏兰终于坐不住了。
我刚把苏兰联合李哥倒卖工厂物资的证据交给保卫科的兄弟。宿舍的门就咔哒一声被打开。
苏兰原本满脸怒气,可看见我平静无波的样子,转而高高扬起下巴:“我还以为你多硬气呢,
一个星期就熬不住,主动把我的东西都搬回来了。”她故作大度地叹了口气:“算了,
谁让我心软呢,你去纪委跟领导们解释一下,说之前都是误会,这事就算过去了。”说着,
苏兰得意洋洋地拿起桌上的存折,准备去取钱,却发现那上面的户主名字已经换成了我。
她震惊地瞪大双眼看着我:“你把钱都转走了?”我厌恶地看着她,默默站起身,
离她远了一些。苏兰见我这副神情,顿时脸上**辣的:“你什么意思?
周建国你别不识抬举!”她嗓门很大,守在门外的李哥听见动静闯了进来。
看见我们剑拔弩张的样子,他心中一喜。可下一秒苏兰说出的话就让他脸色大变。
“你凭什么动存折里的钱?赶紧给我还回来!”4当初我愿意把钱都给苏兰,
是因为我相信她会持家。可现在,我一分钱都不想让她再碰。
倒爷急吼吼地指着我:“周建国你还是不是男人,哪有男人从老婆手里收回工资的?
就算小兰说了几句气话,你怎么能把钱都转走呢!”“她答应我的彩电还没买呢!
你这不是耽误我们做生意吗?”我皱着眉,实在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如此理所当然。
仿佛我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天生就该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苏兰听了李哥的话,
心里更有了底气:“你以为用钱就能逼我跟李哥断了?”“我告诉你,做梦!
”“以前限制我跟朋友交往就算了,现在连我学做生意挣大钱你都看不惯,
你这个没出息的死脑筋!”我诧异地愣住,我什么时候限制过她交友?
如果她说的交友是指跟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半夜去跳黑灯舞,那我确实劝过。
当时我只是提醒她注意安全,她却在外面跟人说我思想僵化,见不得她比我活络。
我看着苏兰,突然觉得一切都那么可笑。而后,我将一沓纸甩在她的脸上:“你要自由,
我给你。”苏兰一愣:“什么东西?”从前只要她一哭二闹,我就会心软投降,
为什么这次完全不一样了?苏兰压下心底的慌乱,嘴上却不饶人:“你再闹,
别怪我真去纪委告你!”我将手写的离婚申请书摆在苏兰眼前:“签,不签我都看不起你。
”苏兰在我面前横行惯了,哪受得了这种挑衅。当即红着眼,
抓起笔在名字后面划下重重的一笔,瞪着我撂狠话:“你最好别后悔!”啪的一声,
她把我送她的第一瓶雪花膏狠狠砸在地上,扭头就跑。
李哥急忙追了上去:“存折的事还没解决,你怎么就签了字!要是他真离了,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苏兰却满不在乎:“周建国爱我爱得要死,我闹了多少回他都求我,
签个字算什么,他不敢去民政局的。”下一秒,他们眼前停下一辆尘土飞扬的北京吉普。
李哥嫉妒地看着这辆稀罕的汽车,下一秒慌乱地扯住苏兰的胳膊:“小兰,你看,
那不是保卫科的车!”苏兰刚皱眉回头,就发现我站在门口,
一个穿着夹克衫的中年男人正准备开吉普车的后门。苏兰傲慢地扬起下巴,“你看,
我就说周建国离不开我,这不就找人来求和了。”“建国!”下一秒,
一个秀丽的身影扑进我怀中,我牢牢地将她抱住,再也不想松开。苏兰目眦欲裂,
朝着我大吼:“周建国!你给我松手!你当我是死的吗!
”5苏兰的尖叫刺破了工厂门口嘈杂的人声。她拨开人群就朝我们扑过来,指甲张开,
目标是林晓燕的脸。我没有躲。只在苏兰冲到面前的瞬间,侧过身,将林晓燕完全护在身后。
然后,我抬起眼,看着她。那眼神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愤怒,没有怨恨,甚至没有一丝波澜。
苏兰前冲的势头猛地刹住,僵在原地,脸上的疯狂褪去,换上了错愕。
旁边的李哥终于反应过来,这辆北京吉普和车上下来的人,都不是他能惹得起的。
他慌忙去拽苏兰的胳膊,嘴里小声嘟囔:“小兰,我们走,快走!”可他刚一动,
吉普车驾驶座的门开了。一个穿着夹克衫,身板挺直的中年男人走下来。
他只用眼角扫了李哥一眼。李哥的腿肚子开始打颤,脸色煞白,脚下像生了根。
中年男人没再看他,径直走到我面前,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建国,好样的。
”“没给咱们当过兵的人丢脸。”他声音洪亮,周围伸长脖子看热闹的工友们瞬间炸开了锅。
“原来周师傅当过兵!”“我说呢,周师傅这身板一看就不一样。”“你看那倒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