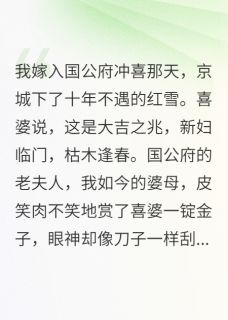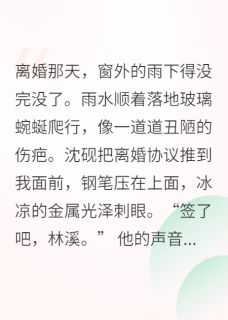
离婚那天,窗外的雨下得没完没了。雨水顺着落地玻璃蜿蜒爬行,像一道道丑陋的伤疤。
沈砚把离婚协议推到我面前,钢笔压在上面,冰凉的金属光泽刺眼。“签了吧,林溪。
”他的声音没什么温度,跟这屋子里昂贵的意大利大理石地面一样冷硬。“五年了,
该结束了。”我看着他,这张脸,看了五年,从最初的悸动到后来的麻木,
现在只剩下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好。”我说。拿起笔,笔尖悬在签名栏上方,
一滴墨水泅开了一小团蓝。沈砚的视线落在那团墨渍上,微微蹙眉,
大概觉得我又在拖泥带水。我其实只是在想,这五年,我究竟得到了什么?
是衣帽间里那些标签都没拆的奢侈品?还是每次家庭聚会时,沈太太这个镶着金边的称呼?
抑或是他深夜应酬回来,身上永远沾染的、不属于我的香水味?我签下名字,林溪。
笔画很稳。沈砚似乎有些意外我的干脆,他拿起协议,目光扫过我的签名,又落在我脸上,
像是在确认什么。“财产分割,律师会跟你对接。该你的,一分不会少。”他顿了顿,
补充道,语气带着一种施舍般的宽宏大量,“你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我扯了扯嘴角,
想笑,没笑出来。“沈砚,”我开口,声音有点哑,清了清嗓子,“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他抬眼看我,示意我说。“这五年,你有没有…哪怕只有一分钟,把我当成过你的妻子?
而不是一个…摆设?或者,一个你不得不应付的责任?”空气凝滞了一下。
沈砚的眼神沉了下去,里面翻涌着我熟悉的、属于沈氏集团掌舵人的那种不耐烦和审视。
他大概觉得我这问题很蠢,很矫情,很不识时务。“林溪,”他的声音冷了几分,
“我们之间,一开始就是协议。沈家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太太,你需要钱给你母亲治病。
各取所需,很公平。现在,你母亲走了,协议自然结束。谈感情?”他嗤笑一声,
那笑声像冰锥扎进我心里,“你不觉得多余吗?”他站起身,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来,
带着迫人的压力。“还有,收起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你永远不可能是她。”他走了,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却在我空荡荡的心里砸出一个巨大的回响。“她”。
那个横亘在我和他之间,像幽灵一样的“她”。沈砚心尖上的白月光。他少年时就爱而不得,
后来因病早逝,成为他心中永恒遗憾的——苏晚。我的存在,从头到尾,
都只是沾了那个名字的光。因为我的眉眼,据说有三分像她。所以,
沈家老爷子拍板定下了我。所以,沈砚娶了我。五年。我扮演着沈太太,
努力模仿着沈砚偶尔醉酒后,嘴里模糊不清提到的苏晚的喜好、习惯。他喜欢她穿素色长裙,
我便扔掉了所有亮色的衣服;他记得她泡茶的水温要刚刚好八十度,我便一遍遍练习,
烫伤了无数次手指;他怀念她弹琴的样子,我甚至去报了成人钢琴班,
手指僵硬地在琴键上敲打,只为在他生日时,弹一曲他提过的、苏晚喜欢的曲子。
我以为时间能改变什么。我以为水滴能穿石。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自导自演的独角戏。
他最后那句话,像淬了毒的刀,精准地捅穿了五年来自欺欺人的泡沫。“你永远不可能是她。
”是啊,赝品永远变不成真迹。窗外的雨还在下。我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
看着这座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城市。霓虹闪烁,像无数双冷漠的眼睛。
玻璃上倒映着我的脸,苍白,疲惫,眼神空洞。这张有三分像苏晚的脸,
此刻只觉得无比讽刺。我抬手,抹掉玻璃上凝结的水汽,也抹掉了那个模糊的倒影。
该结束了。离开沈砚那栋冰冷的、像展览馆一样的山顶别墅,
我没要他一分钱所谓的“赡养费”。只带走了我结婚时带进来的一个小行李箱,
里面装着我自己的几件旧衣服,几本书,
还有一本厚厚的速写本——那是我在无数个他晚归或不归的夜晚,用来打发时间的东西。
画窗外一成不变的风景,画插在花瓶里枯萎的花,画我自己茫然的脸。沈砚的律师打来电话,
语气带着职业化的客气和不易察觉的轻视:“林女士,沈先生交代,
您名下的几张副卡已经停用。关于您放弃财产分割的部分,沈先生表示尊重您的选择,
但也提醒您慎重考虑未来的生活保障。如果您改变主意……”“谢谢,不需要。
”我打断他,声音平静,“麻烦转告沈先生,两清了。”挂了电话,世界彻底安静下来。
我在市区边缘租了个小小的单间公寓。四十平米,朝北,冬天会很冷。但胜在便宜,
而且窗户很大,能看到外面老旧的居民楼和一小片灰蒙蒙的天空。没有了衣帽间,
没有了菲佣,没有了司机。一切都得自己来。我找了份工作。
在市中心一家不大不小的广告公司,做美术助理。工资不高,活儿很杂,
从给设计师修图、排版,到帮客户买咖啡、取快递。同事大多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朝气蓬勃,
偶尔也会八卦。“林溪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看你气质好好,不像刚出来工作的。
”我笑笑,把刚修好的图发过去:“瞎混呗。”“林溪姐,你这包看着质感真不错,
什么牌子的?仿得好像啊!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个结婚时沈砚让人送来的、被我塞在行李箱角落吃灰好几年的包,
随口道:“地摊货,不值钱。”日子忙碌而充实。挤地铁,吃快餐,熬夜加班改方案。
被客户刁难,被上司训斥,和同事一起吐槽甲方是傻X。手指因为长时间握鼠标而酸痛,
眼睛盯着屏幕发干发涩。很累。但心里,却有种奇异的踏实感。这种累,
是双脚踩在地上的累。不像在沈家,那种累是悬在半空,无所依凭,时刻担心粉身碎骨的累。
我开始重新拿起画笔。不是画那些讨好沈砚的、模仿苏晚风格的所谓“艺术品”。
而是画我看到的,感受到的。画地铁里拥挤的人潮,画早餐摊升腾的热气,
画路边被风雨吹打却依然倔强生长的小野花。线条笨拙,色彩也未必好看,但我画得很开心。
那本厚厚的速写本,一页页被填满。时间像流水一样滑过去。半年。沈砚这个名字,
连同那五年虚幻的婚姻生活,渐渐被日复一日的忙碌冲刷得模糊,沉入了记忆的角落。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不会再有任何交集。直到那天。公司接了个大单子,
给本市即将举行的一场高规格慈善拍卖晚宴做宣传册设计和现场物料。
我被临时抽调去现场帮忙,负责核对拍品信息和展示。
晚宴设在市中心的六星级酒店顶楼宴会厅。水晶吊灯璀璨夺目,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空气里弥漫着高级香水和金钱的味道。我穿着公司统一发的黑色套裙,像个背景板一样,
穿梭在光鲜亮丽的人群边缘,仔细检查着展示台上的拍品标签。“女士们,先生们!
接下来这件拍品,非常特别!”拍卖师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全场,带着煽动性的热情。
灯光聚焦在展示台中央。天鹅绒托架上,静静躺着一条项链。铂金链子,
坠着一颗水滴形的、纯净无暇的蓝钻。灯光下,它折射出深海般幽邃而璀璨的光芒,
美得惊心动魄。我的呼吸猛地一窒。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拍品清单,指尖冰凉。
这条项链,我认得。太认得了。沈砚的书房,有一个带密码锁的抽屉。有一次我进去送咖啡,
他忘了锁。抽屉里没有文件,只有这条项链,静静地躺在黑色的丝绒盒子里,
旁边放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十七八岁的年纪,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裙,
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笑容干净得像雨后初晴的天空。她的脖子上,就戴着这条蓝钻项链。
苏晚。沈砚心口那颗永远鲜活的朱砂痣。他无数次醉酒后,喃喃念叨的名字。
我曾鬼使神差地,偷偷拿起那条项链看过。冰凉的触感,沉甸甸的。钻石的光芒,
刺得我眼睛生疼。那光芒里,映照出我苍白而嫉妒的脸,像个小丑。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沈砚十八岁那年,用自己赚到的第一桶金买的。他把它送给了苏晚,当作定情信物。
苏晚病逝后,这条项链就成了沈砚最重要的念想,从不离身。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出现在拍卖会上?“……这条‘深海之泪’,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慷慨捐赠,起拍价,
五百万!”拍卖师的声音激昂。全场响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和惊叹。我的目光下意识地,
越过攒动的人头,投向宴会厅深处,那个最尊贵的位置。沈砚果然在。
他靠坐在宽大的单人沙发里,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高定西装,衬得他身形愈发挺拔冷峻。
灯光在他深邃的轮廓上投下阴影,看不清表情。他手里端着一杯酒,姿态慵懒,
仿佛周围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但他微抿的唇角,和他握着酒杯、指节微微泛白的手,
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他在看那条项链。眼神专注得可怕,
像要把那点幽蓝的光芒吸进灵魂深处。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
钝痛蔓延开来。原来,再深的执念,再重的念想,也是可以拿出来拍卖的。只要价码足够高。
是为了什么呢?沈氏集团最近似乎在谈一个海外的大项目,需要大笔资金?
还是……他终于决定,要彻底放下过去了?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不再看他。拍卖开始了。
竞价声此起彼伏。“五百五十万!”“六百万!”“六百八十万!”价格一路攀升。
这种级别的珠宝,又是慈善拍卖,
加上“深海之泪”本身的故事性和神秘感(虽然捐赠者匿名,但圈子里谁不知道它的来历?
),引得不少富豪名流争相举牌。沈砚一直沉默着。他只是看着,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侧脸的线条绷得像刀锋。价格很快突破了一千万。竞价的人渐渐少了,只剩下两三位在胶着。
“一千两百万!这位先生出价一千两百万!还有更高的吗?”拍卖师的声音拔高,
充满期待。沈砚终于动了。他放下了酒杯,身体微微前倾,似乎要有所动作。
周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等着沈氏总裁出手。就在这时,一个清冷、平静的女声,
透过麦克风,清晰地响彻全场:“一千五百万。”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劈开了喧嚣。
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
齐刷刷地投向声音来源——那个最不起眼的、工作人员专用的区域。我站在那里,
手里拿着工作人员用的报价牌,面无表情。聚光灯追了过来,打在我身上。劣质的黑色套裙,
素面朝天的脸,在这满堂华彩中,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可笑。但我站得很直。
我能感觉到,那道来自宴会厅深处的、几乎要凝成实质的目光,死死地钉在我身上。
充满了震惊、难以置信,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翻涌的复杂情绪。
周围的窃窃私语像潮水般涌来。“她是谁?”“工作人员?疯了吧?”“一千五百万?
她拿得出来吗?”“开玩笑的吧?”拍卖师也懵了,迟疑地看着我:“这位……女士?
您确定?”“确定。”我的声音依旧平静,没有一丝波澜。目光越过人群,
精准地迎上沈砚那双深不见底、此刻却掀起了惊涛骇浪的眼睛。他的脸色,在璀璨的灯光下,
第一次变得有些苍白。他死死地盯着我,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我这个人。“一千五百万!
这位女士出价一千五百万!”拍卖师回过神,激动地喊道,“还有没有更高的?
”全场鸦雀无声。之前竞价的那几位,都摇了摇头,放弃了。一千五百万,
远超这条项链的实际价值。而且,没人想跟一个看起来像是疯了的工作人员较劲。
“一千五百万一次!一千五百万两次!一千五百万——三次!成交!恭喜这位女士!
”拍卖槌落下,发出清脆的声响。尘埃落定。聚光灯刺眼。周围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身上。
但我只觉得一片空茫。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不是因为紧张,
而是一种近乎宣泄的、带着痛感的快意。我放下报价牌,没有再看沈砚的方向,
转身走向后台的结算处。后台的走廊很安静,隔绝了前厅的喧嚣。
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由远及近,带着一种熟悉的、咄咄逼人的节奏。我停下脚步,
没有回头。“林溪!”沈砚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带着压抑的怒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你什么意思?”我慢慢转过身。
他站在几步开外,高大的身影挡住了走廊顶灯的光线,投下一片阴影。他的脸色很难看,
眼神锐利得像刀子,试图剖开我的意图。“沈先生。”我淡淡地开口,用了最疏离的称呼,
“恭喜您,拍品成功售出,为慈善事业添砖加瓦。”“少跟我装傻!”他几步跨到我面前,
距离近得我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雪松香水和浓重的酒气混合的味道。“你哪来的一千五百万?
你故意的是不是?你想干什么?”他的气息带着压迫感,一如从前。换做半年前,
我大概会害怕,会退缩。但现在,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因愤怒而显得更加深刻立体的五官。
“沈先生,”我微微勾起唇角,露出一丝没什么温度的笑意,“竞拍是公开公平的。
我有钱,想拍,就拍了。需要向您解释吗?”“你有钱?”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眼神里的嘲讽几乎要溢出来,“你离开沈家的时候,不是硬气地一分钱没拿吗?怎么,
这么快就找到新的金主了?这一千五百万,是你卖身赚的?”他的话,像淬了毒的冰渣,
狠狠扎过来。心脏还是不受控制地抽痛了一下。我看着他,
看着他眼中毫不掩饰的轻蔑和愤怒。原来在他心里,我始终是这样一个不堪的人。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喉咙口的腥甜,反而笑了出来,笑声清脆,
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有些突兀。“沈砚,”我直呼他的名字,不再用敬称,“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永远都这么**,这么不择手段?”他似乎被我的反应和称呼弄得怔了一下,
眉头拧得更紧。“这条项链,”我抬手指了指后台结算处的方向,
那里正安静地躺着那个装着“深海之泪”的丝绒盒子,“对你很重要,对吧?苏晚的遗物。
你心尖上的宝贝。”提到“苏晚”两个字,沈砚的瞳孔猛地一缩,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
甚至带上了一丝被冒犯的戾气:“闭嘴!你不配提她的名字!”“我不配?”我笑着,
眼泪却不受控制地在眼眶里打转,但我用力眨了回去,“是啊,我是不配。一个赝品,
一个替身,怎么配提白月光的名字呢?”我往前逼近一步,仰头看着他,一字一句,
清晰地说道:“可是沈砚,你听好了。我拍下它,不是为了恶心你,
也不是为了什么狗屁金主。”我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一种近乎凄厉的决绝:“我是要把它买回来!然后当着你的面,砸了它!
”沈砚彻底僵住了。他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错愕和难以置信。
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曾经那个在他面前温顺得像只绵羊、只会模仿苏晚的林溪,
会说出这样的话。“你…你疯了!”他几乎是咬牙切齿。“我疯了?”我笑着,
眼泪终于还是滑了下来,滚烫地划过脸颊,“我是疯了!被你,被这五年,
被这条该死的项链逼疯的!”我抬手,狠狠抹掉眼泪,眼神变得冰冷而锐利。“沈砚,
你永远记得苏晚的好。记得她干净,记得她善良,记得她是你的白月光。可她死了!
她死了很多年了!而我呢?”我指着自己的心口。“这五年,守在你身边的人是我!
给你熨烫衬衫、泡八十度水温的茶、弹你喜欢的曲子的人是我!你胃疼得半夜睡不着,
爬起来给你煮醒酒汤、找胃药的人是我!你妈生病住院,在病床前端屎端尿伺候的人也是我!
”我的声音哽咽,却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可**眼里有过我吗?
你记得苏晚喜欢什么花,记得她弹什么曲子,你记得她的一切!那你记得我对芒果过敏吗?
记得我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吗?记得我生日是哪天吗?”沈砚被我连珠炮般的质问钉在原地,
脸上的愤怒被一种猝不及防的茫然和震惊取代。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
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那双总是深不可测、掌控一切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清晰的裂痕,
甚至……一丝狼狈?“你不知道!**根本不在乎!”我替他说了答案,声音嘶哑,
“因为在你心里,我林溪就是个工具!一个用来填补苏晚空缺的工具!
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意儿!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醒你失去了什么!我的付出,
我的感情,在你看来,是不是特别廉价?特别可笑?”我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
积压了五年的委屈、不甘、愤怒、绝望,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那些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卑微爱意,此刻变成了最伤人的利刃,不仅刺向他,也凌迟着我自己。
“现在好了。”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颤抖的声音,眼神空洞地看着他身后冰冷的墙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