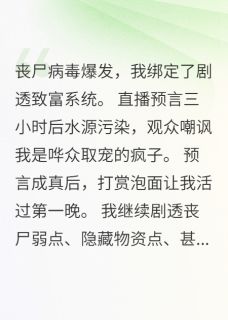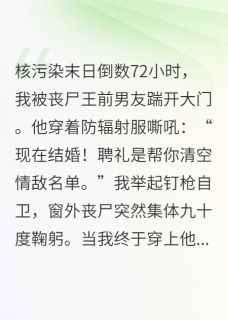
核污染末日倒数72小时,我被丧尸王前男友踹开大门。他穿着防辐射服嘶吼:“现在结婚!
聘礼是帮你清空情敌名单。”我举起钉枪自卫,窗外丧尸突然集体九十度鞠躬。
当我终于穿上他准备的婚纱,防辐射服内却传来腐肉滴落声。他嘶哑道:“当年分手后,
我把自己改造成了最强兵器。”“如今全世界都是丧尸,只有你穿着婚纱最安全。
”钉枪抵住他心脏时,我摸到防辐射服里藏着的旧照片——竟是我们热恋时,
我随口抱怨“情敌太多”的醉酒涂鸦。--------------铅灰色的雪,
落得无声无息,像天地间撒开一张巨大而肮脏的裹尸布。
它们粘在落地窗积满厚厚尘埃的玻璃上,很快又融化,留下道道浑浊的泪痕。窗内,
曾是无数少女梦想绽放的殿堂——“瓷光”婚纱店。如今,水晶吊灯蒙尘,光芒尽失,
散落在地的昂贵蕾丝和缎面婚纱,被踩踏得污秽不堪,与翻倒的展示架、碎裂的镜片一同,
在昏暗中勾勒出末日来临前疯狂的掠影。空气里,漂浮着尘埃、铁锈,
还有一丝若有似无、令人喉头发紧的甜腥。那是外面世界正在加速腐烂的味道。
防辐射警报器那象征性的、微弱的红灯早已熄灭,如同这座城市最后咽下的那口气。
林瓷坐在唯一还算干净的角落,一盏应急灯惨白的光线切割着她的侧影。她低着头,
手中针线在一种特殊的银灰色厚实面料上快速而稳定地穿梭。这不是寻常的婚纱料子,
而是她搜刮来的、内嵌铅纤维的防辐射布。针尖每一次刺入、拉出,
都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专注。她将一块裁剪好的铅衬仔细缝进一件残破主婚纱的胸衣内侧,
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冰冷的金属针不时擦过指腹,留下细微的红痕,她恍若未觉。
时间,是悬在头顶的铡刀。墙上的电子日历,
猩红的数字触目惊心:**倒计时71:59:23**。三天。仅仅剩下三天,
大气层外那场毁灭性的核爆所产生的致命尘埃云,将彻底吞噬这座孤岛般的城市。
留给生者的时间,正在以秒为单位,冷酷地流逝。而比尘埃更早抵达的,
是那些游荡在死寂街巷中的“东西”——辐射催化下,由人类异变而来的行尸走肉。窗外,
铅灰色的雪幕中,一个扭曲的身影骤然扑向玻璃!
一张高度腐烂、眼珠浑浊脱落的脸猛地贴上冰冷的玻璃,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它张大着只剩下残破牙龈和几颗黑黄牙齿的嘴,无声地开合,
粘稠的暗红液体顺着玻璃缓缓流下,拉出长长的、令人作呕的痕迹。林瓷的手猛地一抖,
针尖狠狠扎进食指,一滴殷红的血珠迅速渗出,滴落在银灰色的铅衬上,晕开一小片暗渍。
她倒吸一口冷气,不是因为疼痛,而是那突如其来的、毫无生气的凝视带来的冰冷战栗。
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擂动,撞击着肋骨。她强迫自己移开视线,
不去看那张紧贴着玻璃、徒劳啃咬的腐烂面孔。目光落在不远处工作台上。那里,
一把沉甸甸的工业气动钉枪安静地躺着,冰冷的金属外壳在应急灯下泛着幽光。
旁边散落着几枚粗长、闪着寒芒的钢钉。她伸出手,指尖触碰到钉枪坚硬冰凉的握把,
那金属的寒意顺着指尖蔓延,奇异地压下了心头翻涌的恐慌,带来一丝虚妄的掌控感。
她握紧了它,像握住溺水时唯一的浮木。就在这时——“砰!!!
”一声狂暴到足以撕裂死寂的巨响,毫无征兆地炸开!
婚纱店那扇厚重、镶嵌着繁复雕花玻璃的橡木大门,如同被攻城锤正面击中,整个向内爆裂!
碎木屑、玻璃碴如同霰弹般喷射进来,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危险的光。
狂风裹挟着外面更加刺鼻的腐臭和放射性尘埃的金属腥气,瞬间灌满了整个空间,
吹得地上散落的婚纱碎片疯狂飞舞,如同无数垂死挣扎的白蝶。
一个高大、魁梧到充满压迫感的身影,堵在了那破碎的门洞中央,逆着门外灰败的光线,
宛如一尊从地狱熔炉中直接踏出的魔神。他穿着一身厚重的、科技感十足的全覆式防辐射服。
深灰色的复合装甲外壳覆盖全身,关节处是蜂窝状的防护结构,
头盔面罩是深色的单向可视玻璃,完全遮蔽了面容,
只留下两道幽深的、吞噬一切光线的黑暗。
这套装备将他与这个污秽、充满死亡气息的世界彻底隔绝,冰冷、坚硬、非人。
防辐射服的外壳上,沾满了黏腻的、已经发黑干涸的血污,
还有几处明显的、像是被野兽利爪撕扯过的深痕,无声地诉说着穿越尸海而来的凶险。
林瓷的呼吸瞬间停滞。巨大的惊骇如同冰水当头浇下,四肢百骸刹那间僵硬冰冷。
钉枪被她条件反射般死死攥住,沉重的枪体硌得掌心生疼,却无法给她带来丝毫安全感。
她认得这身形!即使包裹在如此狰狞的装甲之下,那刻入骨髓的轮廓,依旧如同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她的记忆深处。陆灼。这个她曾交付全部真心,
最终却伤痕累累、用尽全力才挣脱的名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在这个连魔鬼都会却步的末日边缘?他怎么可能……穿越外面那活生生的地狱?
不等她脑中混乱的思绪成形,堵在门口的“钢铁堡垒”动了。
他沉重的、包裹着金属防护靴的脚,重重踏过满地的碎玻璃和木屑,
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嚓”声,一步步向她逼近。每一步落下,
都像踩在林瓷紧绷欲断的心弦上。
他无视了角落里那只刚刚还在撞窗、此刻却瑟缩着后退的丧尸,
也仿佛完全看不见林瓷手中那对准他心脏部位、微微颤抖的钉枪枪口。
防辐射服内置的扬声器发出一阵刺耳的电流杂音,紧接着,一个极度扭曲、沙哑,
像是破损的砂轮在生锈铁皮上反复摩擦的声音,穿透头盔的阻隔,
带着一种非人的机械感和压抑不住的疯狂,狠狠砸在林瓷的耳膜上:“林瓷!……现在!
……立刻!……跟我结婚!”每一个字都像生锈的刀片在刮擦神经。林瓷瞳孔骤缩,
钉枪握得更紧,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荒谬绝伦的要求!在这炼狱般的末日,
前男友穿着染血的装甲破门而入,只为逼婚?“你疯了!
”她的声音因为极度的震惊和恐惧而拔高,尖锐得刺耳,“滚出去!陆灼!
你立刻给我滚出去!
”钉枪黑洞洞的枪口死死锁定他防辐射服心脏位置那块看起来相对薄弱的复合板,
她纤细的手指已然扣上了冰冷的扳机,指节因为用力而绷紧、颤抖。
就在这千钧一发、空气凝固如铁的时刻,异变陡生!门外,
那影影绰绰、如同鬼魅般在灰雪中游荡的数十个腐烂身影,动作骤然僵住!下一秒,
在令人头皮炸裂的寂静中,它们齐刷刷地、用一种近乎折断脊椎的诡异角度,
朝着门内林瓷所在的方向——九十度鞠躬!
几十颗腐烂程度不一、有的甚至露出森白头骨的头颅,深深低下。
粘稠的尸液和脱落的腐肉块,随着它们鞠躬的动作,
“啪嗒”、“啪嗒”地滴落在肮脏的雪地上。这并非敬意,
更像是一种源自灵魂本能的、对更高阶存在的绝对臣服!
一种无声的、却比任何嘶吼都更令人胆寒的宣告!林瓷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冻结了。
她握着钉枪的手臂僵硬得如同石雕,一股源自骨髓深处的寒意顺着脊椎急速攀升。
她难以置信地转动眼珠,目光扫过门外那片诡异剧躬的尸群,
再猛地盯回眼前这个散发着冰冷金属气息和血腥味的“钢铁怪物”。
一个荒谬绝伦、却又在眼前这恐怖景象下显得无比真实的念头,
如同毒蛇般噬咬着她的理智——陆灼…他…是什么?!防辐射服内置的扬声器再次响起,
那嘶哑破碎的声音似乎因为尸群的臣服而带上了一丝扭曲的满足感,
如同电流里混杂着腐肉的摩擦声:“聘礼……”声音顿了顿,像是在努力控制那非人的声带,
“……帮你……清空…情敌名单!”“名单”两个字,被他说得格外用力,
带着一种咬牙切齿、又混杂着病态亢奋的意味。
---林瓷感觉自己像是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钉在原地动弹不得。窗外,
那片僵硬鞠躬的尸群如同一幅恐怖定格画,无声地宣告着眼前这个男人——或者说,
这个存在的——绝对掌控力。陆灼?丧尸王?这两个词在她混乱的脑中激烈碰撞,
荒谬感几乎要将她淹没,然而门外那几十个俯首帖耳的腐烂身影,又是铁一般冰冷的事实。
“情敌…名单?”她艰难地重复,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
钉枪依旧死死抵在陆灼防辐射服心脏的位置,冰冷的金属外壳硌得她掌心生疼,
这成了她此刻唯一能抓住的、对抗无边恐惧的浮木。那名单是什么?
他口中的“清空”又意味着什么?一个可怕的联想让她胃部剧烈翻滚。
陆灼那覆盖着深色面罩的头盔微微转动,似乎是在“看”着她。
扬声器里传出沉重的、如同破旧风箱般的呼吸声,带着电流的嗡鸣。他没有再言语,
只是抬起一只被厚重金属手套包裹的手,
指向工作台旁边那面巨大的、镶嵌着华丽鎏金框的落地镜——镜面早已布满蛛网般的裂痕,
映照出无数个扭曲破碎、惊慌失措的林瓷。“穿…上。”嘶哑的命令再次响起,不容置疑。
他指的是林瓷脚边那个被踢倒的展示架旁,唯一一件还算完整、静静躺在尘埃里的主婚纱。
象牙白的缎面,精致的蕾丝,巨大的裙摆……一件本该承载着无暇梦想的圣洁之物,
此刻躺在末日狼藉的地板上,显得如此讽刺而诡异。巨大的荒谬感和冰冷的恐惧交织在一起,
几乎要将林瓷撕裂。她猛地吸了一口气,像是溺水者最后的挣扎,
钉枪的枪口用力往前顶了顶,几乎要嵌入那冰冷的复合装甲:“陆灼!你到底想干什么?!
外面那些……那些东西……是你搞出来的?你变成了什么怪物?!”“怪物?
”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陡然拔高,电流的杂音尖锐得刺耳,带着一种被戳中痛处的狂暴,
“你……当年……甩掉我的时候……想过今天吗?!”他的情绪如同被点燃的**桶。
包裹着金属的手臂猛地抬起,并非攻击林瓷,
而是狂暴地横扫向旁边一个半人高的、摆满水晶装饰品的展示台!“轰隆——哗啦!
”展示台被巨力掀飞,狠狠撞在墙壁上,瞬间解体!无数晶莹剔透的水晶天鹅、铃兰、玫瑰,
如同冰雹般爆裂开来,碎片激射,在昏暗中折射出短暂而凄厉的流光。
巨大的声响在死寂的空间里回荡,震得林瓷耳膜嗡嗡作响,心脏几乎跳出喉咙。“穿上它!
”陆灼的声音透过扬声器咆哮,伴随着沉重的、如同濒死野兽般的喘息,“现在!
……除非……你想亲自……看看……名单上……下一个名字……是谁!”“名单”两个字,
如同淬了毒的冰锥,狠狠刺入林瓷的神经。她猛地想起大学时代,
那个喝醉的、失恋后崩溃的夜晚。她哭着向闺蜜徐薇抱怨,
细数着陆灼身边那些若有若无的“情敌”——学生会温婉的学姐赵明宇,
总找他讨论课题;同系家境优渥、明艳张扬的徐薇,
毫不掩饰对他的兴趣;甚至还有那个儒雅成熟、对他颇为赏识的导师陈教授……那些名字,
被她带着醉意和怨气,
…难道……那张早已被酒精和泪水模糊的、她自己都不记得扔到哪里的纸……被陆灼找到了?
而且……他所谓的“清空”……一个可怕的画面瞬间攫住了她:赵明宇温婉的脸庞,
徐薇张扬的笑容,
被外面那些游荡的、流着涎水的腐烂身影撕碎、吞噬……彻骨的寒意瞬间冻结了林瓷的血液。
她握着钉枪的手,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失去了血色,剧烈地颤抖起来。枪口依旧对着陆灼,
却失去了之前的决绝。她毫不怀疑,如果她再拒绝,门外那些鞠躬的怪物,
下一秒就会扑进来,或者……扑向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时间,在令人窒息的死寂中流逝。
窗外铅灰色的雪,无声地覆盖着这个绝望的世界。倒计时猩红的数字,
在墙上无声地跳动着:**71:02:18**。终于,林瓷紧绷的肩膀,
极其缓慢地、如同承受着千钧重压般,垮塌了一丝。抵着陆灼心脏的钉枪枪口,
一点点、极其艰难地垂落下来。金属枪管划过防辐射服坚硬的装甲外壳,
发出轻微却刺耳的“滋啦”声。她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再看陆灼那深不可测的面罩一眼。
她的目光,空洞地、如同被抽走了灵魂般,落在了地上那件纯白的婚纱上。
象牙白的缎面在应急灯惨白的光线下,泛着一种冰冷的、非人间的光泽。
她缓缓地、一步一步地退后,身体僵硬得像一具提线木偶。
每一步都踩在碎玻璃和水晶残骸上,发出细碎的、令人心悸的破裂声。她退到那件婚纱旁,
蹲下身,手指触碰到冰凉光滑的缎面,那触感让她猛地一颤,仿佛摸到了毒蛇的鳞片。
陆灼如同一座沉默的钢铁堡垒,堵在唯一的出口,深色的面罩纹丝不动,
只有扬声器里传出沉重而持续的、如同破旧鼓风机般的呼吸声,监控着她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林瓷背对着陆灼,动作僵硬地解开自己身上那件沾满灰尘和汗渍的旧外套。
冰冷的空气瞬间贴上**的肌肤,激起一层细小的战栗。她深吸一口气,
后那道如同实质般钉在她背脊上的、充满压迫感的“目光”——即使隔着厚厚的防辐射头盔,
她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目光中的灼热与疯狂。她弯腰,
拾起地上那件沉重的、缀满繁复蕾丝和珠绣的象牙白主纱。缎面冰凉,触感陌生而奢华,
与她此刻灰头土脸、满心恐惧的境地格格不入。
巨大的裙摆拖曳在布满玻璃碎屑和水晶残渣的地板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每一步移动都异常艰难。婚纱的束腰设计极为苛刻,她摸索着背后的绑带,
手指因为冰冷和紧张而不听使唤,好几次都未能准确地勾住细小的绳扣。
时间在死寂中缓慢爬行。倒计时冰冷的数字在墙上无声跳动:**69:48:05**。
身后,那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似乎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
金属靴底摩擦地面的声音响起,陆灼向前踏了一步,沉重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店里回荡。
林瓷的身体瞬间绷紧,如同受惊的鹿。她咬紧下唇,用尽全身力气与那繁复的绳扣搏斗。
终于,指尖勾住了!
她猛地用力一拉——“滋啦…唔…”一声极其细微、却异常清晰的粘稠液体滴落声,
毫无征兆地从身后传来!
伴随着一声仿佛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压抑不住的、非人的痛苦闷哼!
林瓷拉紧绑带的动作猛地僵住!一股难以言喻的、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腐肉腥臭,
毫无预兆地、如同爆炸般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这气味瞬间盖过了尘埃和铁锈味,
浓烈得几乎实质化,直冲她的鼻腔和大脑!她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倒流,
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这不是外面丧尸的味道!这源头……就在身后!近在咫尺!
她如同生锈的机器,一寸寸地、极其缓慢地转过身。陆灼依旧站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
像一座沉默的钢铁雕塑。然而,
接缝处——大概是膝盖弯曲的位置——一小滩粘稠、暗红发黑、混杂着黄色脓液的污秽液体,
正缓缓地渗透出来,无声地滴落在他脚边的尘埃里,形成一小片触目惊心的污渍。
“滴答……”又一滴落下,声音在死寂中清晰得如同丧钟。林瓷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
胃里翻江倒海,她死死捂住嘴,才抑制住那几乎冲破喉咙的尖叫和呕吐的欲望。
那气味……那液体……她太熟悉了!就在昨天,
她还用钉枪击碎了一个试图从后窗爬进来的丧尸的头颅,同样的恶臭,同样的污秽!
他不是穿着防辐射服!他……他的身体……巨大的恐惧如同冰冷的巨手攥紧了她的心脏,
几乎让她窒息。她踉跄着后退一步,巨大的婚纱裙摆绊了她一下,让她险些摔倒。
她惊恐的目光死死盯住那不断渗出污血的装甲缝隙,又猛地抬起来,
死死盯住陆灼那深不可测的头盔面罩。扬声器里沉默了几秒,只剩下那沉重而痛苦的喘息,
接着,那个极度扭曲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腐烂的声带里硬生生撕扯出来,
带着电流的嘶鸣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平静:“呵…看到了?”声音停顿,喘息声更重,
年…你走……之后……”“我……把自己……改造了……”每一个词都伴随着艰难的喘息,
如同破旧风箱在拉扯,
废料……病毒……”“痛……像……被……活剥……”声音里压抑着巨大的、非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