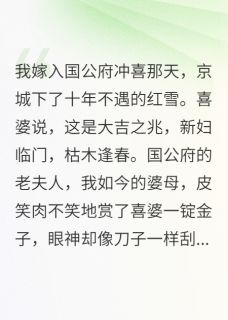喉咙里烧着一团滚烫的烙铁,每一次徒劳的吞咽都像在吞下烧红的刀片。
视野里精心打磨的大理石天花板扭曲旋转,最终沉入一片粘稠、冰冷的黑暗。
意识消散前最后一点知觉,是林晚意那刻意拔高的、带着虚伪甜腻的声音,穿透死寂的空气,
钻进我剧痛的耳膜:“姐,这下好了!沈家那个碍事的真少爷终于……彻底消失了!
”她尾音上扬,每一个字都淬着剧毒,“往后啊,沈家那泼天的富贵,
可都是咱们姐妹俩的了!”那声音里的贪婪和得意,像一把冰锥,
狠狠凿穿我最后残存的一点意识。……意识猛地被拽回躯壳,像溺水的人被粗暴地扯出水面。
“咳!咳咳咳——!”我剧烈地呛咳起来,肺叶火烧火燎,
每一次吸气都带着廉价出租屋特有的、霉菌和灰尘混合的腐朽气味。不是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更不是沈家别墅里那种常年弥漫的、昂贵的木质熏香。我猛地睁开眼。
视线撞上一片斑驳、泛黄的天花板,角落里挂着几缕蛛网,
在窗外透进来的惨淡天光里轻轻晃动。身下是硬邦邦的木板床,硌得骨头生疼。
空气闷热粘稠,几乎凝滞不动。这里是……城西老区。十年前,我流落街头、食不果腹时,
用仅剩的几个硬币租下的那个连老鼠都嫌弃的鸽子笼。
不是沈家那间铺着昂贵羊绒地毯、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璀璨夜景的卧室。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撞碎肋骨。我挣扎着坐起身,动作牵扯着酸痛的肌肉,
骨头缝里都透着一种陌生的年轻感,却也带着长期营养不良的虚弱。我下意识地抬手,
摸向自己的喉咙——那里光滑一片,没有灼烧,没有溃烂,只有汗水的黏腻。
真的……回来了?床头柜上,一部屏幕碎裂、外壳磨损严重的旧手机突兀地震动起来,
嗡嗡作响,像一只垂死挣扎的虫子。屏幕亮起幽蓝的光,照亮了屏幕上方的日期。
XXXX年X月X日。这个日期,像一道雪亮的闪电劈开混沌的记忆!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下午!前世模糊的记忆碎片瞬间清晰、尖锐——那个风雨交加的傍晚,
沈家真正的掌上明珠,我那鸠占鹊巢的“好堂妹”林晚意,就是用她那双看似柔弱无骨的手,
撬开了沈家老宅重重守卫下、存放家族珠宝秘库的保险柜!
她偷走了沈家世代相传、象征继承人身份的那条“绿焰之心”祖母绿项链!
央镶嵌着一颗重达三十克拉、纯净如森林深潭、火彩璀璨夺目的顶级哥伦比亚木佐绿祖母绿!
而她的目标,就是今晚!周氏集团掌门人周慕白为他母亲举办的七十寿宴!
林晚意要踩着沈家的传家宝,把自己送到周慕白面前,
攀上那根足以让她彻底洗白身份、一步登天的黄金枝!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鼓噪,
血液奔涌着冲上头顶,带着前世被毒杀的剧痛和滔天的恨意。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带来尖锐的刺痛,却远不及记忆里那杯毒酒带来的万分之一。机会!
这简直是命运亲手递到我面前的复仇之刃!我猛地掀开身上那条散发着霉味的薄毯,
赤脚踩在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目光急切地扫过这间逼仄、家徒四壁的陋室。唯一的桌面上,
宝石学基础》、《常见宝石鉴定图谱》、《珠宝鉴赏入门》……旁边放着一个简陋的工具盒,
里面躺着几件最基础的鉴定工具:一个边缘磨损的十倍放大镜,一个棱角有些磕碰的折射仪,
一把细小的镊子,还有一支笔尖磨秃了的记号笔。前世作为沈家继承人,
那些刻在骨子里的珠宝知识,
那些被顶尖鉴定大师亲手**过的眼力……此刻如同沉睡的火山,在恨意的催化下轰然苏醒,
滚烫的熔岩在血脉里奔流。林晚意,你偷走的,我会让你百倍、千倍地吐出来!
连同你那张伪善的画皮,一起撕得粉碎!
***“绿焰之心”……它此刻应该正被林晚意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
成为她敲开周家金玉大门的敲门砖。而我的机会,
今晚的寿宴——那个汇聚了全城顶尖名流、安保森严得连只苍蝇都难以混入的周家半山庄园。
前世模糊的记忆里,寿宴前夕,周家似乎为了一件临时出状况的重要展品,
急需一位可靠的珠宝鉴定师坐镇……一个念头如同电光火石,瞬间照亮了幽暗的前路。
我几乎是扑到那张破旧的书桌前,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快速翻开那本《珠宝鉴赏入门》。书页哗哗作响,最终停在某一页的空白处。那里,
潦草地写着一个电话号码,旁边标注着一个小小的名字:陈伯。陈伯!
周慕白身边那位沉默寡言、却深得信任的老管家!前世一次偶然的行业交流会上,
我曾无意中帮过他一个小忙,解决了他随身佩戴的一枚老怀表真伪的疑惑。彼时身份悬殊,
我并未在意,只记得他离去时眼中一闪而过的赞赏,
以及他留下这个私人号码时的低语:“年轻人,眼力不错。若以后……有难处,
可以打这个电话试试,但未必有用。”那声音低沉,带着周家特有的疏离感。
当时只道是寻常客套,谁会想到,这竟成了我此刻唯一的救命稻草!我抓起那部破旧的手机,
冰冷的塑料外壳硌着掌心。屏幕碎裂的纹路在昏暗的光线下狰狞地蔓延。深吸一口气,
指尖带着孤注一掷的力道,重重地按下那串早已烙印在记忆深处的数字。
听筒里传来漫长而单调的“嘟——嘟——”声,每一声都像重锤敲在紧绷的神经上。
汗水无声地从额角滑落,滴在布满灰尘的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出租屋里的霉味似乎更浓重了,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就在那根名为希望的弦即将崩断的刹那——“嘟”声戛然而止。一个沉稳、略带苍老,
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急促的声音传了出来:“哪位?”“陈伯,”我立刻开口,
声音因为紧张和刻意压低而显得有些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力求清晰,“冒昧打扰。我是小沈,
之前在博览会上,曾有幸为您看过那枚维多利亚时期的珐琅怀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似乎在记忆中搜寻。这短暂的死寂几乎让我窒息。“哦……是你。
”陈伯的声音里终于透出一丝恍然,但那份沉重和急促并未散去,“我记得。有什么事吗?
”他的语气简洁直接,带着周家惯有的高效和一丝被打扰的不耐。
“我听说周先生府上今晚寿宴,临时需要一位珠宝鉴定师?”我语速加快,
心脏几乎要跳出喉咙,“我在城西‘石缘斋’,主做鉴定。虽然地方小,
但眼力……自认还行。尤其对祖母绿,有些心得。”我刻意加重了“祖母绿”三个字,
像一枚精准的鱼饵投入深潭。电话那头再次陷入沉默。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
长到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血液奔流的声音和窗外远处模糊的车鸣。出租屋里死寂一片,
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终于,陈伯的声音再次响起,那丝急促似乎更明显了,
甚至带上了一点焦灼:“……城西石缘斋?沈……?”他似乎不确定我的名字。“沈砚。
砚台的砚。”我立刻接上。“……好,沈砚。”陈伯像是下了某种决断,语速快了起来,
“你现在立刻到半山庄园西侧门岗。报我的名字。动作要快!寿宴开场在即,宾客快到了!
”“是!我马上到!”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巨大的狂喜和紧迫感瞬间攫住了我。
电话**脆利落地挂断,忙音嘟嘟作响。我猛地扔下手机,
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冲向墙角那个落满灰尘的旧帆布包。
粗暴地将桌上那几件简陋的鉴定工具——放大镜、折射仪、镊子——一股脑扫进包里,
拉链几乎被扯坏。冲出那间散发着霉味的鸽子笼,
陈旧狭窄的楼道里回荡着我急促沉重的脚步声。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照在破败的街道上,
空气中漂浮着灰尘和路边摊廉价食物的气味。我冲到街边,不顾一切地挥手拦车。
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带着刺耳的刹车声停下。“师傅!半山庄园!西侧门!用最快的速度!
钱不是问题!”我拉开车门钻进去,声音嘶哑地吼道。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我苍白冒汗的脸和洗得发白的旧衬衫,
大概把我当成了去赶着伺候有钱人的穷小子,嘟囔了一句:“坐稳喽!”猛地一脚油门,
破旧的引擎发出不堪重负的嘶吼,车子像离弦之箭般蹿了出去,汇入车流,
朝着那座矗立在城市顶端、象征着无上财富与权力的半山庄园疾驰而去。
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模糊成一片流动的色块。我死死攥着那个破旧的帆布包,
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包里那几件简陋的工具,此刻仿佛重若千钧,是我复仇唯一的武器。
林晚意,周慕白……游戏,开始了。***半山庄园的西侧门岗,与其说是门,
不如说是一座森严的微型堡垒。巨大的黑色雕花铁门紧闭,
门后是郁郁葱葱、修剪得一丝不苟的园林,透出深宅大院的幽深与不可侵犯。
门岗前站着两名身形高大、穿着剪裁精良黑色制服、戴着耳麦的安保人员,眼神锐利如鹰隼,
扫视着每一个靠近的生物。我那辆一路嘶吼、散发着廉价汽油味的破旧出租车,
在距离门岗还有十几米远的地方,就被一名保镖抬手示意,硬生生逼停在路边。
司机紧张地咽了口唾沫,不敢再往前开一寸。“干什么的?
”其中一名保镖大步流星地走过来,声音冷硬,带着不容置疑的审视。
他锐利的目光像探照灯,上上下下地扫视着我,从我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廉价的帆布鞋,
一直落在我肩上那个磨损严重的帆布包上,眉头紧紧蹙起。那眼神里,
毫不掩饰地写着: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想混进去攀高枝的。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
带着无形的压力。我甚至能感觉到身后出租车司机投来的、混杂着同情和看好戏的目光。
“是陈伯让我来的。”我强迫自己挺直脊背,迎上保镖审视的目光,尽量让声音平稳清晰,
“我叫沈砚,珠宝鉴定师。陈伯说,让我到西侧门岗报他的名字。”“陈伯?
”保镖的眉头蹙得更紧,眼神里的怀疑几乎要溢出来。
他对着衣领下的微型对讲机低语了几句。对讲机那头传来的声音模糊不清,
只能看到保镖严肃地听着,目光依旧牢牢锁定在我身上,像钉子一样。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每一秒都像被拉长成一个世纪。周家花园深处隐约传来悠扬的弦乐声和模糊的人语喧哗,
寿宴显然已经开始预热。那声音像一根细线,紧紧勒着我的神经。
就在保镖似乎快要失去耐心,准备挥手驱赶我的前一秒,他耳麦里终于传来了清晰的指示。
他紧绷的神色略微松动,但审视的目光依旧锐利如刀。“跟我来。”他简短地命令,
转身推开旁边一扇仅供一人通过的、毫不起眼的小铁门。门轴发出轻微的嘎吱声。
我立刻跟上,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穿过那道窄门,仿佛从一个世界踏入了另一个世界。
脚下是柔软如毯的进口草皮,修剪得一丝不苟,空气中弥漫着名贵花草的馥郁芬芳,
混合着远处传来的食物香气和高级香水的味道。精心设计过的园林景观移步换景,
巨大的水晶吊灯的光芒从远处主宅的落地窗倾泻而出,将夜色点缀得如同梦幻之境。
保镖沉默地领着我,避开了灯火通明的主路,沿着一条相对僻静的卵石小径快速穿行。
小径两侧是高大的观赏灌木,修剪成各种优雅的几何形状。
前方隐约可见一座灯火辉煌的巨大玻璃花房,里面人影幢幢,衣香鬓影,
悠扬的现场演奏钢琴声如同流淌的蜜糖,正是晚宴的核心场地——琉璃厅。
就在即将靠近花房侧门入口时,保镖的脚步突然顿住。他侧身让开一步,
对着耳麦低声确认:“人已带到。”几乎同时,
穿着深灰色三件套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面容严肃刻板的老者从花房侧门内快步走出。
正是陈伯!他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疲惫和焦虑,额角甚至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与平时那副沉稳持重的形象判若两人。他锐利的目光瞬间落在我身上,
飞快地上下扫视了一遍,重点在我肩上那个破旧的帆布包上停留了一瞬,
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沈砚?”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急促。“陈伯。”我点头,
尽量让自己的眼神显得平静而专业。“时间紧迫,跟我来!”陈伯没有任何寒暄,语速极快,
“晚宴马上正式开场,有件重要的祖母绿展品出了点状况,需要立刻确认。记住,多看,
少说,眼神要准!”他最后一句几乎是咬着牙叮嘱的,带着强烈的警告意味。
他转身推开花房侧门。一股混杂着花香、酒香、食物香气和高级香水味的暖风扑面而来,
伴随着骤然放大的优雅乐声和人声低语。璀璨的水晶灯光芒几乎让人目眩。陈伯领着我,
几乎是贴着墙边、阴影处快速移动。他刻意避开了人群中心,
像一个幽灵穿梭在华服美饰的宾客之间。那些穿着高定礼服、佩戴着耀眼珠宝的名媛贵妇,
端着香槟低声谈笑的商界巨贾,仿佛构成了一幅流动的浮世绘,而我,
一个穿着格格不入旧衣、背着廉价帆布包的闯入者,是这幅画上最刺眼的污点。
无数道或好奇、或疑惑、或毫不掩饰鄙夷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陈伯对此视若无睹,
他的目标明确——花房深处一个相对安静、被几株巨大热带植物巧妙隔开的小型休息区。
那里摆放着几组丝绒沙发,中央是一张铺着雪白桌布、摆放着精致点心和香槟塔的长桌。
而此刻,所有人的目光焦点,
都汇聚在休息区中央那个穿着缀满碎钻的象牙白曳地长裙、如同月光女神般耀眼的女人身上。
林晚意!她微微扬着天鹅般优雅的脖颈,
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混合着矜持与一丝不易察觉的讨好笑容,
正对着沙发上一位穿着深蓝色丝绒礼服、气度威严沉凝的中年男子说话。那男子面容冷峻,
眼神深邃,正是今晚的绝对主角——周氏集团的掌舵人,周慕白。林晚意白皙修长的手指,
此刻正轻轻托着一样东西。那东西在她掌心,在琉璃厅无数水晶灯折射的璀璨光芒下,
正焕发出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绿色光芒!深浓,纯净,
仿佛将最深邃的森林湖泊和最炽烈的火焰同时封存在了晶体之中。那是一种具有魔力的绿,
瞬间攫住了所有人的目光。项链的铂金链条纤细而坚韧,设计繁复古典,
每一处转折都诉说着岁月的沉淀和匠心的极致。而项链坠子的核心,
正是一颗硕大无朋、切割完美、火彩四射的祖母绿主石!绿焰之心!
沈家传承了四代、象征着无上权力与尊荣的传家宝!此刻,正被林晚意,
这个窃取了我身份、最终将我毒杀的凶手,当作她攀附权贵的垫脚石,
小心翼翼地奉到周慕白的面前!一股冰冷刺骨的恨意瞬间从脚底直冲头顶,
几乎要冲破理智的堤坝。我死死攥紧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用那尖锐的疼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能冲动!沈砚,冷静!机会只有一次!陈伯带着我,
悄无声息地绕到休息区侧后方一个不起眼的阴影角落里,
靠近摆放着备用餐具和酒水的服务台。
他快速而低声地对旁边一位穿着侍者服、同样神情紧张的中年男人吩咐了几句。
那男人立刻将一个打开的黑丝绒首饰盒推到我的面前。盒子里躺着一枚胸针,
主石也是一颗祖母绿,但无论颜色、净度还是火彩,都远逊于林晚意手中的那条项链。
更糟糕的是,胸针的铂金镶爪似乎有些松动,
宝石边缘有一道极其细微、几乎难以察觉的……磕碰痕迹?或者只是反光?“就是它,
”陈伯的声音压得极低,语速飞快,带着最后关头的孤注一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