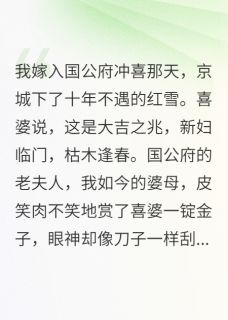血,温热的、冰冷的,混在一起,黏稠得化不开,浸透了我的战靴。
我像个被钉死在原地的木偶,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胸膛被利剑贯穿,
一个心口插着同一把剑的剑柄。两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苍白如纸,
却扭曲出同样诡异、同步的微笑,血沫从他们嘴角溢出,
声音虚弱得像从同一个地狱深处飘上来,
钻进我的骨头缝里:“阿璃…现在…你只能选‘我们’了…”---我叫琉璃。
名字听着脆生,干的却是刀口舔血的营生。在北境的风雪关,老子就是活阎王。黄沙当被,
铁甲为衣,砍过的蛮子脑袋能堆成京城的望月楼。这双手,握惯了刀柄的粗糙和血的滑腻,
早忘了胭脂水粉是什么味儿。可一道金灿灿、带着皇家印泥臭味的圣旨,劈头盖脸砸了下来。
回京述职?扯淡!老子在北疆啃沙子啃得好好的,述职个屁!宣旨太监那张白得瘆人的脸,
笑得跟哭丧似的,尖着嗓子:“陛下隆恩,体恤边将辛劳,特召将军回京,共享天伦,
共商国是…”去他妈的天伦!去他妈的国是!我心里骂翻了天,脸上还得绷着,
像戴了副生铁面具,单膝跪地,领了旨。冰凉的绢帛硌得膝盖生疼。
关外的风刀子一样刮了十年,吹硬了骨头,也吹冷了心肠。京城?那座锦绣堆成的牢笼?
比北蛮子的狼牙棒更让我头皮发麻。老子就想守在这鸟不拉屎的边关,守着我的兵,我的刀,
我的马。离那些弯弯绕绕的肠子、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笑脸越远越好。回去?
简直是逼老虎钻火圈!马蹄踏碎了京郊官道的尘土,离那座金晃晃的囚笼越来越近。
盔甲缝里还塞着关外带来的沙砾,磨着皮肉,提醒我真正的归宿在哪儿。
皇城根儿下那股子甜腻又腐朽的熏香气味,顺着风钻进鼻子,熏得我胃里一阵翻腾。金銮殿。
真他娘的大,大得让人心慌。柱子粗得几个人抱不过来,盘着张牙舞爪的金龙,
眼珠子都像活的,居高临下地瞪着人。空气里飘着昂贵的龙涎香,
混着一股子陈年老木头和权力特有的、冰冷又压抑的味道。“臣,琉璃,参见陛下!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撞出回音,像块石头砸进深潭。龙椅上那位,
老得像是从棺材里刚爬出来的,眼皮耷拉着,浑浊的眼珠慢吞吞地转过来,落在我身上。
那目光没什么重量,却像阴沟里的湿苔藓,滑腻腻地贴着皮肤爬。
“爱卿…戍边…劳苦功高…”老皇帝的声音像是破风箱在抽,
有气无力地念着一堆狗屁倒灶的套话,什么“国之柱石”,什么“功在社稷”。我低着头,
盯着自己沾满泥尘的靴尖,心里盘算着赶紧应付完滚回我的风雪关。“……特赐,黄金千两,
锦缎百匹…”老太监尖利的声音拔高了调门。来了。我心下一沉。果然,
下一句就是:“…另,念及爱卿劳苦功高,年岁渐长,朕心甚悯。特为爱卿,
择一良配…”大殿里死寂一片,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那股子腐朽的甜香更浓了。
我猛地抬头,牙关紧咬,硬邦邦地开口:“陛下!臣…”话没说完,
就被两道身影硬生生截断。左边,墨色的袍子,像凝固的夜。太子凌宸,
不知何时已无声无息地踏前一步,离我不过三尺。他身上那股子冷冽的松香混着冰雪的气息,
霸道地冲散了殿内的熏香,直往我鼻子里钻。他站得笔直,像一柄插在地上的寒铁剑,
那张脸,俊美得毫无人气,只有一片冰封的湖。薄唇微启,声音冷得掉冰渣,
金石般撞击着殿柱:“儿臣凌宸,求娶琉璃将军!”右边,一团灼目的红!二皇子凌焰,
像一团烧着的火,动作更快,几乎和凌宸同时抢出。他红衣张扬,猎猎如火,
带着一股子烈酒和汗水的野性气息,瞬间冲垮了他兄长带来的寒意。那双眼睛,亮得惊人,
像烧红的炭,直勾勾地烙在我脸上,毫不掩饰里面翻腾的、滚烫的欲望。他声音洪亮,
带着不容置疑的蛮横:“儿臣凌焰,求娶阿璃!”“阿璃”两个字,像两颗烧红的铁弹,
砸在冰冷的地砖上,烫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满朝文武,瞬间成了泥塑木雕。
连老皇帝浑浊的眼珠都似乎动了一下。整个金銮殿的空气,
仿佛被这两道截然相反的声音撕成了碎片,一半冻成了冰,一半烧成了灰。我僵在原地,
像被两道无形的巨蟒死死缠住。一股源自骨髓深处的剧痛毫无预兆地炸开!不是伤口疼,
是灵魂深处,有什么东西正被两股狂暴的、对立的力量狠狠撕扯!眼前阵阵发黑,
殿顶那描金绘彩的藻井都在旋转、扭曲。太子的冰,二皇子的火,
在我脑子里、血管里疯狂冲撞。我死死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用尽全身力气才没当场倒下去。喉咙里一股腥甜涌上来,又被我狠狠咽了回去。
那场朝堂闹剧像个引信,把我拖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噩梦。白天黑夜,冰与火轮番上阵,
要把我这块顽铁彻底熔断、冻碎。第一个撞进来的是太子凌宸。那晚的风,刮得跟鬼哭似的。
我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睁着眼看头顶陌生的、绣着繁复花鸟的帐子,
脑子里还是白日里那两张脸,那撕裂灵魂的痛楚。窗户“吱呀”一声轻响,比猫儿落地还轻。
一股裹挟着松针和雪末的冷风,像条滑腻的毒蛇,无声无息地钻了进来。房间里没点灯,
只有窗外惨淡的月光,勾勒出一个修长挺拔的黑色轮廓,像从墨汁里直接裁下来的影子,
悄无声息地立在我的榻边。寒气,带着他身上特有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冷冽松香,
瞬间笼罩了我。“谁?!”我低喝,手已经摸向枕下的匕首。冰凉的手指,
带着玉石般的质感,毫无预兆地落在我脸颊上。那触感太突然,太诡异,
激得我浑身汗毛倒竖!那手指顺着我的下颌线缓缓滑过,动作轻柔得像情人的抚摸,
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力,冻得我皮肤下的血液都似乎要凝固。“琉璃。
”凌宸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低沉,平稳,没有一丝波澜,却像淬了冰的针,扎进耳膜。
“做我的太子妃。”黑暗放大了他声音里的每一个音节,那种冰冷的重量,
沉甸甸地压在我胸口。“这万里河山,锦绣乾坤,”他的气息拂过我的额发,
带着冰雪的重量,“将来,由你我共掌。你无需再忍受边关风霜,无需再沾染血腥尘埃。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母仪天下。”每一个字都像是精心打磨过的冰锥,试图凿开我的盔甲。
共掌江山?母仪天下?我脑子里瞬间闪过北境呼啸的风雪,粗糙的砂砾,士兵们皲裂的脸,
还有刀锋砍进骨头里的闷响。那金丝鸟笼一样的皇宫?那戴着假面跳舞的日子?
那比死在蛮子刀下还让我窒息!“太子殿下,”我声音干涩,
强忍着脸上那冰蛇般手指带来的不适和灵魂深处被触动的撕裂感,“琉璃粗鄙,
只识得弯弓饮血,不懂什么母仪天下。这泼天的富贵,您还是另寻高明吧。
”脸颊上的手指顿住了。黑暗中,他似乎极轻地哼了一声,那声音里听不出喜怒,
只有一片更深的寒意。那冰冷的指尖在我皮肤上最后停留了一瞬,带着一种无声的警告,
然后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收了回去。那股迫人的冷冽松香气息,也随着黑影的消失,
缓缓散去,只留下满室的死寂和我心头一片冰凉的烦躁。灵魂深处的撕裂感,
因他气息的远离,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像被强行压抑的岩浆,翻滚得更加剧烈。
这口气还没喘匀,第二天校场上,又炸了锅。烈日当空,黄尘滚滚。我正对着沙盘,
跟几个副将推演北境可能出现的蛮族动向。喊杀声,操练声,兵器碰撞声,
是这里最熟悉的背景。突然,一阵急促得如同战鼓擂动的马蹄声由远及近,
像疯了一样直冲校场!根本不等辕门守卫反应,一道刺目的红影,如同天边坠落的燃烧陨石,
带着一股灼人的热浪和呛人的尘土,蛮横地撞开了外围的士兵阵列,
马蹄踏碎地上的沙土模型,直直朝着点将台冲来!“二殿下!不可!
”守卫的惊呼被淹没在马蹄声里。是凌焰!他一身烈烈红衣,在黄沙背景中烧得刺眼。
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狂野的兴奋,眼神亮得如同正午的太阳,牢牢锁在我身上。
狂风卷起他散落的黑发,肆意张扬。“阿璃!”他洪亮的声音炸雷般响起,
带着不容置疑的蛮横和滚烫的喜悦。我甚至来不及呵斥,只觉得眼前红影一晃!
一条乌黑油亮的长鞭,如同活过来的毒蟒,“嗖”地一声撕裂空气,带着尖锐的破空声,
精准无比地卷上了我的腰!一股巨大的、不容反抗的力道猛地传来!“上来!
”凌焰一声断喝,手腕猛地发力!天旋地转!我整个人被那鞭子卷着,
硬生生从点将台上拔了起来,凌空飞向那匹神骏异常、正人立而起的黑马!
沉重的盔甲此刻成了累赘,我像个被投石机甩出去的麻袋,狠狠砸落在滚烫的马鞍上,
正好撞进凌焰散发着汗味和阳光气息的、滚烫的怀里。骏马前蹄重重落下,踏起大片烟尘。
凌焰一手控缰,一手还紧紧攥着鞭子,勒得我腰生疼。
他灼热的气息像火焰一样喷在我的耳廓上,每一个字都烫得惊人:“发什么愣!跟我走!
”他大笑起来,胸膛震动,带着一种孩子气的霸道和全然的不管不顾,“看什么狗屁沙盘!
守什么鸟关隘!这京城就是个镶金嵌玉的粪坑!臭不可闻!憋死个人!”他猛地一夹马腹,
骏马如同离弦之箭,根本不顾校场上惊惶闪避的士兵,朝着辕门方向狂飙!风在我耳边呼啸,
刮得脸生疼。“江湖之大,四海为家!”他的声音在疾风中依旧清晰,带着令人心颤的蛊惑,
“纵马天涯,快意恩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看遍天下奇景,揍遍天下不服!阿璃!
那才叫活着!跟我走!现在就跟我走!”他的手臂像烧红的铁箍,紧紧圈着我。
他身上的热力,他话语里描绘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画卷,带着一种原始的、野性的吸引力,
像岩浆一样冲击着我被北境风霜冻硬的心房。有那么一瞬间,那辽阔的天地,那呼啸的风,
那烈酒的味道,几乎要淹没我。腰间的鞭子勒得骨头都在**,
灵魂深处那被太子引动的撕裂感,在凌焰这团烈火炙烤下,非但没有弥合,
反而像被投入滚油的冰水,轰然炸开!剧烈的痛楚瞬间攫住了我的头颅,眼前阵阵发黑,
破碎的画面——太子的冰眸、二皇子的火焰、边关的风雪、江湖的烟波——疯狂地搅在一起,
几乎要把我的脑袋撑爆!“停下!”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声音嘶哑,
带着无法抑制的痛苦和暴怒。手指死死抠住了他箍在我腰间的滚烫手臂。
凌焰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异样,狂奔的势头微微一滞。他低下头,
那张充满野性力量的脸近在咫尺,飞扬的眉峰皱起,明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困惑和……关切?
但那火焰般的热情并未熄灭。“阿璃?你怎么了?”他声音里的狂放收敛了些。
我猛地吸了一口气,压下喉咙口的腥甜和头颅里翻江倒海的剧痛。
校场上所有士兵都停下了动作,惊疑不定地看着点将台方向。几个副将手按刀柄,脸色铁青,
却又不敢上前。“放我下去,二殿下。”我咬着牙,一字一顿,
每一个字都像从冰水里捞出来,“这里是军营!不是你的跑马场!
”凌焰看着我煞白的脸和额角渗出的冷汗,脸上那股子不管不顾的兴奋劲头终于褪去,
被一种混杂着不解、挫败和执拗的神情取代。他勒住躁动的马,手臂的力道松了些,
却没有立刻放开。“你…”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烦躁地“啧”了一声,
手臂一甩,那卷在我腰间的长鞭如同活物般松开、收回。
我几乎是立刻从他滚烫的怀抱里挣脱出来,踉跄着跳下马背,沉重的盔甲撞在地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灵魂的撕裂感并未消失,如同跗骨之蛆,日夜啃噬。这日子没法过了!
白天,凌焰就像个甩不掉的炮仗。校场那次没得逞,他换了花样。
今天送来几大坛子据说是南疆秘酿的“火烧云”,拍开泥封,那酒气冲得能把人顶个跟头。
“阿璃!尝尝!够劲!比你们北境那马尿似的烧刀子强百倍!”他拍着酒坛,
笑得露出一口白牙,眼神亮得灼人。明天又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匹通体漆黑、四蹄踏雪的烈马,
野性难驯,在营地里横冲直撞。“看!乌云踏雪!配你!够不够格?”他翻身上马,
那马人立而起,嘶鸣声响彻云霄。他红衣黑马,在烟尘里驰骋,像一团烧得正旺的野火,
拼命地想把我这块冰疙瘩也点着。更过分的是,他不知从哪儿打听来的,
知道我在北境时偶尔会哼几句不成调的边塞小曲。没过两天,
一个据说是江南最好的琵琶女就被他“请”进了我的临时府邸。那姑娘吓得脸色发白,
抱着琵琶,指尖都在抖。凌焰大喇喇地往我厅堂里一坐,翘着二郎腿:“弹!
拣你们江南最软最糯的曲子!让咱们将军也松快松快筋骨!”丝竹咿咿呀呀地响起来,
软得像没骨头的柳絮。我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听着这靡靡之音,
看着凌焰那副“快夸我”的得意表情,只觉得浑身有蚂蚁在爬!灵魂深处那股撕裂的痛楚,
被这软绵绵的调子一勾,反而像钝刀子割肉,磨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我猛地一拍桌子,
那上好的紫檀木桌面都震了震!“够了!”我低吼一声,声音里压着暴怒和疲惫,“二殿下!
我这儿不是勾栏瓦舍!把这姑娘,还有这些玩意儿,都给我弄走!”琵琶声戛然而止。
那琵琶女吓得噗通跪倒在地,瑟瑟发抖。凌焰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那明亮的火焰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瞬间黯淡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的烦躁和不解。
他瞪着我,胸口起伏了几下,最终狠狠一甩袖子,什么也没说,阴沉着脸,
拽起那吓傻了的琵琶女就走。门被他摔得震天响。这边刚送走一团火,
那边一块冰又无声无息地渗了过来。凌宸从不白天出现。他像个真正的影子,
只在最深的夜里降临。有时是递过来一份誊抄得工工整整、墨迹未干的边防条陈,
上面用朱笔细细批注了他的见解,字字冷峭,却切中要害。“北戎左翼王新丧,诸子争位,
三月内必生内乱。此时增兵易露行藏,不若遣死士潜入,散布流言,使其自溃。
”冰冷的字句,带着洞悉人心的寒意。有时是几卷新抄录的、早已失传的前朝兵法典籍,
放在我窗下的石桌上,用一块压着冰雪的玉石镇着。书页冰冷,仿佛还带着他指尖的温度。
他从不问我要什么,只是把这些我需要的东西,以一种不容拒绝的方式,精准地放在我面前。
像在下一盘无声的棋,一步步,用冰冷的理智和看得见的“好处”,
将我往他预设的棋盘上推。“太子殿下,”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
在他又一次如鬼魅般出现在我院中,放下几份关于西境粮草调度的密报时,开口了,
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您做这些,是想告诉末将,只有跟着您,
才能守住这江山?”凌宸的动作顿住了。他站在清冷的月光下,玄色的袍子几乎融进夜色里,
只露出一张轮廓分明的侧脸,像冰雕。他缓缓转过身,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看向我,
里面没有任何情绪,只有一片沉寂的寒潭。“琉璃,”他的声音比夜风更凉,
“你是个聪明人。守江山,需要脑子,需要力量,更需要站在最高的地方。
”他微微抬了抬下巴,指向皇宫的方向,“只有在那里,你的刀,才能真正砍向该砍的地方。
而不是被埋没在边关的黄沙里,或者…被某些人引向歧路,最终粉身碎骨。”“歧路?
”我咀嚼着这两个字,看着他眼中那片冰冷的笃定,灵魂深处的撕裂感再次翻涌起来。
凌焰描绘的江湖是歧路?那我这十年饮冰卧雪,又是什么?一股无名火猛地窜起。
“殿下高瞻远瞩,”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没什么温度的笑,“只是琉璃愚钝,
只认得眼前的路。北境的风沙磨粗了心肠,受不起殿下这般抬举。这江山,
自有殿下这等龙凤去守。末将,还是回我的风雪关踏实。”凌宸静静地看了我片刻。
月光落在他长长的睫毛上,投下小片阴影。他没有动怒,甚至没有一丝表情的变化,
只是那眼神,似乎比刚才更沉、更冷了,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寒井。“你会明白的。
”他只说了这四个字,声音轻得像叹息,却带着一种奇异的重量。然后,他像来时一样,
悄无声息地退入廊下的阴影之中,玄色的身影瞬间被黑暗吞噬,只留下原地一片冰冷的死寂,
和他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冷冽的松针气息,久久不散。冰与火日夜夹攻,
我像一块被反复捶打的铁,在极寒与酷热中煎熬。灵魂深处那撕裂的痛楚非但没有缓解,
反而愈演愈烈。每一次面对他们中的一个,那痛楚就尖锐一分。我开始害怕入睡,
因为梦里没有黄沙铁马,只有无休止的坠落,被两股力量撕扯着,一边是冰封的深渊,
一边是燃烧的炼狱。醒来时,冷汗浸透中衣,头痛得像是被重锤砸过。我试过躲。闭门谢客,
无论是对那团火还是那块冰。可凌焰能直接策马闯营,凌宸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这京城,
就是个巨大的囚笼,我无处可逃。我也试过强硬。对着凌焰怒斥,对着凌宸冷言冷语。
可那团火,你越泼冷水,他烧得越旺,眼神里的执拗和受伤像针一样刺人。那块冰,
则根本不为所动,你的怒火撞上去,连个涟漪都没有,
反而被那无边的寒意冻得自己心头发颤。我的脾气越来越糟,像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
手下几个跟了我多年的亲兵都察觉了,私下里嘀咕:“头儿这是咋了?回趟京,魂儿都丢了?
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他们看我眼神里带着担忧和不解。
我暴躁地挥开送来的饭食:“不饿!”对着沙盘推演时,
一个副将不小心碰乱了代表蛮族骑兵的小旗,我竟控制不住地厉声呵斥,
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副将吓得脸色发白,连连告罪。我扶着沙盘边缘,
粗重地喘息,努力压下那股翻腾的戾气和脑中针扎般的剧痛。不行,再这样下去,
我没被蛮子的刀砍死,也要被这两个皇子逼疯!必须离开!立刻!马上!我抓起笔,
铺开奏折,墨汁溅得到处都是。我要上书!陈情!求陛下开恩,放我回北疆!哪怕降职,
哪怕去守最苦的烽燧台!也比在这鬼地方被活活撕成两半强!笔尖刚触到纸面,
那股熟悉的、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痛毫无预兆地再次袭来!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凶猛、更狂暴!
像有两只看不见的巨手,抓住我的头颅,用尽全身力气朝相反的方向狠狠撕扯!“呃啊——!
”一声压抑不住的痛哼冲口而出!眼前瞬间被一片猩红覆盖!天旋地转!
手中的狼毫笔“啪嗒”一声掉在刚写了“臣琉璃万死”几个字的奏折上,污了一大片墨迹。
我双手死死抱住头颅,指甲几乎要抠进头皮里,身体不受控制地蜷缩下去,
撞翻了沉重的沙盘架子。轰隆!木架倒塌!
细沙和代表山川河流、千军万马的模型小旗哗啦啦倾泻下来,砸了我一身。“将军!
”守在外面的亲兵听到巨响,猛地冲了进来,看到我蜷缩在地,痛苦抽搐,满身狼藉,
吓得魂飞魄散。“头儿!您怎么了?军医!快叫军医!
”剧痛像潮水般一波波冲击着我的神智。在灭顶的痛楚和眩晕中,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像垂死之人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逃!必须逃出这里!再待下去,我会死!会被活活撕碎!
老皇帝大概是真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也可能是被两个儿子当庭争一个“边关蛮妇”的丑事气着了,
竟下旨要去皇觉寺“祈福静养”。说是静养,排场却大得吓人。金瓜钺斧,旌旗仪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