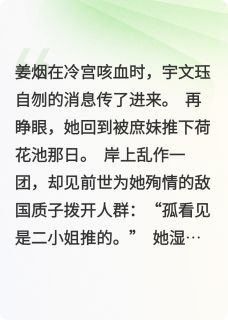楔子十五年前,我见死不救,让他成了孤魂野鬼。如今他以豪商之身归来,买下我家产业,
还成了夫君的座上宾。看着他阴恻恻的笑,我知道,该还债了。可谁能想到,这场复仇棋局,
我才是执子人呢!1宝藏出现的瞬间,我转身就跑,却被身边的胡女一把拉住:“客人,
你要去哪里?”“见鬼了!”我甩开她,慌忙跑出门去。吓死我了,宝藏还魂了?半刻后,
我站在熙熙攘攘的胡市,被初秋烈日照得大汗淋漓。十五年前就被我害死的宝藏,
竟然活生生站在我的眼前,还买下了我们家的产业,到底要干什么?但我毕竟是偷跑出来的,
不敢在外面太久,只好赶回家中,还好,夫君和那个**都不在家。天刚黑,
侍女佛儿就来了,说夫君张元信让我去前厅待客?自从我们家败了,
张元信就娶了姓曹的**,再也没和我同桌吃过饭,更不要说待客。这是失心疯了?
珍馐美馔摆满桌,摇曳灯火,晃得我一脑门冷汗。我想,果真是祸躲不过。
张元信的左手坐着一个衣衫华贵,英俊潇洒的胡人,还是宝藏。“夫人好,
我是布哈拉的商人安宝藏”他阴恻恻笑着向我行礼。我僵硬地坐着,不知道说什么,
倒是张元信举起酒杯,张罗大家喝酒,说什么“一醉一陶然”。我可不信他没有认出宝藏,
毕竟,当年害死宝藏,也有他一份。喝得有点多,我想起了很多。十五年前,
宝藏因为毒死了张元信的大食马,被我爹捆在树上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被赶出门去,
所有人都说他活不了了。我不死心,让侍女佛儿去打听,得到的消息也是他死了。
我记得那是七月的一天,下着大雨,我和佛儿偷偷跑去胡市的祆祠,祭奠粟特人宝藏,
盼望他的灵魂能够回到故乡。晚上,我失眠了。晚宴上,宝藏充满暗示的眼神让我害怕。
十五年前,日头正烈,我躲在二楼垂帘后,大气不敢出,听见院中宝藏被打的哀嚎,
看见满地鲜血,触目惊心。我知道,只要我下楼,说昨晚宝藏和我在柴棚里私会,
一直到天亮,根本没时间毒死张元信的大食马,就能证明宝藏的清白。但我不敢说,
因为我是**,他是奴,整夜厮混,会毁了我的清白。张家在沙州很有势力,
我爹不想得罪他,便往死里打宝藏,说:“我是家主,可以替你赔,但你要说真话。
”但宝藏很倔强:“不是**的!”我只能无声流泪,因为我也不想得罪张元信,
他是我未来的夫君,很小的时候就定下的娃娃亲。我心里清楚,张元信诬陷宝藏,
不惜毒死自己的马嫁祸给宝藏,是因为头一天看到我和宝藏在后院驯马,吃醋了。说起来,
张元信是个变态。小时候,我是很喜欢宝藏,但见到张元信时,我才知道了什么叫门当户对,
公子翩翩,宝藏和他一比,立刻黯然失色,像个小土狗,我开始远离宝藏,讨好张元信,
又是给他绣手帕,又是给他做点心,但他都不领情,把帕子赏了歌妓,点心送了下人,
还说我长得土,没气质。我一生气,就开始故意在他面前和宝藏好,谁知道,
他竟然开始吃醋了。那天半夜,我偷偷溜下楼,轻抚宝藏布满血污的脸,忍不住哭了。
我觉得,我也对不起宝藏。但是宝藏并不领情,冷冷地说:“给我滚。”第二天,
宝藏就不见了,他们都说,宝藏死了,一个奴,竟然敢把自己当人,还敢毒死贵人的宝马。
2害怕管屁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第二天,天刚亮,我就重新去了安家店。这次,
我知道了,那个胡女名叫艾尔肯娜,是宝藏的掌柜。宝藏似乎料定我会来,早已煎好茶,
等我。那是一种熟悉的奶茶香味,少年时代起,宝藏就煮给我们喝。艾尔肯娜离开后,
我故作从容地在他面前坐下,笑着说:“你如今姓安了?”宝藏继续煎茶,斜了我一眼,
又低下头:“给我第二条命的人,姓安。”我讨个没趣,赶紧喝茶,又被烫得直皱眉。
宝藏忍不住笑了。“哎!”我叹了口气,这口气,我昨晚预演了很多次。我赌的,
是宝藏对我还残存的情义,毕竟,他是我第一个男人。“七娘,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就是不能坦诚。”他揶揄我。揶揄就揶揄,我才不在乎。我这次来,就一个目的,这安家店,
是我们索家的,我爹临死前,最放不下的就是这家店,我得赎回来,我攒了这么多年钱,
眼看胜利在望,却被他半道截胡,很难相信他不是处心积虑。我稳了稳心神,
开始按照昨晚排练的,梨花带雨、娓娓道来,从这些年不得不为了家族嫁给张家,
到张元信吃喝嫖赌样样不落还狠狠打我,到娶了一个姓曹的夫人,
把我的儿子打死丢到井里假装是失足落水,再到我许多年没有上桌吃饭,
城里人都以为我死了……说着说着,我痛哭起来。“我攒了十几年的钱,
就是为了完成我爹的遗愿,让家里的产业重新姓索,我做错了什么!
”我哭得自己都觉得头晕,心想今天精心化的妆大概都糊了。这些事,我没有撒谎。
宝藏沉默,但显然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你回来,不就是报仇的吗,我现在这样,
你还不满意吗!”我继续哭。此时,恐惧已经荡然无存,如果他要报仇,最多杀了我。
“你说的没错,我恨你,但我要报仇,首先要找张元信。”宝藏递来一个帕子,淡淡说,
“我理解你,你的身份,下楼为我作证,会嫁不出去的,我当然有怨恨,
但是……”我心里松了口气,只要他不想置我于死地,我的目的就能实现。
“我也想弄死张元信。”我开诚布公,想合作,就得真诚,何况,宝藏是多么聪明的男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回这家店?”我接过手帕,轻轻按着红肿的眼睛。宝藏不说话。
“一开始,我想和他和离,但他将我打个半死,也不同意。他好面子,说他们张家是大族,
不缺我这张嘴。”我又哭起来。宝藏皱眉:“所以,你买回你们家的店能干嘛!
”“我想做生意,赚钱,然后,把张家挤兑垮。”我坚定地说。这件事上,我也没有撒谎,
张家随是望族,但这几年,随着河西局势的动荡,已经风雨飘摇,还在官位上的人越来越少,
因为少主的猜忌,正在被逐渐边缘化。就张元信这个败家的速度,只要给他沾上黄赌毒,
家破人亡那是迟早的事情。宝藏肯定不信,他带着嘲笑,
看着我:“赎回你家的店就能叱咤河西商场了?你这个猪脑子!”他这一声斥责,
倒是带着宠爱,仿佛回到了十五年前,我看着他从领口处露出的好看的锁骨,不由心神一荡。
3宝藏虽然觉得我不可能开了一家店就能搅动河西商场,但还是对我的坚韧不拔给予肯定。
过了几天,我带着亲手做的乳饼,来看宝藏,这次,艾尔肯娜对我态度不好,
挑着眉毛对宝藏说:“安郎,人家给你做的乳饼,心意满满,多吃几个。
”我才不在乎她的阴阳怪气,我只知道,必须抓住眼前的机会,才能翻身,实现我的目标。
“我也专门给妹妹带了加了蜂蜜的乳饼,你尝尝。”我微笑。艾尔肯娜不甘,
但还是在宝藏冷峻的目光中退了出去。宝藏望着我,眼睛里流淌过一阵温柔。
他一定是想起了年少时,我给他做乳饼的那些日子,我们耳鬓厮磨,抱在一起,
他颤抖着说:“**,我们不能……”“我说能,就能。”我扎进他的怀里,
那是我第一次和男人有肌肤之亲。结束后,宝藏仿佛昏厥了,半晌才颤巍巍地给我披上衣服,
将一个甜蜜的吻落在我的嘴唇上。事实上,我很确信,我安宝藏,爱他的身体,
也爱他的灵魂。但是,我无法爱上他的身份,作为沙州望族之女,
我天生就能分清楚什么是爱,什么是婚姻。所以,我对宝藏的那些好,也都是真的。“宝藏,
我……真的很爱你……那时候……”半卷的竹帘帮我抵挡烈日,但我的脸还是红了。
“我知道!”宝藏忽然将我揽入怀中,他的味道很好闻,他的气息如此滚烫,令我浑身颤栗。
“既然我们目标一致,为什么不能合作?”我贴近他的身体,感到宝藏的心跳正在加速。
“合作,为什么?我可以直接宰了张元信!”“你可以,但我要家产,不止索家,还有张家,
甚至还有曹**的私房钱。如果合作,我可以把一切收益都给你,我只要这家店。
”我望着他,努力寻找他眼里的温柔。宝藏有点惊讶,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吻我,
低吟道:“我只要你,我只要你……”他呢喃着,滚烫的手指已经落在我的耳畔,
顺着脖颈向下滑去。诚然,我爱着他,身体很诚实地温热起来,脖子也伸长了,
似乎在享受他的抚摸。“我想要你,我要你……我多么想要你……”他咬着我的耳朵,
吐出一口热气。我沉醉了。此刻,我只要这家店,几乎就是我真实的想法了。但,
人总是会不断变化的。天亮了,我离开安家店,匆匆往家去。我是索家嫡女,
从来就不是弱者,从来就不会头脑昏昧。我七岁学骑马,无论多么艰难,都学成了,
我做一切事情,都会竭尽全力,那么胜算很低。昨晚,当宝藏沉浸在欢愉中时,
提出了一个建议:“我可以把这间店送给你,或者,我也可以带你走。”“宝藏,我不走,
我要得到所有家产后,送给你,作为补偿,我要你风风光光地娶我,就在沙州本地生活,
让他们看看,你和我,都不是任人欺辱的弱者。”我柔和而坚定地说。“好!
”宝藏显然被我打动了,“只要重新得到你,我什么都愿意做,我都愿意,你放心,
这些产业,我帮你全部弄回来!”4说完“什么都愿意做”的宝藏,现在却傻眼了,
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有计划,你放心,张元信现在非常信任艾尔肯娜,已经借了大笔债务,
都投资在萨珊玻璃上了,很快,他就会赔得血本无归。到时候,我们就把张家的家产都收了。
”宝藏信誓旦旦地说。我知道,他不愿意出卖“男色”。“可是……我需要曹**身败名裂,
还要拿走她的小金库。”我娇嗔,斜靠在他怀中,睫毛蹭着他的脸颊。宝藏一哆嗦。
“有完没完!”艾尔肯娜从门外闯进来,站在门口,指着我,“没有我,安郎早死了,
现在被你这个**勾引,完全看不见我了!”“艾尔肯娜!”宝藏站起身来,
紧紧将我揽在怀中。“安郎……”艾尔肯娜哭起来。“你出去!很早之前,你就知道,
我心中只有她!”宝藏的气息将我包裹起来,充满安全感。我早就看到了艾尔肯娜手中的刀,
最终在宝藏字字如铁的话里,失了锋芒。伤心的胡女退出门去,好几天都没有再出现。
“我不能总是和你幽会。”我难过地说。“放心吧,张元信指望我给他生意做,
根本不敢管咱俩,我已经跟他说,他要管着你,我就收回给他的借贷。
我让他把那姓曹的女人休了不就行了?我不想……”我知道,说一千道一万,
他就是不想和曹**私通。我叹了口气:“其实,让她身败名裂,并不是我的目的,
她这样的贵女,只有伤了心,失了体面,才会生不如死!只有她生不如死,
才算给我的孩子报了仇!”“我安排一个人去。”宝藏轻抚我的头发,说。“不,
我已经打听过了,自从上次在府里见过你后,曹**就看上你了,日日魂不守舍的!你信我,
你拿下她,才能让她伤心!”**在宝藏肩膀,任他摆弄我的头发,柔声说,
“只有将她的心绞碎了,我才甘心!你要帮我,你一定要帮我!就这一次!
”我像小时候那样不容置疑地瞧着他,眼神柔弱又可怜。宝藏心动了。小时候,我要什么,
他不答应,我就会露出这种眼神,非常有用。如果还不肯,就亲亲他。
一个香吻落在宝藏唇上,他愣了一下,忽然狠狠地咬住了我的嘴唇,拼命吮吸起来。
上次幽会,他说过,其实他回来,就是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没想到,我真的倒霉了,
本来还挺爽的,但一见到我,又心软了。这就是宝藏,从来都把我当做白月光的宝藏。
我心里一动,开始吮吸他的舌头。5最近,张元信垄断了河西上路入秋前的所有琉璃生意,
惹怒了所有世家大族,大家都说,张家给人留活路,肯定没有好下场。张元信听到只是笑笑,
他最近很少回来,我知道,给他生意做的人,就是艾尔肯娜,给他借钱的,
就是安宝藏和安宝藏的朋友,胡商哈立德。我静**在后院里绣花,听仆从们窃窃私语,
大家说,曹夫人最近很反常。午后,佛儿一面摇着画扇,一面将外面的消息带回给我,
盼望一向被曹**踩在脚下的主母能欢喜几分。我正在窗前绣花,已经入夏,
窗外传来阵阵花香,沁人心脾。听完佛儿的叙述,我故意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低声说:“都是胡说吧,谁看见了?”佛儿见我怀疑,非常不服气,
立刻撅起小嘴说:“阿金看见了,每次都是他送主人过去的,在那胡店外,
一等就是一整天呢,过夜的……也是不少的。”佛儿说着,脸红起来。张元信年轻的时候,
爱骑马,往往都是自己骑马外出,后来喝醉了骑马摔伤了腰,从此便不再自己骑马,
由车夫阿金赶着马车送他去往各处。我笑了笑:“然后呢?”“然后……”佛儿脸更红了,
“他们都说,主人被那胡女勾去了魂儿,还……咳咳,曹夫人发了好几次火,
但也管不住主人,
为此……为此还摔碎了主人送她的红珊瑚串子呢……”佛儿是个未出嫁的女孩,
那些男女之间的龌龊事说不出口,但我听得明白,只是笑而不语。
“还有更奇怪的呢……”佛儿却没有结束八卦的意思,瞧了瞧窗外,凑近了,继续说,
“可是入夏以后,曹夫人突然不闹了,后院的卫苟子说,嗯,曹夫人有了一个相好的,
趁主人不在,独自出去了好多次,有时候还过夜呢……”卫苟子是后院的门夫,
夜夜宿在后门边上,谁从后门出来进去的,他都心知肚明。我依然不说话,
认真地绣着那朵粉白的牡丹,一针一针,十分用心的样子。佛儿见我不说话,开始意识到,
张元信也是我夫君,在外寻花问柳,我的心情也不会比曹**强,于是她闭了嘴,
难为情地低下了头。我反是开朗一笑:“傻丫头,我不难过,我早都习惯了。
”“夫人……我失言了,夫人打我两下吧。”佛儿的头更低了。我放下手中的针线,
望着少女认真梳理的双丫髻,不由笑出声来,“真是傻,打你做什么!”两天后,
安家店后院,我将一个亲手绣了粉白牡丹的手巾放在宝藏手中,他迅速拿起来嗅了嗅,
过来抱住了我。这一刻,我竟然有些心酸,想起十几年前,我当着他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