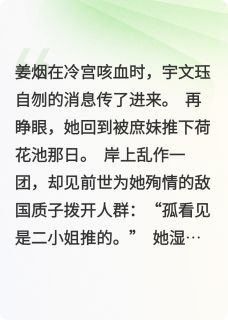我顶着废物女帝的空壳,在龙椅上听着满朝文武哭丧。宰相盼我早死,将军恨我挡路,
连订了婚的皇夫都想往我棺材板上啐口唾沫。行,反正这国也要亡了,大家一起死,
谁也别想跑。可后来,烂摊子被我盘活了,那三个男人看我的眼神,却跟见了鬼似的。
一个深夜,权倾朝野的宰相裴如命,竟跪在我榻前,拽着我的袖子,
声音抖得像筛糠:“陛下,别死……求你,别死在我前面。”我这才想起,我那短命的前身,
似乎是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1龙椅上的屠夫我坐在龙椅上,
听着底下那帮老东西鬼哭狼嚎,眼神空得能跑马。本该死透了的我,又活了。好消息是,
我成了女帝,一步登天。坏消息是,这破国家,马上就要亡了。底下吵得像个菜市场,
武将红着眼说边关没粮草,文官捂着心口说国库能跑老鼠。有本事的站一边看戏,
没本事的等着国家一倒,好冲进去捞最后一笔。乱七八糟,一锅烂粥。
许是这噪音穿透了我死过一次的耳膜,我那潭死水般的心,竟也泛起了几丝不耐烦。
我站起身,龙袍的下摆扫过冰冷的金阶,一步步走了下去。整个朝堂,瞬间死寂。
刚才还哭得最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户部侍郎,正跪在我面前,袖子擦得油光发亮。
“陛下啊!臣在户部十年,兢兢业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国库空虚,年年赤字,
您是知道的……”他叫什么来着?算了,不重要。重要的是,
国库被他和他那帮蛀虫亲戚啃得底朝天,他自己家里金山银山,富得流油。
前几天还花了十万两白银,就为了给他那个不成器的小女儿买了根南海珍珠簪。
边关的将士们,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走到他面前,没跟他废话,手一伸,
直接抽出旁边侍卫腰间的佩剑。那侍卫浑身一哆嗦,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但愣是没敢动。
剑光一闪。“噗嗤——”我一剑抹了他的脖子。动作干净利落,连让他哼一声的机会都没给。
温热的血溅出来前,我还特地侧了半步,免得弄脏了这身华而不实的龙袍。
尸体“砰”地一声倒在地上,血水汩汩地流,染红了光洁的金砖。满朝文武,全傻了。
一个个张着嘴,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鸭子。我甩了甩剑上的血珠,看向那个和他吵架的武将,
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糙汉子。“你,去把他家给朕抄了。抄出来的银子,
先紧着你的军粮军饷用,剩下的,一文不少地给朕滚回国库。听懂了?”我顿了顿,
剑尖指向地上那具还在抽搐的尸体。“给你钱,给你粮,要是还打了败仗,他的今天,
就是你的明天!”那武将先是懵了一瞬,随即脸上爆发出狂喜,像是饿了三天的狼看见了肉。
他“哐”地一声跪下,磕头磕得震天响:“末将领命!谢陛下!”说完,他吼了一声,
带着几个亲兵,真就这么杀气腾腾地冲出大殿去了。这时,
朝堂上那群“正人君子”们才如梦初醒,一个个跟死了爹一样开始对我口诛笔伐。“陛下!
户部侍郎即便有罪,也该三司会审!您……您怎能如此独断专行!”“是啊陛下!为君者,
当以仁德治国,岂能以暴虐立威!”“就算抄家,也该由大理寺和刑部接管,
怎能让一介武夫染指!这不合规矩!”“不合规矩!万万不合规矩啊!”他们吵吵嚷嚷,
唾沫星子横飞,还当我是原来那个被他们几句话就能吓哭的窝囊废。我懒得听,
目光在殿中扫了一圈。有三个人,从头到尾,一言未发。宰相,裴如命。穿着一身绯色官袍,
眉眼温润,像个教书先生,可那双眼睛深得像古井,正一丝丝地剖析我。大将军,顾渊。
一身玄色铠甲,身形如松,脸上带着刀疤,煞气逼人。他看我的眼神,
像是看一个不小心闯进他领地的疯子。太傅,江弘。白发苍苍,仙风道骨,手里捻着佛珠,
闭着眼,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我只扫了他们一眼,便提着还在滴血的剑,
走向那个叫嚷“于礼不合”叫得最欢的礼部尚书。那老头满嘴的仁义道德,看我走近,
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双腿一软,“噗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剑尖的血,滴答一声,落在他面前的地上。他抖得更凶了。一个头铁的御史看不下去了,
站了出来,一脸悲愤:“陛下!您今日之所为,实在令人寒心!臣……臣以死为谏!”说罢,
就要往殿里的蟠龙金柱上撞。我懒得看他演戏,直接打断:“行,朕准了。别光说不练,
赶紧的,现在就撞,死了朕给你风光大葬。”那御史僵在原地,撞也不是,不撞也不是,
一张脸憋成了猪肝色。我眼神一冷,声音淬了冰:“不是要死谏吗?怎么?还要朕帮你一把?
来人,把他给朕架过去,头对着柱子,给朕撞!”那御史“嗷”的一声,直接瘫跪在地上,
涕泪横流:“陛下开恩!臣……臣是一时糊涂!陛下开恩啊!”他这一跪,
像是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哗啦啦跪倒了一大片,嘴里喊着“陛下开恩”,
一个比一个情真意切。我“当啷”一声,将剑扔在地上,看向一直沉默的大将军顾渊。
“看见地上跪着的这群人了吗?”顾渊的目光终于从我脸上移开,
落在那群抖成一团的官员身上。我笑了,笑得像个妖妃:“带兵,挨家挨户地抄。
抄出来的东西,五成归你,充作军用,另外五成,给朕放回国库。”下面跪着的人,
彻底傻眼了。这次的哭嚎,比刚才死了爹妈还要真诚。一直看戏的宰相裴如命,
终于站了出来。他微微躬身,姿态恭敬得挑不出一丝错,可那挺得笔直的脊梁,
没有半分忠诚。“陛下,一朝罢黜如此多官员,恐怕会动摇国本,社稷不稳。”我坐回龙椅,
翘起二郎腿,用手撑着下巴,活脱脱一个亡国昏君的模样,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那正好啊,
裴相。让你的人补上呗,这不都是空出来的肥缺吗?”裴如命的眼角抽动了一下,
垂下眉眼:“臣,不敢。”“在这龙椅上坐着的是我,就由我说了算。
”我用指尖敲了敲扶手上的金龙,“怎么,看不惯?看不惯你们就造反啊?”裴如命,
当朝宰相,朝中过半的官员都与他盘根错节,做梦都想我死得快一点。顾渊,护国大将军,
手握重兵,恨不得我死得远一点,别在京城碍眼。而我,容国女帝文弦月,一个光杆司令,
嘴炮无敌。大不了就一拍两散,这皇帝谁爱当谁当。反正我烂命一条,谁怕谁啊?
我背后的合欢谷可不是吃素的,论玩弄人心,你们这群凡夫俗子,还嫩了点。
2狗男人和馊饭菜我叫弦月,上辈子是合欢谷里最失败的弟子。临死前,我拉着师兄的手,
哭得肝肠寸断。“师兄,我对不起师父的教诲,白学了那么多勾魂摄魄的本事,到头来,
连个男人都没睡过,就要死了。”感受着生命力一点点流逝,
我满心悲凉:“都怪我勘不破情爱二字,迟迟无法突破境界,才落得如此下场。
”师兄那双颠倒众生的桃花眼,此刻只剩下无语。我甚至怀疑自己眼花了,
因为我好像看见他翻了个白眼。“师妹,你但凡回头看一眼,都说不出这么丧尽天良的话。
”我一脸迷茫:“师兄此话何意?”师兄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我问你,
前些日子天云宗那少宗主,送你的那对仙鹤……”“那不是给我炖汤补身子的吗?
味道还不错。”师兄的牙咬得咯咯作响:“好,那药王宗送来的百年百里香呢?
”“说起这个我就来气!好端端地送我药材,他是不是咒我早死?
”师兄的拳头握紧了:“好好好……那归风堂那个傻小子,当着全宗门的面跟你表白,
你总没话说了吧?”我理直气壮地点头:“有啊。师兄你不是教我,要若即若离,
不能让对方轻易得手吗?所以我先假意拒绝了,想着过个几年再去找他。
”师兄的声音都在抖:“你……你拒绝了多久?”“三十年吧。等我前几天想起来这事,
人家孙子都会打酱油了。”师-兄-忍-无-可-忍,最后化作一声长叹。
“我都不知道该骂你渣,还是骂你傻。你仗着那张脸,到处撩拨而不自知,
勾得别人心猿意马,你又转头忘得一干二净。”他扶着额头,一脸痛心疾首。“师妹啊,
咱合欢谷上下,谁有你渣?”我欲哭无泪:“师兄,
可是我真的看不破啊……”随着最后一滴眼泪落下,我的神识彻底陷入黑暗。再睁眼,
我就成了这个容国的废物女帝,文弦月。下朝后,我歪在御书房的软榻上,一边翻着奏折,
一边吃着点心,悠哉游哉。朝堂是空的,国库是空的,边关告急,民不聊生。这国,
早晚要完。挺好,大家一起完蛋。我这块点心还没咽下去,
顾渊和裴如命就一前一后地进来了。顾渊是个急性子,行完礼就跟炮仗似的冲到我面前。
“你今天在朝上说的话,还算不算数?”我懒洋洋地“嗯”了一声。他似乎有些不信,
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你知道那些大臣府里能抄出多少钱吗?”我又“嗯”了一声。
他终于忍不住了,脸上一阵青一阵白:“那你到底想让臣做什么?”我总算放下奏折,
正眼看他:“朕表现得还不够明显?”顾渊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臣,绝不可能当陛下的皇夫!”“你去边关带兵打仗。
”我们俩异口同声,然后齐齐陷入了沉默。哦,我忘了,原主那个恋爱脑,为了收回兵权,
居然想出了“睡服”大将军这种馊主意。我的目光在他身上溜了一圈。身材高大,肌肉结实,
脸上的刀疤更添了几分男人味。可惜,一看就是个榆木疙瘩,满脑子都是打仗,无趣得很。
顾渊被我看得浑身一抖,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立刻抱拳领命。“既然陛下有令,
臣这就去准备!”他跑得比兔子还快,生怕我再提那档子事。外忧解决了,现在轮到内患。
我看着独自留下来的裴如命,有点头疼。对付这种聪明人,太费脑子。裴如命在我对面坐下,
行云流水地给我续了杯茶,那双温润的眼睛里,却藏着刀。“陛下今日,与往日大不相同。
”**在躺椅上,眼皮都懒得抬:“哦,所以呢?”他慢条斯理地抿了口茶,笑得如沐春风,
说出的话却带着审判的意味。“臣几乎要以为,陛下换了个人。”他在试探我。
我无所谓地哼笑一声:“朕还是那句话,裴相,有证据,你就麻溜地造反。没证据,
就给朕老老实实地干活。”对付这种弯弯绕绕的狐狸,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底牌直接甩他脸上。
你越是坦荡,他越是怀疑你背后藏着什么惊天阴谋。果然,裴如命的眼神瞬间暗了下来,
里面的算计和审视几乎要凝成实质。半晌,他才低头,掩去眼底的情绪:“陛下说笑了。
”他不再试探,转而开始跟我聊起了茶道。说他手里这罐“碧螺春”如何难得,采摘于何时,
又经何人之手炒制,说得天花乱坠。我听得昏昏欲睡,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裴如命滔滔不绝的话,罕见地卡壳了。我咂咂嘴:“牛嚼牡丹,浪费了。不过解渴,还行。
”裴如命的嘴角,又抽了一下。我不知道他留下来到底在等什么,直到……“文弦月!
你疯了!”一个火红色的身影,像一团火一样冲了进来,后面拦着的太监被他推了个趔趄。
“容国怎么会落到你这种废物手上!要是皇兄还在……”他看见了裴如命,
硬生生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对着裴如命倒是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见过裴相。”看吧,
这满宫上下,就没一个把我这个女帝当回事的。想骂就骂,想闯就闯。尤其眼前这个,
江家的小公子,江修。我那名义上的未婚夫,太傅江弘的独子。在他们眼里,
先帝那几个死去的儿子,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比我这个女儿强。我看着来人,淡淡地开口。
“跪下。”江修愣住了,掏了掏耳朵:“你说什么?”我加重了语气,
声音冷得掉冰渣:“来人!给朕把这个不知尊卑的东西拖下去!重打二十大板!
然后打包扔回江家,问问江太傅,就是这么教儿子的吗?”我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嫌弃,
“目无君上,言语不敬,这皇夫的位置,他坐不起。”江修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瞬间炸了毛。“谁他娘的稀罕当你的皇夫!要不是你死皮赖脸地非要……”我点点头,
直接打断他:“很好。退婚的圣旨,朕一会就派人送到你府上。”江修那张俊俏的脸,
瞬间呆滞了。我挥挥手,懒得再看他,两个侍卫立刻上前,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了出去。
外面传来他杀猪般的嚎叫和咒骂。看完了全场好戏的裴如命,心满意足地站起身,
对我行了一礼。“陛下今日,真是让臣大开眼界。”临走前,他停在门口,
回头对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只希望明日早朝,陛下也能如今日这般,游刃有余。
”明日?我脑子一转,想起来了。明天,是北边的寒国派使臣过来“议和”的日子。
名为议和,实为羞辱。他想看我的笑话。想看我砍了户部侍郎,得罪了大半文臣,
又逼走了大将军,废了太傅的儿子之后,要怎么独自面对虎狼之邦。可惜,他不知道。
一个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怕的女人,有多可怕。
3谁的拳头大谁有理江弘是连夜进宫请罪的。老狐狸跪在御书房冰冷的地面上,一言不发,
跟我玩起了“比比谁更能熬”的游戏。我坐在椅子上,低头批着奏折,也不理他。
这帮老东西,写的奏折跟裹脚布似的,又臭又长,屁大点事能写三千字废话。我决定了,
以后再有写这种废话文学的,直接赏二十大板。就这么干耗了一炷香的时间,
旁边伺候的小太监先熬不住了,小碎步凑到我跟前,压低声音提醒。
“陛下……太傅大人他……跪了许久了……”我抬起头,凉凉地瞥了他一眼:“你是他的人?
”那太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吓得浑身抖成筛子,求救的目光一遍遍地往江弘那边瞟。
江弘依旧闭着眼,捻着佛珠,不为所动。一个没用的小棋子,不值得他开口。我懒得再看,
直接一挥手:“拖下去,掌嘴五十,扔出宫去。朕的身边,不需要别人养的狗。
”两个黑甲卫立刻进来,堵上那太监的嘴,把他拖了出去。御书房里,再次恢复了死寂。
有了这么个小插曲,江弘那老狐狸终于绷不住了,率先开了口。“陛下,小儿顽劣,
冲撞了您。只是……臣听说,您要与江家退婚?”我直接把早就写好的退婚圣旨,
从桌案上扔到他面前。“正好,省得朕再派人给你送过去了。”江弘没有去捡那份圣旨,
而是抬起头,浑浊的老眼里闪着精光。“陛下,您可想好了?江家,与朝中半数文臣,
皆有往来。您若执意如此,恐怕……”他在威胁我。这朝堂,就是个三足鼎立的牌局。
文臣这边,裴如命占一半,江弘领一半。兵权,在顾渊手上。三方势力互相牵制,
把我这个女帝架在火上烤,没给我留下半分喘息的余地。原主那个蠢货,在夹缝里求生存,
妄图通过联姻,拉拢江弘,获得一丝权力。可她自己都只是个被人摆布的棋子,
又如何能上得了棋盘?想破这个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棋盘给掀了!让他们重新洗牌,
我才有机会,在乱局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我用手撑着下巴,
笑吟“吟”地看着他:“当然想好了。江弘,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
江修今日敢在朕面前大放厥词,想必都是你这太傅教得好啊。”我话锋一转,声音陡然变冷。
“怎么?你也想尝尝坐这龙椅的滋味?”“那你也造反呗!”同样的话,我今天说了两次。
江弘定定地看了我许久,那张老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最终,还是把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
“臣……不敢……”他当然不敢。因为裴如命也不敢。他们谁都没有“师出有名”的借口。
就算有,只要其中一方敢先动手,另外两方势力立刻就会联手,把他撕成碎片。他们不敢动。
但我敢。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场豪赌,优势在我。我勾起红唇,
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太傅,既然不敢,那就该把尾巴夹紧了。今天在场的,
可不止朕一个,裴如命也看得一清二楚。”“你想把刀把子,递到他手上吗?
”江弘的老脸彻底白了。他不再说话,默默捡起地上的圣旨,佝偻着背,退了出去。第二天,
京城就传遍了。江家小公子江修,因冲撞圣驾,被其父江太傅亲手打断了腿,锁在府中静养。
满京城都在感叹,真是父慈子孝的一对典范。4打仗,没钱?抄家!第二天一早,
寒国使臣就到了。由宰相裴如命亲自接待。等我慢悠悠地晃到大殿上时,
一眼就看见了裴如命嘴角那抹看好戏的笑。再一看那寒国使臣身后,
跟着一个贼眉鼠眼、其貌不扬的青年,我就猜到了七八分。果然,几句不痛不痒的寒暄之后,
那寒国使臣就抬着下巴,用鼻孔看人,一把将那青年推了出来。
“吾皇听闻容国女帝陛下风华绝代,特命我国三皇子前来和亲,以结两国秦晋之好。
这位便是我国三皇子,最是仰慕贵国风情,想必与陛下一定能琴瑟和鸣。”他嘴上说着和亲,
那语气,却像是赏饭的。送个歪瓜裂枣过来,就是想当众羞辱我,
看我这个孤立无援的女帝怎么下台。大殿上的大臣们,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心,
装起了木头人。毕竟我昨天才把两派的人都给得罪狠了,现在谁也不想出头当这个冤大头。
没人开口?行,我自己来。我嗤笑一声,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殿。“来人,
把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朕绑了!”我话音落下,殿内却无人敢动。
那些侍卫都拿眼去瞟裴如命和江弘。我也不恼,缓缓从龙椅上拿起旁边装饰用的长剑。
这剑沉甸甸的,满是华丽的宝石,中看不中用。我提着剑,一步步走下台阶,
直直地看向裴如命。“怎么,裴相,想让朕亲自动手?”裴如命那张温润如玉的脸,
终于阴沉了下来。他盯着我看了半晌,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抬了抬手。得了宰相的令,
禁卫军这才如狼似虎地冲上来,将那还在叫嚣的寒国使臣和三皇子捆了个结结实实。
“你们敢!文弦月!你想挑起两国战争吗?”使臣还在破口大骂。我嫌他聒噪,
直接道:“堵上他的嘴。”这一次,没人再敢迟疑。大臣们像是终于回过神来,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口诛笔伐,一个个痛心疾首,仿佛我刨了他们家祖坟。
我懒得理会这群嗡嗡叫的苍蝇,直接看向站在武将前列的几个人。“回去告诉顾渊,
让他把寒国也给朕打了。钱不够,马不够,粮不够,就来抄这些叽叽歪歪的大臣的家!
抄出来的钱,全给他送去!”这一下,大殿彻底炸了锅。刚才还义正辞严的大臣们,
瞬间哭天抢地,有几个当场就扯下官帽,说要辞官归隐。我笑着一一应允:“可以。不过,
滚之前,把这些年吃进去的不属于你们的东西,一文不少地给朕吐出来。否则,就不是辞官,
是抄家灭族。”这下,连裴如命和江弘也坐不住了。裴如命的脸黑得能滴出水:“陛下此举,
无异于自毁长城!必将引起朝堂大乱,动摇国本!”江弘也收起了那副仙风道骨的模样,
疾言厉色:“陛下年少,万不可因一时意气,毁了文家百年江山啊!”我笑着拔出剑,
华丽的剑身在殿内烛火下闪着寒光。剑尖,直直地指向他们二人。“想让朝堂稳住,
就让你们手下那群狗,老老实实地把钱给朕掏出来打仗。”“你们想要这江山,
就给朕安安分分地干活。不然,”我笑得灿烂,眼神却如寒冬里的冰,“就都别想要了。
”裴如命的牙都快咬碎了。“文弦月,你疯了!”“是啊,我疯了。”我坦然承认,
一步步逼近他们,“裴如命,江弘,你们敢跟我这个疯子拼吗?”“文家就剩我一个了,
烂命一条,我不怕死。那你们呢?你们身后有偌大的家族,有数不清的荣华富贵。
你们敢用全族人的身家性命,来跟我拼个鱼死网破吗?”他们不敢。奋斗了一辈子,
眼看就离那至高无上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了,他们怎么敢赌?第二天,
一条消息就跟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女帝疯了。在朝堂上当众杀人,
逼捐大臣,还要同时跟两个国家开战。所有人都等着看,我这个疯子,
什么时候会把自己玩死。5想辞官?先把家产留下他们以为用几句谣言就能拿捏我?
我偏要借着这股东风,再烧一把火。我直接下了一道新令:普天之下,减免赋税一成。
刚被我提拔上来的新任户部尚书,当场就坐不住了,一张脸皱成了苦瓜。“陛下,
万万不可啊!国库本就空虚,再减免赋税,那……那下官就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也变不出银子来啊!”我笑眯眯地看着底下战战兢兢的众人:“爱卿莫急,国库里没钱,
不是还有各位爱卿吗?”“从今日起,七品以上官员,
按家中妻妾子女、奴仆护院的人头收税。五品以上,双倍。”这朝堂腐败到了什么地步?
一个清水衙门的七品小官,家里都能养着十几房小妾,奴仆更是数都数不清。这道政令一出,
朝堂上顿时哀鸿遍野。不少官员当场就递上了辞呈,哭着喊着要告老还乡。
我笑呵呵地将辞呈一一收下,等他们哭得差不多了,才慢悠悠地补上下一句。“准了。
辞官可以,按我大容律例,辞官还乡者,朝廷赐银十两,以安度晚年。其余家产,
全部充入国库。”这一下,已经有人气得开始破口大骂了。但他们刚骂出声,
就齐刷刷地闭上了嘴。因为不知何时,殿门外已经站满了身穿黑色甲衣、手持长枪的士兵。
他们面无表情,眼神森冷,将整个大殿围得水泄不通。这是顾渊临走前,我跟他做的交易。
我给他钱,他给我人。这一万黑甲卫,便是他留给我保命的底牌。看着这阵仗,
在场的人脸都白了,一个个抖如糠筛。当然,除了裴如命和江弘,
以及他们身边几个真正的心腹。那两只老狐狸,依旧是那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
冷眼看着我到底要怎么收场。我当然不会把这些被他们抛弃的棋子真的逼上绝路。人嘛,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死不了心。我继续开口,声音里带着诱哄:“当然,
各位爱卿为国操劳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朕也不是不近人情。
”看着他们眼中重新燃起的希望,我笑弯了眼。“这样吧,朕跟你们玩个游戏。
”“只要你们能举荐出真正有才干、能胜任本职的人来,朕就酌情,让你们抵扣一部分家产。
”“举荐的人越能干,给国家赚的钱越多,你们能带走的家产,就越多……”我话还没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