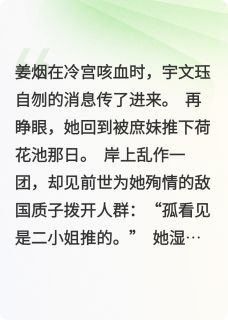1金凤凰的坠落养母临终前递给我一张泛黄地址:“去找你亲妹妹,替我赎罪。
”推开生锈铁门,生母把抹布砸我脸上:“金凤凰飞错窝了?滚!
”聋哑妹妹用猩红的眼瞪我,手语打得像刀:“小偷!滚出我家!
”香槟塔折射着水晶吊灯刺眼的光,空气里浮动着昂贵香水、雪茄和法式甜点腻人的甜香。
我的二十八岁生日宴,在自家临湖的玻璃宴会厅里,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身上这件当季高定礼服,据说是母亲特意从巴黎空运回来的,浅金色的丝绸紧贴着皮肤,
冰凉顺滑,却莫名让我觉得像一层裹尸布。“安宁,快过来!
”养母许太太的声音带着惯有的、不容置疑的亲昵,穿过人群。她保养得宜的手腕上,
那串帝王绿翡翠镯子水头极好,在她招手时映着灯光,绿得晃眼。
她身边围着几个珠光宝气的太太,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聚焦在我身上。
我端着几乎没动过的香槟,努力维持着嘴角的弧度,像个提线木偶般走过去。
高跟鞋踩在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空洞的回响。“瞧瞧我们安宁,
真是越大越有许太太当年的风范了!”王太太笑着奉承,眼神却带着审视。“可不是嘛,
许太太好福气!”李太太附和,目光扫过我颈间,“哎哟,
这项链……是许太太上个月拍的那条‘人鱼之泪’吧?真是疼女儿!
”我下意识地摸向锁骨间那颗冰凉的蓝钻。这是养母半小时前亲手给我戴上的,沉甸甸的,
像一道枷锁。养母的笑容雍容华贵,伸手亲昵地替我理了理耳边的碎发,
指尖带着凉意:“我的安宁,自然值得最好的。”她的目光扫过全场,带着女主人的矜持,
“今天大家尽兴,酒水管够!”话音未落,一个侍应生端着托盘匆匆穿过人群,
不小心被某位太太的曳地长裙绊了一下,身体猛地前倾!托盘上几杯斟满的香槟瞬间脱手,
划着弧线,精准无比地朝着我泼洒而来!“啊——!”惊呼声四起!冰凉的酒液混合着气泡,
劈头盖脸地浇下!瞬间浸透了我精心打理的头发、昂贵的礼服前襟!
浅金色的丝绸狼狈地贴在皮肤上,深色的酒渍迅速晕开,如同丑陋的伤疤!
香槟顺着头发、脸颊狼狈地往下淌,滴落在冰冷的地板上。
几片柠檬片滑稽地粘在我的头发和肩膀上。时间仿佛凝固了。巨大的屈辱感像滚烫的岩浆,
瞬间从脚底板直冲头顶!脸颊火烧火燎,全身的血液都涌了上来!
清晰地感觉到周围那些目光——震惊、错愕、幸灾乐祸、强忍的笑意……像无数根烧红的针,
密密麻麻地扎在我身上!“哎呀!我的镯子!
”养母许太太的惊呼声带着一种夸张的、撕裂空气的尖利,瞬间压过了所有的嘈杂!
她猛地抬起手腕,脸色煞白,声音因为“惊怒”而颤抖:“我的镯子!我的翡翠镯子不见了!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从狼狈不堪的我身上,聚焦到养母那只空荡荡的手腕上!
刚才还绿意盎然的帝王绿镯子,此刻不翼而飞!死寂。令人窒息的死寂。养母的目光,
像淬了毒的冰锥,缓缓地、带着一种令人心寒的审视,
一寸寸地扫过我湿透的、紧贴身体的礼服前襟,最后死死地钉在我脸上!她的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寂静的宴会厅,
带着一种沉痛的、难以置信的冰冷:“安宁……刚才……只有你离我最近……”轰——!!!
仿佛一颗炸弹在脑子里炸开!我瞬间懵了!全身的血液仿佛在刹那间冻结!
难以置信地看着养母那张写满“失望”和“痛心”的脸!她……她在暗示什么?!
周围的抽气声和窃窃私语如同潮水般涌来!
“天啊……不会吧……”“刚才好像就她们母女俩站一起……”“啧,
听说不是亲生的……”“为了条镯子?不至于吧……”每一句低语,每一个眼神,
都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反复切割!我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扼住,
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徒劳地摇头,眼泪混合着冰凉的香槟,滚烫地流下。
“妈……我没有……”我的声音嘶哑破碎,带着绝望的颤抖。养母却猛地别开脸,
不再看我,仿佛多看一眼都嫌脏。她用手帕按着眼角并不存在的泪,声音带着哽咽,
对旁边的管家吩咐:“还愣着干什么!报警!立刻报警!我许家容不下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人!
”“报警”两个字,像最后的宣判,彻底将我钉死在耻辱柱上!管家面无表情地走过来,
像对待一件肮脏的垃圾,冰冷而强硬地抓住了我的胳膊:“**,请配合一下,
去休息室等警察。”“放开我!不是我!我没有偷!”我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
猛地挣扎起来,声音凄厉!香槟残液甩落,溅在管家笔挺的西装上。
周围的宾客像躲避瘟疫一样纷纷后退,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厌恶。
那些平日里亲热地叫着“安宁”的叔叔阿姨,此刻只剩下冷漠的看客嘴脸。
巨大的、冰冷的绝望瞬间将我淹没!就在这时,我的“妹妹”,养母的亲生女儿许安然,
像一只骄傲的孔雀,分开人群走了过来。她身上穿着最新款的Valentino高定,
妆容精致,脖子上戴着一条耀眼的钻石项链。她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狼狈的样子,
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胜利者般的讥诮弧度。她伸出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
慢条斯理地、极其轻佻地拨弄了一下我颈间那条沾满酒渍的“人鱼之泪”蓝钻项链,
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的人都听清:“姐姐,妈给你的‘人鱼之泪’还不够吗?
非要……偷那只镯子?”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我湿透的前胸,恶意几乎要溢出来,
“还是说……你觉得妈给你的……都是假货?”“假货”两个字,像两记响亮的耳光,
狠狠扇在我脸上!我猛地想起刚才养母亲手为我戴上项链时那意味深长的眼神!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电般劈入脑海!难道……我颤抖着手,猛地抓住颈间的项链坠子!
那颗硕大的蓝钻在混乱的光线下,折射出的光彩……似乎……有些不对?过于刺眼,
缺少了顶级钻石应有的温润深邃感?周围瞬间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紧接着是更加肆无忌惮的、压抑不住的嗤笑声!“天!真是假的!”“赝品!
戴个假货还偷东西!”“啧,许家养了只白眼狼!”最后一丝尊严被彻底碾碎!
我像被剥光了丢在冰天雪地里,全身冰冷,止不住地颤抖!养母冷漠的侧脸,
许安然恶毒的笑容,宾客们鄙夷的目光……交织成一张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网,
将我死死困住!原来……这场盛大的生日宴,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为我准备的羞辱!
目的,就是为了此刻,将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巨大的悲愤和灭顶的绝望,
让我眼前阵阵发黑。管家冰冷的手像铁钳一样箍着我的胳膊,将我粗暴地往外拖。
我最后看了一眼养母许太太。她依旧用手帕按着眼角,避开了我的目光。
但嘴角那丝极快掠过的、冷酷的弧度,像一把淬毒的冰刀,狠狠扎进了我的心窝!
浑浑噩噩地被“请”回房间,像个等待发落的囚徒。
门外隐约传来养母安抚宾客、处理“失窃事件”的声音,虚伪得令人作呕。没过多久,
管家敲门进来,身后跟着养母的私人律师,张明远。张律师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金丝眼镜后的目光锐利而冰冷,带着职业性的疏离。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声音平板无波,
没有任何感**彩:“许**,夫人念在多年情分,镯子的事不予追究。
但许家……容不下品行有失的人。
这是夫人委托我拟好的声明和……一份放弃遗产继承权的协议。签了它,夫人会给你一笔钱,
足够你下半生衣食无忧。今晚就离开。以后……好自为之。”放弃遗产声明?断绝关系?
我看着那份冰冷的文件,又看了看张律师那张毫无波澜的脸,
巨大的荒谬感和更深的寒意席卷全身。原来……这才是最终目的。用一个卑劣的栽赃,
彻底斩断我与许家的联系,让我净身出户!心,彻底死了。我没有哭闹,也没有争辩。
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我拿起笔,在张律师指定的地方,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许安宁。每一笔,都像在亲手埋葬过去的二十八年。放下笔,
我甚至没有再看那份文件一眼,也没有再看张律师。转身,开始机械地收拾东西。
属于“许安宁”的奢侈品、珠宝、华服,我一件没拿。
只带走了几件自己用稿费买的普通衣物,一个旧笔记本电脑,
有……钱包里那张珍藏的、早已模糊的童年照片——照片上的小女孩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裙子,
笑容却灿烂得像阳光。那是被领养前的我,仅存的模糊印记。拖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在管家和佣人无声的注视下,我像个幽灵,走出了这座生活了二十八年、金碧辉煌的牢笼。
厚重的雕花大门在身后缓缓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彻底隔绝了那个虚假的世界。
深秋的夜风冰冷刺骨,卷起地上的落叶。我站在空旷的别墅区外,路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很孤单。回头望去,那栋灯火通明的巨大别墅,像一个冰冷的、张着巨口的怪兽。再见了,
许安宁。2清水塘的真相从现在起,我只是秦芳。地址上那个地方,
位于城市地图几乎被遗忘的角落,一个叫“清水塘”的棚户区。
出租车司机在狭窄、污水横流的巷口停下,皱着眉收了钱,像逃离瘟疫般一脚油门开走了。
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煤球燃烧的刺鼻气味、腐烂垃圾的酸臭和公厕飘来的浓重氨味。
脚下的路坑坑洼洼,积着浑浊的污水。低矮、歪斜的砖房挤在一起,
墙壁上布满油烟熏出的黑痕和乱七八糟的涂鸦。晾晒在竹竿上的廉价衣物在风中飘荡,
像招魂的幡。我拖着行李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昂贵的羊皮靴很快沾满了污渍。
按照门牌号,停在了一扇锈迹斑斑、油漆剥落的绿色铁门前。门牌号模糊得几乎看不清,
门缝里透出昏黄的光线和隐约的电视声。心,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着。紧张,不安,
还有一丝连自己都说不清的、微弱的期盼。我深吸了一口带着浓重异味的空气,鼓起勇气,
抬手敲响了门。“谁啊?”一个粗哑的、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女声从里面传来,
带着明显的不耐烦。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一条缝。
一张刻满了风霜和劳苦的脸出现在门缝后。女人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枯黄,
胡乱地用一根黑色橡皮筋扎着。眼角嘴角下垂,法令纹深刻得如同刀刻。
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沾着油污的深蓝色工装外套。她的眼神浑浊,
带着长期疲惫生活磨砺出的麻木和警惕,上下打量着我,像在看一件来历不明的物品。
她的目光扫过我身上质地精良但沾了污渍的大衣,扫过我脚上价格不菲的靴子,
最后落在我那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行李箱上。那浑浊的眼底,
瞬间涌起一股浓烈的、毫不掩饰的……厌恶和怨怼!“找谁?”她的声音又冷又硬,
像块石头。“请问……周桂兰女士是住这里吗?”我喉咙有些发干,
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是……秦芳。”听到“秦芳”这个名字,
女人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那双浑浊的眼睛猛地睁大,死死地钉在我脸上!那眼神,
不再是麻木,而是瞬间燃起了熊熊的怒火和……深入骨髓的恨意!“秦芳?
”她重复了一遍,声音陡然拔高,尖利得像砂纸摩擦,“哈!
你就是那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秦芳?!”没等我反应,她猛地拉开了门!
一股更浓重的油烟和潮湿霉味扑面而来!她抓起门边脏水桶里一块油腻发黑的抹布,
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朝我脸上砸了过来!“啪!”带着馊臭味和冰冷油腻的抹布,
重重地糊在了我的脸上!“滚!”女人——我的生母周桂兰,用尽全身力气嘶吼着,
唾沫星子喷溅在我脸上,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刀子,“拿着你金凤凰窝里掉下来的毛,
滚回你的金窝去!少来这穷酸地方恶心人!这里没你的地方!滚!
”巨大的羞辱感和冰冷的现实,像一盆冰水,狠狠浇灭了我心底最后一丝微弱的火苗。
脸上油腻冰冷的触感和刺鼻的馊臭,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僵硬地站在原地,
抹布从脸上滑落,掉在沾满泥污的靴子上。
“妈……”一个极其微弱、带着怯生生的试探的声音,从周桂兰身后昏暗的屋子里传来。
我下意识地抬眼望去。周桂兰身后狭窄的过道里,站着一个女孩。她看起来二十岁左右,
身材纤细得有些过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明显不合身的旧毛衣。头发有些枯黄,
脸色是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最令人心惊的是她的眼睛——很大,黑白分明,
却空洞得没有一丝神采。此刻,这双眼睛正茫然地“望”着我的方向。她的双手垂在身侧,
手指纤细,却有些神经质地蜷曲着。她的左腿……似乎有些不自然的僵硬?
站立时重心明显偏向右边。安然?我的……孪生妹妹?许安然口中那个“又聋又哑的残废”?
巨大的冲击让我一时失语。这就是……我错位了二十八年的人生里,另一个“我”?
那个替我承受了所有贫瘠、苦难和不幸的影子?周桂兰察觉到我的目光,猛地侧身,
像护崽的母兽一样挡在了女孩身前,用身体隔绝了我的视线。她回头对女孩吼了一句,
语气是截然不同的、带着一种粗暴的安抚:“安然!回屋去!没你的事!
”那个叫安然的女孩身体瑟缩了一下,空洞的大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她似乎想说什么,
嘴唇动了动,却只发出几声模糊的、如同幼兽般的“啊……啊……”声。她听不见,
也说不出。但她没有走。那双空洞却异常执拗的眼睛,依旧穿过周桂兰的肩膀,
死死地、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浓烈得近乎实质的怨恨,钉在我身上!然后,她抬起了手。
那双手,手指纤细却显得有些笨拙,带着一种长期劳作留下的粗糙痕迹。她开始飞快地比划!
动作幅度很大,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愤怒!像两把无形的尖刀,在空气中狠狠劈砍!
她的眼睛死死瞪着我,因为用力,苍白的脸颊泛起不正常的红晕,额角的青筋都微微凸起!
每一个手势都充满了刻骨的怨毒和排斥!虽然我不懂手语,但那肢体语言传达出的意思,
强烈到足以刺穿一切语言障碍:“小偷!”“骗子!”“滚出去!”“这是我的家!
滚!”最后那个“滚”的手势,她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手臂猛地挥出,直直指向门外!
指尖因为用力而颤抖!那无声的控诉,像无数把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我的心脏!
比刚才那块肮脏的抹布更让我痛彻心扉!我像个闯入者,一个掠夺者,
一个被亲生母亲和孪生妹妹同时憎恨驱逐的……罪人。行李箱的拉杆被我攥得死紧,
指节泛白。我最后看了一眼周桂兰那张写满憎恶的脸,
看了一眼安然那双燃烧着无声怒火和泪水的空洞眼睛。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浸了水的棉花,
又酸又涩。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弯下腰,捡起地上那块油腻肮脏的抹布,
轻轻放在门边的破旧木凳上。然后,我拉起行李箱,转身,一步一步,
走进了棚户区昏暗污浊的夜色里。身后,那扇锈迹斑斑的绿铁门,“砰”地一声,
被重重摔上!隔绝了两个世界。3无声的控诉我在离清水塘不远的一个老旧小区里,
租了一个只有十几平米的单间。房间狭小、潮湿,墙壁斑驳,家具是房东淘汰下来的旧货,
带着经年的污渍和霉味。但这里便宜,且暂时能让我栖身。养母“给”的那笔钱,
像烧红的烙铁,被我原封不动地锁进了抽屉最深处。
我用自己工作几年攒下的积蓄支付了房租,
又去附近的批发市场买了最便宜的被褥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当我把那张小小的单人床铺好,
环顾着这个冰冷简陋的“家”时,巨大的落差感像潮水般涌来。从云端跌落泥潭,
不过一夜之间。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我还是去了清水塘。不是为了认亲,而是……为了安然。
那个无声控诉我、眼神里充满怨恨的妹妹。她的腿伤,她那空洞的眼睛……像一根刺,
扎在我心里。我买了一些水果和营养品,还特意挑了一盒看起来很松软的奶油蛋糕。
走到那扇熟悉的绿铁门前,我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再次敲响了门。开门的依旧是周桂兰。
看到是我,她脸上的厌恶丝毫不减,像驱赶苍蝇一样挥着手:“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让你滚吗?这里不欢迎你!”“阿姨,”我放低了姿态,将手里的东西往前递了递,
“我……我买了点东西,给……给安然……”周桂兰的目光扫过我手里的东西,
尤其是那盒包装精美的蛋糕,眼神里掠过一丝复杂,但很快又被更深的冷漠覆盖。
她冷哼一声:“用不着!我们穷酸命,吃不起金贵东西!拿走!”说着就要关门。
“妈……谁啊?”安然的声音从屋里传来,带着一丝怯生生的好奇。
她的身影出现在周桂兰身后,空洞的眼睛“望”向门口。周桂兰的身体僵了一下,
没好气地回头吼了一句:“没谁!收破烂的!回屋去!”安然显然不信。她慢慢地挪到门边,
那双空洞的大眼睛,准确地“捕捉”到了我。当看清是我时,
她脸上的那一点点好奇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比昨天更甚的、冰冷的排斥和怨恨!
她猛地抬起手,再次开始快速地比划!动作比昨天更加激烈!充满了驱逐和愤怒!“滚!
”“骗子!”“小偷!偷走我的人生!”这一次,我努力辨认着她的手势,
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紧!偷走她的人生……原来她恨的是这个……她认为,
是我偷走了她本可能拥有的、富足无忧的生活?周桂兰看着安然激动的样子,
烦躁地推了她一把:“行了!闹什么闹!回屋去!”她转回头,恶狠狠地瞪着我,
“看见没?她不想看见你!赶紧滚!别再来添堵!”门再一次在我面前重重关上。
我提着东西,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门外。邻居家有人探头探脑,窃窃私语。
巨大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将我淹没。安然那无声的控诉,像烙印一样刻在脑海里。
但我没有放弃。第三天,第四天……我每天都去。有时带点水果,有时带些小点心。
周桂兰的态度依旧恶劣,十次有九次直接把我关在门外,或者隔着门骂几句。偶尔门开了,
也是冷着脸,勉强把东西接过去,像打发叫花子,然后立刻关门。
安然则永远用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睛“瞪”着我,用手语一遍遍无声地驱赶我。
她从不接受我给她的任何东西,甚至会在我试图靠近时,像受惊的小兽一样猛地后退,
眼神里充满恐惧和警惕。直到第五天下午,我去得晚了些。刚走到巷子口,
就看到周桂兰推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堆满了回收来的纸板和塑料瓶,正艰难地往家走。
她佝偻着背,枯黄的头发被汗水打湿,贴在额角,脸上是深深的疲惫。安然跟在她旁边,
手里也抱着几个空瓶子。她的左腿明显使不上力,走路时一瘸一拐,动作迟缓笨拙。
夕阳将她们一大一小、同样被生活重压扭曲的身影拉得很长。那一刻,
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酸涩,疼痛。我默默地走过去,没有打招呼,
直接伸手扶住了三轮车后面沉重的纸板堆,用力往前推。周桂兰身体一僵,猛地回头,
看到是我,浑浊的眼睛里先是愕然,随即涌起熟悉的厌恶和愤怒:“谁让你碰的!脏手拿开!
”“路不平,我帮你推一段。”我低着头,声音很轻,手上却加了力。周桂兰还想骂什么,
但三轮车因为我的助力确实轻松了不少。她喘着粗气,最终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不再说话,埋头继续拉车。安然抱着瓶子,默默地跟在后面,
空洞的眼睛“看”着我推车的动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也没有再比划驱逐的手势。
就这样,沉默地走完了剩下的半条巷子。到家门口,我松开手。周桂兰头也不回地打开门,
把三轮车推进窄小的院子。安然也抱着瓶子跟了进去。我站在原地,
看着那扇依旧紧闭的绿铁门。夕阳的余晖落在斑驳的门板上,也落在我沾满灰尘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