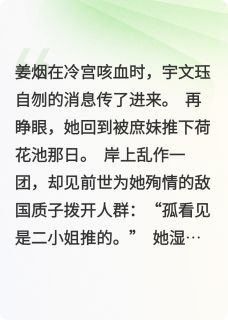结婚六年不孕,婆婆天天逼我喝苦药。直到我在老公书房发现一支验孕棒——阳性。
更致命的是,验孕棒边上是婆婆心腹助理的钥匙扣。我崩溃质问丈夫,
他却递来一份结扎报告:“六年前就做了。”“那孩子是谁的?”我浑身发冷。
婆婆突然推门而入,慈爱地摸着我的头:“儿媳,药不能停啊。”当晚我偷偷倒掉药渣,
里面竟混着白色避孕药片。而丈夫的结扎报告下,
压着婆婆签署的家族信托文件:“若唐瑾无亲生子女,全部财产由指定**人继承。
”**人签名处,赫然是助理的名字。一付蔓端着那碗黑褐色的药汁,指尖被烫得微微发红。
浓烈苦涩的气味直冲鼻腔,熏得她太阳穴突突直跳。这味道早已深入骨髓,
成了她这六年婚姻生活里最刺鼻的背景音。“蔓蔓,趁热喝,凉了药效就差了。
”婆婆周明慧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她坐在客厅昂贵的欧式沙发里,
手里捻着一串油亮的紫檀佛珠,目光却像精准的手术刀,牢牢锁在付蔓手中的药碗上。
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在她保养得宜的脸上投下明暗分明的界限,一半是菩萨般的慈和,
一半是深不可测的阴影。付蔓喉咙发紧,胃里条件反射般泛起一阵酸水。她闭上眼,
屏住呼吸,将那碗滚烫的苦水一股脑灌了下去。黏稠的液体滑过喉咙,
留下火烧火燎的灼痛感和令人作呕的腥苦。她强忍着翻腾的呕意,硬生生咽了下去,
一滴不剩。“妈,我喝完了。”她放下碗,声音有些发虚,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周明慧这才满意地点点头,脸上绽开一个堪称完美的笑容:“这就对了。为了唐家,
为了瑾儿,再苦也得忍着。专家说了,你这体质,就得靠这老方子慢慢调。
瑾儿是唐家的独苗,开枝散叶,是你的本分。”佛珠在她指间不紧不慢地转动着,
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像某种无声的倒计时。付蔓垂着眼,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用那一点尖锐的疼压下心口翻涌的酸楚和无力。六年了。她和唐瑾的婚检报告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写着双方都没问题。可任凭他们如何努力,她的肚子就是不见动静。
婆婆从最初的暗示,到后来的明示,再到如今每日亲自“监工”这碗苦药,
压力像一座无形的山,压得她喘不过气。唯一支撑她的,是唐瑾。
每当她被这药灌得脸色惨白,胃里翻江倒海时,他总会适时地递上一杯温水,
掌心温热地覆上她的手背,低声说:“辛苦你了,蔓蔓。别太有压力,孩子随缘。
”那眼神里的疼惜,是她在这冰冷豪门里唯一的暖意。这份暖意,在半小时后,被彻底冻结,
碾得粉碎。二唐瑾去公司处理急事了。
偌大的别墅只剩下她和几个轻手轻脚、仿佛隐形人的佣人。付蔓习惯性地走进唐瑾的书房,
想帮他整理一下散落在书桌上的几份文件。书房是他的领地,深色调的胡桃木书架顶天立地,
空气里弥漫着他常用的那种清冽的雪松混着淡淡烟草的气息。
她拉开书桌中间那个他常用的抽屉,里面是些钢笔、名片夹之类的杂物。
指尖无意间触碰到抽屉深处一个硬质的方角。不是文件袋的触感。她有些疑惑,往里探了探,
勾出一个巴掌大小的、被揉得有些皱的硬纸盒。目光落在盒子正面的瞬间,
付蔓全身的血液仿佛“唰”地一下退得干干净净。那是一个验孕棒的包装盒。
一个陌生的牌子,不是她常用的那种。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骤然停止了跳动,
随即又疯狂地、失控地擂动起来,撞得她耳膜嗡嗡作响。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猛地窜起,
瞬间席卷全身。她几乎是凭着本能,颤抖着手,在抽屉深处摸索。
指尖很快碰到了一个细长的、塑料质感的东西。她把它抽了出来。三一支用过的验孕棒。
她的视线死死钉在显示窗口上。清晰无比的两道红杠。刺目,狰狞,像两道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她的视网膜上,烫进她的脑子里。阳性。怀孕了!窒息感猛地扼住了她的喉咙。
这不是她的!绝不可能是她的!她上个月刚查过,依旧是冰冷的单杠。绝望的泪水还没干透。
而且,这个牌子……她从未用过。一个恐怖的念头,带着冰冷的毒液,
瞬间注入她的四肢百骸。她僵硬地转动着脖颈,目光像受惊的鸟,
在抽屉凌乱的杂物里疯狂扫视。在几份文件的下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抹鲜亮的颜色刺入了她的眼帘。那是一个小小的、造型别致的金属钥匙扣。钥匙扣上,
挂着一个手工编织的彩色绳结挂饰。样式独特,配色大胆,带着一种年轻女孩特有的张扬。
付蔓的瞳孔骤然缩紧,呼吸彻底停滞。她认得它!记得清清楚楚!四就在上个月,
她参加完一个无聊的太太茶会,身心俱疲地回到家。唐瑾的助理林薇,
那个总是妆容精致、笑容甜得发腻、一口一个“蔓姐”叫得亲热无比的年轻女孩,
正等在客厅。看见她回来,林薇立刻迎上来,
手里还贴心地端着一杯温水——就像每次付蔓喝完那碗苦药后,唐瑾做的那样。“蔓姐,
累了吧?喝口水。”林薇的声音清脆悦耳。付蔓当时心烦意乱,只胡乱点了点头。
林薇放下水杯,大约是看出她情绪低落,便故作轻松地从包里拿出这个小钥匙扣,
献宝似的在她眼前晃了晃,笑容里带着几分得意:“蔓姐,你看,好看吧?
我朋友专门给我做的生日礼物呢,独一无二!”付蔓当时心不在焉,只瞥了一眼,
随口应付了一句:“嗯,挺别致的。”那独特的绳结纹路和跳脱的颜色组合,
让她有那么一点印象。而现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生日礼物,这个属于林薇的小玩意,
正静静地躺在唐瑾的私人抽屉里,躺在一支宣告着怀孕的验孕棒旁边。“嗡——”的一声,
付蔓只觉得天旋地转,耳边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血液冲上头顶的轰鸣。
信任、温存、那些“心疼”的安慰、“坚定”的维护……唐瑾那张总是带着温和笑意的脸,
瞬间在眼前碎裂,扭曲,变成一张无比陌生、无比丑陋的面具!六年喝下的苦药,
婆婆冰冷的眼神和催促,自己内心日复一日的愧疚和煎熬……所有的一切,
在这一刻都变成了最恶毒的笑话!原来他不是没有问题。他只是和她“没问题”!
那碗药的苦味,混合着强烈的羞辱和背叛感,猛地涌上喉头。五她死死捂住嘴,
才没有当场呕吐出来。身体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她扶着冰冷的书桌边缘,
才勉强支撑住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视线模糊了,
巨大的悲恸和一种即将毁灭一切的愤怒在胸腔里疯狂冲撞。她不知道自己在书房里站了多久,
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直到楼下隐约传来汽车引擎熄灭的声音,
然后是唐瑾熟悉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踏上楼梯,朝着书房的方向走来。那脚步声像鼓槌,
一下下敲在她濒临崩溃的神经上。书房的门被推开了。“蔓蔓?
你在……”唐瑾的声音带着一丝工作后的疲惫,
在看到付蔓背对着他、僵立在书桌前的背影时,戛然而止。付蔓猛地转过身。
她的脸色惨白如纸,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因为用力抿着而微微泛青。
那双总是含着温柔笑意的眼睛,此刻却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寒潭,
里面翻滚着惊涛骇浪般的痛苦、难以置信,还有……一种唐瑾从未见过的、冰冷刺骨的恨意。
她手里紧紧攥着那支验孕棒和那个刺眼的钥匙扣,指关节因为用力而绷得发白,
几乎要将这两样东西捏碎。唐瑾的目光落在她手中的东西上,脸上的疲惫瞬间冻结,
随即被一种巨大的震惊和慌乱取代,瞳孔猛地一缩。“蔓蔓,
你听我解释……”他下意识地上前一步,声音干涩发紧。“解释?”付蔓的声音嘶哑得厉害,
像是砂纸摩擦着喉咙,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淋淋的颤抖和尖刻的嘲讽。她举起那支验孕棒,
两道红杠在灯光下刺眼得如同嘲笑,“解释这个?
解释林薇的钥匙扣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抽屉里?唐瑾!”她猛地拔高声音,尖锐得几乎破音,
压抑了六年的委屈、痛苦和此刻滔天的背叛感如同火山般喷发出来,
“六我像个傻子一样喝了六年的苦药!六年!婆婆天天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
我每天都在想,是不是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才不配当母亲!结果呢?
”她往前逼近一步,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唐瑾煞白的脸,泪水终于汹涌地冲出眼眶,
滚烫地滑过冰冷的脸颊,砸在地板上。“结果是你!是你在外面养了个小的!
还让她怀了你的野种!唐瑾!你告诉我!这六年的药,我喝下去的都是什么?
是我自己的愚蠢吗?是你和你妈合起伙来给我灌的迷魂汤吗?”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像风中残烛,随时都会熄灭,“看着我把那些苦水当救命稻草一样灌下去,
看着我在你妈面前抬不起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痛快?
是不是在心里笑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巨大的痛苦和愤怒抽空了她所有的力气,
质问到最后,只剩下破碎的呜咽。她死死抓着桌沿,支撑着自己不滑倒在地。
唐瑾的脸色由白转青,嘴唇翕动着,看着付蔓崩溃的样子,
他眼中掠过浓重的痛苦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挣扎。他猛地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大步走到书桌旁,弯腰拉开了最下方那个带锁的矮柜——付蔓平时很少留意的地方。
他动作有些粗暴地翻找着,几份文件被带了出来,散落在地。终于,
他抽出一个薄薄的牛皮纸文件袋,手指竟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转过身,
没有看付蔓的眼睛,只是沉默地将那个文件袋递到她面前,仿佛那里面装着千钧重担。
付蔓泪眼模糊地看着他,巨大的悲愤让她甚至不想去接。但唐瑾固执地举着,
手指关节绷得发白。她颤抖着,一把抓过文件袋,用力撕开封口。几张纸滑了出来。
最上面是一份打印的医疗报告。
付蔓的目光落在报告抬头的医院名称和日期上——那是他们婚前体检的同一家顶级私立医院,
日期赫然是六年前,他们结婚前的一个月。她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她。
视线飞快地向下扫去,掠过那些复杂的医学术语,最终死死钉在报告末尾的“结论”栏。
那行加粗的黑体字,像淬了毒的冰锥,
狠狠扎进她的眼底:【手术名称】输精管结扎术【术后诊断】手术成功。永久性避孕。
【患者签字】唐瑾日期清晰无误,正是六年前。“轰隆!
”付蔓只觉得脑子里仿佛炸开了一个惊雷,震得她魂飞魄散!她所有的愤怒、控诉、指责,
在这一纸冰冷清晰的报告面前,瞬间变得无比可笑,无比苍白!
她捏着报告的手指抖得如同筛糠,纸张发出不堪重负的簌簌声。她猛地抬起头,
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瞪着唐瑾,
那眼神充满了极致的震惊、荒谬和一种被推入更深更冷深渊的恐惧。
嗓子像是被滚烫的砂砾堵住,嘶哑得几乎不成调:“六……六年前?你……结扎了?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血沫,“那……那林薇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头顶,瞬间蔓延到四肢百骸,她浑身冰冷,如坠冰窟。
书房里死一般的寂静。空气沉重得如同凝固的铅块,压得人喘不过气。
只有付蔓急促而破碎的喘息声,还有她自己血液冲上太阳穴的疯狂鼓噪。唐瑾的脸色灰败,
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眼神里充满了痛苦、愧疚和一种深深的无力。
他避开付蔓那几乎要将他凌迟的目光,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成了拳,指节捏得咯咯作响,
却终究一个字也没能吐出来。这无言的沉默,比任何辩解都更令人心胆俱裂!
八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中,
书房虚掩的门被一只保养得宜、涂着精致裸色甲油的手轻轻推开了。周明慧站在门口。
她脸上依旧是那副菩萨低眉般的慈和表情,仿佛刚才书房里那场山崩地裂的争吵从未发生。
她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关切,
目光柔和地落在付蔓那张惨白如纸、泪痕交错、写满了惊骇与绝望的脸上。“蔓蔓?
”周明慧的声音温和得如同春风拂面,她款步走了进来,
身上名贵的真丝旗袍随着步伐轻轻摇曳。她径直走到付蔓面前,
无视了散落在地上的验孕棒、钥匙扣和那份刺眼的结扎报告,仿佛它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尘埃。
她抬起手,带着一种近乎宠溺的姿态,轻轻抚摸着付蔓冰凉汗湿的额头,
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孩子。她的指尖带着保养品特有的滑腻触感,
却让付蔓感到一种毒蛇爬过般的黏腻和冰冷。“看看你这孩子,怎么哭成这样?
”周明慧的语气带着一丝嗔怪,更多的却是包容一切的宽厚,“夫妻间拌几句嘴是常有的事,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好?”她微微侧头,
目光扫过付蔓刚才放在书桌角上的空药碗,那眼神里飞快地掠过一丝满意,
随即又恢复了那种无懈可击的慈爱。“药喝完了就好。”她微笑着,
加重了抚摸付蔓额头的力道,指尖的凉意仿佛要渗进付蔓的颅骨里,“蔓蔓,听妈的话,
这药啊,一顿都不能停。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唐家香火的大事。你身子骨弱,更要按时调理,
知道吗?”她的声音温和依旧,像最柔软的丝绸,却字字句句都裹着淬毒的尖针,
精准无比地刺进付蔓此刻最鲜血淋漓的伤口!
在丈夫结扎、助理怀孕的惊天真相被血淋淋撕开的当口,婆婆这看似关心的“药不能停”,
无异于最恶毒的诅咒和最**的嘲弄!付蔓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胃里那碗刚灌下去不久的苦药混合着滔天的恨意和恐惧,剧烈地翻滚起来。她猛地偏开头,
躲开了周明慧那只冰冷的手,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
她死死咬住下唇,尝到了浓重的血腥味,才勉强克制住没有当场吐出来或者尖叫出声。
九周明慧的手停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却纹丝未动,眼神深处闪过一丝极快、极冷的锐芒,
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她若无其事地收回手,转向一旁脸色灰败、如同石雕般僵立的唐瑾。
“瑾儿,你也真是的。蔓蔓身子不舒服,你也不多体谅些。”她轻描淡写地责备了一句,
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谈论天气,“公司还有几个文件等着你处理呢,别耽误了正事。
蔓蔓这里有我陪着就好。”她的话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力,像一张无形的网,
将书房里所有失控的情绪都强行按了下去。唐瑾的肩膀几不可查地塌了一下,
他飞快地看了一眼付蔓,那眼神复杂得难以形容,有痛楚,有愧疚,似乎还有一丝……哀求?
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极其轻微地点了下头,脚步有些踉跄地走出了书房,
背影透着一种沉重的疲惫和狼狈。门轻轻合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书房里只剩下付蔓和周明慧。空气里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苦药味、背叛的腥气,
还有周明慧身上那股昂贵却冰冷窒息的香水味。付蔓僵立在原地,身体冰冷,
灵魂却像是在油锅里煎熬。婆婆那慈爱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却像毒蛇的信子,
舔舐着她的皮肤,让她每一根汗毛都倒竖起来。“傻孩子,别站着了,坐下歇歇。
”周明慧仿佛没看见付蔓的抗拒和恐惧,自顾自地在旁边的单人沙发里优雅地坐下,
顺手理了理旗袍的下摆,姿态闲适得如同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品茶。“瑾儿有时候是任性了些,
但他心里是看重你的。男人嘛,在外面难免……唉,”她叹了口气,
语气带着一种过来人的宽容和无奈,“只要他心还在这个家里,知道回家就好。蔓蔓,
你是唐家明媒正娶的媳妇,要大气些,别学那些小门小户的眼皮子浅。把身子调理好,
早日给唐家添个嫡孙,这才是顶顶要紧的正事。”她的话语如同最锋利的软刀子,
一刀刀凌迟着付蔓早已破碎的心。“大气”?“别眼皮子浅”?“添个嫡孙”?
付蔓只觉得一股腥甜猛地涌上喉头,眼前阵阵发黑。她死死掐着自己的掌心,
尖锐的疼痛让她勉强维持着最后一丝清醒。她不能倒下去!绝不能在这个女人面前倒下去!
“妈……我,我有点不舒服,想回房躺一会儿。”付蔓的声音嘶哑得厉害,
每一个字都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周明慧抬眼看着她,目光在她惨白的脸上停留了几秒,
那眼神像在审视一件物品的损耗程度。片刻,她才缓缓绽开一个理解的笑容:“去吧,
好好休息。晚上我让厨房给你炖点燕窝补补。记住……”她的语气陡然加重,
带着一种不容违逆的威严,“药,一顿都不能落下。”最后那句话,像一道冰冷的枷锁,
重重地套在了付蔓的脖子上。十付蔓几乎是逃离般地冲出了书房,
踉跄着冲回二楼自己的卧室。反手锁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
她才像被抽掉了所有骨头一样,软软地滑坐在地毯上。冰冷的泪水再次决堤,
无声地汹涌而出,浸湿了衣襟。书房里那场毁灭性的风暴,婆婆看似关怀实则诛心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