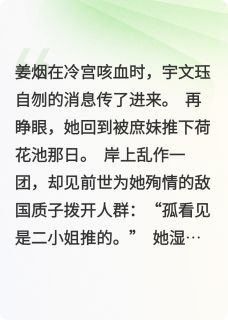我是霸总的白月光替身。兢兢业业当了三年替身,却没想到白月光一回国。我就失业了。
我想小说里的恶毒女配一样,想了很多阴损的招。可是看到白月光的那一刻,
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失魂落魄的去酒吧买醉,
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是硬邦邦的学姐把我抱在了怀里。第二天醒来我浑身酸痛,
看着满身红痕。学姐端着热水走了进来,看着我疑惑的样子。
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你酒精过敏。”在我逐渐被学姐掰弯的时候,
却发现香香的学姐竟然是男的!!1.做替身的第三年,我被扫地出门了。
我那点可怜巴巴的自尊心,和三个歪七扭八的行李箱一起,
被毫不留情地扔在别墅门外湿漉漉的石阶上。轮子坏了一个,箱子像条瘸腿狗,歪斜着,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张妈那张老脸皱成一团,眼神躲躲闪闪,
把最后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帆布包硬塞进我怀里。
声音压得比蚊子哼哼还低:“林**快走吧!”她背后,管家那一声假模假式的咳嗽,
跟催命符似的。正主儿驾到,我这赝品,自然得麻溜儿滚蛋。我仰起脖子,
冰凉的雨水顺着发梢流进领口,激得我一哆嗦。三楼的露台,弧形的玻璃后面,
影影绰绰站着两个人。那个穿着米白色羊绒开衫、背影窈窕的女人,微微侧过头,
耳垂上那一点小小的、褐色的痣,清晰得刺眼。那个位置,我对着镜子,用遮瑕膏点上去,
擦掉,再点上去,再擦掉,足足折腾了三个月。直到有一天,陆沉渊捏着我的下巴,
带着薄茧的指腹用力擦过那个点,他眼底那点千年寒冰才裂开一丝缝隙,
漏出点近乎满意的光。“像。这个位置,”他声音低沉,没什么温度,“很像她。
”模仿她成了我的工作,我的本能,我赖以生存的空气。她唇角上扬的弧度,
她喝咖啡时小指微微翘起的弧度,她说话时尾音那一点点似有若无的娇嗔。
我像个最敬业的演员,演了整整三年,演到连我自己都恍惚,我到底是谁。雨更大了,
砸在脸上生疼。露台上,陆沉渊似乎抬手,极其自然地揽住了苏晚的肩。动作熟稔,
带着一种失而复得的珍重。那画面像根烧红的针,狠狠扎进我眼底。心脏那块地方,
后知后觉地传来一阵闷痛。也好。这场荒谬的替身游戏,终于落幕了。我弯腰,
用力拽起那个轮子坏掉的箱子,帆布包甩到肩上。不再看那刺眼的一幕,
拖着我一地狼藉的“身家”,头也不回地扎进冰冷的雨幕里。背影,大概挺像条落水狗。
震耳欲聋的音乐像无数根针,扎着我的太阳穴。空气里混杂着劣质香水、酒精和汗液的味道,
黏腻得让人窒息。吧台冰凉的触感透过薄薄的衬衫传到皮肤上,我趴在台面上,
眼前的一切都在晃,五彩斑斓的光晕旋转、扭曲。2.“再来一杯!”我用力拍了下吧台,
声音嘶哑,舌头有点捋不直。威士忌那玩意儿,烧刀子似的从喉咙一路滚到胃里,烧得慌,
可那股灼热劲儿,居然奇异地压住了心底那片荒芜的空洞。
酒保小哥面无表情地又推过来一杯琥珀色的液体。我端起杯子,仰头就灌。又苦又辣,
呛得我眼泪鼻涕一起涌出来,狼狈地咳嗽。脑子里走马灯似的闪过露台上依偎的身影,
陆沉渊那三年里偶尔施舍般的温和眼神,还有张妈那躲闪的、怜悯的目光,
最后定格在苏晚耳垂上那颗小小的痣上。**像啊。像到我有时候都分不清。
陆沉渊透过我这张脸,看的到底是谁。心口那股被酒精暂时压下去的闷痛又泛了上来,
带着一股酸涩的腥气直冲喉咙。我捂住嘴,跌跌撞撞地从高脚凳上滑下来,
凭着最后一点模糊的意识,朝着记忆中洗手间的方向踉跄冲去。灯光在头顶诡异地旋转,
地板像波浪一样起伏。人群的缝隙变得狭窄而扭曲,我像个失控的保龄球,撞了好几个人。
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对不起,换来几声不耐烦的咒骂。脚下猛地一绊,身体彻底失去了平衡。
我甚至没来得及惊呼一声,就朝着坚硬冰凉的地板直挺挺地栽下去。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
一双手臂,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稳稳地捞住了我。那手臂很有力,隔着薄薄的衣料,
能感觉到底下肌肉的轮廓,硬邦邦的。一股清冽的、带着点冷调的雪松气息,
混合着一丝极淡的消毒水味道,强势地冲破了周遭浑浊的空气,钻进我的鼻腔。
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下意识地死死揪住了对方胸前的衣服。布料是柔软的棉质,
触感陌生。“唔……”我晕得厉害,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呜咽,努力想抬起头看清是谁。
视线所及,是线条清晰流畅的下颌,还有一小段在昏暗灯光下显得异常白皙的脖颈。再往上,
是一双垂下来的眼睛。光线太暗,看不清具体模样,只觉得那目光沉沉的,带着点审视,
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站稳。”声音在头顶响起,一时分不清是男声还是女声。
不是陆沉渊那种低沉。就很……特别。脑子里乱成一锅粥,酒精彻底烧断了理智的弦。
管他是谁呢。我像个树袋熊一样,
把全身的重量都挂在了这具硬邦邦的、散发着好闻雪松味的身体上,
脸颊蹭着那片柔软的棉布,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姐姐,带我走,
好晕……”彻底失去意识前,最后的感知是身体被横抱起来,
那硬邦邦的怀抱出乎意料的稳当。3.意识是被一种陌生的酸痛唤醒的。
眼皮沉重得像灌了铅,费了好大劲儿才勉强掀开一条缝。头顶是陌生的天花板,简洁的线条,
暖白色的吸顶灯,散发着柔和的光。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洗衣液清香。
不是陆沉渊那间奢华冰冷、永远弥漫着昂贵雪茄味的主卧。我艰难地转动僵硬的脖子,
打量四周。房间不大,布置得极简,色调是舒服的米白和浅灰,干净得一丝不苟。
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清晨灰蒙蒙的天空。昨晚。酒吧。那个硬邦邦的怀抱,雪松味。
记忆碎片猛地涌上来,我心脏一缩,下意识地掀开盖在身上的薄被。低头一看,
浑身的血液“嗡”地一下全冲到了头顶!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质地柔软的纯棉T恤,
明显是男款的。更要命的是,**在外的皮肤上,从锁骨到手臂内侧,甚至蔓延到胸口上方,
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红痕!透着点说不出的暧昧。我惊恐地坐起身,薄被滑落,凉意瞬间袭来,
也让我看清了更多。腰侧,大腿外侧都有!“醒了?”一个清泠泠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瞬间把我从混乱的思绪里拽了出来。我猛地抬头。门口站着一个人。高挑,清瘦。
穿着简单的白色家居服,裤腿宽松。黑色的长发柔顺地垂在肩头,发梢微卷,
带着刚洗过的湿气。此刻正平静地看着我,没什么多余的情绪。
她手里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白瓷杯。昨晚酒吧里光线太暗,
我只记得那个硬邦邦的怀抱和模糊的下颌线。现在看清了,原来她这么高?
学姐端着杯子走过来。她在我床边坐下,离得不远不近,那股清冽的雪松气息更清晰了。
她把温热的杯子递到我唇边,里面是淡黄色的液体,散发着淡淡的蜂蜜甜香。“温蜂蜜水,
”她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却奇异地带着一种让人安定的力量,“解酒,喝了舒服点。
”我像个提线木偶,被她平静的目光笼罩着,下意识地就着她的手喝了一口。
温热的甜水滑过干涩的喉咙,确实舒服了些。但身体上的酸痛和那些刺眼的红痕,
像针一样扎着我。“我……”声音沙哑得厉害,眼神不受控制地往自己身上那些红痕瞟,
充满了疑问。学姐的目光顺着我的视线,落在我锁骨那片最密集的红痕上。
她的眼神闪过一丝回味。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我心脏差点停跳的事。她伸出了手。
微凉的指尖,带着薄薄的茧,极其自然地、轻轻地拂过我颈侧那片敏感的皮肤,
掠过那些暧昧的红痕。我浑身一僵,像被电流击中,汗毛都竖起来了。“别担心,
”她的指尖离开,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听不出任何波澜,“你酒精过敏。
”酒精……过敏?我懵了。我活了二十三年,啤酒都能吹瓶的人,什么时候对酒精过敏了?
“我……”我试图反驳,声音却卡在喉咙里。宿醉的头痛,身体的酸痛,
还有眼前这人过于冷静强大的气场,让我脑子一片浆糊。“你昨晚在酒吧醉得很厉害,
吐了两次,还一直抓挠自己。”她收回手,
端起蜂蜜水又递到我唇边:“这些红痕是你自己抓出来的。吐脏的衣服我帮你换了,
我的T恤,干净的。”我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红痕,
又看看学姐那双平静无波、坦坦荡荡的眼睛。昨晚断片前的记忆确实模糊不清,
只记得自己很难受,好像真的在抓挠……难道…真的是我自己挠的?酒精过敏还有这种症状?
我紧绷的神经瞬间松懈下来。后怕和委屈涌了上来,鼻子有点发酸。“谢……谢谢学姐。
”我小声嗫嚅着,接过她手里的蜂蜜水,小口小口地喝起来,不敢再看她。
那微凉的指尖触感,似乎还残留在我皮肤上,带着一种奇异的酥麻。4.学姐叫沈言。
名字和她的人一样,带着点清冷的书卷气。她收留了我。理由很简单,
也很符合她言简意赅的风格:“客房空着,你找到地方前可以住。
”我拖着我的“瘸腿”行李箱和帆布包,正式入住了沈言这套位于市中心高级公寓的小次卧。
房间不大,朝北,但收拾得干净整洁。窗外是林立的高楼和川流不息的车河,繁华又疏离。
沈言的生活规律得像台精密仪器。早上七点准时起床,厨房会传来轻微的响动,
然后是咖啡机工作的声音。等我顶着鸡窝头、挣扎着爬起床时。
餐桌上通常已经摆好了简单的早餐。她自己则端着一杯黑咖啡,
坐在晨光里看平板电脑上的财经新闻,侧脸线条干净利落。她话很少。大部分时间,
公寓里安静得只剩下钟表指针走动的滴答声,或者她敲击笔记本电脑键盘的清脆声响。
这种安静,起初让我窒息。习惯了陆沉渊别墅里佣人的小心伺候,
也习惯了那三年里时刻紧绷着模仿另一个人的神经。但很快,
我就发现了沈言没有面上那么冷淡。她会在我笨手笨脚差点把厨房点着时,
不动声色地接过我手里的锅铲,三下五除二挽救那锅面目全非的意面。
她会在我半夜被噩梦惊醒,端着一杯温水递给我,淡淡一句:“做噩梦了?喝点水。
”她会在我对着招聘网站唉声叹气时,
圈出几个合适岗位的招聘信息推到我面前:“试试这几个。”最要命的是,
她身上那股清冽的雪松气息,无处不在。我开始不自觉地关注她。
看她工作时微微蹙起的眉头,看她喝咖啡时握着杯柄的、骨节分明的手指,
看她靠在阳台栏杆上眺望远方时,被风吹拂起的黑色长发。心,像一颗被投入温水里的硬糖,
在沈言无声的、带着雪松气息的温柔里。一点点得偏离了原本的轨道。某个周末的下午,
阳光很好。我窝在沙发上看着肥皂剧,沈言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看书。
她穿着宽松的灰色毛衣,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腕。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她身上,
给她冷硬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连那长长的睫毛都根根分明。鬼使神差地,
我拿起手机,偷偷对着她的侧影按下了快门。咔嚓一声轻响,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
沈言翻书的动作一顿,抬眼看过来。我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脸颊腾地一下烧起来,
手忙脚乱地想藏起手机,像个被抓包的偷窥狂。“拍我?”她挑了挑眉,语气听不出喜怒。
“没…没有!”我矢口否认,声音因为心虚而拔高,“我我拍阳光!对,今天的阳光特别好!
”沈言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双深潭似的眼睛仿佛能洞穿一切。几秒钟后,
她唇角似乎极其细微地向上牵了一下,快得让我以为是错觉。然后,她又低下头,
翻过一页书。“嗯,是挺好。”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仿佛刚才那点小小的插曲从未发生。
可我的心跳,却在她那句挺好里,彻底乱了节奏。咚咚咚,像揣了只受惊的兔子,
在胸腔里疯狂蹦跶。一种陌生的、带着甜意的慌乱,悄然弥漫开来。完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沐浴在阳光里的清冷侧影,脑子里只剩下这两个字。
我好像……真的有点不对劲了。5.我开始像个怀春的傻子,笨拙地靠近沈言这座冰山。
她看书时,我就抱着电脑蹭到旁边的沙发,假装在认真投简历,
实则眼角的余光全黏在她翻书的手指上。骨节分明,修长有力,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
她做饭时,我就赖在厨房门口。她偶尔会对我投来一瞥,眼神依旧平静。但我觉得,
那平静底下,多了一丝纵容。就像看一只在自己脚边笨拙打转、试图引起注意的小动物。
让我胆子也肥了起来。那天逛家居网站,一组模特图猝不及防地撞进我眼里。两个女孩子,
穿着同款不同色的真丝睡裙,依偎在柔软的沙发里,笑容温暖又亲昵。浅紫色和雾霾蓝,
真丝面料流淌着柔润的光泽,蕾丝花边点缀得恰到好处,甜美又不失慵懒。鬼使神差地,
我的手指就点了下去。等我回过神来,订单已经提交成功。完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支付成功,感觉脸颊烫得能煎鸡蛋。我在干什么?给沈言买情侣睡衣?!
她要是发现了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变态?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等待审判的囚徒,坐立不安。
每次门铃响,都吓得我一哆嗦。终于,那个包装精致的快递盒还是被快递员放到了门口。
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把它抱回房间,反锁上门,心脏狂跳。拆开包装,
两件睡裙安静地躺在盒子里,柔软得像云朵,颜色比图片上还要好看。我拿起那件雾霾蓝的,
想象着它穿在沈言身上的样子。冷白的皮肤,被柔和的蓝色衬着,
蕾丝花边缠绕着她修长的脖颈和手腕。“嘶——”我猛地吸了口气,捂住了发烫的脸颊。
不行不行,太**了!礼物送出去那天,我像个上刑场的勇士,抱着盒子,
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了十几圈,手心全是汗。沈言从书房出来倒水,看到我这副样子,
脚步顿住了。“有事?”她端着水杯,靠在门框上,姿态随意,
目光落在我怀里那个扎眼的盒子上。“那个……”我舌头打结,眼神飘忽,根本不敢看她。
“我逛街看到这个,觉得挺适合你的,就顺手买了!”我一股脑把盒子塞进她怀里,
语速快得像机关枪,“你试试!不喜欢就……就扔了!”说完,不等她反应,
我像只受惊的兔子,嗖地一下窜回了自己房间,砰地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
门外一片寂静。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我才听到极轻微的脚步声走向主卧的方向。
她收下了?她会不会试?她穿上会是什么样子?无数个问题在我脑子里炸开,
搅得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出来,
餐桌上依旧摆着温热的牛奶和吐司。沈言已经坐在那里,穿着她惯常的白色衬衫和黑色长裤,
头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清冷又禁欲。没有睡裙。我心头那点隐秘的期待,
像被戳破的气球,噗嗤一下瘪了下去。她肯定觉得我很奇怪吧?我沮丧地拉开椅子坐下,
食不知味地戳着盘子里的煎蛋。“睡裙,”沈言突然开口,声音没什么起伏,
却像一道惊雷劈在我耳边,“很好看。”我猛地抬头,撞进她深潭似的眼睛里。她正看着我,
手里端着咖啡杯。“谢谢。”她又补充了一句。轰——!我感觉全身的血液瞬间涌上了头顶,
脸颊烫得快要冒烟。她试了!她说好看!她还说谢谢!“不……不客气!”我慌忙低下头,
恨不得把脸埋进牛奶杯里,声音细如蚊呐。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鼓,咚咚咚,
震得我耳膜发麻。嘴角却控制不住地拼命往上翘。一顿早餐吃得我魂不守舍,
脑子里全是那件雾霾蓝的真丝睡裙,想象着它包裹着沈言身体的样子。
还有她身上那股好闻的雪松味。完了完了,林晚晚,你没救了。我咬着吐司,在心里哀嚎。
这条名为沈言的弯道,我好像已经一头栽进去,并且……乐不思蜀了。6.公司新项目启动,
连着加了三天班,人都快熬干了。第四天下午,主管大手一挥,
难得开恩:“今天都早点回去,养精蓄锐,明天决战!”我如蒙大赦,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
只想立刻飞回公寓。扑进我那张柔软的小床,睡它个天昏地暗。推开公寓门时,
里面静悄悄的。我把包随手一扔,踢掉鞋子,像一缕游魂飘向自己的房间。经过主卧门口时,
里面隐约传来哗啦啦的水声。哦,沈言在洗澡。这个念头在疲惫的大脑里一闪而过,
没激起半点波澜。我继续梦游般地往前走。一步,两步等等!主卧的门,怎么是虚掩着的?
我下意识地停住脚步,鬼使神差地往里瞟了一眼。就这一眼。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全身的血液,瞬间冲到了天灵盖,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浴室的门大开着,
氤氲的热气正从里面弥漫出来,带着沐浴露的清新水汽。而门口,站着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