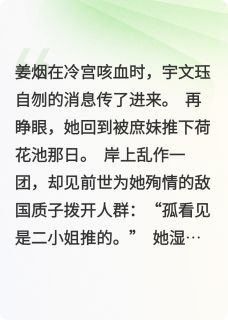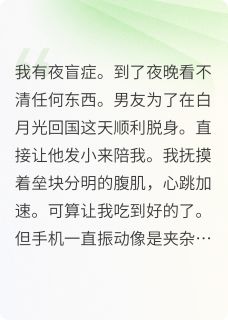
我有夜盲症。到了夜晚看不清任何东西。男友为了在白月光回国这天顺利脱身。
直接让他发小来陪我。我抚摸着垒块分明的腹肌,心跳加速。可算让我吃到好的了。
但手机一直振动像是夹杂癫狂的怒意。“姐姐,不要和他在一起。”“姐姐,求你看看我。
”“姐姐,全世界我最爱你啊。”1恋爱周年纪念日这天,
陈斯年打电话说公司加班要晚点儿回来。我看着一桌子丰盛的菜,深吸一口气。
估计又得进垃圾桶。手机叮咚一响。我以为是陈斯年发来的。下意识翻看信息。“姐姐,
今天一个人在家吗,我好想你。”我怔住,眼神慌乱。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条骚扰短信了。
这几个月内总是断断续续收到。我睡的不太安稳告诉陈斯年。他只觉得无关紧要,
认为是别人的恶作剧罢了。我将短信删除,号码拉黑。
紧接着一条跟着一条的短信让手机振动起来。“他今晚不会回来的。
”“让我和你在一起好吗,姐姐。”“我真的好爱你。”[图片]图片内容模糊不清,
我还是手一抖。就算背影模糊我还是看见那是陈斯年,怀里抱着一个女人,耳鬓厮磨,
表现亲昵。我焦虑啃指甲,将手机关闭。陈斯年明明说的公司加班,怎么会出轨。
就在我极力想为他开脱的时候。眼前一黑。停电了。我慌乱抓起手机,拨打陈斯年电话。
电话那头男人不耐烦的声音响起:“喂,文璟,说了公司应酬打电话催什么。
”我捧着手机看着属于自己的一小圈光晕。声音颤抖,夹杂害怕:“斯年,
家里停电了...你早点回来陪我好不好。”听筒内是长时间沉默,
我甚至还听到女人娇俏的声音。心里头一紧,继续祈求:“斯年,我真的好害怕,
手机快没电了。”我有夜盲症,只要一黑我就看不清任何东西。
空洞洞的黑暗是我最害怕的东西。“好,我尽快赶回来。”得到男人肯定的答复,我松口气。
为了节省手机电量,我将屏幕光打到最低。惶恐不安蜷缩在沙发。
我快不记得陈斯年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只见钥匙转动门阀的声音。昏暗的室内,
隐隐约约看见熟悉的身影。手机恰好没电,我伸出手环抱赶回来的陈斯年。眼前漆黑一片,
让我抱他抱的更紧。陈斯年明显僵住,没有说话,只是借着些许月光将我抱回卧室。“斯年,
公司的事情忙完了吗?”我抬臂圈住他劲瘦腰身,微微皱眉。陈斯年什么时候去锻炼了。
手下意识隔着布料触摸到腹肌,细细数了数。八块?陈斯年在公司都不忘锻炼吗?
其实我和陈斯年已经好几个月没亲密接触了。他总说自己忙。我眷恋般将脸埋在人胸口,
面颊发烫:“斯年,今天是我们恋爱五周年纪念日,我好想你。”他没有说话。
铺天盖地的吻强势入侵,淹没我破碎的音调。2一觉醒来,我腰上酸痛,但身边早已没了人。
晃眼就看见床头柜留下的字条。“早餐在桌上,好好休息。”我脸一红,穿上睡裙。
陈斯年什么时候这么温柔了。跟陈斯年在一起五年,几乎都是我照顾他。
我还记得陈斯年因为白月光出国。在酒吧里喝到烂醉。是我吃力的将他捡回家,细心照顾。
而陈斯年似乎也被我打动。没过三个月,我们就顺理成章在一起了。日子也算蜜里调油。
陈斯年不记得纪念日没关系。我记得就好。他只要愿意回来,心里有我。
我低声笑着看餐桌上的早餐。一勺接着一勺往嘴巴里送肉粥。
给陈斯年发消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眼神扫到新弹出的消息,直接愣住。勺子从掌心内滑落,
在瓷碗里乒乓作响。图片拍的异常清晰。是陈斯年搂着他的白月光景瑶在烟花下接吻。
“姐姐,现在死心了吗?”“你男朋友有别的对象了。”我深吸一口气,
第一次回复这个陌生人的信息。“我男朋友昨天一整夜都在陪我,
请你不要再搞这种ps的拙劣伎俩,小朋友就该好好念书。
”我原以为对面就是一个中二病少年。看了不少奇奇怪怪的小说才会整这一出。
没想到对方并没有知难而退,反而说出真相。“你真以为昨天来你家的是你男朋友吗?
”一则简短的录音揭开真相。“林木,帮我个忙。”“什么忙?”“帮我回家看看文璟,
我俩身形差不多,她有夜盲症,看不出来。”陈斯年轻佻放荡的话让我耳晕目眩。
手指遏制不住颤抖,将这个号码再次拉黑。怎么可能。陈斯年不会这样做。**司楼下,
我局促不安等待陈斯年。熟悉的身影浮现眼前。身姿挺拔绰约,眉宇间的冷漠疏离让我怔神。
陈斯年压着一丝不快,将我牵走。“文璟,这是公司,你来闹什么。
”咖啡杯内是一圈圈涟漪,我抿唇看向陈斯年想得到求证。“斯年,你昨晚回来过对吗?
”陈斯年拧眉,下巴微抬:“不然呐,难不成是别人?”得到肯定的答复,我松口气。
是陈斯年就好。“他在说谎。”“姐姐不要被他骗了。”手机叮咚提示音不断,
一条一条短信让我陷入冰窖。到底是谁,为什么会知道我现在和陈斯年在一起。我慌乱起身,
撞倒咖啡。褐色污渍将我白色裙摆打湿。陈斯年皱眉,不悦昭然若揭。“文璟,你在做什么,
赶紧回家,丢人。”陈斯年抛下这句话,径直就走了。根本没有注意无措的我。
咖啡厅的客人纷纷侧目。我被探求的视线盯的后背灼烧。裙摆上的咖啡渍洇开成花。
鼻尖一酸,心尖苦涩蔓延,看向陈斯年消失的方向。“没事吧。
”温润如玉的声音带着淡淡幽香向我袭来。一件大衣盖在我腿面,遮掩弄脏的裙摆。
我蓦然抬头,撞进那双琥珀色眼眸,碎光尽显。迟疑开口:“林木?”林木扬唇,眼眸弯起。
他跟陈斯年虽然是发小,但跟陈斯年却像两个极端。陈斯年骨子里透着冷漠疏离,五官硬朗,
狭长的眼眸总是深不可测。但林木始终带着丝漫不经心,唇角上扬,
有种让人莫名想要亲近的滋味。两个人在学校里,追求者不断。林木会耐心婉拒女性。
陈斯年则是淡漠回应。所以当时在我摘下这朵高岭之花的时候。室友都无比羡慕。
4我尴尬的绾起头发,掩饰眸子里的慌乱。林木打开车门护住我发顶。狭仄的车内,
只剩下他身上独有的幽香。“定位。”他清嗓唤回我的思绪。我回神在屏幕上输入家的位置。
静谧无言,我想问的话在喉咙内翻涌,直至车辆行驶到小区门口。林木似乎看出我的犹豫,
眉梢微挑。“你想问什么?”被戳破窘意,我偏头对上林木含笑的眸子。
“陈斯年昨晚到底有没有...”“没有。”林木打断我的话,面不改色停稳汽车。
得到肯定答复,我如释重负。下一瞬,林木的话让我如坠冰窖。“景瑶回来了,文景,
你还想在他身边待多久?”嗡地一声,我只觉得颅内有烟花噼里啪啦的炸响。为什么。
为什么都在告诉我景瑶回来了。“你们是什么意思,都觉得我配不上陈斯年吗?
”林木对上我泛红的双眸,僵在原地。虚掩清嗓,宽掌轻轻抚摸过我发顶。
如沐春风的声音掠过耳畔。“文景,你值得更好的。”他顿了顿,
琥珀色的眼眸再次注视我:“陈斯年不该耽误你。”我推开林木的手,薄唇咬紧,
嗫嚅着哆嗦起来:“你们到底想怎么样?斯年他是爱我的!”吼出这句话,
我拉开车门朝着家里奔跑。直到被家里熟悉的气息包裹才敢松懈下来。浑身陡然丧失力气,
慢慢跌坐在地板。良久,直至夜幕降临,我才伸手打开客厅的灯。
拖着疲乏的身体经过陈斯年书房。陈斯年说过,文景在家里你哪里都可以去,
唯独书房不可以。书房的门像旋涡,奇怪的吸引力在指引我打开。咔哒一声,门开了。
就算这里是我住了几年的地方,我还是像个小偷。我伸手想拉开陈斯年上锁的抽屉。
几乎是癫狂着用蛮力,将锁搞烂。一张照片就这么静静躺在抽屉内。眼泪模糊视线,
指尖颤抖拿起照片。大学时候的陈斯年,怀里还抱着景瑶。照片边角翘起,
看起来像在夜里摩挲过很多遍。这一切,都好像是我一厢情愿。
五年都无法暖化冰封的陈斯年。我打电话给陈斯年。机械女音告诉我暂时无法接通。
消息框还停留在昨天,我告诉陈斯年要回家过纪念日的时候。心渐渐冷下去。
陌生号码再次给我传送来一张图片。刺眼的红玫瑰被捧在景瑶怀里,笑靥如花跟陈斯年接吻。
我起身手指摁键盘给陌生号码发去消息。“你不用再告诉我这些了,我和陈斯年分手了。
”再次拉黑,我收敛情绪将家里属于自己的东西收拾整理。天刚破晓,陈斯年没有回来。
我关闭那扇有我和他回忆的门。拖着行李箱离开。就在下楼的转角处,湿帕盖住口鼻。
瞬间昏厥过去。5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一片黑暗。只剩下树枝击打窗柩的声音。
手脚都被麻绳绑在椅子上,我挣扎着想起身。手腕被磨的红肿。
温柔的一双大手就这么轻轻的覆盖,摩挲红肿的位置。“姐姐,你不乖哦,这样会受伤的。
”变声器内是机械男音。我看不清任何东西,只能听见强有力的心跳在耳畔擦过。
在稳住心神后,我开口:“你到底是谁,绑架是违法的。
”我这句话根本没有起到震慑的作用。身上宽掌游走,专注做自己事情。“姐姐,
我喜欢你好久了。”“可是为什么你的目光都在陈斯年身上。”“这么不忠的人,
不配留在姐姐身边。”唇瓣狠狠一痛。轻微铁锈味在空气中逐步蔓延。我被迫扬颅,
两腮被衔住只能忍受男人侵略性的吻。恶心在胃里翻涌,
声音颤抖:“你到底是谁...我要是失踪了陈斯年会来救我的。”那人只是轻蔑一笑,
手掌将我眼睛蒙住。从指缝间我模糊看见视频。景瑶娇俏搂着陈斯年,语气上挑:“斯年,
你整夜陪我,文景知道了怎么办。”“哄哄就行了,她不敢对我生气。
”熟悉又轻蔑的声音灌入耳内。我浑身血液逆流,甩头想要覆盖自己的手掌挪开。
视频被关闭,男人的手掌适时抽离。我也因为没有光线,再次陷入黑暗。
“既然姐姐都和他分手了,那姐姐以后就属于我了。”“疯子。”我嘲讽出声。
耳畔只剩下轻笑。“如果能得到姐姐,就算疯掉又能怎样呐。”一条黑色丝巾覆盖我的眼眸。
漆黑的房间内,没有时间,没有光线,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绑架我的人除了抱着我,
就是温柔亲吻接踵而来。捆绑的麻绳也被替换成了柔软的丝绸。炙热手掌大肆抚摸,
引起身体颤栗。我忍住作恶,沉重闭上眼眸。我就这么被囚禁在陌生人家里,不知道日夜。
6房门突然被打开,我惊恐不安从床上抬起头。“文景,你没事吧?”眼前丝带被人解开,
林木焦虑的脸被放大。身上束缚如数被解开,在看见熟悉的人后。
我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轰塌,抱着林木泣不成声。林木小心翼翼将我抱起来放进车内。
几日的囚禁让我异常敏感,蜷缩在林木宽大的怀抱内。林木看见我这般模样,
狠狠拍了方向盘。镇定自若说话:“绑架你那小子已经被控制住了。”我恍惚,抬起头,
喉咙干涩:“他在哪里。”林木抿唇,拧眉发动汽车:“派出所,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你不必担心。”我的心沉下来:“陈斯年在哪里。”林木僵住,将不悦情绪闪过:“出国了,
和景瑶。”酸楚席卷全身,我只觉得眼皮沉重。离开家那天,我将陈斯年拉黑,
甚至没有告诉分手的消息。我甚至还残存一丝期许。
被囚禁的几日都在想陈斯年会不会主动来找我。燃起的火苗被一点点掐灭,心如死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