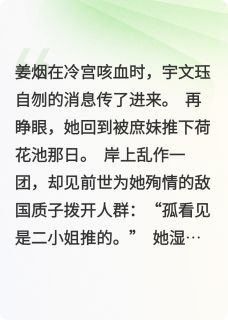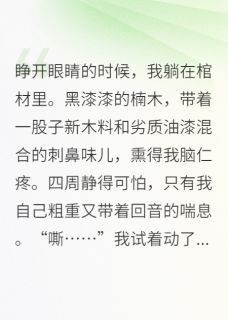
睁开眼睛的时候,我躺在棺材里。黑漆漆的楠木,
带着一股子新木料和劣质油漆混合的刺鼻味儿,熏得我脑仁疼。四周静得可怕,
只有我自己粗重又带着回音的喘息。“嘶……”我试着动了动手指,僵硬得像木头。
记忆像冰水一样,猛地灌进来,冻得我一个激灵。前世,我是安远侯府嫡长女顾昭,
标准的大家闺秀,温婉贤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矩刻进了骨头缝里。结果呢?
十五岁被家族当成筹码,塞给了兵部侍郎那个死了三任老婆的老鳏夫做填房。
那老东西暴虐成性,后宅里乌烟瘴气,一群庶子庶女虎视眈眈。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熬了五年,好不容易怀上孩子,却因为“冲撞”了他最宠爱的、同样有孕的妾室,
被罚在雪地里跪了两个时辰。孩子没了。我也没熬过那个冬天。冰冷的绝望和刻骨的恨意,
比棺材里的寒气更刺骨。指甲狠狠抠进棺材内壁粗糙的木刺里,尖锐的疼让我彻底清醒。
这不是梦!我重生了!回到了我十五岁及笄礼的前一天!
“呵……”一声短促的、带着血腥气的冷笑从我喉咙里挤出来。上辈子当够了温顺的羔羊,
这辈子,这京城小霸王的名头,老娘要定了!“砰!砰!砰!”我抡起拳头,
用尽全身力气砸向头顶的棺材板,发出沉闷的巨响。“来人!放我出去!我没死!听见没有!
放我出去!”外面死寂了一瞬,随即响起一片惊恐的尖叫和慌乱的脚步声。“诈尸啦!
”“大**……大**活了!”棺材盖被七手八脚地撬开,刺目的光线猛地扎进来,
我下意识眯起眼。
映入眼帘的是几张惊骇欲绝、涕泪横流的脸——我那个“贤惠”的继母柳氏,
一脸精明相的管家顾全,还有几个面生的粗壮婆子。柳氏脸色煞白,
抖得跟秋风里的落叶似的,指着我:“你……你是人是鬼?!”我撑着棺材边缘坐起身,
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发出咔哒的轻响。阳光照在我惨白但年轻得过分的脸上,
我扯出一个极其缓慢、冰冷的笑容。“继母,我睡了一觉,做了个很长很长的噩梦。
梦见有人巴不得我死,好给她亲生的女儿腾位置呢。”我声音沙哑,
带着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森然,“托您的福,阎王爷嫌我命硬,不收。这不,我又回来了。
”柳氏被我盯得浑身发毛,强撑着:“昭姐儿,你胡说什么!你昨日突发急症昏厥,
大夫都说没救了……我们也是……”“哦?急症?”我打断她,扶着棺材边沿,
利落地翻身跳了出来。脚踩在坚实的地面上,那种活着的真实感让我心口发烫。
我环视着灵堂里刺目的白幡和我的“遗像”,眼神像刀子一样刮过柳氏的脸,
“什么急症能在我及笄礼前一天要了我的命?又那么巧,我死了,明日的主角,
不就换成你的宝贝女儿顾莹了?”“你!”柳氏气得嘴唇哆嗦,却又不敢发作。
她身边一个婆子想上前扶我,被我一个冷眼钉在原地。“都愣着干什么?
”我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沉,
“把这晦气的东西撤了!烧干净!还有,我饿了,让厨房给我炖碗燕窝粥,要血燕,
炖得浓稠点。”“大**,这……这不合规矩……”管家顾全硬着头皮上前。
他是柳氏的心腹,以前没少给我下绊子。我停下脚步,转头看他。十五岁的身体,骨架纤细,
但此刻的眼神却像淬了冰的刀子,直直捅进他眼睛里。“规矩?”我轻笑一声,
带着无尽的嘲讽,“顾管家,躺在棺材里的时候,规矩可没保住我的命。从现在起,我的话,
就是安远侯府的规矩。懂?”顾全被我看得冷汗涔涔,腿一软,差点跪下:“是…是,
大**!老奴这就去办!”柳氏气得浑身发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把她的灵堂搅得天翻地覆。及笄礼,照常举行。
地点从原本柳氏安排的偏厅小院,被我强行改在了侯府最气派的正厅“荣禧堂”。前世,
我的及笄礼简陋寒酸,柳氏借口父亲在外办差未归,草草了事。这一世,
我让人快马加鞭给远在江南“办差”的父亲送了信,
字里行间只提了一句“女儿险些命丧黄泉,幸得上天垂怜,盼父归”。柳氏的脸,
绿得像春日里新发的嫩韭菜。宾客如云,京城有头有脸的夫人**几乎都到了。
柳氏强颜欢笑地应酬着,她身边的顾莹,穿着一身**的新衣,娇俏可人,
眼神却时不时瞟向主位,带着掩不住的失落和嫉恨。我穿着大红的正装,端坐在主位,
脊背挺得笔直。前世谨小慎微、生怕行差踏错的气质被彻底碾碎,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锋利的平静。“吉时到——请正宾!”唱礼声起。前世,
我的正宾是柳氏请的一位没落宗室的老郡君,身份不高,态度敷衍。
这一世……门口一阵小小的骚动。
一位穿着深紫色诰命服、满头银丝梳得一丝不苟、面容严肃的老夫人在丫鬟搀扶下,
缓步走了进来。她目光如炬,扫过全场,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满堂宾客瞬间安静下来,
随即响起压抑不住的吸气声和低语。“天!是陈太夫人!”“定国公府的老封君?
她老人家多少年不出府走动了?”“安远侯府这位大**……好大的面子!
”柳氏和顾莹的脸,彻底白了。陈太夫人,定国公的母亲,皇帝亲封的一品诰命,
京城最顶级的贵妇,连皇后娘娘都对她礼敬三分!她怎么会来给顾昭做正宾?!我起身,
规规矩矩地行了个晚辈礼:“劳烦太夫人了。”陈太夫人锐利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
似乎想穿透这身皮囊看进骨子里。半晌,她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声音沉稳:“起来吧。
顾家丫头,你这命,够硬。”我微微一笑:“托您的福,阎王不收,只好回来继续折腾了。
”陈太夫人眼中闪过一丝几不可见的讶异,随即归于平静。她没再多言,按照古礼,
一丝不苟地为我加笄。整个仪式庄重而肃穆。簪子插入发髻的那一刻,
我清晰地从下方宾客眼中看到了惊疑、审视,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忌惮。及笄礼成,
该是开宴的时候了。柳氏深吸一口气,脸上堆起标准的笑容,刚想宣布开席。我抬手,
轻轻一压。全场再次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感谢诸位长辈亲朋,
今日拨冗前来观礼。”我声音清晰,传遍整个荣禧堂,“顾昭及笄,本该是喜事。然则,
昨日我险些命丧黄泉,心中颇有疑惑,趁今日诸位做个见证,想请教继母柳夫人一事。
”柳氏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血色褪尽:“昭姐儿,你…你又要胡闹什么!
今日是你的好日子……”“正是好日子,才要把话说清楚。”我打断她,眼神平静无波,
却带着千钧之力,“昨日我突发‘急症’,府医束手无策,是继母您当机立断,
吩咐人将我移入……棺木之中。我想请问继母,是哪位‘神医’诊出我已无生机?
又是哪本医书上写着,病人未断气便可入殓?”死寂。绝对的死寂。针落可闻。
柳氏的脸由白转青,再由青转紫,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她身边的顾莹更是吓得小脸惨白,紧紧抓着母亲的袖子。宾客席上,
所有人的表情都精彩纷呈。震惊、鄙夷、看好戏、难以置信……目光像无数根针,
扎在柳氏母女身上。“我…我……”柳氏急喘着,试图辩解,“我是看你气息全无,
浑身冰冷……府医也说回天乏术……我是怕……怕你……”“怕我什么?怕我死得不够快?
还是怕我死不透?”我往前走了一步,逼近柳氏,声音陡然拔高,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
“怕我挡了你女儿顾莹攀附权贵的青云路?!”“轰——!
”这句话像一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湖面,瞬间炸开了锅!低语声再也压不住,嗡嗡作响。
“天爷!竟是为了这个?”“难怪……顾家二**也快及笄了……”“这柳氏,心也太毒了!
那可是原配嫡女啊!”“嘘……小声点……”陈太夫人坐在上首,闭目养神,
仿佛没听见这惊涛骇浪。但她微微紧绷的下颌线,泄露了她并非无动于衷。
柳氏被这**裸的指控和满堂的鄙夷目光逼得几乎崩溃,尖叫一声:“顾昭!你血口喷人!
我是你继母!我待你如亲生……”“亲生?”我嗤笑一声,带着无尽的讽刺,
“亲生到在我棺木未盖时就急着给我庶妹裁新衣、备新礼?亲生到连一日都等不得,
就要把我抬出去烧了干净?
”我猛地指向角落里还没来得及撤走的、属于顾莹的那套崭新头面,“那是什么?!
”铁证如山。柳氏彻底瘫软在地,掩面痛哭,
语无伦次:“我没有……不是我……老爷……老爷救我……”“够了!
”一声威严又带着疲惫的怒喝从门口传来。我那便宜爹,安远侯顾长风,
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荣禧堂门口。他脸色铁青,显然是刚赶回来就撞上了这场闹剧的最**。
他狠狠瞪了一眼瘫在地上的柳氏,又看向站在场中,脊背挺直、眼神锐利如出鞘利剑的我,
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昭儿,”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声音平稳,“今日是你及笄的大日子,
有什么委屈,过后再说,莫要惊扰了贵客。来人!把夫人扶下去休息!”两个婆子上前,
半拖半拽地把失魂落魄的柳氏弄走了。顾莹也哭着跟了出去。顾长风转向满堂宾客,
勉强挤出笑容:“家门不幸,让诸位见笑了。些许误会,本侯自会查明。开宴!开宴!
”一场风波,被他强行压了下去。但所有人都知道,安远侯府的天,
从顾昭从棺材里爬出来的那一刻,就彻底变了。宴席的气氛有些诡异。没人再提刚才的事,
但投向我的目光,充满了探究和敬畏。我安之若素地坐着,该吃吃,该喝喝,
甚至还主动给陈太夫人布了菜。老太太看了我一眼,没拒绝。宴席将散时,
一个穿着体面的管事嬷嬷走到陈太夫人身边,低声说了几句。陈太夫人放下筷子,
看向我:“顾家丫头。”我立刻恭敬起身:“太夫人请吩咐。”“三日后,
城郊青岚山有场马球会,都是些年轻后生和小姑娘们闹着玩。”她语气平淡,
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那不成器的孙子也去。你若有空,也去散散心。年轻人,
总闷在家里,不好。”满堂再次一静。青岚山马球会!那可是京城顶级勋贵子弟的聚会!
门槛高得吓人!陈太夫人这意思……是要提携顾昭,带她进那个圈子?!
无数道羡慕嫉妒恨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顾长风更是惊得差点站起来,眼中精光闪烁。
我压下心头的波澜,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谢太夫人垂爱,顾昭一定准时赴约。
”重生后的第一场硬仗,我不仅活了下来,还撕开了柳氏的伪善,
更一脚踹开了通往京城顶级圈子的门。但这只是个开始。“小霸王”的名头,
可不是靠撕继母就能得来的。马球会那天,天气极好。我穿了身利落的骑装,枣红色,
衬得肤白如雪,头发高高束起,只簪了一支简洁的金簪,是陈太夫人及笄礼上插的那支。
这身打扮,少了闺阁女子的柔弱,多了几分英气。安远侯府的马车到了青岚山马场,
递上陈太夫人的帖子,守门的护卫立刻换了副恭敬面孔,直接放行。马场极大,绿草如茵。
已经有不少华服少男少女到了,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或牵着马遛弯,或坐在凉棚下说笑。
锦衣华服,骏马雕鞍,空气里都飘着金粉的味道。我的到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探究,好奇,鄙夷,不屑……还有毫不掩饰的看戏意味。“哟,
这不是安远侯府那位‘起死回生’的大**吗?”“棺材里爬出来的那位?胆子可真大,
还敢出门?”“嗤,仗着陈太夫人一句话,真当自己能挤进咱们这圈子了?
”“看她那身骑装,倒像模像样,就是不知道会不会骑马,别待会儿从马上摔下来,
又得躺回棺材里去……”低低的议论声毫不避讳地飘进耳朵。我面不改色,
地扫过那群聚在一起、明显以一位穿着孔雀蓝骑装、容貌娇艳却眼神倨傲的少女为首的圈子。
那是承恩公府的嫡女赵明霞,京城贵女圈里有名的跋扈,前世就曾带头奚落过我。
“顾昭妹妹?”一个温和带笑的声音响起,打破了这微妙的僵持。我转头,
看到一个穿着月白骑装、气质温雅的少年牵着马走过来,笑容和煦,让人如沐春风。
是永昌伯府的世子,陆文谦。前世他名声极好,谦谦君子,最后却娶了赵明霞。“陆世子。
”我微微颔首。“顾妹妹初次来,可还习惯?”陆文谦笑容不变,仿佛没听见周围的议论,
“若是不熟悉场地,我可以……”“文谦哥哥!”赵明霞像只花蝴蝶一样快步走过来,
亲昵地挽住陆文谦的胳膊,占有欲十足。她上下打量我,眼神轻蔑得像在看一件劣质瓷器,
“你跟这种晦气的人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怕沾了霉运!顾大**,
这马场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地方,我劝你还是去那边凉棚里老实坐着,
免得待会儿惊了马,又得劳烦大家给你收尸!”她话音一落,
她身后那群跟班**立刻发出一阵哄笑。陆文谦皱了皱眉,想说什么。我却先笑了。
不是冷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带着点新奇和玩味的笑。“赵**说得对。”我点点头,
语气诚恳,“这马场确实不是阿猫阿狗都能撒野的地方。
”我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赵明霞和她那群跟班,声音清晰,“不过,我顾昭既然来了,
就是来打马球的。赵**与其操心我会不会惊马,不如担心担心自己待会儿输得太难看,
会不会哭鼻子?”“你!”赵明霞没料到我敢直接顶回来,还如此犀利,气得俏脸通红,
“好大的口气!就凭你?一个棺材瓤子里爬出来的……”“明霞!”陆文谦沉声喝止,
语气带着一丝不悦,“慎言!”赵明霞被他当众呵斥,面子更挂不住,
狠狠瞪了我一眼:“行!顾昭!你有种!咱们球场上见真章!我倒要看看,
你这口气能撑到几时!”说完,怒气冲冲地拉着陆文谦走了。陆文谦回头,
略带歉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无所谓地耸耸肩。君子?不过是权衡利弊下的选择罢了。
正打算去挑匹马,一个略带沙哑、透着浓浓不耐烦的少年声音斜刺里**来。“喂,
你挡路了。”我侧身,
只见一个穿着玄色劲装、身形高挑的少年牵着一匹通体乌黑、神骏非凡的大马走了过来。
他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鼻梁高挺,嘴唇紧抿,一双眼睛黑沉沉的,带着股桀骜不驯的野性,
看人时像带着钩子,又冷又利。他手里拎着根马鞭,看都没看我一眼,径直往前走,那气势,
仿佛前面是堵墙他也能直接撞过去。是他?靖国公府那个出了名的混世魔王,萧衍。
京城真正的“小霸王”,行事全凭喜好,天不怕地不怕,连他爹靖国公都管不住。
前世我对他只有耳闻,是个绝对的麻烦人物。我没动,只是在他经过时,
平静地开口:“萧世子,你的马,蹄铁该换了。”萧衍脚步猛地顿住。他缓缓转过头,
那双黑沉沉的眼睛第一次聚焦在我脸上,带着审视和一丝被冒犯的戾气:“你说什么?
”我指了指他牵着的乌骓马的后蹄:“左后蹄,外侧蹄铁边缘磨损严重,
内侧蹄钉有松动迹象。跑平地或许无碍,但若在球场上急停变向,极易打滑。轻则伤马腿,
重则……”我顿了顿,迎上他陡然变得锐利的目光,“……人仰马翻。”萧衍眯起了眼,
那股子不耐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野兽般的专注和危险。他慢慢松开缰绳,
走到马匹后侧,蹲下身,仔细查看那左后蹄。片刻,他站起身,拍了拍手,脸上没什么表情,
眼神却深了许多。他没对我说谢谢,反而问了句:“你懂马?”“略知皮毛。”我淡淡道,
“总比看着人摔死强。”萧衍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扯了扯嘴角,那笑容又野又邪:“顾昭?
棺材里爬出来那个?行,有点意思。”他不再多言,牵着他的乌骓马,
大步流星地朝马厩方向走去,显然是去换蹄铁了。这个小插曲,落入了不少有心人眼里。
赵明霞那边看我的眼神,除了鄙夷,更多了几分惊疑。很快,分组开始。不出所料,
我被有意无意地“剩”下了。没人愿意跟我一组。赵明霞更是得意地扬着下巴,
仿佛在说:看,你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陆文谦有些歉意地看向我,似乎想说什么。“顾昭,
过来。”一个冷淡的声音响起。是萧衍。他已经换好了装备,骑在他那匹神骏的乌骓马上,
手里拎着球杆,下巴朝旁边一点,“你,跟我一组。”全场哗然!萧衍!
他居然主动要跟顾昭一组?!那个煞神!他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还是……纯粹想整她?
赵明霞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我挑了挑眉,没有丝毫犹豫,
径直走向分配给我们的那匹温顺的栗色母马,利落地翻身上马,
动作流畅得不像第一次碰马的人。前世为了讨好那个老鳏夫,我被迫学过骑马,虽不精,
但足够唬人。“我不需要拖后腿的。”萧衍骑着马踱到我身边,声音没什么温度,
“球传给你,接不住,就滚下去。”“彼此彼此。”我握住球杆,掂了掂分量,
“球到了我杆下,就是我的。你抢不到,也别急眼。”萧衍嗤笑一声,没再说话,一夹马腹,
率先冲了出去。比赛开始。马球场上瞬间尘土飞扬,骏马嘶鸣,球杆挥舞,
激烈的碰撞声不绝于耳。萧衍果然如传闻中一样,球风极其彪悍凶狠,横冲直撞,
像一头发怒的豹子。他的球技也极好,控球精准,突破犀利,
一个人就搅得对方防线人仰马翻。但他太独了!球到了他杆下,除非万不得已,
绝不会传出来。好几次明明有位置更好的我就在旁边,他也视而不见,宁可自己硬闯,
或者干脆把球打飞。赵明霞那组的人被他冲得七零八落,气急败坏,
防守的重心几乎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我看得直皱眉。这样打下去,就算萧衍再能打,
体力消耗巨大,迟早被拖垮,而且得分效率太低。又一次,萧衍带球突破三人包夹,
强行起杆射门,角度太刁,球擦着门框飞了出去。“萧衍!”我策马冲到他附近,
在他又一次准备单干时,扬声喝道,“右边!空档!”萧衍动作顿了一下,几乎是出于本能,
手腕一抖,那枚硬木球划出一道弧线,
精准地飞向我指的方向——一个对方防守完全被萧衍吸引后露出的巨大空档!机会!
我早已催马赶到,球杆迎着来球,一个干净利落的挥击!“砰!”木球应声入网!“好球!
”场边响起几声稀稀拉拉的叫好,更多的是惊愕。萧衍勒住马,回头看向我,
黑沉沉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意外,随即是浓烈的兴味。他什么也没说,调转马头,
再次投入拼抢。接下来,局面开始微妙地改变。萧衍依旧凶悍,依旧独,但当他陷入重围,
或者看到我跑出绝佳位置时,竟真的会毫不犹豫地将球传过来!他的传球又快又刁,
力道十足,充满了信任(或者说,是赌徒般的疯狂)。而我,没有辜负这些传球。
前世被压抑的、属于“顾昭”本身的、被规矩磨灭的锐气,在这激烈的对抗中彻底释放!
我不再是那个温婉的闺秀,每一次策马奔驰,每一次挥杆击球,
都带着一股狠劲和精准的判断。接球,突破,传球,射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言语交流,
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充满攻击性的默契。像两把出鞘的利刃,互相砥砺,又互相成就。
“砰!”又是我接萧衍的妙传,一记刁钻的贴地射门,球应声入网!“漂亮!”这次,
场边叫好声多了起来,甚至有人开始鼓掌。赵明霞的脸已经黑如锅底。她几次想故技重施,
像前世那样故意策马冲撞我,都被我提前预判,灵巧地躲开,反而让她自己差点摔下马。
“顾昭!你这个**!你使诈!”赵明霞气急败坏地尖叫。我勒住马,球杆斜指地面,
微微喘息,汗水顺着额角滑落,眼神却亮得惊人:“赵**,球场上,实力说话。输不起,
就别玩。”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全场。“你!”赵明霞气得浑身发抖,
扬手就想用球杆抽我。“赵明霞!”“赵**!
”陆文谦和场边维持秩序的管事同时出声喝止。就在这时,异变陡生!
赵明霞身下的马匹不知为何突然受惊,猛地人立而起,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
赵明霞猝不及防,尖叫一声,眼看就要被甩飞出去!她慌乱中死死抓住缰绳,
整个人吊在马脖子一侧,惊马发疯似的朝场边人群冲去!“啊——!
”场边贵女们吓得花容失色,尖叫着四散奔逃。眼看惊马就要撞入人群!电光火石间,
一道枣红色的身影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是我!我几乎是本能地催动坐骑,
斜刺里截向那匹惊马!在它即将撞入人群的刹那,猛地探身,左手死死抓住了惊马的笼头,
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往侧下方一拽!“吁——!”惊马被这巨大的力量带得一个趔趄,
前冲的势头被强行遏制。同时,我右手闪电般探出,一把揪住赵明霞的后衣领,
在她即将被马蹄踏中的前一秒,猛地将她从马背上扯了下来!“噗通!
”赵明霞像个破麻袋一样被我甩在地上,滚了两圈,狼狈不堪,吓得魂飞魄散,
只会放声大哭。那匹惊马也被我死死拉住笼头,在原地暴躁地打着转,喷着粗气。全场死寂。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场中央。枣红马上的少女,一手死死控住惊马,
一手还维持着抛掷的动作,发丝微乱,脸颊因用力而泛红,眼神却沉静锐利如寒潭,
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杆宁折不弯的红缨枪。刚才那一连串的动作,快、准、狠!
完全不像一个深闺弱质,更像久经沙场的……悍匪?萧衍不知何时策马到了我身边,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难辨,有惊异,有审视,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灼热。
他沉默地伸出手,帮我一起用力,彻**住了那匹还想挣扎的惊马。
管事和护卫们这才如梦初醒,慌忙冲上来接手。陆文谦也赶了过来,
看着地上哭得不成人形的赵明霞,又看看骑在马上、气息微乱却眼神明亮的我,
神色复杂到了极点。“顾…顾妹妹,你没事吧?”他声音有些干涩。我松开手,
活动了一下因用力过度而有些发麻的手臂,平静道:“没事。”然后看向地上哭嚎的赵明霞,
声音没什么起伏,“赵**,下次骑马,记得检查好鞍辔。马镫带子快断了都不知道,
心太大。”赵明霞的哭声戛然而止,惊恐地看向自己的马镫,果然,
一侧的皮带已经磨损得极其严重,几乎断裂!她猛地打了个寒颤,
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后怕和……一丝难以言喻的恐惧。这场马球会,
以一种谁也未曾预料的方式结束。我顾昭的名字,
、“敢跟萧衍叫板”、“当众撕继母”、“马球场上一杆定乾坤”、“徒手拽惊马救仇敌(?
)”这些标签一起,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京城。“京城小霸王”的名号,隐隐约约,
开始落在了我的头上。不再是嘲讽,而是带着一丝敬畏和……不可思议。安远侯府的日子,
表面平静了下来。柳氏被我爹顾长风禁足在她自己的院子里,美其名曰“静养”。
顾莹也老实了许多,见到我像老鼠见了猫,远远就绕道走。顾长风对我的态度变得极其微妙。
他看着我时,眼神里有探究,有忌惮,但更多的是一种……待价而沽的精光。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一个能得陈太夫人青眼、敢跟萧衍那个煞神并肩打球、还闹出这么大动静的女儿,
价值可比一个只会哭哭啼啼的顾莹高多了。果然,没过几天,他就在书房“召见”了我。
书房里燃着上好的沉水香,顾长风坐在书案后,努力摆出一副慈父的面孔。“昭儿啊,坐。
”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前些日子,你受委屈了。柳氏糊涂,为父已经重重责罚了她。
”我垂着眼,没坐,也没接话。等着他的下文。顾长风清了清嗓子,
继续道:“你如今也及笄了,名声……也闯出来了。为父思前想后,
觉得是时候给你定下一门好亲事了。女儿家,终究还是要有个好归宿。”来了。
“父亲心中可有人选?”我抬起眼,语气平淡无波。顾长风眼中精光一闪,
身体微微前倾:“你可知,吏部尚书的嫡次子周文轩?周尚书深得圣眷,前途无量。
文轩那孩子,为父见过,温文尔雅,才学出众,与你正是良配!若能结下这门亲事,于你,
于我们侯府,都是天大的好事!”周文轩?我心底冷笑一声。这个名字,我可太“熟悉”了。
前世,他同样“温文尔雅”、“才学出众”,是京城有名的佳公子。可背地里呢?狎妓成性,
还在外头养了好几房外室,其中有一个,
甚至被他偷偷安置在离安远侯府只隔两条街的甜水巷!他娶的正妻,
是柳氏娘家一个远房侄女,过门不到两年,就被他和他那个刻薄的娘活活磋磨死了,
对外只说是“病逝”。现在,顾长风想把我推进这个火坑?“父亲,”我缓缓开口,
声音不高,却带着冰碴子,“您说的这位周公子,确实‘名声在外’。只是不知,
他养在甜水巷槐树胡同第三家,那个叫‘怜娘’的外室,
还有他常去捧场的‘醉春楼’头牌‘莺歌’,知不知道他快要‘温文尔雅’地娶妻了?
”顾长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血色“唰”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震惊地看着我,
像见了鬼:“你……你胡说什么!”“我是不是胡说,
父亲派人去甜水巷槐树胡同第三家问问,或者去醉春楼打听打听‘周公子’的阔绰,
不就一清二楚了?”我勾起唇角,露出一个毫无温度的笑,“女儿刚从棺材里爬出来,
惜命得很。这种‘良配’,还是留给更‘贤惠’的妹妹吧。比如,顾莹妹妹?
她不是一直羡慕我能攀高枝么?这个‘高枝’,我让给她了。”顾长风指着我,手指都在抖,
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精心挑选的“好女婿”,内里竟如此不堪!更让他心惊的是,
顾昭是怎么知道这些阴私的?!“父亲若没别的事,女儿告退了。
”我懒得看他那张变幻莫测的脸,屈了屈膝,转身就走。走到门口,我停住脚步,没有回头,
声音清晰地传回去:“对了,父亲。我的婚事,就不劳您费心了。阎王殿前走过一遭的人,
自己的命,自己挣。谁敢再把手伸过来……”我顿了顿,语气森然,
“我不介意让他也去棺材里躺一躺,试试滋味。”书房门在我身后关上,
隔绝了顾长风铁青的脸和粗重的喘息。撕破脸皮,摆明车马。这安远侯府,以后谁说了算,
他心里该有数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小霸王”的名头越响,
某些藏在阴沟里的臭虫就越按捺不住。这天,我带着贴身丫鬟春桃出门,
想去西市新开的“玲珑阁”看看首饰。春桃是我重生后亲自挑的,机灵忠心,
拳脚功夫还凑合。马车行至相对僻静的梧桐巷,突然被几个人高马大的身影拦住了去路。
车夫吓得勒住马:“吁——!什么人?敢拦安远侯府的车驾!
”为首的是个一脸横肉、穿着绸衫却掩不住匪气的壮汉,他手里掂量着一根粗木棍,
嘿嘿一笑,露出满口黄牙:“安远侯府?拦的就是你家大**!顾昭是吧?有人花钱,
让哥几个给你松松筋骨,长长记性!识相的,自己滚下来,免得哥几个动手,
你这细皮嫩肉的,可经不起折腾!”车帘被掀开,春桃探出头,厉声道:“放肆!
你们知道我家**是谁吗?光天化日,天子脚下,你们敢行凶?!”“行凶?
”那壮汉啐了一口,“老子这叫替天行道!
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到处惹是生非的小**!兄弟们,上!把人给我拖出来!
”几个打手狞笑着围了上来。车夫吓得瑟瑟发抖。春桃脸色发白,却还是咬牙挡在车门前。
我坐在车里,听着外面的叫嚣,眼神一点点冷下去。看来,
有人是觉得我“小霸王”的名头是纸糊的,想试试成色了。也好。正愁没地方立威。“春桃,
退后。”我平静地吩咐一声,掀开车帘,利落地跳下马车。今天为了方便,
我穿的是一身便于行动的窄袖胡服。那壮汉见我居然自己下来了,愣了一下,
随即淫笑道:“哟,小娘皮还挺有胆色?怎么,知道怕了?乖乖跟爷走,
爷还能……”他话没说完。我已经动了!没有废话,没有预警。
身体像蓄满力的弓弦骤然崩开!脚尖一点地,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冲向那壮汉!速度太快!
快到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那壮汉只觉眼前一花,一股劲风扑面!他下意识想抡棍子,
手腕却猛地传来一阵剧痛!“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嗷——!
”壮汉发出杀猪般的惨叫,粗木棍脱手飞出。他捂着自己软绵绵耷拉下去的手腕,
痛得冷汗瞬间冒了出来。我动作丝毫不停,借着前冲的势头,手肘如铁锤般狠狠砸在他肋下!
“呃!”壮汉的惨叫声戛然而止,眼球暴凸,捂着肋骨蜷缩下去,像一只煮熟的大虾。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剩下的几个打手都懵了,看着瞬间倒地哀嚎的老大,
又看看站在场中、眼神冰冷、仿佛只是掸了掸灰尘的我,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鬼……鬼啊!”一个胆小的打手怪叫一声,转身就想跑。“一个都别放走。”我冷冷开口。
早就按捺不住的春桃应声而动,像只灵巧的豹子扑了出去,拳脚生风,专门招呼下三路,
缠住了两个想跑的打手。我则盯上了那个想跑的。脚下发力,几步追上,一记凌厉的侧踢,
狠狠踹在他腿弯!“噗通!”那打手应声跪倒。我顺手抄起地上那根掉落的粗木棍,掂了掂,
分量十足。另外两个打手见势不妙,嚎叫着一起扑了上来,一个挥拳砸向我面门,
一个抬脚踹向我腰腹,配合倒是默契。我眼神一厉,不退反进!身体如同灵蛇般一扭,
险之又险地避开砸向面门的拳头,同时手中木棍由下向上,一个迅猛的撩击!“砰!
”狠狠砸在踹向我腰腹那人的小腿迎面骨上!“嗷——!”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那人抱着腿在地上打滚。最后那个挥拳的打手拳头落空,还没来得及收势,
我已经旋身到了他侧面,木棍带着呼啸的风声,毫不留情地横扫在他腰侧!“噗!
”那人被打得横飞出去,撞在巷子的墙壁上,滑落下来,口吐白沫,抽搐着爬不起来。
前后不过半盏茶的功夫。五个凶神恶煞的打手,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哀嚎翻滚,
再无还手之力。巷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和尿骚味。春桃那边也结束了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