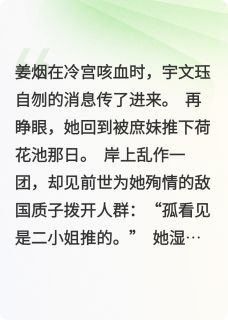1逃离污浊“站住。”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惯有的、不容违逆的威压,冷硬地砸过来,
如同冰雹。蓝衣人脚步顿住,缓缓转过身。面具后的目光平静地迎上谢珩锐利的视线,
并无丝毫退让或畏惧。两个同样气势迫人的男子,在这污秽之地的后门口,无声地对峙。
空气仿佛瞬间凝固,紧绷得能听到细针落地的声音。我心头猛地一沉。他终究还是拦下了!
苏皎又对他说了什么?难道重活一世,连这第一步逃离,都要被他们联手扼杀?
袖中的铜簪几乎要被我捏碎,冰冷的金属刺痛掌心,带来一丝残酷的清醒。
谢珩的目光越过蓝衣人的肩膀,像淬了毒的针,狠狠刺在我脸上。他的声音更冷,
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和警告:“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花了多少银子。这个女人,
”他抬手,直直指向我,指尖仿佛带着无形的寒气,“心术不正,惯会攀附,满口谎言。
你今日带她走,来日必受其累,悔之晚矣!”每一个字,都像前世的鞭子,
狠狠抽打在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心术不正?惯会攀附?满口谎言?这些罪名,
哪一桩不是拜他身边那朵“皎皎明月”所赐!滔天的恨意如同岩浆在胸腔里翻涌,
几乎要冲破喉咙。我猛地抬起头,第一次,毫无畏惧地迎上谢珩那冰冷审视的目光。
四目相对。我眼中不再是前世的怯懦、哀求或绝望,而是冰封的恨意,是燃烧的怒火,
是刻骨的讥诮!那目光太过锐利,太过复杂,竟让习惯了掌控一切的谢珩微微一怔。
蓝衣人并未回头看我,却仿佛感知到了我情绪的剧烈波动。他微微侧身,
不着痕迹地挡在了我与谢珩之间,隔断了那道冰冷的视线。“谢世子。
”蓝衣人的声音透过面具传来,依旧是那种奇异的低沉平稳,听不出喜怒,
“在下不过一介行商,花银钱买个伺候的人罢了。是好是歹,是福是祸,自有在下承担。
不劳世子挂心。”他的话语客气,却带着一种针锋相对的强硬。那“伺候的人”几字,
更是刻意点明了我此刻在他眼中的“身份”——一件用一千五百两黄金买下的货物。
这直白得近乎羞辱的定位,反而让谢珩一时语塞。他脸色铁青,拳头在袖中紧握,
骨节发出轻微的脆响。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靖国公府侍卫服饰的人匆匆从侧门跑进来,
在谢珩耳边低语了几句。谢珩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他狠狠剜了我一眼,
那眼神充满了警告和一种莫名的烦躁。最终,他猛地一拂袖,
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好自为之!”说罢,竟不再纠缠,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去,
背影都透着压抑的怒火。看着那道玄色身影消失在醉芳楼侧门外的夜色里,
我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松懈,后背已被冷汗浸透。刚才那短暂的对视,
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蓝衣人似乎并未将谢珩的威胁放在心上。他转向我,
面具后的目光依旧沉静:“上车。”没有多余的话。我沉默地跟着他,
踩着矮凳上了那辆简陋的青布骡车。车厢里光线昏暗,只铺着一层普通的青布坐垫。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干净的皂角味和一种若有若无的、类似雨后松针的冷冽气息。
骡车启动,颠簸着驶离了醉芳楼后巷那片令人窒息的污浊之地。车轮碾过青石板路,
发出单调的“辘辘”声。我蜷缩在车厢一角,背脊挺得笔直,全身的肌肉依旧紧绷着,
像一只受惊后随时准备暴起伤人的小兽。袖中的铜簪并未收起,
冰冷的触感是我唯一的安全感来源。车窗外,是金陵城初冬的夜。寒风穿过帘隙,
带来刺骨的凉意。远处的灯火和喧嚣渐渐被抛在身后,
道路两旁开始出现稀疏的民居和光秃秃的树木。骡车似乎朝着城外偏僻的方向行去。
未知的前路,如同这深沉的夜色,浓得化不开。不知过了多久,骡车终于停下。
车帘被随从从外面掀开。“到了。”男人的声音响起。我深吸一口气,攥紧袖中的簪子,
弯腰下了车。眼前并非想象中的深宅大院或荒郊野外的破屋,
而是一座看起来颇为雅致的院落。粉墙黛瓦,院墙不高,门口挂着两盏素雅的灯笼,
映照着门楣上“静园”二字。虽地处偏僻,却自有一股清幽之气。蓝衣人率先推门而入。
我紧随其后。院内格局不大,却布置得极为用心。几竿翠竹在寒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轻响。
墙角堆着假山石,引了一小股活水,在月光下泛着粼粼微光。正屋三间,灯火通明。
一个穿着干净布裙、面相和善的中年妇人闻声迎了出来。“公子回来了。
”她的目光随即落在我身上,带着一丝好奇,但并无轻视或探究,“姑娘也请进吧,外面冷。
”这平静得近乎诡异的氛围,反而让我心头疑窦更深。那人径直走进了正屋。我犹豫了一下,
也跟了进去。屋内陈设简洁而舒适,一张花梨木圆桌,几把圈椅,
靠墙的多宝格上放着几件古朴的瓷器,墙上挂着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山水。暖炉烧得正旺,
驱散了冬夜的寒意。男人在桌边坐下,终于抬手,缓缓摘下了脸上的银质面具。面具滑落,
露出一张年轻却异常沉稳的面容。肤色是久经风霜的小麦色,剑眉浓黑,鼻梁高挺,
嘴唇的线条显得有些薄而坚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深邃如同古井,目光沉静而锐利,
仿佛能穿透一切表象,洞察人心。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我依言坐下,
脊背依旧挺直,目光警惕地落在他脸上,沉默着,等待着他的“宣判”。他并未立刻说话,
而是提起桌上温着的白瓷茶壶,倒了三杯热茶。一杯推到我面前,一杯自己端起,
另一杯放在旁边空位上。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些许轮廓。“我叫沈砚。”他开口,
声音褪去了面具的阻隔,更显清朗沉稳,却依旧带着一种奇特的、仿佛能安抚人心的力量,
“一个行走四方的商人。买你,并非为色。”他抬眼,目光如实质般落在我脸上,
那审视的意味更浓,仿佛要将我从里到外看个通透。“我见过你写的字,也听过你谱的曲。
”他缓缓道,语气平淡无波,“在醉芳楼那种地方,能写出那般筋骨力道、隐含锋芒的字,
谱出清越脱俗、不落窠臼的曲...姑娘,你绝非池中之物。更非刘三娘口中,
一个简单的、被拐卖的孤女。”我的心猛地一跳!他调查过我?什么时候?
那场所谓的“拍卖”,难道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我来的?这个沈砚,他到底知道多少?
“我买你,是因为我需要一个'身份'合适、却又足够聪明的人,帮我做一件事。
”沈砚放下茶杯,杯底与桌面接触,发出清脆的一声轻响,
“一件...需要深入金陵官场、甚至可能触及某些权贵核心利益的事。”他顿了顿,
深邃的目光牢牢锁住我的眼睛:“比如,查清当年拐卖你的幕后真凶。比如,
帮你拿回...你真正的身份。”轰隆——!仿佛一道惊雷在脑海中炸响!我浑身剧震,
瞳孔骤然收缩,死死地盯着沈砚那张平静无波的脸!他知道!他竟然知道我是被拐卖的!
他甚至...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你...你到底是谁?!
”我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带上了一丝颤抖。袖中的铜簪几乎要脱手而出。
巨大的震惊和一种被彻底看穿的恐惧攫住了我。这个男人,远比谢珩更可怕!
谢珩的恶意在明处,而沈砚,他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平静的水面下,
藏着足以吞噬一切的未知力量!沈砚对我的震惊似乎早有预料。他并未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反而端起茶杯,慢条斯理地又啜了一口。“我是谁,眼下并不重要。”他的目光越过杯沿,
落在我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手上,“重要的是,苏晚姑娘,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
”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带来一股无形的压迫感。那深邃的眼眸里,
是洞悉一切的了然和近乎残酷的坦诚。“你恨谢珩,恨苏皎,
恨那个夺走你人生、害死你的所谓'妹妹'。你更恨那个将你推入火坑的幕后黑手。
”他每说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砸在我的心上,“你重生回来,不是为了苟且偷生,
是为了复仇。”“但复仇需要力量,需要筹码,需要...一个支点。
”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你孤身一人,身陷泥沼,纵有滔天恨意,又能如何?
”他精准地戳破了我所有的困境和前世惨死的根源!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刀锋,
割开我强装的镇定,露出下面血淋淋的、孤立无援的现实。“而我,
”沈砚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像暗夜里的灯塔,“可以给你这个支点。我查过当年的事,
线索虽少,却并非无迹可寻。”他抛出的信息如同惊雷!刘三娘?苏皎背后还有人?
前世我只当苏皎是出于独占欲的恶毒,从未想过她背后可能还有更深的黑手!“帮我做事,
你便有了一个暂时的庇护所,一个'沈氏商行管事侍女'的合理身份。”沈砚继续道,
“你可以借助我的力量和人脉,在金陵城活动、探查。”“作为交换,
我需要你利用你的身份接近一个人。”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变得更加幽深,“金陵转运使,
周炳坤。”周炳坤?这个名字像一块巨石投入心湖。此人掌管江南盐铁漕运,权柄极重,
是金陵城真正的地头蛇之一。“此人表面是太子一党,实则贪得无厌,
暗中与三皇子往来密切。”沈砚的声音冷了下来,带着一丝凛冽的杀意,
“我要你设法接近他,获取他勾结三皇子、走私军械的确凿证据。”接近周炳坤?
获取走私军械的证据?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你怕了?
”沈砚迎着我惊疑不定的目光,唇角似乎勾起一丝极淡、几乎看不见的弧度,“还是觉得,
这代价太大,不值得?”怕?我心中冷笑。死过一次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代价?
只要能撕开真相,只要能复仇,再大的深渊我也敢跳!“为什么是我?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声音因为紧绷而显得有些沙哑,
“醉芳楼里会写字、会弹琴的女子不止我一个。”沈砚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难辨。
“因为你的眼神。”他缓缓道,“别人看到的是惶恐和认命,
我看到的是...冰层下的岩浆,是绝境中也要撕咬猎物的孤狼。”他顿了一下,
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扫过我放在膝上的手:“而且,你的字...很像一个人。一个很多年前,
对我有恩的人。”字?像谁?这又是一个谜。但此刻,这些都不重要了。机会就在眼前,
一个可以借力、可以深入虎穴的机会!风险与机遇并存,一步踏错便是万丈深渊。但,
我还有退路吗?我闭上眼,前世苏皎那杯毒酒的灼痛感仿佛再次在喉间燃烧。再睁开时,
眼中所有的犹豫和惊疑都已褪去。“好。”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清晰、冷静,
带着一种斩断所有退路的决然,“我答应你。”“但我要知道,
你查到的所有关于当年拐卖的线索。还有,事成之后,我要苏皎和谢珩,身败名裂,
生不如死!”沈砚看着我,那双深邃如古井的眼眸里,
终于掠过一丝清晰的、名为欣赏的光芒。他拿起桌上那杯一直放在空位上的茶,
轻轻推到我面前,仿佛某种无声的契约。“成交。
”---2神秘商人神秘商人沈砚以千两黄金拍下我的初夜。静园烛下,
他摘下银质面具:“买你,并非为色。”“帮我查金陵转运使周炳坤走私军械。
”“作为交换,我助你查清拐卖真相,拿回身份。”我盯着他深邃的眼:“事成之后,
我要苏皎和谢珩,身败名裂,生不如死!”他推过一杯茶:“成交。
”---静园那声“成交”的余音,像一滴墨落入死寂的深潭,在我心底缓慢洇开,
留下沉甸甸的印痕。沈砚推过来的那杯茶,我终究没有碰。指尖抚过温热的杯壁,
那暖意如同虚妄的幻象,无法穿透我骨髓里沉淀了十一年的冰冷。这里不是归宿,
只是一处暂时停泊的码头,前方,是暗礁密布、惊涛骇浪的复仇之海。静园的日子,
是带着枷锁的平静。沈砚言出必行,给了我这个“沈氏商行管事侍女”的身份。
每日不过是整理些无关紧要的商队文书,清点些从南边运来的丝绸、香料样品。
那中年妇人姓王,都唤她王婶,手脚麻利,不多言不多语,
只在我需要时递上干净的衣物和热腾腾的饭菜。沈砚大多时间不在园中,偶尔回来,
也只在书房处理事务,周身弥漫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冷冽。他允诺的“线索”,
在抵达静园的第三日清晨,被放在了我房中的小几上。只有薄薄一张纸。纸上寥寥数语,
却像淬毒的针,狠狠扎进我的眼底:“五岁上元夜,靖国公府后巷,牙婆孙氏经手。
孙氏已于七年前暴毙。”“醉芳楼刘三娘,十年前曾有一笔不明巨财入账,
来源疑与京城某贵妇有关。”“疑点:苏皎生母柳氏,原为苏夫人陪嫁侍女,
苏夫人产女当日,柳氏亦于别院‘早产’。”京城某贵妇?柳氏?纸张在我指间被攥紧,
发出不堪重负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血液似乎瞬间冻结!
那伪善的面孔和毒蛇般的低语在脑中疯狂闪回——“爹爹和娘亲一直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
伤心了好些年呢……”原来如此!原来从一开始,就有一张精心编织的网!苏皎的得意,
谢珩的鄙夷,父母兄长的“遗忘”……所有加诸我身的痛苦,都源于这桩肮脏的买卖!柳氏!
那个看似温顺卑微的侍女!是她?还是她背后那所谓的“京城贵妇”?
滔天的恨意几乎要将我吞噬,我猛地闭上眼,强迫自己将翻涌的杀气压下去。
指甲深深掐入掌心,尖锐的疼痛带来一丝残酷的清醒。证据!我需要证据!光凭这张纸,
撼动不了任何人!沈砚在逼我,逼我走出静园,
逼我去接近那个足以将我碾碎的目标——周炳坤。机会来得比预想中快。十日后,沈砚回园,
身上带着淡淡的酒气和一种不易察觉的疲惫。他递给我一张素雅的帖子。“明日未时,
城西‘漱玉轩’。”他的声音听不出情绪,“周炳坤新纳的第五房小妾生辰,他包了场听曲。
你随我去。”“我?”我抬起眼。“嗯。”沈砚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带着审视,“你的琴艺,
该派上用场了。记住你的身份,沈氏商行新聘的琴师,苏晚。”身份?一个商行琴师。
一个即将被推入猛兽视线的饵。漱玉轩,雅致如其名。楼阁临水,飞檐斗拱,
丝竹管弦之声隔着雕花木窗隐隐透出,与窗外秦淮河上的画舫笙歌遥相呼应。
二楼临河的雅间已被周府包下。厚重的锦帘隔绝了大部分视线和喧嚣,
只留一扇雕花木窗半开,正对着中央一个小小的水榭戏台。周炳坤年约四旬,身形微胖,
穿着宝蓝色团花绸缎便服,一张富态的圆脸,眼袋松弛,此刻正半眯着眼,
惬意地斜倚在主位的宽大软榻上。他怀里依偎着一个穿着桃红撒花袄裙的年轻女子,
想必就是那位新得宠的如夫人。沈砚带着我进去时,雅间里已有几位作陪的官员和富商,
谈笑声不绝。空气里弥漫着酒气、脂粉香和一种官场特有的虚伪逢迎之气。“沈老板来了!
快请坐!”周炳坤懒洋洋地抬起眼皮,目光在沈砚身上打了个转,随即落在我身上,
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品评货物般的兴味,“哟,这位是?”“周大人。”沈砚拱手,
态度不卑不亢,侧身将我让出些许,“这是敝商行新聘的琴师,苏晚。听闻夫人今日芳辰,
特带来献上一曲,聊表心意。”“苏晚?”周炳坤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
眼神在我脸上逡巡片刻,那目光黏腻得令人作呕,“好名字!人更水灵!沈老板好眼光啊!
那就…请苏姑娘弹上一曲,给夫人助助兴?”“是。”我垂眸应下,
抱着沈砚为我准备的一架半旧七弦琴,走向水榭戏台。指尖触上冰凉的琴弦,心跳如擂鼓。
台下,周炳坤探究的目光,沈砚沉静的侧影,以及雅间内那些或审视或玩味的视线,
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我深吸一口气,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底只剩下古井无波。
前世在醉芳楼,琴是取悦恩客的工具,是刘三娘榨取价值的筹码。今日,它是我的剑!
指尖拨动,清越的琴音如流水般倾泻而出。我弹的是一曲《潇湘水云》,曲意本是寄情山水,
淡泊高远。然而此刻,我指下流淌出的,却是压抑了十一年、沉淀了血泪的孤愤与不甘!
琴音时而如寒泉幽咽,时而如风入松涛,激越处隐有金戈之鸣!水榭临水,琴声借着水波,
清越悠远地荡开。雅间内的谈笑声不知不觉低了下去。一曲终了,余音在水面袅袅散去。
短暂的寂静后,是周炳坤带头抚掌:“好!好!想不到沈老板手下还有这等妙人!琴好,
人更好!苏姑娘这一曲,颇有大家风范啊!”他转向沈砚,语气带着一种上位者的施舍,
“沈老板,你这商行在金陵的几桩货物通关事宜,本官记下了,回头让人给你行个方便!
”沈砚起身,神色如常地拱手:“多谢周大人抬爱。”就在这时,
雅间的锦帘被一只修长的手猛地掀开!一道玄色的身影挟带着门外凛冽的寒气,
突兀地闯入这片奢靡温暖的天地。谢珩!他站在门口,俊朗的脸上罩着一层寒霜,
锐利的目光如同鹰隼,瞬间就锁定了水榭戏台上的我!那眼神里翻涌着惊愕、难以置信,
以及一种被深深冒犯的、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怒火!他怎么会在这里?!“周大人好雅兴。
”谢珩的声音冷得像冰渣子,每一个字都砸在凝滞的空气里。他大步走进来,
目光却死死盯在我身上,如同两把烧红的烙铁,“想不到在此处,还能遇到‘故人’。
”周炳坤显然没料到谢珩会突然出现,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
随即堆起更热络的笑起身相迎:“哎呀!世子爷!稀客稀客!您怎么有空光临这漱玉轩?
快请上座!”他一边招呼,一边目光狐疑地在谢珩和我之间来回扫视。沈砚也站起身,
对着谢珩微微颔首:“谢世子。”谢珩却连眼风都没扫沈砚一下,
径直走到离水榭最近的位置,撩袍坐下,一双寒眸依旧紧紧攫住我,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
“方才弹琴的,是你?”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重的威压,清晰地传到台上。
整个雅间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抱着琴,缓缓站起身。
隔着几丈的距离,隔着水榭的雕栏,迎上他那双燃着怒火的眼睛。
前世被他鄙夷唾弃、被他视如敝履、被他亲手推向绝路的痛楚,如同淬毒的藤蔓,
瞬间缠紧了心脏。袖中的指尖深深掐入掌心。“回世子,”我的声音出乎自己意料的平静,
甚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近乎挑衅的疏离,“正是奴婢。”“奴婢?
”谢珩唇角勾起一抹极冷的弧度,满是讥讽,“几日不见,苏姑娘倒是很懂得‘审时度势’,
攀上了新的高枝,连身份都换得这般利索!沈老板,”他这才终于将目光转向沈砚,
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和警告,“好心提醒你一句,这女人心思诡谲,手段下作,
最擅长的便是装可怜博同情、攀龙附凤!小心引火烧身!”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鞭子,
狠狠抽打在我早已破碎不堪的尊严上!
临死前他那些冰冷的斥责、苏皎得意的笑脸、毒酒穿肠的剧痛……无数画面在脑中轰然炸开!
一股腥甜猛地涌上喉头!我死死咬住牙关,才将那口血咽了回去。
身体因为极致的愤怒和恨意而微微颤抖。“谢世子!”沈砚的声音响起,依旧沉稳,
却带上了明显的冷意,“苏姑娘如今是我沈氏商行的人,她的品性如何,在下自有判断。
不劳世子费心指教。”他上前一步,不着痕迹地隔断了谢珩那几乎要将我刺穿的视线。
“沈老板这是要护短?”谢珩的眼神更加阴鸷,周身散发的低气压让雅间内的温度骤降。
周炳坤见状,连忙打圆场:“哎呀呀,世子爷息怒!沈老板也别见怪!都是误会,误会!
来来来,喝酒喝酒!别为了个下人扫了兴致!”他一边说,一边给旁边的侍女使眼色。
那侍女会意,立刻端着一只盛满琥珀色酒液的玛瑙杯,袅袅婷婷地朝我走来,
脸上堆着刻意的笑:“苏姑娘琴弹得真好,夫人听得欢喜,赏姑娘一杯酒润润嗓子。
”那酒杯递到我面前。一股极其细微、却异常熟悉的甜腻香气,丝丝缕缕地钻入我的鼻腔!
栀子花香!和五岁那年上元夜,捂住我口鼻的手帕上,那令人作呕的香气,一模一样!
轰——!脑海中的某根弦瞬间崩断!前世今生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恨意,
在这一刻被这缕香气彻底点燃!就是这股味道!它刻在我灵魂最深处,
是我十一年噩梦的源头!是谁?周炳坤?还是他身边那个看似无辜的如夫人?
亦或是……这雅间里的某个人?我猛地抬头,目光如同淬了毒的利箭,
狠狠射向递酒的那个侍女!不,不是她!她的眼神只有奉承和一丝茫然!
我的目光疯狂扫过雅间内每一个人!周炳坤正谄笑着给谢珩斟酒,
他的如夫人娇笑着依偎在他身边……都不是!是那香气本身!它就来自这杯酒!“啪嚓——!
”一声脆响!我抱着琴的手臂猛地一挥,狠狠撞开了那递到面前的玛瑙杯!
昂贵的酒杯砸在坚硬的水榭地面上,瞬间碎裂!琥珀色的酒液和着碎片四溅开来,
那浓烈的栀子甜香骤然爆开,弥漫在空气中!“啊!”递酒的侍女吓得尖叫一声,连连后退。
整个雅间死一般寂静!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周炳坤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
随即化为震怒:“大胆贱婢!竟敢打翻夫人的赏酒!来人……”“这酒!”我厉声打断他,
声音因为极致的激动和恨意而尖锐得变了调,直直指向地上那片狼藉的湿痕和碎裂的玛瑙,
“这酒里有毒!”“毒”字一出,如同平地惊雷!间内所有人脸色剧变!“胡说八道!
”周炳坤身边的如夫人首先尖叫起来,花容失色,“你…你这**血口喷人!
这酒是老爷特意从西域带来的葡萄美酒,怎会有毒?!”“是不是有毒,验过便知!
”我毫不退缩,胸脯剧烈起伏,眼中燃烧着不顾一切的火焰,“周大人若心中坦荡,
不妨现在就请个大夫来!或者,”我的目光猛地转向脸色同样阴沉难看的谢珩,
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孤注一掷,“请谢世子身边的护卫验看!世子爷秉公执法,
定能还夫人一个清白!”我赌!赌谢珩那深入骨髓的傲慢和所谓的“公正”!
赌他对任何“阴私手段”的本能厌恶!更赌他此刻对我强烈的嫌恶,绝不会偏袒周炳坤这边!
果然,谢珩的眉头紧紧蹙起,眼神锐利如刀地扫过地上的酒渍,
又扫过周炳坤和他身边惊惶的如夫人,最后落在我因激动而苍白的脸上。那眼神里有惊疑,
有审视,更有一种被卷入麻烦的极度不耐。“周大人,”谢珩的声音冰冷,
“这婢女所言虽荒谬,但为免瓜田李下之嫌,还是查一查为好。免得传出去,
说本世子在你的宴席上,坐视有人投毒而不理。”周炳坤的脸一阵青一阵白。他死死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