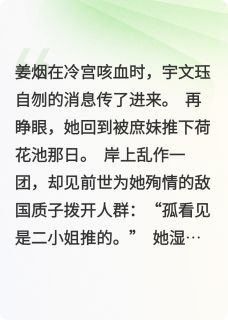第一章病房鬼影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里,林伯庸的睫毛上沾着层白雾。
刚做完搭桥手术的胸口像压着块烧红的烙铁,每呼吸一次,
都有细密的疼顺着血管爬向四肢百骸。
七十二岁的他躺在私立医院顶层VIP病房的记忆棉床上,身下的凉席印着暗纹,
是他年轻时在苏绣店定做的“松鹤延年”,此刻却硌得肩胛骨生疼。
窗外的白玉兰开得正疯,花瓣簌簌落在防弹玻璃上,带着点甜腻的香混进消毒水味里。
他半睁着眼,看见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栅栏似的光斑,
有粒尘埃正顺着光柱慢慢飘——这是他住院的第七天,也是意识最清醒的一天。
“咔嗒”一声轻响,磨砂玻璃门外的影子动了动。林伯庸的心跳漏了半拍,
监护仪的频率突然快了两格。那影子很高,肩线却有些佝偻,像只蓄势待发的猫,
贴着门框晃了晃。复活的他想喊护工,喉咙却被痰堵住,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
“叔叔醒着吗?”林薇的声音裹着笑意飘进来,门把转动的瞬间,
他看见她裙角扫过走廊的地毯。月白色连衣裙是上周刚在米兰时装周秀场拍下的高定,
颈间的白丝巾据说是民国时期的老物件,
边角绣着极小的“薇”字——这丫头总爱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跟她妈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刚换的药布,您看看还渗血吗?”林薇推着治疗车进来,
车轮碾过地板的声音很轻,像某种爬行动物在吐信子。她俯身时,白丝巾擦过林伯庸的脸颊,
带着股檀香味,盖过了他熟悉的祖玛珑橙花味。林伯庸的目光落在她的手腕上。
昨天她来的时候戴的是百达翡丽的星空表,今天换成了只银镯子,款式很旧,
接口处有道明显的焊痕。他突然想起三十年前,
在老宅阁楼的樟木箱里见过只一模一样的——那是林薇母亲的遗物,
据说当年被追债的人抢走时,镯子上还沾着血。“董事会上午又来电话了。
”林薇解开他胸前的纱布,指尖冰凉,不像刚从外面进来的样子,
“张副总说城西那块地的合同得您签字才能生效,不然违约金要赔三个亿呢。
”她的指甲修剪得圆润,涂着透明指甲油,却在揭开纱布时,
不经意间用指甲刮了下他的缝合线。疼得钻心。林伯庸猛地攥紧拳头,
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哎呀,对不起叔叔。”林薇慌忙按住他的肩膀,
另一只手却趁机翻了翻床头柜上的病历夹,“我太不小心了……您别生气,
医生说您不能激动。”她的袖口滑下去,露出半截小臂,
有道浅粉色的疤痕——那是去年在股东大会上,为了抢他手里的钢笔被笔尖划破的。
阳光突然被云遮住,病房里暗了下来。林伯庸看见治疗车下层的托盘里,除了碘伏和棉签,
还躺着个棕色药瓶,标签被刻意朝下扣着。他想起今早护士换药时,托盘里根本没有这东西。
“叔叔?”林薇的声音突然近了些,他感觉那股檀香味里,混进了点极淡的杏仁味。
“您要是现在签不了字,我先替您代签?反正都是一家人,张副总他们不会说什么的。
”她的影子投在天花板上,像只展开翅膀的蝙蝠。林伯庸盯着那只棕色药瓶,
突然想起二十年前,林薇的母亲就是握着类似的瓶子,
倒在公司的茶水间里——那天也是个晴天,白玉兰开得正盛,
尸检报告说她喝了掺了氰化物的咖啡。监护仪的“滴滴”声又乱了。林伯庸闭上眼睛,
感觉那道磨砂玻璃外的影子,好像又贴了上来。
第二章遗嘱疑云**午夜十二点的钟声从远处教堂飘来,
病房里的电子钟跳成00:00。监护仪的滴答声突然慢了半拍,
像是被无形的手拨慢了齿轮。林伯庸的眼皮黏在一起,麻药的后劲让四肢像灌了铅,
可后颈的汗毛却根根竖起——那是他年轻时在商战里练出的直觉,危险靠近时总会这样。
月光不知何时转了方向,百叶窗的缝隙漏下道银线,恰好落在床头柜的紫檀木盒子上。
那盒子是他去年在拍卖行拍下的,据说是清代内务府的藏品,
此刻却被林薇的手指反复摩挲着,发出细不可闻的“沙沙”声。“叔叔睡沉了吗?
”她的声音压得比呼吸还低,林伯庸能感觉到她俯身时,白丝巾扫过自己手背的凉意。
他屏住气,睫毛在眼皮底下颤,假装发出均匀的鼾声——下午护士给他打了镇静剂,
这正是最好的伪装。紫檀木盒子的锁扣“咔嗒”弹开时,林伯庸的心跳撞得肋骨生疼。
他听见纸张翻动的声音,带着股陈年樟木的味道,那是他放在书房保险柜里的股权**协议,
怎么会到她手里?“城西地块……码头项目……”林薇的指尖划过文件,
念出的字眼像淬了冰,“这些本该是我爸的,当年若不是你用阴招逼他签下竞业协议,
林氏集团哪轮得到你儿子继承?”月光突然晃了晃,
林伯庸透过眼缝看见她从盒子里拿出支钢笔,
笔帽上的钻石在暗处闪着冷光——那是他送给亡妻的五十周年纪念礼物,
上个月刚在老宅失窃。她旋开笔帽,金属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在寂静的病房里像蛇吐信。
“签个名字而已,老东西。”她把协议铺在林伯庸胸口,纸张的凉意透过病号服渗进来,
“你现在签了,还能落个体面。不然等你成了植物人,我照样能找人仿你的笔迹,
到时候连你儿子那份,我也一并收了。”林伯庸的手指蜷在被单下,指甲几乎嵌进掌心。
他想起二十年前那个暴雨夜,林薇的父亲跪在公司楼下,手里举着“还我公道”的牌子,
淋得像只落汤鸡。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他挪用公款的新闻,三个月后,
那人在看守所里用牙刷柄划破了手腕。钢笔尖离签名处只有半寸时,林薇突然停住了。
她侧耳听着门外的动静,月光照在她脸上,林伯庸看见她嘴角的梨涡里,
藏着点不易察觉的狠戾。走廊传来护工推车的轱辘声,她迅速把协议塞回盒子,
抱着紫檀木盒子贴在墙角的阴影里,像只受惊的鼬鼠。护工的脚步声在门外停了停,
大概是在看监护仪的数据。林伯庸的鼾声打得更响了,
眼角的余光却瞥见林薇把盒子塞进了通风管道——那里有块松动的挡板,
是他年轻时躲债藏金条发现的秘密。护工走远后,林薇重新走到床边,
这次手里多了个玻璃小瓶。她拧开瓶盖,一股苦杏仁味飘进林伯庸的鼻孔,
跟二十年前亡妻临终前的味道一模一样。“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她的声音里再没有笑意,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把张开的镰刀,“就别怪我心狠了。
”第三章白裙魅影**玻璃小瓶的苦杏仁味在病房里弥漫开来,像一张无形的网,
缓缓收紧。林伯庸的后颈渗出冷汗,浸湿了枕头,每一根汗毛都竖得笔直,仿佛要刺破皮肤。
他死死闭着眼,眼角的余光却能捕捉到林薇的身影——她的白裙在月光里泛着冷光,
像一朵开在坟头的白菊,诡异而妖冶。林薇踩着地毯,悄无声息地靠近床边。她的脚步很轻,
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又像是在享受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白丝巾从她颈间滑落,
飘到林伯庸的脸上,带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像是从地下室的角落里拖出来的旧物。
林伯庸下意识地屏住呼吸,那霉味却顺着鼻腔钻进肺里,呛得他喉咙发痒,却不敢咳嗽一声。
“叔叔,您别装睡了。”林薇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像一根细针,
轻轻刺着林伯庸紧绷的神经。她俯下身,脸离林伯庸只有几寸远,
睫毛在月光下投下淡淡的阴影。“您以为我不知道您醒着吗?您的心跳声,
监护仪都告诉我了。”林伯庸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监护仪的“滴滴”声也随之乱了节奏。他能感觉到林薇的呼吸落在他的脸上,
带着那股甜腻的香水味和苦杏仁味混合的气息,令人作呕。他想起亡妻临终前,
也是这样躺在床上,呼吸微弱,身上带着相似的味道,那是死亡的味道。林薇的手慢慢抬起,
指尖划过林伯庸的脸颊,冰凉的触感让他浑身一颤。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却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红痕。“您还记得我小时候吗?”她轻声说,
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怼。“那时候我总跟着我爸去公司,您还抱过我呢。可后来,
您为什么就变了呢?
”林伯庸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模糊的画面——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穿着粉色的裙子,
怯生生地躲在她父亲身后。那时候,他还没有和林薇的父亲反目成仇,
公司里的气氛也不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可往事如烟,早已被利益和仇恨吹散。
林薇的手继续往下移,停在林伯庸的胸口。她的手指轻轻按压着他的伤口,
那里的缝合线还没有拆除,隐隐作痛。“您知道我爸在看守所里最后说什么吗?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利,像一把刀子划破了寂静的病房。“他说,要让你血债血偿!
”话音刚落,林薇猛地加大了手上的力气。林伯庸感觉自己的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压住,
疼得他眼前发黑,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他想挣扎,却发现自己像被钉在了床上,
四肢动弹不得。监护仪的警报声再次响起,尖锐而急促,像是在为他发出最后的哀嚎。
林薇却像是没听见一样,脸上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她的白裙在挣扎中被风吹起,
露出了藏在裙摆下的一把小刀,刀身闪着寒光。“叔叔,别怪我。”她轻声说,
语气里却没有一丝歉意。“要怪,就怪你当年太狠心了。”小刀慢慢靠近林伯庸的胸口,
林伯庸的瞳孔骤然收缩。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了。他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抬起手,
却发现手臂沉重得像灌了铅。绝望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
他难道就要这样死在这个女人的手里吗?就在这时,窗外突然刮起一阵风,
吹得百叶窗“哐当”作响。月光被乌云遮住,病房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
林薇的动作也顿了一下,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林伯庸抓住这个机会,
猛地睁开眼睛,死死地盯着林薇的方向。在黑暗中,他仿佛看到了林薇那双闪着凶光的眼睛,
像两盏鬼火,在黑暗中跳动。第四章千斤重压**黑暗像被打翻的墨汁,
瞬间浸透了整个病房。林伯庸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撞在耳膜上,“咚咚”作响,
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林薇的呼吸声就在耳边,粗重又急促,带着股狠戾的热气,
混着那股挥之不去的苦杏仁味,压得他喘不过气。“老东西,装不下去了?
”林薇的声音在黑暗里淬着冰,手却没闲着,死死按在他的胸口伤口上。
那力道像是带着三十年的积怨,每一寸都往骨头缝里钻。
林伯庸感觉缝合线“嘣”地一声挣断了,温热的血顺着肋骨往下淌,
在病号服里洇出一片黏腻的湿。监护仪的警报声突然哑了半拍,大概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
林伯庸的视线在黑暗里渐渐适应,能模糊看到林薇的轮廓——她整个人几乎趴在他身上,
白裙的下摆扫过他的手腕,冰凉得像蛇皮。那把小刀还攥在她另一只手里,
刀尖偶尔划过他的皮肤,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您当年把我爸的手指按在玻璃碎片上时,
他也是这么疼吧?”林薇俯在他耳边低语,气音里裹着笑,却比哭更渗人。
“他求您放过我们母女,您却让保镖把他拖出去,像拖一条死狗。现在这滋味,
您尝着怎么样?”胸口的压力突然翻了倍,像是凭空压上了块铅板。
林伯庸的肋骨发出“咯吱”的**,肺里的空气被挤得只剩一口,眼前开始冒金星。
他想抬手去掰她的手,胳膊却像焊在了床架上,指尖连颤抖的力气都快没了。
这感觉太熟悉了——三十年前他在工地上被横梁砸中时,就是这样的绝望,
每一寸肌肉都在尖叫,却连求救的声音都发不出。林薇的指甲抠进他的伤口里,
带着股铁锈味的血溅在她手背上。“您看,血都是红的。”她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
用沾血的手指在他胸口画着圈,“可您当年怎么就没心呢?我妈跪在雨里给您磕头,
磕得头破血流,您连窗帘都没掀开过一下。”黑暗里突然闪过一道闪电,照亮了林薇的脸。
她的眼睛瞪得滚圆,瞳孔里映着窗外的惨白电光,嘴角却咧开个诡异的弧度,
血珠从她指尖滴下来,落在他的脖颈上,凉得像冰。林伯庸猛地偏过头,
看见监护仪的屏幕被她用枕头捂住,绿色的波形在布料下挣扎着闪烁,像只濒死的萤火虫。
“快了,老东西,很快就结束了。”林薇的手又加了几分力,刀尖已经刺破皮肤,
抵在他的心脏上方。“等您死了,我就把您的遗嘱改成我爸的名字,让他在天上也能看着,
林家的一切,终究是我们的。”窒息感像水草一样缠住了林伯庸的喉咙。
他感觉自己的意识正在飘远,耳边似乎响起亡妻的声音,还有林薇父亲当年在雨里的哭喊。
不,不能就这么死了!他猛地咬紧牙关,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绷紧了脖颈的肌肉——就算手脚动不了,他还有牙齿,
还有这口咬碎过无数难关的牙。闪电又亮了一下,这次他看清了林薇按在他胸口的手腕,
青筋在皮肤下突突跳动,像条挣扎的小蛇。就是现在!林伯庸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
积攒的所有力气都聚到了牙关。第五章齿间血肉**闪电的余光还没从视网膜上褪去,
林伯庸的下颌已经像捕兽夹般猛地收紧。假牙嵌入皮肉的瞬间,
他听见“嗤”的一声轻响,像是咬开了灌满血的塑料袋。林薇的手腕在他齿间剧烈颤抖,
带着股劣质香水混着汗味的气息,顺着牙缝往喉咙里钻。他咬得更狠了,牙龈被硌得生疼,
烤瓷牙的边缘刮过她的肌腱,那触感像咬着根浸了血的橡皮筋。“啊——!
”林薇的尖叫像被踩住尾巴的猫,尖锐得能刺破耳膜。她手里的小刀“哐当”掉在地上,
在瓷砖上滑出老远。另一只手疯了似的捶打林伯庸的脸,指甲刮过他的颧骨,
留下几道**辣的血痕。可他像块生了根的石头,牙关咬得死紧,
连半分松动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他从鬼门关爬回来的唯一绳索,绝不能松手。
血腥味在口腔里炸开,带着股铁锈般的腥甜。林伯庸的太阳穴突突直跳,
三十年前工地上的记忆突然涌上来:那天他也是这样,被横梁压住腿时,
死死咬着块木板才没昏过去。此刻齿间的皮肉在剧烈挣扎,像条活鱼在嘴里扭动,
他却把牙床都用上了力气,感觉假牙都快嵌进骨头缝里。“松口!你给我松口!
”林薇的声音劈了叉,带着哭腔和暴怒。她整个人骑在林伯庸身上,白裙被血浸透了大半,
贴在皮肤上像层湿纸。林伯庸能感觉到她的膝盖顶在自己的肋骨上,
每一下都像要把骨头顶断,可他依旧死死闭着眼,任凭她的拳头落在脸上——疼,
钻心地疼,但这种疼让他清醒,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突然,林薇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杯,
狠狠砸在林伯庸的额角。“啪”的一声脆响,玻璃碴混着血水流下来,糊住了他的眼睛。
他的牙齿松了半分,林薇趁机猛地抽手,带起的血珠溅在天花板上,像开了朵诡异的红菊。
可还没等她爬起来,林伯庸又偏过头,用尽全力咬住了她的袖口。“疯子!你这个老疯子!
”林薇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更多的却是恐惧。她拽着袖子往回扯,
白丝巾缠在了林伯庸的脖子上,勒得他喘不过气。窒息感再次袭来,林伯庸的眼前阵阵发黑,
但他的牙齿像焊死了一样,死死咬着那块布料——他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
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尿骚味,这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女人,现在怕了。
窗外的雷声越来越响,雨点噼里啪啦砸在玻璃上。
林伯庸的嘴里已经分不清是自己的血还是她的血,只觉得整个口腔都在发烫,
像含着块烧红的烙铁。他想起亡妻临终前喂他喝的藕粉,想起儿子小时候掉的第一颗牙,
想起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这些念想像根绳子,拽着他往活路上走。
林薇的力气渐渐小了,大概是失血过多。她瘫坐在他身上,手腕上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
滴在他的胸口,汇成一小滩温热的水洼。“放过我……求你放过我……”她开始哀求,
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林伯庸却突然松了口——他听见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还有儿子林默焦急的呼喊。“爸!爸你怎么样?”门被撞开的瞬间,
林伯庸看见林默带着保镖冲进来,手电筒的光柱扫过满床的血污。林薇像是突然回了魂,
尖叫着指向他:“是他!是他咬我!”她的手腕在光柱下白得像纸,伤口处的皮肉外翻着,
露出里面鲜红的筋膜。林伯庸张了张嘴,想说话,却只吐出一口血沫。
齿间还残留着她的皮肉碎屑,腥甜中带着股说不出的腻味。他看着林薇被保镖扶起来时,
偷偷往床底踢了一脚——那里藏着她掉的那小块肉,像块被踩烂的猪肝,
在阴影里泛着暗红的光。监护仪的警报声重新响起来,尖锐而刺耳,却在此刻听来,
像极了重生的号角。第六章破门而入**手电筒的光柱在病房里乱晃,
像被狂风撕扯的火把。林默的声音裹着惊慌撞进来,他身后的保镖踩着碎玻璃冲过来,
黑色皮鞋碾过地上的血渍,发出黏腻的声响。“爸!”林默扑到床边,
手指刚触到林伯庸额角的伤口就猛地缩回,血珠在他指尖滚成了小红球。
目光扫过满床的狼藉——浸透血的白裙碎片、散落的玻璃碴、监护仪上疯狂跳动的曲线,
最后落在林薇渗血的手腕上,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林薇趁机往保镖身后躲,
手腕上的血顺着指尖滴在地板上,连成条蜿蜒的红线。“阿默你看!”她突然拔高声音,
带着哭腔的语调在空旷的病房里回荡,“你爸他疯了!我好心来看他,他二话不说就咬我,
你看这伤口……”她把手腕凑到林默眼前,外翻的皮肉在光柱下泛着惨白,
筋膜上还沾着点深色的碎屑——那是林伯庸的假牙碎片。林伯庸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
想抬手指床底,肩膀却被保镖按住。他看见林薇的裙摆下露出半截沾血的纱布,
正随着她的颤抖轻轻晃动,那是她刚才偷偷塞进去的——用来擦掉床底那块肉的证据。
怒火猛地冲上头顶,他挣扎着想要挣脱,胸口的伤口却裂开了,疼得眼前发黑。“都住手!
”林默吼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他转向林薇,语气缓和了些:“薇薇,